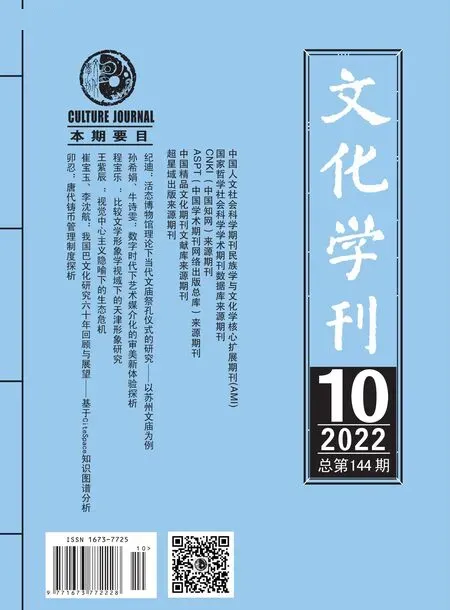數字時代下藝術媒介化的審美新體驗探析
孫希娟 牛詩雯
2020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了新媒體融合發展的總體要求,強調全媒體時代中媒體技術內容自主創新要以人民群眾為中心、增強自我造血機能、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等發展戰略,深刻認識到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緊迫性。該《意見》的貫徹落實對媒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勢之下媒介的能力對于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培養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都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
一、藝術媒介化的審美心理特征:媒介即認識
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取決于客體在語言中的表達形式,而不同的媒介對話語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使之能在無形之中引導主體認識世界,認識論的發展階段正是伴隨了每一個媒介的發展階段。
(一)口頭語言的主觀性
口頭語言媒介存在較為復雜的敘事特征,由于人自身主體的媒介化的傳播機制,使信息的數量、來源、象征、所處的語境與傳播過程融為一體,凸顯了人作為媒介時敘事主觀性的性質。在口口相傳的文化中,口頭敘事媒介孕育于諺語和俗語,之后參與構建了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寓言史詩等文學體裁,口耳相傳是口頭傳播時的媒介形態,聽覺成為了首要語言加工的知覺,口頭的對話構成了思想自身的內容,思想便存在于口語的表達形式之中。這時媒介本身的中立性、客觀性因遭受主體的參與喪失了獨立的存在,媒介被主體的心境情感所支配,甚至在傳播過程中與個體的行為舉止、語音語調、前因后果、儀容儀表產生互文,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形成內在紐帶,導致每一次敘事都呈現完全獨立的認知意義。同時,口頭敘事媒介為藝術創造提供了途徑,是主體脫離了粗野殘暴的自然枷鎖的起源。因此,口頭敘事媒介的主觀性局限就在于其流逝性與不可重復的“這一個”,隨著新興媒介的發展,這種局限性也讓口頭語言退居于日常生活交流的位置,而不再承擔敘述藝術媒介的身份。
(二)書面語言的客觀性
隨著文化媒介從口頭語言轉向書面文字,書面語言媒介逐漸脫離口語的主體性,對象化為認識客體,認識從有限的現實提高到無限的觀念,人們開始追求脫離感性世界飛躍到純粹觀念的王國。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沃爾特·翁曾提出“文字已有幾分預言的性質[1]59”“新技術不只被用來傳達批評,實際上它還使批評的存在成為可能[1]60”。書面語言的客觀性讓文字成為延伸意義的物質載體并對主體思辨的知性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以客觀理性的思維鼓勵著嚴肅專注、邏輯明確的公眾話語,從此“闡釋”成為時代的重心。因此,當藝術表達以文字為媒介時則拉大了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距離,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處于孤立的存在之中,當作者扮演審美主體進行審美創造時,要求虛構一個對象或者留白,便于讓缺席的讀者去展開,就像是一項嚴肅而理性的事業,而當讀者扮演審美主體進行審美體驗時,首先主體看見的是抽象冷靜的符號,由于閱讀的過程本身便具有邏輯理性、有序排列的命題特點,讀者必須以認知客觀事物的態度來感受,才能運用想象力自由的翅膀進入審美的狀態觀照世界。書面語言媒介正是這樣在使審美主體產生強大自主性的同時剝奪了等值的感受性,它需要設置門欄并訓練主體一種特殊的技巧才能達到期待的審美效果。
(三)視聽語言的主客觀交替性
經過電子媒介技術的重大變革,制造出了全新的媒介環境,使得視聽語言媒介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視聽語言媒介又重返主體感官感知層面,主體對于外在信息的接受從單一的一端發展推升至知覺重新組合或時空分離的模式,為主體直觀的知性與思辨的知性相互碰撞、交錯發展,提供了全面實現的可能。縱觀媒介變化與人主體性關系的歷史,人類文明從原始文明到數字文明,主體的感性與理性在美的覺醒中也呈現出否定之否定規律,從口語與圖形的感官刺激到文字的理性精神,再到視聽影視回歸感官卻令部分理性被消解。但當視聽語言媒介在主體面前進行敘事時,并沒有將感性與精神分裂,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把它們組合起來,例如電影中美的視覺喚醒審美主體的感受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時,好的電影藝術也是創作家反復斟酌的產物,風格化的電影視聽語言元素又使主體拉開與現實生活的審美距離進行抽象思考,于是感受力與創造力超越了現實,在自然純真的地方中和諧交流。“人以單純的生活開始,以形式終結[2]144,”由感官過渡到思維要經過一個中間狀態——即審美狀態,這種中間狀態需要感性與理性同時活動,才能脫離限制達到自由的心境,視聽語言媒介正是因為縮小了主體感性與理性傾向的局限,因此,可以更進一步培養主體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體達到盡可能的和諧。
二、“跨媒介敘事”建構的審美心理新范式
媒介的差異性重塑再生產著原初母版內容,尤其是在影視文化中更為顯著,電影與游戲、漫畫、戲劇、小說、期刊等不同媒介的融合已經是后信息時代下傳媒藝術開發的新趨向,而這種對基礎文本再創造性表達的跨媒介性,在審美過程能夠給審美主體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
(一)脫離利害與拉開常態
一方面,“影游融合”的跨媒介化敘事方式使“娛樂雜耍”的審美價值重獲新生。網絡游戲的主要任務是要以富有變化的故事世界和新奇的視覺形象不斷刺激受眾的感官,通過游戲玩家內在視角的設置,打造出虛擬與現實雙重敘事的交織,這種逃避現實世界的“偽療法”依然置審美主體于虛幻游戲世界的欲念希冀之中,其不同于莊子“逍遙游”之“游”,也不同于席勒“歡樂的游戲”之“游”。
另一方面,“影游融合”“影戲融合”等跨媒介化敘事方式使審美主體出乎常態,徒然“天啟”。“媒介之跨”混合了多元的文化視域,創作者利用各個媒介的基礎元素資料進行再創造,間離原有的敘事范式,使其陌生化、反常化、異象化。如此以來,存于主體意識的形象以新奇的途徑顯現,沖破主體期待視野和常態化的感受定式,將日常生活的認知上升為審美鑒賞,延長主體審美體驗。《頭號玩家》《無敵破壞王》《失控玩家》等“影游融合”的電影,并非根據游戲文本改編而成,而是加入了游戲的元素,借鑒游戲之形,展現電影之式,激勵著各類受眾群體在不同的媒介之間來回探索。
(二)相似相生與異質同構
“跨媒介敘事”的發展使媒介再度復歸主體感官,它以感性刺激為核心,超越時空的距離延伸至主體整體感官,再以知覺為基礎拓寬理性邊界,最終完成感性與理性、物質與精神、形式與內容之相融。從傳統媒介敘事跨越至新時代媒介敘事,各媒介之間在本源上便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主體即使是用文字印刷思維去理解圖像影視產物,同樣可以剖析其內涵與外延,各媒介之間相輔相成、來回切換、共生共載,促成“跨媒介”實現傳播方式的有機結合。愛因漢姆基本美學的第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藝術活動和審美活動歸根結底是在感性上對形式的把握[3],”由于視聽語言的照相化學、光學、機械學、電學的技術特質與主體感官的心理特征最為相符,影視語言的形式便升華成為視聽感官的形式。因此,審美主體在對影視作品進行審美判斷時,在藝術家利用巧妙的藝術形式之下,將自身的感官材料納入特定的形式過程,在視聽形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知覺力的平衡,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媒介形式與內在心理場的“同構性”。
(三)內在超越與外在侵襲
“跨媒介敘事”的發展建立在完備的數字媒介的基礎之上,以建設元宇宙生態為未來前景,通過數字媒介技術超越了人作為主體感知的物理存在,延展了人的新型感知主體——“數字虛擬軀體”,借由“數字虛擬軀體”突破審美主體身體局限,實現從現實世界到虛擬世界的感官全方位連接。5G的技術革命使“跨媒介敘事”的表達方式和交互體驗逐漸跨越時空的距離踏入三維的存在,特別是VR、AR、MR等數字技術代表完整的復制再現了極具真實感的某一時刻或某一場景,不斷推動著主體意識的延伸。在此階段,審美主體體驗到的不只局限于物化的藝術品,還有侵襲式的空間性載體,使審美主體全身心地進入到豐滿的感性中來,并將被人遺忘的感官意識送還給人。審美主體則以這種方式被這個空間所規定了,它取消了在審美活動中傳統的主、客二分,取消了審美客體在傳統的物的存在論的第一性質,而是根據它“走出自身、登臺亮相的方式”來展現的“物的迷狂”[4]。谷歌在前幾年就推出了VR繪畫應用,將繪畫的方式、范圍拓展至虛擬的3D空間。雖然在藝術的媒介當中,對VR、AR、MR的實際運用還存在一段距離,但是從傳統媒介跨越至此類新型的數字媒介已是大勢所趨,洞悉把握好其特征是我們面向未來構建審美媒介化社會的重中之重。
三、藝術媒介化之思:數字文化語境下的審美教育
在新媒介形成的交流互動的傳播鏈條之下,媒介對藝術的創作形態和傳播方式展開了一場全新的改革,立足于當下的時空發展,媒介的社會功能探索著審美體驗發展的可能性,對于審美教育的實踐研究有著重要的指引作用。
首先,防止藝術媒介化的極端娛樂性。印刷文化的認識論逐漸讓位于影視文化的認識論,人們對于真善美相關規則的看法與認知習慣也隨之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正在蛻化。現如今,大量的抖音短視頻、淘寶直播、微信微博等APP充斥著社會生活,但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只適合傳播轉瞬即逝的信息,“刷屏”成為了現代人無法割舍的生活方式和當代公眾話語權土崩瓦解的象征,“刷”體現了內容之淺、時間之短、信息之多,人們看見的信息沒有背景、沒有語境、沒有歷史,這種不連貫性的媒介販賣的不是藝術而是娛樂,以富有激情的視聽渲染代替了文字邏輯理性的思考理解。
其次,確保藝術媒介化的發展可持續性。藝術的媒介形式必須是藝術家深思熟慮后的選擇,即使是利用“跨媒介敘事”的方式也要注意“美在于形式”,好的內容應當通過美的形式來表現,對美的形式感受是作用于人的感知、情感、想象的第一把交椅,審美主體只有通過形式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而如何通過不同的媒介形式進行表意、敘述、想象,是“跨媒介敘事”得以實現的重要基礎,許多電影形式的創新其實都參考了小說、戲劇、漫畫、游戲、期刊等不同的媒介敘事方法論,例如“元電影”的理論就是由“元小說”的理論被引用至電影領域之后才開始建構的,還有許多舞臺劇的電影形式也是參考了戲劇中對歌隊的運用來區分現實與虛擬。這些特殊的形式都能夠使主體從緊張的劇情中抽離出來,以旁觀者的角度操縱理性分析的能力,推動感性沖動與理性沖動同時運轉,來完成影視媒介的美育任務。
最后,關注藝術媒介化的社會治愈性。藝術媒介的敘事形式與內容必須以促進個人全面發展為宗旨,藝術形象的選擇也必須符合“美的形象”,即審美客體以情感性質的形式揭示原初的經驗世界,生成審美意象。行為藝術,它主要借助人的身體為媒介創作,不受傳統藝術的束縛用即興式的表演與現場或線上觀眾進行互動,但是有一些行為藝術卻打著“藝術”的幌子與美相對立,其整個過程給主體帶來的恐懼迂腐遏止和消解了審美體驗的產生加重了人性的分裂和異化,甚至給人帶來生存的危機而阻礙現代文明的進步。“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2]115。”藝術作品還需要靠藝術家對其內容與形式反復斟酌,選取恰當的形式與內容(生活與形象)進而追求感性與理性、偶然與必然、受動與自由的統一。在數字時代下,隨著互聯網與電子媒介的參與更加讓藝術的呈現表達魚龍混雜,因此,正確地利用藝術媒介化的手段調和個體的精神平衡穩定是美育任務的核心。好的藝術作品應能治愈人身心的病變,使人處于一種和諧的生活狀態,督促人有意識地追求審美的人生,其既是出于個體性格高尚化的教育,又是為整個社會的發展進行考慮,從而保障個體與整體的協調一致,這是幸福的基礎也是道德發展的前提。
如前所述,人類的藝術史便是從傳統的口頭語言媒介到書面語言媒介再到視聽語言媒介,由此發展而來的,現如今藝術媒介的“跨媒介敘事”形式已成未來的趨勢,媒介的邊界正在消失,虛擬與現實的融合逐漸成為了數字時代媒介語境的常態。審美體驗方式和藝術傳播途徑深受影響,然而全面認識了解藝術媒介的變遷和特性能夠為探索審美體驗的形式提供新的可能性,發揮媒介社會功用的價值突破審美教育目前面臨的困境,從而更廣而深地引導公眾尋覓一個有意味、有情趣、有詩意的自由完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