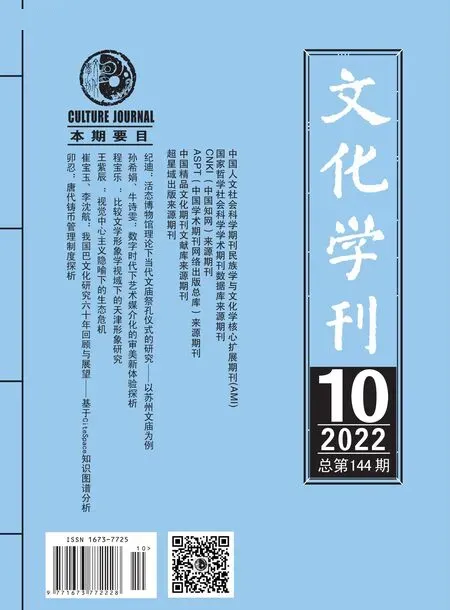習得影像技術后藏族從自發到自覺的生態保護觀
——以草根影片《牛糞》《卡爾貢噶》為例
楊辛玥
一些觀點認為,現代化的技術和觀念會讓藏族的傳統生態保護觀徹底消失,因此,應該將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置于文化“真空”。本文選取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公益影像行動計劃“鄉村之眼”中藏族草根影片《牛糞》《卡爾貢嘎》為研究對象,對兩部影片的內容和拍攝后續進行分析,駁斥上述觀點,認為:藏族在歷史發展中自發形成的生態保護觀,在近年來影像拍攝技術傳入涉藏地區的背景下,逐步變成自覺。農牧民通過鏡頭,留意觀察周圍的生態與文化,并使用現代影像手法將它們拍攝、制作成影片,展現自身頭腦里的生態觀念,使以往樸素的“生態保護”觀念變得具象起來,這是一種經由新技術的習得而帶來的文化自覺與觀念現代化的過程。接受了現代技術的藏族民眾,通過技術手段看待本民族文化,產生文化自覺,并采取行動,讓自發的生態保護觀念在現代化過程中成為自覺,進而促進當地生態文明建設。
一、藏族草根影片中的生態觀念分析
(一)《牛糞》:質樸生態觀的影像展現
藏族在歷史發展中,自發形成了許多保護自然、保護生態環境的民族傳統文化。在2010年“鄉村之眼”項目由青海果洛州久治縣白玉鄉牧民蘭則拍攝的《牛糞》中,這種自發的生態觀念通過描繪人與牛糞的共生關系進行展現。影片開頭,藏族婦女帶著孩子一起在草場上撿拾牛糞,拉回家后便開始使用牛糞做出肉凍房、狗窩、籬笆、牛鞍等日常生活用品。片中幾乎所有的畫面都是在呈現一家藏族牧民如何利用牛糞來生活,基本沒有對話,樸素地忠實記錄青海藏族牧民的日常生活錄,故事性很弱。“牛糞有那么多好處,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沒有牛糞,我們藏族人是無法在高原上生活的。”這兩句臺詞卻反復出現,由藏族牧民阿媽說給孩子聽。在他們眼里,既普通而又被城市人嗤之以鼻的牛糞不是骯臟的排泄物,而是草原文化的真正根基,也是天然的“萬能”再生資源。
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藏族的文化即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為了適應高原環境而產生的一套生存策略,比如撿拾牛糞作為天然能源,就是藏族在青藏高原長期養成的獨特生活方式[1],距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2]。縱觀影片,《牛糞》沒有出現一句“生態保護”“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等對白,可正像影片所展現的那樣,青藏高原藏族民眾通過牛糞這一“中介”,聯結起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橋梁,阿媽在做,小孩兒在看,千百年來,草原上的牧民正是這樣代際傳承他們樸素的生態觀,起到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客觀作用。
(二)《卡爾貢嘎》:環境變化下主動環保行為的記錄
在歷史發展中,藏族傳統文化中形成提倡世間萬物循環作用、相互影響,告誡人們要與自然界和解的思想理念,這一主張對人們形成保護自然環境、愛護動植物的環境觀提供了思想基礎[3]。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藏族人民的觀念也相應產生變化,由此作出一系列自覺的生態實踐。四川磽磧藏族鄉藏族牧民能卡曼拍攝的影片《卡爾貢噶》體現了藏族人民對于生態環境變化的關注與自覺保護意識。2003年,由于水庫的修建,當地最大的神山山梁卡爾貢嘎被淹沒,能卡曼關注到該情況,通過6次集中拍攝,選擇了8位有代表性的當地人講述他們對于當地自然文化的見解。村民阿杰講述,他原本是牦牛養殖大戶,光自家的牦牛就超過了100頭。可是“草山危機了,載畜量大了,草‘長不贏’,”于是阿杰主動地減少家養牦牛數量,來達到與周邊環境承載力相適應的目的。
這位只上過小學的村民在影片中講到,“少養牦牛是大自然的一種平衡,為了實現這種平衡,未來想搞新興旅游業謀生。”阿杰的想法,在藏族傳統文化中能找到濫觴:藏族傳統文化中,借助人類對大自然的尊重和畏懼約束他們向大自然索取的貪婪之心[4]。阿杰意識到“草山危機”,從而自覺地去協調人、牦牛與草場的關系,起到了保護生態環境的作用。
二、影像技術對生態觀念的具象和引導作用
對于攝像技術的長期接觸和運用,藏族人民習得“拍攝”行為,受到“鄉村之眼”項目的引導,以鏡頭這一現代化的媒介看待身邊的生態環境,也用鏡頭拍攝的影片展現頭腦中對于生態變化的看法、態度,改變了以往“無意識”地對自然的保護,學會逐漸用鏡頭語言去主動尋找、記錄日常行為中能夠體現因環境變化而產生的變遷。《卡爾貢嘎》與《牛糞》拍攝的時間相隔9年。對兩部影片進行橫向分析,相比蘭則的平實記錄,能卡曼不僅知道運用現代影像的手法記錄周遭的生態環境變化,也在這種記錄過程中,逐漸產生通過自覺實踐來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想法,影片中有大量畫面講述藏族群眾自覺保護生態環境的方法。她對于身邊自然環境的關注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經過“鄉村之眼”攝影技術的培訓后,通過不斷的拍攝經歷、長期摸索而成的。2014年,沒有任何拍攝經驗、高中讀了兩年就輟學的能卡曼,成為“鄉村之眼”發展的對象。當時,能卡曼覺得“拍攝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記錄下很多生活中的美好。再加上還要免費發相機,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生活拍出來,以后給孩子看”;自己所在的村莊因為近十年來的水電開發和旅游推廣,已經徹底改變了這里延續千年的傳統農業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她希望把這些變化留下來,并從本土文化持有者的角度表達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因此,能卡曼在《卡爾貢噶》中通過口述的方式記錄村民在生態環境變遷中自覺、主動轉變的生計模式。
從影視人類學角度來看,影片主題、人物、切入角度的選擇,是拍攝者觀念的一種表達。從蘭則對樸素生活方式的平實記錄,到能卡曼通過人群的講述來直擊現象本身,實現二者轉變的原因之一,正是攝像技術不斷地深入涉藏地區、相關草根拍攝者不斷地熟悉攝像機、選擇拍攝主題、用攝像這種新技術來觀察生活,并越來越會使用它來將自己頭腦中想要表達的東西具象化。
三、草根拍攝者后續的生態參與
由攝像機帶來的觀念變化,不僅在影片的對比中得以體現,也體現在:草根拍攝者不僅只關注影像本身,而是在后續的生活里,自覺地走上了生態保護的實踐道路。攝像技術帶來對生活的全新觀察,拍攝完《牛糞》后,蘭則觀察到了家鄉年寶玉則高山牧場草場破壞的問題,并由此產生心理活動的變化,促使他產生一種迫切地想要去保護家鄉生態環境的自覺責任感。于是蘭則著手“種草”并且將這一過程用紀錄片形式記錄下來,最后成片《鼠兔》,并動員牧民一起保護草原。僅2018年,蘭則就帶領家鄉牧民完成了200畝草場的修復。
與蘭則的環保行動不同,能卡曼辦起了面向游客的自然教育,在跟外界交流的同時,也強化著自己對傳統精神的認知,把家鄉的自然和本民族的文化在更大范圍內傳播。上文提及,能卡曼一開始并沒有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拍攝行為的意義,也不知道為何要拿起攝像機。但在一步步通過鏡頭看家鄉的過程中,她意識到了生態的重要性,也意識到了影像記錄對于保護生態的重要性。
拍攝者們關注生態主題,緣于鄉村生活與自然環境的直接聯系,村民或牧民們對于牧場退化、河流污染等環境問題有著切膚之痛,因為自然環境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計,所以他們也更愿意用手中的攝像機記錄身邊的生態及環境變遷。而掌握了新技術的村民、牧民,因為新技術的使用,不僅更好地、自覺地觀察并思考自己周遭的生態環境,也與外界產生了借由影片架起的聯系。因為有了這一聯系,他們的訴求和觀念能夠便捷地向外界傳播——通過影像的方式,由此呼吁更多的人投身生態保護的行列,這是草根拍攝者在后期轉向生態保護實踐的原因之一。
四、影像技術推動自發到自覺的生態保護行為
藏族群眾樸素、傳統的環境保護行為,在接觸到了以攝影攝像為代表的現代技術后,被引導向文化自覺的轉變。這一轉變中,現代化技術培訓者對于藏族民眾自身的觀念進行反思、產生覺醒,起到相當大的推動作用。《牛糞》《卡爾貢噶》影片本身,以及草根拍攝者后續的生態保護實踐,是歷史積淀下藏族樸素的生態保護觀在習得現代技術后的集中體現。
(一)推動新舊觀念的調試
“鄉村之眼”作為“參與式影像”,是“一種創造性地利用影像設備,讓參與者記錄自己和周圍的世界,來生產他們自己的影像的集體活動”[5],是社區進行自我教育、對外發聲的途徑[6],讓各民族群眾自內而外地思考民族生存發展之道、反思傳統文化現代化變遷的渠道[7],是通過當地的視角看世界[8]。新的技術、新的生產工具的創新會使本文化中的人的觀念、生活方式產生變遷[9]。正是因為攝影機等現代技術在原本處于相對閉塞文化環境的傳播,使得中國西部農牧民自有的樸素生態觀、自發保護自然的生活方式受到現代技術的引導,向現代觀念和話語采借,接受現代化的“生態保護”觀念,將他們腦海中模糊、樸素、自發的概念進行統合與過濾,有選擇性地截取與自身所處的藏族傳統文化觀相適應的生態文明思想,在影片中體現出來。
而在尊重現代化新技術和知識的同時,也要將它們的實用部分與本文化相調適[10]。在對攝像技術與本民族傳統文化進行調試的過程中,藏族民眾并沒有在新技術與新觀念傳入的過程中迷失自我。藏族在漫長歷史中沉淀下來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觀念,是他們的本文化得以與現代性有機結合的原因之一。因此“鄉村之眼”合作攝影師通常會要求學員們不僅要學計算機、攝影技術,也必須要學藏文,因為不會藏文,就無法理解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也無法以局內視角看待本文化。
(二)推動生態保護實踐
通過攝像技術對中國西部農牧民的傳統觀念進行現代化引導的過程,同時也是以草根拍攝者為例的藏族民眾對于本文化的自覺過程。文化自覺指文化中的人在接觸、理解多種他文化的基礎上,對自己的文化有清晰的認識,并把握與取得新文化到來時的文化自主地位[11]。如蘭則、能卡曼這樣的農牧民,通過“拿起攝像機、拍攝影片”這一行為,走上了認識本文化、產生文化自覺的道路,體現為前文曾提到的草根拍攝者后續的生態參與實踐。草根拍攝者是涉藏地區文化轉型過程中產生文化自覺的典型代表:利用攝像的方式,認識到本文化中的精髓,通過影片拍攝、放映和宣傳,利用科技對地方性知識集中表達的過程,影像記錄的過程也是重新審視本文化的過程。掌握了攝像機和電腦編輯技術的當地人,進一步認識到本文化中樸素生態觀的現實意義,并把影像當作深入生活的橋梁,通過這一橋梁向現代化、全球化的世界展現藏族傳統文化,并且帶動更多的人參與生態保護實踐。這種文化自覺的過程,無疑加強了藏族文化在新的宏觀環境中轉型的自主能力。
五、結語
對于文化的變遷,有人持全盤否定的觀點,認為民族文化要保持獨特性,應該放在完全的“文化真空”中。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民族文化與現代化、全球化相互碰撞之后的文化自覺,有利于促進藏族傳統文化當中對于生態環境的自發保護行為,向自覺實踐去轉變。
草根拍攝者通過影像技術進行自我表達,是在涉藏地區的社區教育由外來者推動過渡到本土自覺行動的轉折點[11]。在藏族文化悠久的歷史發展中,不僅積淀孕育出樸素自然保護觀念,使得藏族民眾在長期浸潤中培養出傳統生態保護觀念與行為;在現代化背景下,伴隨現代技術手段的綜合運用和引導,藏族人民主動用攝像這種現代技術拍攝影片,向外界傳遞自身的生態觀念,后續又投身到參與、呼吁生態保護的實踐中。研究表明,通過現代化的技術正確引導藏族民眾將本文化優秀傳統向現代化轉型,諸如通過攝像機、專業培訓等等方式,樹立現代化的生態觀,并不會讓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色彩,而是有利于讓越來越多的藏族同胞接觸現代化觀念、了解并且獻身于新時代的生態保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