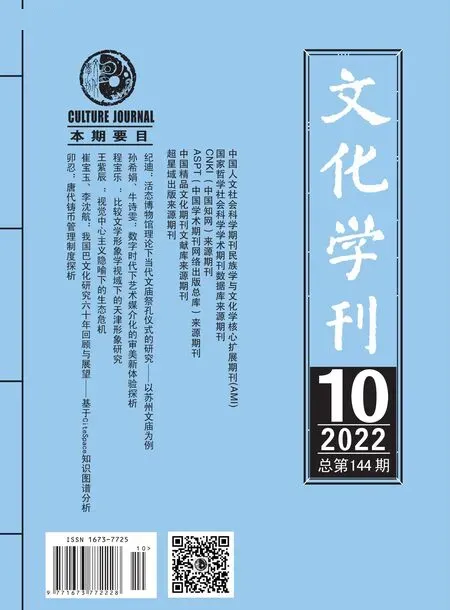有限與無限之間:聚焦于愛情的存在之思
——以小說集《好笑的愛》為例
李 琳
米蘭·昆德拉筆下的人物在偶然、微妙的具體生存中籌劃出無限可能性。他的小說集《好笑的愛》聚焦于現代人的愛情,除了象征永恒的“大寫的愛情”,還有除去“嚴肅”的愛情,他將承載宏大意義、界限分明的“愛”消解于個體于具體存在中復雜、飄忽不定、矛盾且虛無的旋渦,對立于理性主義的超越抵達無限,呈現了個體存在的有限。“大寫的愛情”扮演著個體超出自身有限性的媒介,是此在抵達無限的橋梁。除去嚴肅的愛情看似消解了愛情的形而上意義,卻是對無限的另類想象。
一、哲學背景及對存在的探索
昆德拉認為現代人陷入“存在的遺忘”這一狀態。海德格爾對“存在”一詞進行詞源學意義上的考察,認為自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史便將“存在”的問題等同于“存在者”的問題。他提出的人的存在形式,即“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1]45”。在此基礎上,昆德拉通過審美的藝術形式,將棲身于經驗世界中的人及其生存的真實境況呈現出來。由此,人的具體存在(concrete being)扎根于大地,作者在具體的生存情景中追溯人的存在,探索人“將是”的多元可能性。
(一)西方理性傳統:被遺忘的“存在”
在胡塞爾看來,歐洲人文危機根植于歐洲科學的片面本性,它將人存在于其中的具體世界作為不斷征服的“他者[2]3”。這可回溯到希臘哲學,它意不在人類如何更好地在實際生活中生存,而是發乎于一種認知激情,諸如發現普遍事物、脫離時間性的抽象本質,將理性“完全從無意義的原始水準超拔出來[3]86”。笛卡爾將人拔高為自然的主宰者,而面對超越性的利維坦,包括技術、政治、歷史等力量,人只是作為單一客體而存在[2]4,人的具體存在即“生活世界[2]4”被預先遮蔽和遺忘了。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一切事物的價值都被抽象為了符號-貨幣的關系[4]。現代科學的迅速發展,將人局限于專業化的領域內,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專家沒有靈魂[5]”。昆德拉同樣發現:現代知識在專業化、精確化層面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是人們對整個自然以及人自身的遺忘,人的存在陷入被海德格爾稱作“存在的遺忘[2]4”這一狀態。在此基礎上,昆德拉主張,人物與其周圍世界都應考量為“一種極限的、未實現的可能性[1]54”,在無限可能性的領域中認識你自己。
(二)存在的多元可能性
存在問題的本質以關鍵詞的形式在行動與情境中逐漸顯示出來[1]38。不同的存在情景以“復現模式[6]6”流動在小說集《好笑的愛》中的多個故事中。復現,顧名思義:某個現象或某一事件再次發生或重復出現,現代文學中與循環形式相關的理論可追溯到“德國文學中抒情詩歌的循環[6]4”,該作品研究了德國浪漫主義詩人采用的循環形式,對這一形式的基本特征進行了界定。Forrest L.Ingram在此基礎上將“故事循環”定義為“一組相互關聯的故事,由此來維系每一故事的獨立性或個性與大的單元之間的平衡[6]5”。《好笑的愛》中強調的“復現”,呈現為同一主題或情景在多部小說之間流動輾轉,“不斷經受著形式或者意義的改變[7]332”,因此,讀者可從不同的視角沉浸思考。
昆德拉對“存在”的探索,指向對人類生存可能性的探索。這可能性并非由人的本質決定,而是在具體的存在中理解,正如海德格爾所述:此在是什么,依賴于怎樣去是,而怎樣去是依賴于它將是什么[8]42。他用“生存”來規定此在的存在,怎樣去是先于是什么,此在總是在意識中先行于自身而存在(being),并籌劃(envisage)出各式各樣的可能性,此在總是以不是其自身的方式(mode)去是其自身。此在的“所是”是它去存在的種種可能方式,即此在“作為它的可能性存在[8]42”。昆德拉進一步主張“存在包括著現實的各種可能性[9]”。他筆下的人物被賦予極大的象征意味,不同個體與同一情景或動機,在周圍世界中呈“根莖狀”延展開來。
二、有限與無限之間
(一)人類建構無限以超出自身的有限
“現代哲學始自一種徹底的主觀主義,主觀以一種隱蔽的對抗性面對著客體[3]216”,笛卡爾以來,自我作為思想的實體被稱為主體,自然是具有廣延的客體世界,人立志要成為自然的征服者。萊布尼茲超越笛卡爾,提出“萬物都有某種驅動力,以便及時向前運動[3]217”。克爾凱郭爾否認抽象思維凌駕于人類現實(human reality)之上,強調對“我存在”這一命題的思辨不能替代且完全不同于個體于經驗中的存在,他認為生活中的“自我”對于存在的把握不是源于思想的“超然”狀態,而是“自我”面對生命之有限而不得不陷入的“非此即彼[3]173”的選擇中。在尼采這里,存在個體從理性的光暈中滑落,理性“主體”將人的身體、欲望即感覺世界遮蔽,將思想抽象化為超經驗的理念,這種抽象概念相對于經驗世界中“生成”的恒長之流,代表著永恒的“存在”。現實中的人唯有馴服或抑制人性中被理性所拒斥的部分,否定或貶抑生命本身的某些部分,在怨恨與內疚中實現社會化。尼采以“力量意志[3]217”揭示力量本身成為目標,而人類永遠抵達不了至高,始終都留有對更深遠處虛空的恐懼。
1.抽象對具體經驗的遮蔽
昆德拉筆下的小說人物,時常追求某一抽象理論或抽象概念,妄圖將具體的經驗或感受列入括號懸置起來。
如《搭車游戲》中,“他”將“女友”勾勒為只有忠實和純潔的抽象姑娘,因此,在兩人共同扮演的搭車游戲中,嫻熟于輕佻、淫蕩的游戲角色的女友引起他對其靈魂的質疑。雙重形象的野蠻混淆使他厭惡,正如拉康所說,完整統一的人是抽象物,存在于經驗中的人是矛盾、分裂、破碎的人[10]。“他”意識到經驗世界和以概念抽象出的系統知識與直觀認知之間無法彌合的裂隙,女友的“所是”被他的欲望、抽象思維、理性傲慢所遮蔽。
對于生命有限的焦慮,往往需要人為建構種種“超越性所指”。赫拉克利特曾說,萬物無法逃脫死亡與變化[3]89,而柏拉圖出于對生命有限的焦慮轉向永恒,使絕對理性的人成為永恒存在的“人”。昆德拉筆下“人的死亡”被消解為墓碑,而這塊墓碑在時間的流逝中須讓位于后死者:《讓先死者讓位于后死者》中,“她”丈夫的墓碑被另一陌生者的墓碑替代,這一“讓位”使她憤怒于人類至高尊嚴受到踐踏,先死者的死亡不再擁有一種“死亡之存在權”。與此同時,“她”一直被迫束縛于“寡婦”這一抽象概念,并賦予這一身份宏大的意義與價值,面對男主人的引誘,她堅守著自己設立的“青春之碑”,但于經驗中,墓碑事件的荒誕使她迅速消解了宏大的意義而投向了欲望。
巴門尼德曾說:“能被思考的和能存在的是在那里的同一事物[11]”。但經驗世界遠非純粹的邏輯推理或抽象理論能夠直接演繹出的真理,抽象之道德理論及行為準則在界限模糊、錯綜復雜的現實中顯得無力。《座談會》中關于伊麗莎白被誤以為自殺這一事件的歸因,幾人以嚴謹有序的邏輯思辨得出了完全相異的因與果。他們挑選和處理不同的材料,演繹出各自的完美結論,在偶然中錨定必然的決定性因素,即使推理合乎邏輯,極具說服力,但都無從定論自殺的真實動機,伊麗莎白也并非確知自身的意志。顯然,存在(being)的被遮蔽才是常態,人們在分析“現象”之前往往被自己所帶入的偏見和預設所遮蔽,從而在“假象”的面具下挑揀著某一可能性,正如女大夫所言:若歸因的結果能拯救靈魂便試圖認定它。
時間于人,并非人被拋入世后才延展開的,流俗的時間觀念將時間理解為現成事物“在其中”生滅的無終或無限的時間。人操勞于世,將時間抽象為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客觀估算精準的時間,但在計量之前,時間“乃是某種做成我的東西[12]”。時間融入個體的生命,諸如對事物狀態的特殊感知,對時間的特殊記憶,組成個體的存在經驗。《永恒欲望的金蘋果》中“我”渴望體會文化歷史的緩慢,而人的生活類似于歷史進程,逐漸加快實則是距離的遠近。
《愛德華與上帝》中的阿麗絲將“空泛、彌漫和抽象的上帝”具體化并植入她的經驗生活,成為“反通奸的上帝”,在與愛德華的相處中,她在身體上區分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態度的轉變,與愛德華近乎虔誠的愛的宣言、絞盡腦汁的理性辯論都毫不相關,阿麗絲卻因披在愛德華身上的宗教外衣而主動背叛上帝,而這恰是出于偶然的謊言。
2.必然作為吞噬偶然的幻象
人類個體在充滿偶然性的生存體驗中,妄想以必然的先驗價值將其懸置。
如《誰都笑不出來》中,“我”的意見成為扎圖萊茨基先生的論文能夠發表的決定性條件,“我”不愿將恭維的崇拜者變為敵人,也堅決不寫該文章的閱讀報告。應對他日益頻繁的來訪,“我”以主導者的身份開啟了他企圖引誘女友的游戲,這卻使“我”無法將整件事從荒誕的嚴肅性中抽離出來,“我”和女友的關系破裂;失去了視為嚴肅的科研工作。“我”意識到不存在一個現成的“我”,“此在”永遠都在展望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來籌劃自身,只有在事后,我們被解開布條審視過去的時候,才會認清“此在”的“曾在”,以及它們的意義。
《座談會》中的哈威爾提到,恰恰在因果論不得施展之時,充滿鐵定規律的世界才得以留存一點兒無序的空間。哈威爾拒絕了伊麗莎白的性暗示,統計學家或大數據的結論都會指向他接受的結論,但正是逃脫了普遍的決定論之外,他得以在自身的偶然性中自由籌劃各種可能性。
(二)個體存在的有限性
海德格爾表明,康德提出的關于人類理性局限性的學說,立足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3]121。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類總是沉溺于無限,昆德拉認為:人自在世便禁錮于并非自我選擇的身體,并注定要死亡[1]34。此在“被拋”在世,死亡于存在者而言,是最本己、最極端的可能性,是此在“不得不承擔下來的生存可能性[8]201”。然而,“何時死亡”具有不確定性,此在于日常生活中往往掩蓋這種不確定性并遮蔽死亡的確定可知,由此減輕被拋入死亡的狀態。
昆德拉筆下的人物共同顯現此在存在的有限性。
《誰都笑不出來》中“我”因一句“玩笑”陷入了生命的虛無,他迷戀于自己主導的歷險,但事態不斷違背意志戲劇化的延展,女友和工作同時拋下他,他意識到所謂的歷險并非自己的選擇,而是“外界”強加于我們,不知它們從何來、去往何處,被遺棄感和失落感向他襲來,我們為何于“此時、此地”被拋入世,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偶然以及來自深層存在的無力。
此在“被拋入世”必然指向此在向終結存在,人類知或無知則說明了其在實際生存中如何向終結存在,而無論知或不知其將死,“首先和通常是以沉淪的方式死著[8]202”,即沉陷于常人或日常的種種事務之中,借此遮蔽向死存在。《哈威爾二十年后》中的記者從自身“所能是”之中脫落,消融于公眾視野中,躲避在看似實用的普遍規范下,恐于自身在無限的可能性中作出抉擇,沉溺于不自知的非本真狀態。然而,這正是海德格爾所描述的“常人(das Man)[8]109”即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身,“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著[8]163”,此在拋棄自己向“常人”籌劃自身,日常此在總是先行將自己與其他并非本己的一切進行比較,趨向異化,將本真的能在拒斥于心外,“哪怕只是本真地面對失敗的能在[8]163”。雖然記者極度關注自我,但他慣于在他人的眼光下尋求自己的“能是”,只得躲避在所謂“大師或內行”的權威下,以免直面自身。
生命個體無法逃脫經由歲月產生的變形,在有限的虛空中身處無遮無蔽的狀態,被孤獨和對死亡的無限恐懼纏繞。《先死者應讓位于后死者》中的墓碑,揭示出人類對生命有限的有所作為,在世者將死者的生存之“無”的存在立身于墓碑,表示哀悼和思念,耽留于死者。然而,象征生命延續的墓碑也無法逃脫時間,需讓位于后死者。故事中的女客拒絕談論死亡話題,借他物遮蔽身體的變形,將人生的意義嫁接到“人的事業”并外化到他人身上。男主人極力為自己籌劃出可抵消過往經驗中一切失意與不足的砝碼,以此來撫慰自己面對生命消逝而一如既往虛無的心靈。
人生而有限,正如《座談會》中主任醫生所言:“我”是即將回歸于大自然的灰塵。
三、“嚴肅”的愛情與除去“嚴肅”的愛情
昆德拉將“大寫的愛”延展為非嚴肅、小寫、復數的愛,“愛情的概念始終與嚴肅相連”,好笑的愛“是除去了‘嚴肅’的愛情范疇[2]43”。他于存在中聚焦愛情,愛的情感以及性欲在現代社會的陷阱中變成了什么,承載宏大意義、界限分明的“愛”在現代個體的存在中有著怎樣的變幻?
(一)“大征服者”與“大收集者”的辯證關系
在文本中,“大征服者”與“大收集者”顯現為愛情這一極管的兩端。《座談會》中,哈威爾大夫對“唐璜的結局”以及他的承繼者“大收集者”神話光暈的消解作出一番陳述。唐璜的角色在西方的想象中是“性愛的某些非神圣化[7]338”的象征。在哈威爾看來,唐璜是一個大寫的征服者,承受著“悲劇性的包袱[7]156”,在大征服者的世界中,情人之間的一瞥抵得收集者無數性愛的累積,但這崇高的意義正如唐璜最終被雷電劈死墜入地獄一樣消失了。大收集者與“悲劇”毫不相關,是順從常規與法則的奴隸,將性愛日常化和平庸化,種種激情和感情遠離大地,輕如鴻毛。大收集者將重負消解為鴻毛,而這重負幫助個體克服生命有限的不可承受之輕、奔向無限。
然而,大征服者與大收集者在文本中又呈現為辯證關系。在愛情領域,大征服者賦予愛情嚴肅意義與崇高建構,是個體通向永恒與無限的象征;大收集者看似消解了愛情的嚴肅意義,反對愛情的崇高建構,而本質上是對無限的另類想象,某種意義上是對大征服者的回歸。
1.“大征服者”向“大收集者”的滑落
對于“大征服者”而言,愛情不局限于雙方以及雙方關系問題,性愛不僅在于肉欲,還需要透過對方看到“其他東西”。《座談會》中主任醫生認為性愛是對榮譽的渴望,性伴侶作為“自我”的鏡子以衡量自身的價值。當愛情從嚴肅的范疇滑入非嚴肅的領域,性愛成為日常生活中平庸的瑣事時,人不得不“從反面”尋求性愛榮譽,即拒絕一個求愛者。對于拒絕者而言,通過對方的苛刻來凸顯自身,實現價值的“外化”;于被拒絕者而言,作為唯一選定的人,獲得“例外的榮譽”。伴侶成為自我的“鏡”與“燈”還體現在弗雷什曼身上,作為一個被拋入世的少年,編織著崇高的情感之網,投注無限力量的向往并從中汲取宗教式的撫慰。形而上學式“大寫的愛情”將他圈定在崇高價值的光暈下,以便逃離有限、非嚴肅的領域。他作為現代版特里斯丹,手握丘比特之箭,幻想極端挑剔的女大夫對自己的欣賞成為照亮他的一束強光。當他瞥見伊麗莎白美妙的肉體時,他遇見的是站立在死神之門的“愛情”,美麗或丑陋輕若鴻毛,愛情只有唯一的標準——死神,這“如死亡一般偉大”的愛使他更感強大。
“大收集者”于性愛游戲中渴求獲得不可想象的刺激與不可預見的存在之輕。無論是沉溺于其中的哈威爾、馬丁,還是愛德華。愛德華將愛情劃入“可自行決定的”嚴肅范疇中,用近乎虔誠的態度對待愛情。令他困惑的是,阿麗絲對他的接受建立在自己殉道的傳奇新聞上,而這件宗教外衣只是作為不得已的謊言披在了愛德華的身上,將他戲劇性地卷入生活的荒謬境況,他對愛情的嚴肅意義產生質疑,其重要性與他付諸實踐的效力完全不相稱,相反,性行為的發生如此容易和自然,顯得無意義。他厭惡地趕走阿麗絲這個“漂亮身體”之后,不僅沒有因此而厭惡“游戲的愛”,反而更加渴望與熟練于收集游戲,他從愛情的嚴肅領域滑入大收集者世界。
2.“大收集者”向“大征服者”的回歸
然而,“大收集者”追尋的是欲望的永恒再生,是對無限的另類想象。
在《哈威爾大夫二十年后》中的哈威爾,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魅力光環黯淡失色,無論是路過的姑娘、還是做水療的女護士,都對他視而不見,他總是處于“丟臉狀態”。然而,當他的妻子,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站在他身邊并同他親昵時,他重新獲得了失去的可見度,心中便涌現對她濃郁的愛,他的身體變成著名女演員的“等同物”,再次贏得“機遇和強健姑娘們的寵愛”。然而,哈威爾在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準備著逃脫她。哈威爾意識到自身及流傳的軼事都必然會遵循衰老和遺忘的規律,恐懼自身被遺忘、被模糊。生命終將衰竭,他面對自身的有限,唯有投身于愛欲,由它們將青春與年齡連接在一起,追求永不熄滅的欲望,并在其中抵抗遺忘。
其中的記者,請求哈威爾幫他鑒定自己深愛著的女友,動機在于獲得大師對自己趣味的贊許,他并不在意女伴的形象,而是她在他人眼中的評判。哈威爾具有敵意的評價,使不安詢問的年輕人陷入失望,他得出女友毫無價值、無趣且不美的結論并離開她,即使他仍真摯地愛著她。他追隨“高見”掀開了女大夫的裙底,滑稽地咀嚼著她平庸外表下“神秘的美”,這一稱贊出自哈威爾之口。年輕人因其取勝的速度、交歡中的女人、哈威爾的才華感到心醉神迷,幻想著自己正在成為像哈威爾一樣的“高手”。
《永恒欲望的金蘋果》中的馬丁,為自己樹立一面“永遠追逐女人的旗幟”,他將追逐簡化為“標定”“掛鉤”等賣弄技巧的行為理論,就像每日必行的宗教儀式,追逐本身成為終極目標,這面旗幟象征著馬丁建構的某種生命秩序或絕對價值,他將自己裝束為永恒欲望的金蘋果。
《讓先死者讓位于后死者》中,男主人堅持引誘與之有過一次艷遇的寡婦,即使對方年長得多,他仍不惜克服自己對她身體的厭惡與其交歡,只是為自己的 “生命密度”尋找一個證據,這位女客抽象化為曾經逃脫他的一切,成為生命永恒的意義。
四、結語
昆德拉的小說聚焦于被遺忘的“存在”,在人類的具體生存和偶然性中探索存在的可能性。在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下,現代人陷入虛無主義危機,現代所張揚的樂觀主義,即通過人類理性與科學改變世界與建立美好未來,其與現實的矛盾和沖突使現代人陷入生存的焦慮、破碎與虛無中。個體不再能夠棲息于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學的虛幻光圈,是徹底的無遮無蔽的狀態。以往承載個體“生命之重”的先驗價值成為謊言,現代人在虛無中急于尋求新的替代物。
小說集《好笑的愛》聚焦于愛情,看似現代人深陷于愛情的嚴肅與非嚴肅范疇的二元對立,實則是在有限與無限之間掙扎,愛情扮演著個體超出自身有限性的媒介,成為此在抵達無限的橋梁。昆德拉在文本中演繹著現代人在愛情領域如何面對有限與無限的終極悖論。在此悖論下,小說人物呈現為“大征服者”與“大收集者”的辯證關系,前者向后者滑落的同時,后者在悄悄回歸前者,展現出對無限的另類想象。尼采自理性主義傳統轉向對現世、此岸、現時的關注,前者是對于“美好的未來世界”的虛幻建構,對超越、來世的關注;而后者認為個體只能認清和直面自我的處境,不再包庇、辯護和自怨自艾,立足于自身去尋求自我超越的可能性。海德格爾認為本真的存在應先行到死,認清此在“喪失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8]210”,不再沉淪于日常種種事務的操勞或操持,“面對由畏敞開的威脅”確知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