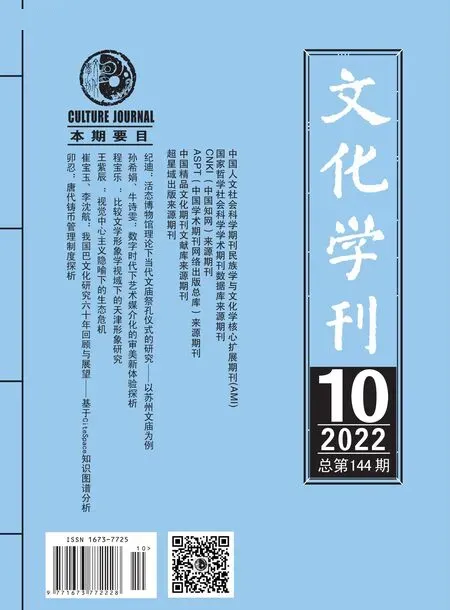論葛水平對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克諾西斯”式繼承
張林霞
誠如哈羅德·布魯姆所言,批評家們在內心深處是悄悄偏愛著連續性的[1]58,這一點是將葛水平和趙樹理兩位作家放在一起談論文學創作聯系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布魯姆的“克諾西斯”重復理論,深度挖掘趙樹理與葛水平兩位作家的創作聯系,探尋當代鄉土創作的可行之徑。
一、人物結構之“克諾西斯”
由于趙樹理與葛水平生活的年代不同,筆下人物的身份差異、思想差異以及行動力的差異較大。比如說,二位作家筆下都是以黃土高原農村的底層群眾為主要抒寫對象,但是對于底層的闡述明顯不同。就趙樹理而言,他筆下的底層群眾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真正的生活貧困者,這類人群的特點是憨厚老實的同時又帶著愚昧或者蒙昧,比如福貴;第二種是金旺、興旺之流,這個人群是趙樹理強調過的不同的群體,從經濟結構上講他們屬于貧下中農,但是他們飛揚跋扈,欺負鄰里。在葛水平的農村底層群體中,女性群體是比較矚目的,比如《喊山》中的紅霞、《甩鞭》中的王引蘭。相對于趙樹理這一前輩強者詩人(布魯姆將前輩的優秀作家稱為強者詩人),在底層農村群體的選擇上留給葛水平的空間比較狹促,將女性群體作為自身創作的關注點或許是一個偶然,葛水平是一位女性作家,她在觀察農村各階層群體時會因為自身的緣故更早地關注到女性。但這一關注的結果是比較可喜的,被辯證地提高到再創造地位的“重復”乃是新人的入門之道[1]60。這一“重復”可以說是成功的,至今為止葛水平創作的小說形象以女性形象最為典型。
趙樹理和葛水平的筆下還有一類相似的群體,他們是農村生存環境中的“權力”擁有者,權力分為三類:一為政治權力,常見為村長;二為財富權力,也就是地主和富人;三為暴力持有者,惡霸。福貴就是受制于第二種“權力”的傾軋,一步一步走向了生活的不可解,成為鄰里鄉親的“防備對象”。而紅霞和王引蘭屬于第三種權力的迫害對象,蘇紅則遭受到政治權力的迫害。在對三種權力擁有者的刻畫中,趙樹理和葛水平較為“鐘愛”的選擇是暴力持有者,農村惡霸暴力現象在特定的年代是尤為突出的,特別是趙樹理生活的社會動蕩期,且這三種勢力通常會雜糅勾結在一起形成農村權力網,客觀意義上這張大網是束縛農村發展的力量,外在的社會動蕩和內在的文明缺失共同促成了這張網狀權力的形成。“文革”期間趙樹理的一樁罪名就是描寫中間人物,其實他是在客觀呈現農村的斗爭,只是因為趙樹理本身對農村的情感鏈接,他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去看待農村的各個階層。葛水平作為后來者作家,她對暴力權力的抒寫是不留余地的,這很明顯是因為時代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
總體而言,趙樹理筆下的農村群體是全面的、普遍的也是鮮活的,客觀地展示出那個時代的農村群像,歡樂與苦痛并存,進步與蒙昧共生。葛水平筆下的農村群體相對是集中的,尤其是對女性形象的描述可謂獨到,但在普遍性上略顯不足,有血、有肉、有理想的男性形象是比較少的。韓沖較為典型但卻是作為女性形象光芒之下的男性,這大概是葛水平作為一名后來女性作家對趙樹理的“克諾西斯”式重復。
二、主題結構之“克諾西斯”
自從魯迅開創鄉土題材的現代小說以來,農村和農民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發展中的一筆色彩的飽和度從未下降。并且在此基礎上還形成了鄉土小說家群體,諸如東北流亡作家群中的蕭紅就是典型作家。趙樹理的鄉土小說創作與魯迅、蕭紅等作家存在明顯不同,那么作為與趙樹理生長在同一片土地的葛水平,她的小說創作又屬于兩派中的哪一派?有評論家在論文中提到,魯迅與趙樹理很明顯的不同在于自身的定位,魯迅是將自己放置在農村和農民之上的“喚醒者”,盡管“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心憂其思想未能開化,也會在祥林嫂死去的除夕夜不能安枕,但他還是明顯不同于吃住與農民混在一起的趙樹理。魯迅是精英知識分子,趙樹理是農民的兒子。葛水平作為21世紀鄉土題材小說家的延續者,屬不屬于精英知識分子,這一問題只怕是難于去下定論的。但至少葛水平的小說主題仍然是農村和農民,在這一點上同趙樹理是相同的,不過具體到這一主題的闡釋,兩位作家仍然存在明顯不同。
趙樹理筆下的農村主題呈現出很明顯的暖色調,而葛水平筆下的農村主題存在很明顯的冷色調,但兩位作家的主題內容存在明顯一致。細分其主題層次主要有三種,第一層次揭露農民生活狀態、展示農村發展現狀;第二層次揭露農民思想落后的現實困境。這兩個層次的主題是兩個作家共有的,也是一致的,也正是因為這兩個層次的一致性評論家才把兩位一前一后的作家放在一起做對比性研究。但這兩個層次的主題是眾多鄉土題材作家的共性,并不能凸顯出作為開創了“山藥蛋派”的趙樹理的個性也不能作為葛水平的創作特性。能夠體現趙樹理創作主題特色的是第三層次,趙樹理的筆下有一批老實本分、生動鮮活又心地善良的農民,他們會受制于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縛,但也善于接受時代進步力量給予他們的教育。這樣的農民群像在搬上舞臺之后,又起到了教育廣大農民群眾的作用,這是趙樹理作為“山藥蛋派”的最大特點,在農村生活過的人應該理解“三仙姑”“二諸葛”是怎樣“神性”的存在;也能感知金旺、興旺兄弟是作為一種什么樣的勢力影響百姓的生活;李有才這樣的人物十里八村也是有名氣的。趙樹理作為農民作家,他對農村的了解是徹骨的,或許魯迅面對祥林嫂的疑問會給出模糊又清晰的回答,但趙樹理面對她時會一眼看穿其內心活動,不得不說趙樹理的筆尖上融入了太多對農民的關心和喜愛,但是如此生動的農民必然攜帶“中間人物”嫌疑,真實的農民是落后的,是蒙昧的,甚至是愚昧的,也是麻木的,甚至有時候是可恨的,但趙樹理從來沒有拋棄過這片黃土地。如果一定要說趙樹理受到的迫害理由,所謂描寫中間人物,這個理由是成立的。農民不但是可愛的,也是可憐可恨的,因為他們需要教育和改造,但是這正是文學的本質,也是趙樹理的小說可以在精英文學當道的現代小說史上留下自己印跡的根本原因。
反觀葛水平,她的小說主題除去以上兩個層次之外也有屬于自己的特色主題,她的筆下總有一些“可憐人”,或遭命運的戲謔,或遭歹人的殘害成為孤獨的存在者,紅霞如此,王引蘭也如此,相對比趙樹理的“大團圓”式歡慶結局,葛水平的小說更多的是悲涼式結尾。盡管紅霞的喊山喊出了生命的力量感,但那只是存在于作者與讀者內心的一種發泄,紅霞還是紅霞,世界還是那個世界,從未有過一絲改變;盡管王引蘭報仇雪恨了,但仍然改變不了自身悲劇的命運和生活;失去女兒的蘇紅只能以掩耳盜鈴的方式繼續面對冰冷殘酷但卻舍不得離開的這個世界。葛水平的小說從來都是悲涼的,她筆下的農村與趙樹理溫情式的農村有著截然不同的一面。究其緣由,究竟是農村變了還是作家變了?事實上,趙樹理在寫《小二黑結婚》的時候是有現實原型的,現實中的結局是男主角岳冬至因自由戀愛而被活活打死,但是經過趙樹理改編后大部分青年男女受到自由戀愛的鼓舞。據當時數據顯示,在案件數量中,離婚案占到了50%以上,在整個晉冀魯豫邊區根據地出現一派追求新婚姻、新生活的氣象,所以《小二黑結婚》成為了我國婚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趙樹理的創作是源于生活的,這個故事是他自己考察到的第一手資料,但是經過趙樹理高于生活的藝術化處理,這一故事帶來的現實反響可謂空前。
總體而言,兩位作家的主題創作是相似的,都是取材于農村和農民的現實主義創作,也都能展示出作家對農民的關懷和對鄉土的眷戀。但是在創作的目的上,或者說創作意圖的抉擇上兩位作家存在明顯的分野。這一暖一冷的兩種處理其實并不是趙樹理與葛水平的區別,事實上趙樹理之前或者之后的鄉土作家都是采用冷色調的處理方式去面對農村以及農民的水深火熱,魯迅如此,葛水平也是如此,只有趙樹理采用了暖陽式的藝術處理方式,讓整個黃土地上的農民綻放出憨實滿足的笑容,這是他的小說能夠在劇院演出場場爆滿的根源所在,他讓文學不再束之高閣,而是成為百姓前進的行動指南,這一點是葛水平沒有做到的,事實上魯迅也沒有做到,帶血的饅頭一樣沒有驚醒華老栓之流。至于葛水平為何會有這樣后現代的處理原因是復雜的,時代的演進,個體作家的情操和藝術追求,都是原因所在。布魯姆曾說,一個詩人對不再成為詩人的懼怕也會經常體現為一種視覺病癥[1]58。葛水平面對同地域趙樹理的創作成就必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焦慮感的,但是焦慮帶給作家的影響卻是因人而異的。筆者認為,在創作主題上葛水平的創作方式明顯帶有濃厚的后現代和西方小說的特色,加入了模糊處理和人性分辨,這兩個主題或許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思想雜糅無意識進行的,又或許是作家有意為之,不管動因如何,葛水平作為趙樹理家鄉的后起之秀在講述黃土地上的故事中脫離了“強者詩人”也就是趙樹理的影響,至于這種脫離的得與失又是另外一個研究課題。
三、召喚結構之“克諾西斯”
在召喚結構中,趙樹理與葛水平的結構模式差異甚大。就葛水平目前創作的小說和散文來說,讀者群體較為集中的是學院派,作家的創作也基本上集中于這兩種文體;除去小說之外,趙樹理的劇本創作也是獨具一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趙樹理和葛水平都有戲劇學習的經歷和生活,甚至相較于趙樹理而言,葛水平最早考入的是戲劇學校,但是葛水平目前的作品集中于小說和散文。趙樹理的小說成就也是矚目的,但是相對于葛水平的小說而言,趙樹理的小說“劇場性”特征極為明顯,拿《李有才板話》來說,雖然它是一部小說,但是似乎劇場才應該是它的場所,一個張口就來的李有才可比停留在紙上的李有才生動鮮活得多。《小二黑結婚》也是如此,并且它的群眾效應是在公演之后才全面取得的。趙樹理作為“山藥蛋派”的創始人,如何把這股子“土味兒”做成了現代小說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是有講究的。趙樹理作品的召喚模式是雙向性的,精英知識分子把趙樹理的作品當作鄉土題材去看待,而農民群體把趙樹理的作品當作茶余飯后的談資,更是提升自身見識的知識來源渠道,這樣雙重的召喚讀者模式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古代與其類似的有宋代的“話本”和元雜劇,現代小說史上趙樹理的召喚結構是獨一無二的,再加上特定的時代背景,自然而然就有了“趙樹理方向”。趙樹理的作品是真正地取材于農民,服務于農民,他的群眾效應并不僅僅是萬人空巷,而是農民接受教育的藍本,這樣的作家倒和莎士比亞的戲劇有異曲同工之處。莎士比亞對自己的觀眾是沒有任何要求的,而對于演員頗有微詞[2],趙樹理對于農民的熱愛和幫扶由此可見。
葛水平的召喚模式是較為傳統的,迄今為止,葛水平的作品影響力僅限于山西和全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中,學者和知識分子是關注最多的群體,也就是說,葛水平的召喚結構是典型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學術陳列。誠然,葛水平的作品也被改編成電影,比如作品《喊山》,但是這樣的作品卻并不是農民喜聞樂見的,作品的悲劇感太強,中國的觀眾素喜團圓不喜西方社會的悲涼和人性剖析(其實這二者并無高下之分),所以帶有典型后現代特色的葛水平的作品在召喚讀者上比趙樹理少了農民群眾的參與。
當然,評價一個作家的體系不因其作品模式的異同論高低,文藝創作本應百花齊放,或許更換了趙樹理的作品產生年代也一樣不會有當時的反響力,至今也有很多讀者對于趙樹理的精英文學地位存疑。但是葛水平作為趙樹理的后輩作家并沒有在趙樹理已經獲得成功的路線上繼續創作,其中原因也是復雜的。現代農民的生活環境不再是幾十年前閉塞不堪的狀態,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農民獲取知識的渠道也在逐漸增加,手機和電腦的普及也讓劇場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葛水平選擇不走趙樹理的老路也無可厚非。況且目前文壇上的作家創作方向中鄉土題材并不多,這也是葛水平能夠獨樹一幟的原因,按照布魯姆《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中所述,后來者作家想要獲得超越強者詩人的途徑在于能夠具備創造性的重復的創作能力,從這一點上看,葛水平的召喚結構是進步的。
四、結語
作為同一片黃土地上的兩位作家,趙樹理與葛水平有著天然的聯系,高原上的風和日麗和雨雪風霜灌溉了他們的創作靈感,幾十年前的趙樹理作為農民群體中的一員,哀嘆農民的不幸,歡呼農村的進步和改革,也同樣刻畫農民的蒙昧和無知,他筆下的農村是動人的,這源于作家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21世紀的葛水平循著前輩的足跡又開始進行黃土地上的創作,她的創作自然而然刻上了當下農村的現實問題:思想落后、污言濁行、命運悲涼、人情冷暖,這種種的抒寫或許是源于最初的逃離,也或許是逃不開的鄉情。有人說,葛水平筆下的鄉村是藏污納垢的,但文學評論家終究只是旁觀者,作家在創作的筆端融入的情感是無法完全把控和體會的。
葛水平在作品中彰顯了農村生命體的微小與磅礴,這一點是葛水平作品的精華所在,也是不同于趙樹理之處,尤其是葛水平對農村女性的抒寫別具一格:男權社會的女性,又是農村社會的女性,是底層中的底層的描寫。作為趙樹理的同鄉后輩,葛水平內心存在布魯姆所說的焦慮是必然的,但就葛水平目前的作品來說,其并未表現出雷同甚至過多的相似之處,這對于評論家來說是一件失望的事,但對于文學本身而言卻是一件幸事。
春耕秋收,星沉月落,任何一個作家都難于去罄竹抒寫這片黃土地上的人和事,好在時光更迭,天地混然,兩位作家作為黃土地的兒女對它的心靈寄托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