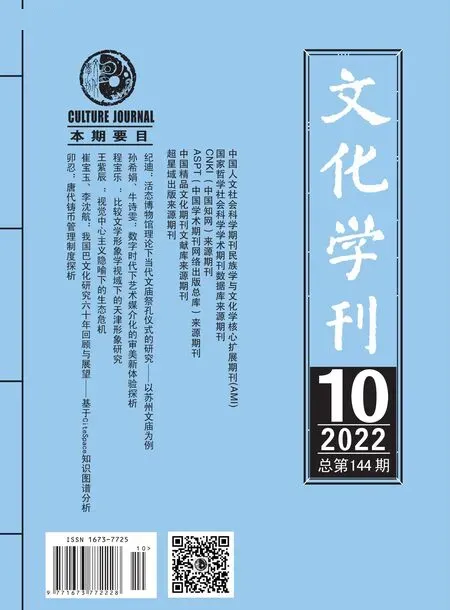視覺中心主義隱喻下的生態危機
王紫辰
一、引言
視覺中心主義一直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內含在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很多西方哲學的關鍵概念如理念、啟蒙、現象學等都在辭源上與人的“視覺”相關,理性主義傳統也在視覺中心主義的基礎上得到全新的詮釋與發展,從而形成了一種視覺在場的西方哲學,而這種思維模式深刻地改變了人們面對自然的態度及行為,甚至成為生態危機產生的重要思想原因。
二、西方視覺中心主義傾向的緣起
光與存在問題是西方哲學史上本體論與認識論的交叉問題。在本體論中光是事物產生的源頭,宇宙大爆炸的能量以光和熱的形式輻射,然后冷卻并固化成各種物質。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光揭示其他事物,引導人們的存在。[1]被“光”照亮的世界可以從邏輯上追溯到一個終極光源的存在,因此,古希臘的自然神、基督教人格化的神都暗含著類似“光”的存在,在揭示世界的意義和發展路徑方面具有同樣的邏輯意義。
(一)柏拉圖理念論:兩個世界的劃分
視覺中心主義是西方學者對傳統哲學主要特征的一種概括,是指由古希臘哲學所開啟的重視“視覺”在人類獲取知識、通達真理上的重要作用。[2]視覺在各種感覺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西方哲學中的思想大多包含視覺隱喻,甚至建立了一套以“視覺”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柏拉圖劃分了可感世界與可知世界,并區分了兩種“眼睛”,一是“肉體之眼”,一是“心靈之眼”,對應現象界的“眼睛”屬于肉體,而對應理念界的“眼睛”則屬于心靈。太陽發出的光使眼睛看見事物,“善”的理念則使心靈之眼認識真正的對象。同樣,在洞穴隱喻中,困在洞穴中的囚徒是以肉眼觀察世界,他們看到的只是世界的幻相,當某個囚徒解除枷鎖,走出洞穴,看到太陽時,才認識到自己之前所看到的世界是不真實的,只有擺脫了肉眼的局限,用“心靈之眼”才能看到事物本身。在柏拉圖看來,兩種“看”的方式和結果大相徑庭,“心靈之眼”才是通達“認識”的真正途徑。[3]
雖然柏拉圖貶低人們感覺的作用,認為用眼睛觀察事物是謬誤的來源,但是他也承認感覺所起到的輔助作用。另外,從“理念”的本意來看,它有“觀看”和“認識”兩種內涵。因此,無論是從感覺與認知的關系來看,還是從認知對象本身來看,柏拉圖哲學都呈現出視覺中心主義的特征。事物都是可知的,他偏重于用理智的“心觀”來真正實現對理念的洞察。[2]這種二元論影響了后來的西方哲學,從此,哲學家們要么從“眼觀”走經驗論路線,要么從“心觀”走唯理論路線。
柏拉圖之前,人們對事物的考察無論側重感覺還是側重心靈,都是在一個現實世界中進行的。柏拉圖劃分出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通過將眼睛的不同方式的“看”隸屬于不同的世界而使它們對立起來,建立起視覺中心主義與西方哲學的最初關聯,從此成為了傳統哲學中的視覺中心主義思維方式的起點。
(二)笛卡爾透視法:主體哲學的發端
理性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推動與笛卡爾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視覺中心主義哲學的邏輯起點。在他看來,首先能被確定的是作為主體的“我”的存在,在“我”思考的時候,主體的“我”是起作用的,是一個心靈實體。“我思”是一個人最重要的部分,不依賴于其他部分而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笛卡爾認為觀看的主體是“我”,是人的“心靈”在看,而非“眼睛”在看。事物只能由心靈所知覺,只有依靠心靈才能達到對事物的根本認識,才能避免幻象的誤導。[4]
笛卡爾認為人們用肉眼對事物的“觀看”是一種視覺的欺騙,是不完整的、不真實的,人可以懷疑一切事物。認識事物則需要運用透視的數學方法,為了保證主體“觀看”的清晰、準確,必須將事物具體化、理性化,透視法暗含了人的眼睛是主體,是視覺行為的主導,它把時間和空間暫停于一點,描繪事物時將其從整體中分離出來,然后展示為一種必然的、寫實的可視化圖景,從而使“控制”“支配”一切事物的思想漸入人心。
透視法使人們化感性為理性,化被動為主動,最終成為了一種認識世界的模式化方法,一種靜態的、理智的、固定的觀看方式,只有運用這種方法人們才能真正認識事物、掌握事物。由此,笛卡爾二元論哲學確立了理性在視覺中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真正開啟了主體哲學,為后來人與生態關系的轉變埋下了種子。
(三)近代實證主義:二元對立的深化
實證主義的發展則進一步強化了視覺中心主義的地位和影響力。事物的客觀性使人們的認識能夠科學化,從而使知識成為科學的一個根本條件。孔德認為,社會學的基礎是可以數學證明的,它應該使社會現象可以被觀察、被實驗、被分析。就連人本身也是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可視化、對象化的。只有實證的方法,才能還原事物本身的真相,這就使得理念與現實的分裂不斷擴大,自然界成為被人們所審視的對象。
實證主義者認為通過對數據的歸納就可以得到科學規律,力圖將哲學歸于科學之內。實證主義的目標是一種可規定的明確性和簡潔性,它忽視了人類樸素的、個體的經驗,創造出了一個標準的、可量化的世界,實驗方法被認定為處理一切事物最優的方法。經驗是知識的來源和基礎,科學知識之所以是精確的、有用的,也是因為它來自經驗。近代自然科學就是這一知識的范例。
實證主義認為真正的知識就是科學知識,知識是對客觀世界的解釋,知識是世界本來面目的記錄,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一種“唯科學”論。它拋棄了認識論的反思維度,切斷了知識的其他可能條件,知識的意義完全取決于科學的成果,知識被貶低為狹隘的“事實調查”,從而讓認識的具體主體排除在知識構成的要素之外。知識被限定在自然科學之中,那些無法被證實的理論都是無意義的。這種對科學和理性的追求使得自然界失去了原本的神秘性,陷入越來越被動的地位。
三、視覺中心主義的生態展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主體與客體的對立在視覺中心主義的發展中不斷強化。隨著近代哲學的興起,人們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推崇進一步加深了二者的分裂。近代哲學一方面將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肯定人主動“觀看”的存在和意義;另一方面,隨著自然科學取得巨大突破,人們開始大力發展科學和技術。人們越來越依賴理性能力,“觀看”也越來越多地與科學和技術聯系在一起,人的地位不斷上升,自然開始“祛魅”。
(一)視覺性技術:人與自然交往的手段
伴隨著西方科學的不斷發展、主體支配客體認識的深化以及科學主義認識論在西方哲學中的地位進一步加強,以透視法為主導的視覺中心主義觀看原則不斷強化,遵循理性原則的科學儼然成為支配視覺觀看的主宰。[5]科學理性在視覺觀看中的發展使得“觀看”成為了一種主觀的判斷,而事物變成了單純的被判斷的客體。科學方法在各個領域的廣泛運用,使得理性至上和科學萬能的認知得到了普遍認同,尤其是現代,人文科學的知識、人們的個性的、直接的感性體驗成為了科學與技術的附庸。
視覺中心主義進一步的發展使得人類越來越渴望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對技術的依賴也在不斷增強。技術是人的延伸,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能夠制造和使用工具,并能有目的地、有計劃地進行生產勞動,而動物更多的是生理的本能。雖然人類的視覺能力比不上某些動物,但是人可以通過科學技術來強化自己的視覺能力。借助于技術人們一方面強化了自己“觀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技術成為人作為主體與自然客體之間的必不可少的“中介”。
視覺技術的發展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增長的對周圍世界的好奇和欲望,它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通過科學技術去強化人類視覺感官的能力,主要表現為研發各種延伸人類視覺的工具。它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人們克服肉體的局限,讓人們“觀看”到肉眼看不清或者看不見的物體,以增強視覺體驗;另一種形式是直接創造能夠被“觀看”的對象。人們不滿足于只觀看自然中原本存在的事物,而是開始創造自然界沒有的東西來滿足自己的欲望,例如圖畫、短視頻、電影、建筑等。總之,人們利用視覺的技術來推動視覺能力不斷地向前發展,這種視覺需求逐漸不再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了一種對視覺技術的癡迷,這也就使得人們加重了對自然的掠奪,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生物滅絕等生態問題愈演愈烈。
(二)主客兩分:人類與自然相處的模式
主客二分不是歷來就有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隨著視覺中心主義的不斷擴張,人與自然的關系被還原為簡單的線性關系,從而催生了人們支配、改造自然的意識。為了滿足人類無止境的需求,自然界淪為人類審視和改造的客觀對象,更為嚴重的是,視覺中心主義思維和強調數學標準的理性思維已經滲透到了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人們形成了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變得越來越麻木,本應對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行為進行的反思和過去對自然界的人文關懷慢慢消失。隨著人們的主體性越來越強,自然好像除了被利用、被改造,沒有任何別的效用,只有服務于人類,自然才是有價值的。
至此,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敬畏自然、依賴自然轉向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不斷凸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6]
視覺中心主義把人類從本應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界中抽離出來,使二者成為相互對立的兩面,不斷榨取自然的價值,制造出大量超過自身需要的人工物,實質上是在摧毀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破壞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動態平衡,直接激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人們開始不再注重精神需求,只滿足于眼前的物質需要,為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不惜以犧牲和破壞生態系統甚至損壞子孫后代長久發展的利益為代價,這對于自然界的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再生性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也助長了人的異化,人們完全成為被視覺中心主義所驅使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批判性。
四、對視覺中心主義的解構與超越
從經濟角度來看,人類與生態的緊張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的后果,但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隱藏著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從根本上說,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是西方思想危機的現實表征。只有超越這種哲學范式,才能真正地協調人類與自然的矛盾。
(一)超越視覺霸權:追求人文關懷
對視覺中心主義的絕對遵從,占據了感性經驗在人類活動中的生存地位,使得科學與技術被視為一切活動的基礎與方法,盲目追求更高層級的科技,使其已經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重要標準。但是人們并非沒有反抗,20世紀以來人們對視覺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意味著影響人們幾百年之久的“視覺中心體系”開始發生轉變,人們強調的不再只是圖像的形而上意義,而是圖像本身就顯露著內在的思想。人文要素開始不斷凸顯,胡塞爾、海德格爾、德里達、福柯等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批判觀點,形成了哲學理論的多元格局。
比如,海德格爾解構了傳統形而上學中的視覺中心主義,通過重新對“世界圖像”的認識,揭示了被遺忘的存在本身,試圖消解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立。視覺中心主義將整體性的世界人為地分割開,通過等級劃分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破壞了世界和存在的原初性,這種割裂和對立使得人類面對自然毫無憐憫,肆意地攫取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海德格爾強調了觀看的地位,它是揭示存在的重要方式,對事物的觀看既不是用肉眼去具體地感受,也不是依靠心靈去抽象地知覺。而是在觀看中,世界以其自在的面目呈現出來,存在也得以真正地顯現。存在是不可言說的,只有人們不再向外探索而是重新關注自身時,世界才會在人們對自身的領悟中顯現。
視覺中心主義和技術把一切存在者都納入了數理計算之中,自然的尊嚴不復存在。由此,海德格爾批判性地提出了“詩意地棲居”,人們應該為自己開辟出新的生存可能性。海德格爾將棲居看作是天、地、神、人四方相互交織,一同構筑起人類生存的美好世界。人從來都不是自然的主人,“詩意地棲居”與之前的觀點最大區別在于它是一種對自然的非對象化保護,這是一種嶄新的生態價值選擇。人的本質是生存,人是存在的守護者、地球的棲居者。面對生態環境,我們既不應該持有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也不應該持有生態中心主義的觀點,而是應該追求一種“更高級別的人道主義”。海德格爾認為,最根本的東西是人與自然的相處方式,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去思考,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當下嚴峻的生態危機。
(二)走向和諧共存:共建生態文明
這種對視覺中心主義的超越在處理人與生態的種種矛盾中尤為重要,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視覺技術的發展是為了滿足人類的視覺活動的需求,技術是被人創造出來并服務于人的。在社會生活中不論是追逐資本的圖像觀看還是對生態環境的無止境掠奪都是人們為了某種目的而進行的。所以,在視覺活動中作為主體的人要在為自身的合理需求而“看”,而不是單純為了“看”而“看”。“看”應該是他的真實需求和體驗,否則就是異化的。所以,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視覺中心主義造成的對人的消解和對自然的破壞。[7]人類應該守護自然,順應自然的內在規律,正確認識并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摒棄視覺中心主義的弊端。
人們應該學會區分合理的視覺技術和失當的視覺技術,最重要的原則是判斷視覺技術是否真正地服務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以及是否符合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未來趨勢。視覺技術是源于人“觀看”的欲望,是溝通人與“觀看”對象的橋梁,而不是異化人的工具。它是維系人與自然關系的紐帶,而不是割裂二者的元兇。否則,就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否定。一個真正服務于人類視覺的技術應該在滿足人們“觀看”的欲望的同時又維系和加強了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并非我們要拒絕一切技術,只要加強引導與約束,堅持科技向善,打破視覺中心主義的神話,把握人與自然之間的自在的交往尺度,就能還原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
從本質上來說,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在生態環境中進行的。世界是一個整體,人類思維和科學理性的發展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推動了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和社會財富。但所有的部分都屬于某一個整體,人類也不例外。人類與自然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人類可以借助于技術建立起自身與視覺對象之間的聯系,繼而通過實踐活動將彼此之間的聯系拓展到現實世界,人和自然最終應該成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主客對立的兩方,這才是人與自然的“交往方式”的應有之意,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與長久發展。
視覺中心主義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我國乃至世界各國都應該追求生態文明這種更高級別的文明形態。人類應該把自然放在與自身平等的一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主動承擔起對自然的道德義務和社會責任,共同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我國堅持自然觀與歷史觀的辯證統一,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生態思想,為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中國方案。
五、結語
在當下,保護自然環境已經成為人類整體利益之所在,要解決生態環境的危機不能僅僅局限于生產領域的變革,生態觀念的革命也十分重要。我們要冷靜地看待近兩百年來人類實踐過程給生態帶來的利弊影響,走出視覺中心主義思想的局限,建立起人與自然平等的生態意識,倡導共生共榮的生態倫理觀念,不斷地摸索自然與人類相處的更好方式,最終實現回歸生活世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