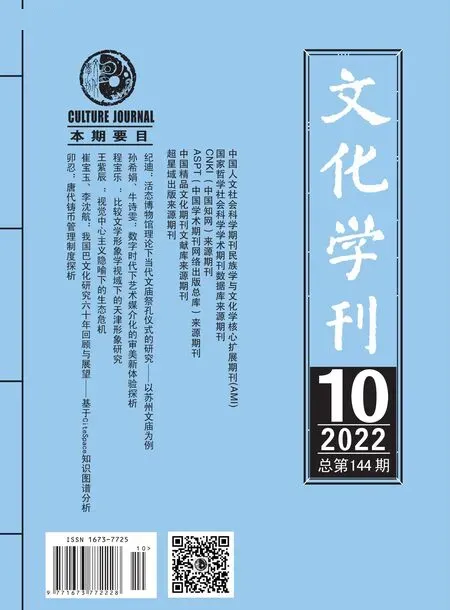權益保障與檢察主導: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省思
馬華學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制度設計之一,對緩解當前我國案件處理與司法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具有重要意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以來,司法效率水平顯著提升,被告人權益保障水平整體向好,被告人的上訴率也維持在較低水平。2019年,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還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和相關要求作出了進一步明確。但是,在制度運行和適用過程中,各地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出現分歧,依然存在一些偏離改革預期的情況,需要進一步明確標準,選準路徑。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價值體現
(一)對抗與合作模式的二元呈現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使公訴不再是公權力的單方行為,被追訴人的意見得以充分表達。檢察院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具體的定罪量刑進行協商,并在雙方認可的前提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充分體現了協商性司法的特點,并將之前的對抗模式逐步扭轉,使合作成為可能,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敵對心理。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更好地體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悔罪的態度,實現了對抗與合作模式的二元并存,也大大降低了案件的上訴率和抗訴率,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二)公平與正義價值的更好表達
認罪認罰從寬的思想在自首和坦白制度以及簡易程序、刑事速裁、刑事和解等制度中早有體現。除此之外,最高法2010年發布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也是從寬處罰的依據之一。但是,直到2018年才在《刑事訴訟法》中以基本法的形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刑事訴訟的本質是公權力通過正當的程序保障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落地,確保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充分聽取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見,并通過設置相關配套制度,如值班律師、程序選擇、權利救濟等切實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益[1],更好地體現刑事司法的公平正義。
(三)質量與效率目標的統一實現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一方面體現出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傳承,另一方面傳遞了實體和程序的價值追求,確保在兼顧辦案質量的基礎上實現司法效率的最大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落地降低了公安機關的取證難度,優化了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的程序設置,緩解了案件辦理與司法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實現了訴訟全流程的加速改革。對簡單案件,公檢法機關還可以通過集中辦理等工作機制以提高辦案效率。最高檢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要充分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及時有效懲罰犯罪、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恢復社會秩序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將質量和效率的雙重目標統一起來。
二、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考察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價值的彰顯依賴檢察機關主導作用的充分發揮,這是強化人權司法保障的迫切需要,也是助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司法實踐中依然存在一些偏離預期的情況。
(一)重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制度存在障礙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限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范圍,但是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適用的案件絕大多數都是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重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制度依然存在障礙。審查起訴時還存在檢察官因為程序變更時要求高而不愿用或者因案件影響大而不敢用的情況。從理論層面來看,重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制度符合刑罰輕緩化的趨勢,體現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表達了懲罰與教育并重的雙向價值追求,有利于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那就不能因為罪輕、罪重或者罪名的特殊等原因而人為地排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從寬處罰的機會[2]。因此,如何在重罪案件中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充分發揮該制度在促進人權司法保障、提高訴訟效率方面的積極作用依然是一個亟需討論的問題。
(二)“認罪”“認罰”的界定存在分歧
理論界對“認罪”的界定存在幾種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認事說,有人主張認事認罪說,也有人主張認事認罪加認罪名說。認事只要求如實供述全部罪行,而認罪要求完全認可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認罪名指的是對指控的罪名表示認同。也有學者指出,認罪認罰制度中的“認罪”應當包括全部罪行和罪名[3]。在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應當統一對“認罪”的認識,實現刑事司法的公平正義價值。
認罰主觀上體現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的主觀心理態度,在檢察環節外化為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接受。客觀上可表現為退贓、退賠等悔罪行為。《指導意見》明確規定,有賠償能力而不賠償損失的,不能認定為認罪認罰。對此,理論界也有不同的解讀。有的認為只需要達到自愿接受刑罰處罰的最低限度就可以認定為“認罰”。也有學者指出,對自愿接受處罰和既接受處罰又愿意退贓退賠的“認罰”的從寬幅度應當有所區別。
(三)程序從寬的效果并不明顯
認罪認罰是前提,從寬是結果。《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從寬包括實體從寬和程序從寬。其中,程序從寬的主要表現就是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適用。《指導意見》規定,對罪行較輕、有認罪認罰情節的可以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然而,在具體實踐中,程序從寬的效果并不明顯。分析某市檢察院近兩年刑事案件的統計數據發現,審前羈押率同比下降3.3%,不捕率上升7%。數據的背后體現的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價值的逐步呈現,也反映出檢察機關在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實施的大背景下,主動適應變化、規范羈押必要性審查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在所有的案件中,存疑不捕的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因為情節輕微而不予批準逮捕的案件數量并沒有顯著增長。由此可見,檢察機關在對審查批捕社會危險性條件的把握上還是相對嚴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程序從寬方面的表現偏離預期。如何將刑事強制措施控制在必要且合理的范圍之內,能不捕就不捕,盡可能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避免審判前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必要剝奪,充分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人權司法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四)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的采納率并不理想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在對認罪認罰案件作出判決時,一般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這樣的法律規定使檢察機關成為認罪認罰案件訴訟中的樞紐和實質影響者。然而,檢察官依然存在“重定性、輕量刑”的司法慣性,導致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的采納率不高。2021年,全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不起訴率為15.5%[4],同比增長2.4%,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案件做出相對不起訴決定的案件比例在10%左右,而法院對認罪認罰案件判處緩免刑的比例在40%左右。通過兩組數據對比不難看出,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的采納率并未達到預期。
(五)值班律師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
值班律師制度是適用認罪認罰制度的一項配套制度。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了促進控辯雙方的協商,平衡雙方地位,有效保障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然而,囿于人力物力財力等因素的限制,具體推行的效果參差不齊。同時,由于值班律師的經濟補償相對較少,某種意義上是法律援助性質的工作,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案件的積極性。目前,對值班律師的定位比較模糊,值班律師主要通過查閱法律文書了解相關案情,有的律師甚至從未會見過犯罪嫌疑人。很多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僅僅作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見證人而存在[5],無法充分發揮其權益保障的制度功能。
三、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建議
(一)明確制度適用的重罪案件類型
從前期偵查辦案的角度看,適用認罪認罰有利于偵查人員的取證調查,在審查起訴階段有利于建立被告人和檢察官之間的信任關系,強化檢察官的內心確信,防止發生冤假錯案。但是由于重罪案件的被告人人身危險性較大,社會影響惡劣,從寬空間非常有限,在具體適用認罪認罰時,檢察官個人很難做出定論,有時甚至為了穩妥起見對認罪認罰避而不用。筆者認為,重罪案件關系重大,可以明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罪案件類型,由刑事檢察部門組建專門的辦案組織來審查是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而兼顧檢察主導和權益保障的需求。例如,基于辦案提速增效的現實動因,對在確信被告人有罪的情況下,充分取證確有困難或者過度消耗司法資源的重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6]。
(二)統一認罪、認罰的認定標準
基于制度完備性的考量視角,檢察機關應當統一“認罪”“認罰”的認定標準,重視自愿性審查,確保認罪認罰的自愿合法。對“認罪”的界定,筆者比較贊成認事認罪說,罪名的選擇是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的法律適用,應當由專業的檢察官予以確定。其實,統計認罪認罰上訴案件的數據不難發現,被告人上訴的原因主要是不認同所判的刑罰[7],對罪名基本沒有異議。因此,只要被告人如實供述全部罪行,并且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表示認可,就可以認定為“認罪”。對“認罰”的界定,理論界有“最低標準說”和“理想狀態說”。筆者認為,不論是對量刑建議的認可還是承擔賠償責任,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犯罪行為所應當承擔的后果。因此,可以將接受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作為最低標準,對確有能力賠償而不予賠償的情況,以被害人或其家屬是否諒解、是否影響被害人或其家屬正常生活為考量標準,如果無法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影響被害人或其家屬正常生活仍然不予賠償的,不適合從寬處理。反之,可以將能賠而不賠作為降低原有的從寬幅度的依據。
(三)構建社會調查的社會支持系統
《指導意見》規定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都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社會調查,為適用認罪認罰提供依據。但是,實踐中經常出現到了審判階段才開始社會調查,有時候由于時間限制、人力緊張等原因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可以構建相應的社會支持系統,將社會調查和前期審查、逮捕風險評估以及再犯風險評估等工作予以銜接,在節約司法資源的同時擴展社會調查范圍,為案件的量刑提供更為可靠的數據支撐。目前的技術可以實現在公安、檢察院、法院、監獄等系統數據相互獨立的前提下,開放一個社會調查的數據共享通道。同時,受限于司法行政機關人力資源緊張,也可以聘請專業的外部第三方獨立機構進行社會調查,完善最新數據。
(四)重視檢察官隊伍的專業化建設
在認罪認罰案件的審查起訴過程中,部分檢察官由于長期的司法慣性,存在量刑能力不足的情況。在認罪認罰案件的庭審過程中,檢察官的職能也發生變化,由原來的證明案件事實、指控具體罪名等內容轉變成證明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態度、證明具結書的真實合法以及防止被告人反悔、案件訴訟程序變更情況下的庭審應對等內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在無形中對檢察官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檢察官履職能力、強化司法履職是助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加強新增能力需求的訓練和培養,重視檢察官隊伍的專業化建設。可以借鑒法院系統量刑規范化改革的經驗,對檢察官進行系統的量刑方法和量刑規范的培訓。同時,對認罪認罰案件的辦案流程進行細化,明晰標準,統一要求,提升效能,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
(五)持續推進智能輔助系統的開發運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賦予檢察官更大的刑罰裁量權,在重視檢察官隊伍專業化建設的基礎上,也要持續推進智能輔助系統的開發運用,提升案件量刑建議的精準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以確保刑法實施的穩定,彰顯司法的公平正義。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主要包括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具體內容。智能輔助系統的主要功能在于利用大數據對類案的量刑內容進行分析解決類案量刑的幅度和種類的數據統計,為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提供參考。同時,也可以利用智能輔助系統的大數據分析模塊對檢察官量刑建議的精準度和采納率進行統計,促使檢察官提升自身的量刑能力和專業化水平。
(六)重視外部監督
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在認罪認罰適用過程中,檢察機關對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都應當履行法律的監督職責,對強迫被告人認罪風險、倚重有罪供述而輕視證據收集風險、檢察官濫用職權風險等進行及時的監督和管控,確保制度適用的合法有效,防止出現以錢買罪、被迫認罪等情況。全過程的法律監督更加凸顯了檢察機關的主導地位,但同時也增加了檢察機關的辦案風險。特別是在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限擴張的背景下,重視內部監督的同時也應當重視外部監督,從而對檢察官的權力形成制約。外部監督的力量主要包括辯護人、值班律師、被害人、被害人家屬、社會媒體等。被害人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重要主體和利益相關者,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應當及時聽取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意見。檢察機關應當主動接受社會監督,特別是對社會影響較大、社會民眾關注度較高的案件,可以主動邀請相關部門的人員進行專項調研,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值班律師可以就律師會見、程序保障等問題提出意見,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要進一步完善值班律師的制度設計,鼓勵認罪認罰案件律師辯護的全覆蓋,適當增加推行值班律師制度的財政支出,提高對值班律師的經濟補助標準,明確值班律師的職責范圍,保障值班律師在刑事訴訟各個階段的會見權、閱卷權、建議權等訴訟權利,進而保障刑事處罰的公正性。
以上是對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幾點思考,以期有益于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主導作用,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彰顯司法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