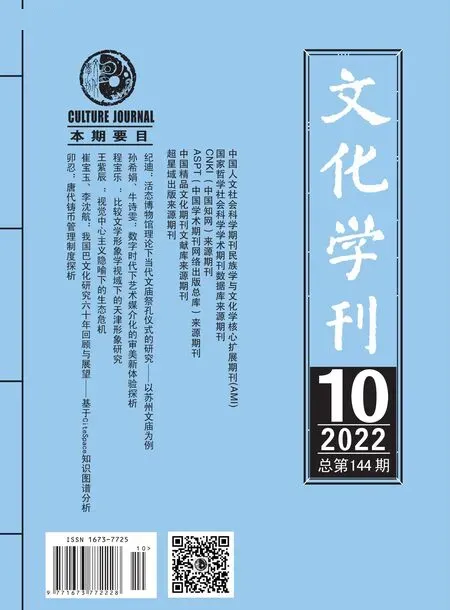俞樾晚年文學創作活動與學術觀照
李雯雯
一、引言
晚清文化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俞樾以突出的文學觀念和務實的治學實踐聲譽海外。他躬身于學術活動,著述繁富,尤其告別官宦仕途,安居蘇杭期間的文藝創作活動與文學藝術主張皆具研究價值。
二、隱逸情懷的外化建構
同治七年(1868),俞樾主講西湖詁經精舍,“講舍數楹高據圣湖,緊傍孤山”[1]391,于是泛舟湖上,“興之所至,縱其所如”[1]403。擺脫官羈后高唱“老夫無別好,所好只山林”[1]210,標榜“但存山林意,便存猿鶴心”[1]391。同治十三年(1874),俞樾在蘇州鳩工經營曲園,取《老子》“曲則全”之意。“曲曲園林本不寬,草堂春在未知寒。盤中細搗長生果,爐內深埋歡喜團”[1]251,難掩對曲園之愛。俞樾仿“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為泭浮”[1]105,在曲園疊石鑿土,“截木為桴,屋于其上”造小浮梅”[1]105。光緒五年(1879),弟子們循地選盛在杭州造俞樓,俞樾感“得此屋暫作主人,夢幻泡影大率類此”[1]399,開啟西湖側畔栽桃培李的生涯。
俞樓內亦設舫,“舟不必大”名“小浮梅俞”[1]404,青山為屋水為鄰的詩意生活照進現實,“俞舫搖來綠水清,俞樓筑向青山趾”[1]226,弟子徐琪《俞樓記》“小子與及門諸君追隨其間,誦考藥之什,賦招隱之詩,蓋以子陵、君復故也”[2]665。將老師與嚴子陵、林和靖并提,贊其“高潔不在兩賢下”[2]665。俞樾言“此樓于我蘧廬耳,天地吾逆旅,樓中人更如寄”[1]391,曲園、小浮梅和俞樓是俞樾人生如寄隱逸志趣的外化,是他于廣袤天地間選擇聊以慰藉的精神棲息地。
俞樾晚年“得力于老子之學”,感嘆“人生斯世,養空而浮”[1]472,深愿“以此治心,以此處世”[1]520,逍遙之致頗有傳統隱逸意味,在灑脫逍遙的人生態度中領悟“萬人如海浩無邊,身作飄飄不系船”的隱逸志向,遠離喧囂的詩意狀態是俞樾晚年自得其樂的人生抉擇。
三、觥籌雅集的耆老文學活動
明清文人社事“迭合和交融,不同讀者個人、群體之間……有了可以對話的共同語言”[3],俞樾晚年以文會友,加入江南士人的社事活動。
同治十二年(1873),俞樾與李鴻裔、潘遵祁、杜文瀾等人開真率會。真率會是除去官場虛假的德高望重者的雅集,“賢者規模眾所遵,摒除外飾貴全真”[4],會昌五年(845)白居易香山九老會后,真率會、怡老會、尊老會等雅集皆以高齡士大夫或方紳為主。外地士人寓居蘇杭,與本地士人文化組合,結社亦屬水到渠成之事。俞樾開設九老會,詩稱“九人八百有七齡,堪步香山九老后”[1]243。后與朱修庭、汪郒亭、盛旭人有五髯會,“八翰林才成雅集,五髯仙又聚耆英”[1]262。銷寒與銷夏是社事的重要契機,俞樾有《立夏日循俗例稱重秤人戲賦》[1]243、《銷寒吟》[1]241。真率會、五髯會、節日會等集群性質的社交“以消暇日”為目的凝聚當地名士,再現了典型的江南耆老的雅集盛況,是地域間彼此建立文化認同的表現。
江南縉紳囊橐殷盛,園林府邸是結社頻發地。同治六年(1867),俞樾與趙烈文、曾國藩、孫衣言有玄武湖雅集,“至元武湖看荷花……與諸幕客相會”[5]415,后連續三年皆舉玄武湖雅集[5]446。同治六年(1867),俞樾在詁經精舍有湖舫吟社,“諸君結湖舫吟社,半月一敘,必有詩”[6]。另舉日下詩人社,有社集《日邊酬唱集》存錄。俞樓也是社事寶地,“喜故人三兩其尊,……雅集俞樓遂成韻事”[1]391,與徐琪、楊君榮結小蓬萊社,“俞樓后山有小閣……小蓬萊,……招集同人期于九月十九日。”[1]238同治十三年(1874),俞樾、秦緗業、李肇增有湖舫詩酒會。蒙古詩人“三多六橋都護集詩會……從之游者甚眾”[7],俞樾參與其紅香吟社、蘋香吟社。光緒元年(1875),與顧文斌“以著書課子為事,或薄游蘇滬,與諸老輩文酒讌游”[8]。俞樾與壇坫耆宿、門人弟子間的文學社集,在代序乞詩、拜師交友、互贈書籍等文學活動場景中促進了近代文學的地域互動。
四、對女性文學的關注與尊重
明清女性獨立意識覺醒,主動進入文化空間追求公眾認可,以群體面貌參與文學創作和社會生活。她們擺脫封建制約聊以群聚,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
俞樾夫人和次女繡孫皆能詩文,“余曲園之中,有曲池焉……僅容二人促膝。夏日,余與內子坐其中”,《右仙臺館筆記》多載與夫人姚文玉切磋品評之事,光緒五年(1879),姚夫人離世葬于右臺山,俞樾將二百五十卷著作埋藏愛妻之畔名之“書冢”,“老妻地下聞知否,回首夷門定惘然”[1]206。光緒八年(1882),“遭愛女之喪,心緒甚劣”的俞樾,“布告海內諸君子,請以本年八月為始,停止作文三年”[1]133。不辭掂拾繡孫生前詩作,搜輯刊行。寄與北方心泉“亡女詩一百本,……所有亡女遺詩望與吟香居士分致吟好,以廣流轉,不勝盼切”。
《東瀛詩選》收錄菅茶山《問妹病途中作》[9]343,菅茶山有三妹,瀧十六歲離世,二妹千代病久孱弱,三妹好丈夫早逝。或是同情菅茶山憐妹心境,或是憐憫女性命運的共情,俞樾感曰“憂時感事之忱往往流露行間,亦彼中有心人也”[9]343。《東瀛詩選》編選時“有愛女之喪,女名繡孫,字米裳。余擬刻其詩詞遺稿……不知涕之無從也”,詩曰“紅闌、湘夢兩芬芳,彤管由來別有光。我選東瀛閨秀集,惜無愛女共商量”[9]1299。俞樾以學者視角和學術立場鑒選閨秀漢詩,拾遺補闕,“東瀛閨秀,其嫻吟詠者固稀矣……《閨媛吟藻》搜羅頗富,乃錄其佳者,合成一卷,以存彼國彤管之美”[9]1299。
俞樾以開明眼光審視女性作品,《哀小獬犰》贊重孫女“聰明渾似母,珍惜不殊男。上口詩篇熟,居家禮數諳”[1]213。慈溪張貞竹攻善學術,被俞樾破格收為女弟子。才女寥惟珍《慧花軒稿》頗得俞樾賞識,贊曰“文章要得江山助,不謂閨中亦有之”[1]495。其不拘傳統觀念束縛,通過對女性作品的編纂、文本的交流促進中日女性文學作品的傳播,有助于近世女性文學的構建。
五、結語
俞樾安心于“暮景晨曦,隨時領略,庶幾不負湖居”[1]403的隱居情志。晚年社事招飲東南名士呈現了晚清文人文學的創作圖景。他賞識女性文學,提倡“觀其詩,知其人”[1]495。其文學創作活動與學術觀照為晚清文學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