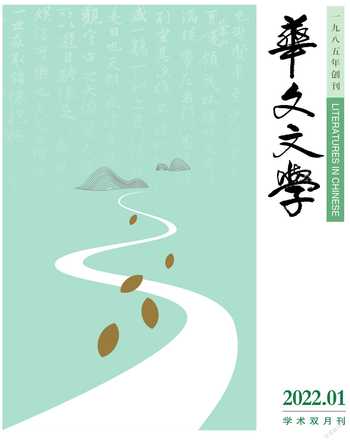“香港書寫”與傳統再造
摘 要:縱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小說的“香港書寫”,其表現出來過度內在化的傾向和過于西化的創作技法使香港文學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面臨自我設限的障礙。要真正突破這一限制,可以用“如何尋根,怎樣書寫?”的理念來做出重新思考。在“如何尋根”的層面,需要聚焦的是“如何自處的存在之思”,也就是重新審視文化身份在作家尋根的路上所帶來的價值和限度,并在流徙文化空間里重新發掘自身的文化根性。在“怎樣書寫”的方面,從過于講究西化的書寫形式里回到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尋求藝術創新和突破,從而拓寬文化香港想象的領域。這一理念成為當下切入反思研究“‘香港書寫’與傳統再造”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20世紀80年代;香港小說;香港書寫;傳統再造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2)1-0024-11
發展到今日的“香港書寫”,在建構文化身份這一層面聚集了大量有關“我是誰”以及“我從哪里來”的問題,并說出了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然而,在全球化的危機下,“有機社群”面臨解體的困境,人文精神的傳承遭遇斷裂,“尋根”重新成為香港社會熱議的話題。①文學界同樣如此,“家園”變成作家不約而同聚焦香港文化現狀與未來的重要書寫對象。因此,“我要到哪里去?”自然而然成為不少“香港書寫”念茲在茲的話題,指向的是人文香港的重塑。讓香港重返人文家園,建立充滿文化自信的“人文主體”,便成為不少作家的愿景。
一、尋根與書寫:重塑人文香港
香港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城市,在每一段時間序列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斷裂”。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歷史、文化的建構同樣發生著不同程度的裂變,致使不少作家的內心產生“失根感”。具體到“香港書寫”的層面,這種“失根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香港文化的探尋與定位,尤其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沒有形成清晰的認識;其二,地方文化精神的傳承在全球化語境下面臨斷裂的危機,對資本成長的追逐構成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作家未能從中找到走出危機的書寫路徑。可見,“尋根”與“書寫”之間存在著復雜而微妙的對話關系,即:“如何尋根”成為不少作家“重塑人文香港”的課題,而“怎樣書寫”被視為走向尋根之路的主要方法。
在走向尋根的路上,當下有一種現象值得審視,那就是不少“香港書寫”呈現出過度內在化的傾向,缺少帶有溫度的人文關懷氣息。有學者考察“九七”回歸以來香港小說的“香港書寫”后便一針見血指出:“不少寫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敢問:人在何方?固然,‘我’也是人,但這種目光只盯著自己,只在私我處挖掘的寫作,與人何干?不錯,喬伊斯、卡夫卡、卡繆,都是孤獨的寫作者,都是這樣寫,但我要指出一點,他們是我們的代言人,在他們筆下看到了我們的處境,人類普遍的精神危機。如果沒有同樣的心智和思想高度,同樣的寫作只會畫虎不成反類犬”;“正是‘不成魔不成活’,香港小說二十年來可謂鬼氣森森、魅影處處,缺少的正是人間氣息,以及小說應有的人情世態、市井風情”②。關于這點,王德威也深有同感,他在閱讀劉以鬯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一書后感慨道:“從憂郁癥(melancholia)到妄想癥(paranoia),從都會奇觀(spectacle)到海市蜃樓(simulacrum),從毛骨悚然的怪魅(gothic)到似曾相識的詭譎(uncanny),用在香港敘事上儼然都順理成章。”③由此可見,“疾病化”、“妖魔化”和“鬼魅化”的寫作風格當道。為了配合這些寫作風格,“香港創作人在敘述方式上大都擅長陌生化技法,以‘鬼眼’看世界,以夢幻為法寶,或以時空轉換為能事”④。從寫作風格以及創作技法上的選擇可知,這實際上暗示了不少作家對香港文化的現狀以及異化的人性深感困惑與失望。據此,他們不得不選擇避世的夢境、“反求諸己”的形式、“下沉”的寫作姿態以及黑暗的審美趣味。對這一問題有深層探討的代表性作家非董啟章莫屬。從“自然史三部曲”到20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神》,他通過完全沉浸于個人世界或者嘗試聯系現實來持續思考“如何文學”的問題。在全球化危機的侵襲下,作家選擇這些寫作方式來表達內心訴求本無可厚非,但過于沉浸形而上的哲思世界,甚至無法從中走出來,表現出拒絕現世的態度,那么寫作就會有“失重”的危險。長期下去,這既會使作品喪失人間氣息與生活趣味,也遠離有力的精神向度以及美好的審美精神追求。不少香港新生代作家⑤同樣面臨此類問題,即:空間意識強烈,歷史意識淡漠,顯得輕靈有余而厚重不足⑥。長此以往,這導致其中不少作家陷入地域限制和歷史迷思,內心的無根感從殖民時期延續至今,未能從歷史和現實中找到朝向未來的路。
當從“魅影處處”的小說里感受到作家對人文精神危機表現出無力消除的姿態時,這也暗示了由西西等作家于20世紀70年代建立起具地方特色的人文情懷在21世紀面臨斷裂的困境。如果說《我城》表現出一種地方精神,那么它的價值也在于處理地方題材的態度,即:站在對等的角度,關注社區和民眾過去和今日的各種情況,也透過文學性的具想象的語言建立思考和批評的方法和空間,最終要建立的不是排外和自我膨脹,而是人文關懷⑦。為走出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危機,西西“寄望于人際的溝通、文化的覺醒和多元開放”⑧,從而建立互助信任和開放包容的有機社群。在《我城》的結尾處,西西借阿果撥通電話線來連通另一個世界,以此展示70年代民間自發的一輩對地方文化認同的信心:“人類將透過他們過往沉痛的經驗,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麗的新世界。”⑨同樣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麗大廈》,展示的是“我城”世界的另一面——封閉式的世界。在美麗大廈這個近乎封閉的空間里,一個多聲部的世界展現在眼前:這里住著來自各地的平民,說著各地的方言,但大家都和睦相處、互相尊重。加深住戶彼此之間感情的事件,是美麗大廈的電梯失靈。電梯失靈的日子,住戶(尤其是住在高層的住戶)取消了不少外出活動,甚至很多時候在大廈內就可以將衣食住行解決了。由此,這幢大廈似乎與外界隔絕,并走進了“時間零”的狀態。正如西西在小說《后記》所言:“時間也不同了,時間之所以不同,其實是因為空間的變化。我目睹這種種變化,并嘗試把它存記下來。”⑩也斯對城市書寫也發表過類似西西的觀感:“看城市光看高樓大廈看不到什么,建筑的空間是固定的、外加的,要看城市里的人怎樣生活,像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所說的那樣,要看人們怎樣發展日常生活的應變計謀,使用那些空間,變成自己活動之處。”{11}在此期間,大家眾志成城、互幫互助,期間重新發現日常被乘坐電梯遮蔽的平凡人事和日常經驗,感受美好而溫暖的生活點滴,共同走過一段“沒有電梯的日子”。到了小說結尾,西西借電梯門的重新敞開來暗喻“封鎖”時間的解除,“一個開放的美麗新世界”即將出現。由此可見,西西通過觀察和思考“我城”的“一體兩面”(《我城》的開放式世界和《美麗大廈》的封閉式世界)來試圖在危機重重的“我城”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精神傳統。這也是不少70年代香港文人所致力于追求的創作目標。
到了21世紀,西西等一代文人希冀建立的“有機社群”面臨解體的危機。全球性的資本擴張不斷壓縮香港的社會空間和港人的生活空間,一系列的社會事件、急遽消逝的城市歷史景觀以及異化的人心使得不少港人失去了生活保障和歷史記憶,對社會發展和規則制度表現出極大的焦慮和抗拒,無法定位自我,尤其體現在年輕人找不到上升發展的機會。
西西在21世紀初出版的小說集《白發阿娥及其他》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表現出對轉折時代香港人文精神危機的失望和反省。從該小說集最后也是最為悲觀的一篇《照相館》可見,香港已不再是《我城》里的香港,人文價值的失落顯而易見。照相館的飾櫥里記錄著阿娥的過去,是阿娥所珍視的“歷史淵源”。然而,這個照相館“位于廉租屋邨的邊緣地帶,又是橫街的街尾”{12}。舊區的位置使照相館隨時面臨被清拆重建的命運,阿娥眼中的地方人文傳統也會隨之消失。有學者指出,西西敏銳地遇見了全球化征象下的市區重建、經濟轉型所導致的“有機社群解體”,在經驗和理念都處于傳承斷裂的狀態時,20世紀70年代所建立起來的地方文化認同在理念探求上的“有”又還作“無”。{13}這個“無”以照相館的結業和小女孩被婉拒的扣問來隱喻地方文化經驗傳承的斷裂。《我城》是“一本有關年青人在這個城市的故事”、“既描畫美好一面,亦帶有時代隱憂,整體是一片希望、朝氣勃勃,正立于發展起步點的年青城市”{14};“那一年香港的年青一代就是這么樂觀好奇,充滿元氣”{15}。在這里,小女孩作為新生的力量接續的是《我城》里的年輕一輩,可是這種被賦予“未來”的意義遭到懸置。
在高效運轉的商業環境和追求競爭有序的生存語境下,西西的擔憂和反省同樣反映在香港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中。《我城》誕生30周年之際,潘國靈和謝曉虹根據原著理念重寫,變成兩個不同的《我城05》版本,表達無限積累的商業資本“把城市空間塑造為適合資本集中和高速流通的城市之深切憂慮,亦批判了資本形塑身體空間的壓迫性方式”{16}。
潘國靈眼中的“i城”是一個充滿輕省氣氛的世界,“世界愈來愈輕省了”{17}。小說讀起來與原著一樣輕松愉快,而且還有不少自嘲幽默的語氣。然而,撥開文字的迷霧,支撐這種輕松氛圍的背后其實是沉重的人文精神危機,伴隨著作者尖銳的批評與反思。謝曉虹筆下21世紀的“i城”充滿著許許多多的“分裂人”,并被官方視為“病變的現象”和“社會沉重的負擔”{18}。這兩個版本除了是向《我城》致敬外,更為重要的是以《我城》作為當下“重塑人文香港”的起點,以青年一代的生存現狀與理想追求作為書寫對象,以此反思地方人文價值的失落和傳承斷裂的困境。假如青年一代對“我城”的歷史記憶越來越淡漠,失去日常生活記憶載體的“我城”又該寄身何處?
如果說70年代的“香港書寫”希冀找到能夠落地生根的“地理家園”,那么“九七”回歸以來的“香港書寫”主要探討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家園”。因此,兩部作品關注如何培養充滿人文價值的地方情懷,對《我城》的重寫是有著獨特而重要的意義。具體而言,就是“以七十年代的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喚回七十年代創建文化、修補斷裂的樂觀理念”{19},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開啟了“香港書寫”對“我城”應往何處去的思考,以此回應并反省當下的人文精神危機。此外,兩部作品對青年一代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途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充滿期待的,希望能承接70年代青年群體的人文理想和文化追求,并創造屬于新一代的人文精神理念,為共同體的社群內容注入更多“情與志”的人文想象,從而抗衡“有機社群”的解體。文學“有各種新興事物,也應包括歷史視野與人文關懷”{20},所以可作為傳承地方文化資源和保存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創建具有城市文化想象的人文遠景。可見,貫穿在本時期“香港書寫”中的地方情懷,是應該將其塑造成一個“廣闊的概念”,即需要正視“土地和人的關系,批判短淺的經濟或市場利益,批判無根和無視人文環境的政策”。{21}
從《我城》到《我城05》的演變軌跡,我們可以看到人與城市逐步走向封閉緊縮的關系。《我城05》已經意識到需要從20世紀70年代的地方文學資源中續接已斷裂的歷史人文傳統。然而,是否僅僅做到這點就能真正實現尋根的愿望?這里就需要對香港文化身份的特征和意涵做出更進一步的理解和闡釋。
二、如何尋根:聚焦“如何自處的存在之思”
當今不少地方都在不約而同地追逐現代性,所以有走向文化趨同的態勢。縱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小說的“香港書寫”,我們發現面對全球化危機的爆發,作家們在追憶和重述時空的氛圍下已經意識到要“文化尋根”,以此拯救因商業資本侵蝕而漸趨消亡的地方文化。文化尋根已經“成為二十世紀后期最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文化運動,像‘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實際上已經波及到全球的宗教、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22}。通過“小說”香港,不少作家發現心中的“香港”早已不存在,“此地他鄉”成為形容他們面對香港這座現代都市發展“變動不居”特征的最貼切感受。這如同一位學者所感慨的:“香港,沒有時間回頭關注過去的身世,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緊緊追隨世界大流適應急劇的新陳代謝,這是她的生命節奏。好些老香港,離開這都市一段短時期,再回來,往往會站在原來熟悉的街頭無所適從,有時遠得像個異鄉人一般向人問路,因為還算不上舊的樓房已被拆掉,什么后現代主義的建筑及高架天橋呈現在眼前,一切景物變得如此陌生新鮮。”{23}
一方面,異化的都市生態使得港人對這個城市感到陌生與疏離,常常需要面對虛假的都市景觀和不合理的生存秩序。如果無法完全適應,就會心生恐懼乃至排斥的情緒,從而加劇他們的困惑:是否這個城市從來就不屬于他們?面對此問題,有的作家用具體感性的筆觸來回望和追尋已消逝的人、物和時間,以此緩解不安與恐懼,比如:王璞和辛其氏筆下的香港。王璞《紅梅谷》中的主人公小島與香港的距離不只停留于現實中的相隔,更重要的是無法找到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侶,無論是妻子還是朋友。于是,小島只能在現實的迷宮里不停地迷失與尋覓,執著于對過去時間的叩問以及對“精神原鄉”的重構,可結局是伴有質疑與失落之感。同樣,辛其氏《瑪莉木旋》暗藏著作者內心焦灼的情緒。無論置身何種環境,四位主人公都無法忘懷過去,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尋根來緩解對未知前途的不安。
另一方面,即便已經意識到要進行文化尋根,不少作家也因持過度保護地方文化的本土意識而使其拒斥外來文化,未能把握本土文化多樣性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在尋根的路上自我設限。這種二元對立的渲染與香港不少媒體操弄單一偏頗的立場有關,香港新生代作家李維怡的小說集《行路難》通過小說與報道文學文類跨界的形式對這種片面修辭提出質疑,以“社會紀實”的方式尋回香港原有異質混雜的文化空間。
香港文學歷來都是南來北往的文人共同締造的文學自由港。為此,有研究者為“香港書寫”原本富有混雜多元的文化活力正走向片面單一局面表達深切憂慮,這種自我設限“是否構成了對香港這樣一座混雜中西文化的單一化想象?或者將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吸收的文化排斥在外,這一問題的思考其實對于重塑香港的文化內涵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24};“狹隘的本土主義,只會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而且會造成文學族群的撕裂”{25}。長期下去,這種“自我—他者”的二元對立局面會逐步演變成“原生、本土—外來、他者”的無形分界,尤其表現在香港文化與中國內地文化那種既融合又沖突的關系,潛在表達建設自身主體性的訴求{26}。
在全球化的環境里,要想真正實現“尋根”,就不能脫離“混雜性”作為流徙空間下香港文化身份特征的語境。“混雜性”的文化身份使得多元文化同時并存于香港這個獨特的空間里。在此情形下,港人希冀尋找根源文化認同的努力顯得艱難,因為這種認同既不指向純粹的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完全為西方文化價值所同化,更不能等同于地方文化。
因此,除了從地方文學中尋找適合“重塑人文香港”的書寫資源外,也要對其做出距離性的反思。具體而言,需要聚焦“如何自處的存在之思”,重新審視文化身份在作家尋根的路上所帶來的價值和限度。目前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切入:
一方面,香港的半唐番文化自成系統,讓運行其中的多種文化并行不悖,而地方文化的多樣性是由“混雜性”的文化身份決定。它使得香港經驗由本地和多種“他異”經驗共同組成,并且處于不斷變動調整的過程中。對于“混雜性”的文化身份建構,“除了華商/非華商、華人文化/非華人文化,以及新/舊歷史認知的問題外”,還受到“階級、性別、性取向、原居民/土生代/新移民等等的異質緊張關系”所影響{27}。可以這樣說,“香港經驗”不再僅僅局限于地理意義上的理解,而是已超出地域范圍并融進了世界各地的元素。在與全球化的互動中,半唐番文化能讓香港的文化身份保有自身的復數性。
另一方面,要走出“混雜性”文化身份所生發的限制,尤其要注意“混雜性”概念本身的游移與含混,也會阻礙作家尋找根源文化的努力。事實上,“混雜性”內在蘊含明顯的“有我”意圖,隱含的是希望香港文化能建構突顯自身“主體性”的策略。在現實語境下,對“混雜性”的過分強調其實源自他們期望探尋與定位香港文化,尤其是與中國內地文化的關系未能形成清晰的認識。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書寫”所表現出來的過度內在化傾向與這種模糊的認知密不可分。這也成為“香港書寫”無法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走向實質性突破的重要原因。實際上,他們已經意識到過于強調文化身份建構的主體性是不利于為香港文化的未來提供更多富有可能性的想象。相反,此時作家應著眼于帶有“精神性”的概念,也就是本文所認同的文化根性。所謂“文化根性”,指的是“作家與腳踏著的土地以及在此凝聚起來的文明和文化生死相依的一種認同感,是根植于母語的一種血緣意識在生命中的覺醒”{28}。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中國香港作家嘗試借助小說尋求文化根性、重返精神原鄉,進而解決英殖民統治時期留下的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去歷史化”行為;另一個是刻畫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香港歷史形象,尋根的意識在此彰顯。具體到敘事領域,他們將目光聚焦百年殖民史,在城市史、家族史以及個人史敘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以此試圖治愈殖民時期留下的“無根癥”,在中西文化融合視角下重新思考“香港”的前世今生。具體到敘事領域,主要產生以下四種代表性的敘事形態:雙重顛覆性敘述聲音(如: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馬家輝《龍頭鳳尾》等)、個人/集體口語體的敘述方式(如:黃碧云《烈女圖》《烈佬傳》等)、充滿象征意味的家族書寫(如:西西《飛氈》、陳慧《拾香記》、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等)、多聲部交錯的空間敘述(如:董啟章《地圖集》《繁勝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等),由此可看出“賡續歷史”與“精神尋根”之間存在復雜而微妙的對話關系。{29}
從以上分析可知,要想真正找到屬于香港文化的根,就要在流徙文化空間里重新發現并審視自身的文化根性。香港文化“其實是包括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內的世界經驗的聚集,最后形成以嶺南語言、文化、民俗為主體,同時混合外來殖民文化及其現代消費文化的地域性文化特征”{30},在高度西化和商業化的環境下延續著中華文化根脈,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1)追溯文化意象與中華戲曲淵源,比如李碧華《胭脂扣》、海辛《塘西三代名花》等鉤沉粵曲與20世紀30年代“塘西風月”文化的關系等;(2)探尋文化身份與中華飲食聯系,像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莞香”想象、也斯《狂城亂馬》的港菜混雜敘事、西西《飛氈》里的涼茶店堅守等;(3)強化粵語寫作與中華語言的承傳,黃碧云、董啟章等作家常出現粵語書寫,以此確證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傳承;(4)從信仰神巫、節慶風俗、葬俗禮儀等繼承與再造中華傳統民俗文化,也斯、王良和、黃碧云、董啟章、李碧華等筆下的香港民俗書寫呈現出“狂歡性”,進而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到混雜的平衡點。由此可見,香港的半唐番文化是從中國文化的根性中生發出來的。同理,香港文學有著半唐番文化的顯著特征,但根依舊在中國文化。
香港的混雜性文化身份離不開以中國內地文化作為參照系,正好說明香港離不開中華文化這個母體。為此,劉俊的提議是恰切的,他認為:“香港文學之所以會具有‘中間性’、‘在其間’和‘兼間狀態’,從根本上講是由香港文學是中國‘特區’文學這一特質決定的——作為中國文學中的‘特殊區域’文學,香港文學既在中國文學之中又區別于中國文學中的其他地區文學(大陸文學、臺灣文學),這樣的一種特殊性就使得其‘中間性’、‘在其間’和‘兼間狀態’,說到底其實是香港文學中的香港特質和中國屬性交織重疊的結果。”{31}有中國香港學者同樣將香港文學的特質形容為“中間狀態”:“在一場辯論中,一名女子談到愛是什么,便打了個比方,說那是一條‘愛的梯子’(ladder of love),在梯子上攀上攀下的人,就是為了尋索最適合自己生存的位置。我所知道的香港文學,約略也是一條這樣的梯子。香港的人和文化的流動性,說來何嘗不是這樣一條第俄提瑪的梯子呢?”{32}馮偉才也說過一番客觀而中肯的話:“香港在地理環境、歷史源流、文化根源各方面,都是中國的一支。”{33}由此可見,香港文學的“中間性”是需要依托中國母體才能更好地凸顯出來,即:它應該是以中國文學中的其他地區文學(內地文學、澳門文學、臺灣文學)作為參照的語境來談獨特性和豐富性。其他地區文學無法代表香港文學,香港文學亦然,但它們都是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怎樣書寫:重擷失落的東方美學
在作家“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如果說“如何尋根”的焦點在于思考“如何自處的存在之思”,也就是明確香港文學的根在中國文化,那么“怎樣書寫”就要落實到文學上“詞與物”關系的審美之思,即作家如何通過美學趣味的選擇來重構人文精神傳統乃至于創造新的人文精神理念。“香港書寫”作為對本地“文學記憶”和“文學審美”的記錄、保存、傳承乃至創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此作為思考的原點,就可以在“怎樣書寫”的層面做出相應地思考。
作為中西文化碰撞的交匯點,“香港書寫”的先鋒形式探索可謂得西化風氣之先。縱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小說的“香港書寫”,我們發現在形式探索的西化方面確實走在中國其他地區文學的前面,不少中國香港作家更為熱衷于如何取法西方現代與后現代的創作技法,比如說堅持走歐化路線的董啟章曾坦言“閱讀受西方的影響較大”,寫作繼承自劉以鬯、西西、也斯等這一脈現代主義文學傳統,而20世紀50、60年代的寫實傳統則與他本人的寫作不太相關{34}。相較而言,則較少從中國傳統文化里獲取書寫資源,這尤為體現在本地生長的新生代作家身上。袁良駿曾批評當今年輕一代的香港現代主義作家走入了如下誤區和困境:“其一是有些作品單純玩弄現代主義技巧,甚至故弄玄虛,寫來寫去,誰也看不懂,只好靠文友之間互相捧場了。其二是他們對歷史悠久的現實主義傳統采取了十分輕率的一筆抹殺的態度。”{35}為此他下了一個結論: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事實上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36}。當然,這個結論有點失實了,因為到目前為止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依舊是香港文學的活力所在。可是,這個結論也有它的合理之處,那就是過于熱衷對“西化”的強調也使得他們的“書寫”遇到了無法突破的瓶頸,失去了對中國傳統小說審美趣味和講故事方法的傳承和探索創新的興趣。如果只迷戀在形式上師法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派,過于突顯形式和語言的獨特性,那么就很容易迷失書寫的方向。也就是說,“在書寫中所經歷的不可回轉的歷史性的破壞,在漢語的母語的意義上,他們成了離家失所的人”{37}。不少中國香港作家在“怎樣書寫”的層面是有走向自我封閉的危險。與中國傳統文化接續的斷裂使得作家作為敘事主體在審美精神位格(person)的追求上顯得無力而平庸,并在人文精神和審美話語方面無法回到真正的原鄉。這種現象的發生主要源自現代性危機給香港文化所帶來的巨大沖擊。
現代性的“危機和困惑”,若放到香港“重商輕文”的文化語境里,指涉的則為現代性的“工具理性”大勢壓倒“價值理性”。對于西方現代性的質疑,既來自后現代主義,也來自后殖民主義。對于中國而言,后殖民視角的批判更有啟發。后殖民主義認為,西方現代性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非西方的世界,從而壓抑了殖民地第三世界的歷史。更大的問題在于,殖民地第三世界自覺將西方現代性視為普遍性,貶斥本地的文化,從而構成自我殖民化{38}。陳國球在撰寫《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序》時曾明確指出香港產生“自我殖民化”現象的原因,那就是:香港的文化環境與中國內地最大分別是香港華人要面對一個英語的殖民政府{39}。葉維廉也曾對這種“自我殖民化”現象在香港的具體表現做過精辟分析:“呈現在社會的內在結構的是香港高度的商業化。商業化游戲的規則是依據西方文化工業的取向;貨物交換的價值取代帶有靈性考慮的文化價值。貨物交換價值之壓倒靈性文化價值的考慮正好幫助了殖民主義淡化、弱化民族意識和本源文化意識,使原住民對文化意識、價值的敏感度削減至無。”{40}韋伯曾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將“現代性”描述成“一個理性蘇醒、逐步給世界祛昧的過程。就是說,理性引導社會脫離傳統束縛,轉而依賴它的合理與理智去認識并征服世界。然而,這一歷史過程大大伸張了工具理性”{41},并“喪失了價值或意義的維度”{42}。同時,他將工具和價值同視為互相對立的理性行為,并尖銳指出:工具行為講究效益,追求利潤;而價值行為不計成敗,只認道德義務。由于這兩大理性行為水火不容,此長彼消,就造成社會價值領域的持續分裂{43}。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理性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對立分裂中,葉舒憲認為現代性危機在21世紀的全球文化格局中“以前所未有的明晰形式爆發出來。從更深廣的背景看,現代性的危機之終極根源是文明本身的危機,是人類自5000年前邁入文明門檻以來漸進累積的癥結在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空前激化情況下的大發作”{44}。與此同時,這種重“工具理性”甚于“價值理性”的觀念,實則與現代性具有的“變動不居”特征聯系在一起,并引發了普遍的人文精神危機。實際上,這種人文精神危機來源于現代性將人從現代化的“主體”轉變成現代化的“對象”。這里可以借韋伯的一個觀點做進一步理解。他認為,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合理化的過程,工具理性逐漸取得支配地位。于是,“規章統治人”成為生活的普遍景觀。人是現代化的主體,是他們創造了規章;但反過來,他們又是現代化的對象,不可避免地變成規章統治的對象{45}。因此,當技術(工具理性)成了解決“一系列無法解決的難題”的信仰后,如卡爾·施米特所言,精神中立性隨著技術駛進了精神虛無(beim geistigen Nichts)的港灣{46}。
在經歷現代性危機(尤其以工具理性為主導)對傳統文化生活及其人文精神的侵襲以后,香港許多社群文化面臨喪失原有文化遺產的危機,民族精神能量也日漸削弱。與此同時,“語言的衰落對文化傳統的侵蝕,不可小覷”{47},漢語母語的書寫至此失去具有藝術本真的靈暈。在本雅明看來,靈暈的消失“導致了傳統的大動蕩——作為人性的現代危機和革新對立面的傳統大動蕩,它們都與現代社會的群眾運動密切相聯”{48}。由此可見,對工具理性的膜拜致使“香港書寫”無法真正抵達精神和語言的原鄉。作家意識到需要文化尋根已經是實現走出危機的第一步,而接下來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著眼于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性如何在這個流徙空間里撞擊、融合和砥礪的情形,也就是需要在現代性基礎上找到適合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當代性的生發土壤。簡而言之,就是探討“‘香港書寫’與傳統再造”這一問題。
鑒于此,在“如何尋根”的層面,需要“重新打量那些生長在傳統內部的、被我們慢慢遺忘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能量”{49}。在“怎樣書寫”方面,如何從過于講究西化的書寫形式里回到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尋求藝術創新和突破,包括講述香港故事的方法和路徑并將獨具情懷的語言與文化想象融為一體,從而拓寬文化香港想象的領域,是接下來中國香港作家需要著重思考的問題。
無可否認,中國香港作家創作時所使用的“中文”語言背后就有著一套完備的中華文化思維模式。也斯在分析香港教育時曾明確指出:“英文教育雖然占盡優勢,但中文教育未像亞洲其它一些地區那樣受到壓抑,只不過是更著重傳統的古典文學教研、著重儒家思想等比較正統而無顛覆性的思想。”{50}實際上,在香港新文學萌芽期,文壇就熱衷于“西化”創作觀念問題已經有了反省的跡象。據趙稀方考察,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小說星期刊》“雖然發表新文學作品,卻并不放棄舊文學,并且能夠從香港自己的歷史語境出發,反省‘西化’觀念”{51}。由此可見,一百年前的香港新文學已經注重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那割舍不斷的關系。
殖民性在香港是長期以現代性的名義出現,并且在“自我殖民化”的過程中不斷弱化中國傳統文化對香港的影響。趙稀方已反撥了一部分人所認為在香港新文學時期新舊文化處于相互排斥的現象,事實應該是“英文和中文的對立”,孱弱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的作用更多是“成為民族認同和反抗的工具”。{52}這種看法得到不少中國香港學者的認可,如陳國球認為:“為了帝國利益,港英政府由始至終都奉行重英輕中的政策。這個政策當然會造成社會上普遍以英語為尚的現象,但另一方面中國語言文化又反過來成為一種抗衡的力量,或者成為抵御外族文化壓迫的最后堡壘。”{53}在代表作《小說香港》里,趙稀方對這種新舊文化處于同盟關系的境況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在大陸,舊文化象征著千年來封建保守勢力,而在香港它卻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認同的積極作用。在大陸,白話新文學是針對具有千年傳統的強大的舊文學的革命;在香港,‘舊’文學的力量本來就微乎其微,何來革命?如果說,在大陸文言白話之爭乃新舊之爭,進步與落后之爭,那么同為中國文化的文言白話在香港乃是同盟的關系,這里的文化對立是英文與中文。香港新文學之所以不能建立,并非因為論者所說的舊文學力量的強大,恰恰相反,是因為整個中文力量的弱小。因而,在香港,應該警惕的是許地山所指出的殖民文化所造成的中文文化的衰落,而不是中國舊文化。一味討伐中國舊文化,不但是自斷文化根源,而且可能會造成舊文學滅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54}
因此,要想實現人文精神傳統的重塑乃至于再造新的人文精神理念,需要回到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尋求藝術資源。為此,有兩點是作家在走向“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可以考慮的:
一方面,克服并走出對西方文化的“仰賴情結”,重新培養對東方文脈的自信與想象。由于香港長期為西方殖民主義所統治,“英語所代表的強勢,除了實際上給予使用者一種社會上生存的優勢之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對本源文化和語言的自卑,而知識分子在這種強勢的感染下無意中與殖民者的文化認同,亦即是在求存中把殖民思想內在化。……這種殖民者文化內涵的內在化是一種自覺不自覺間的同化,在香港極其深入和普遍”{55}。黃傲云也指出:“我到過不少受過殖民地統治的國家,發現殖民地政府的共通點,是提倡宗主國語文,壓抑被統治民族的文化。懂得宗主國語文的人可以做大官,那么這些大官的語文程度,肯定是比不上來自宗主國的人,更肯定的是他們很易有很重的自卑感。”{56}這種由殖民者制造的“同化”及其引發的情結,屬于殖民活動的第二階段,屬于在軍事征服后的統治階段。這種情結,是“殖民者思想的內在化過程和這個過程同時引發的對本源文化意識和對外來入侵的文化意識‘既愛猶恨、既恨猶愛’的情結”{57}。不少中國香港作家對這種充滿矛盾的“同化”情結是懷著復雜的態度,因為“一面要為兩種文化協調,一面又在兩種文化的認同間彷徨與猶疑”{58}。趙稀方對這種態度導致的結果做出客觀總結:“本土港人的自覺不自覺的西方文化認同傾向是明顯的,其直接結果就是香港政治上的相對穩定,這是香港的一個獨特之處。”{59}由此可見,實現香港去殖民化仍任重而道遠。
另一方面,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使他們的內心產生不適感。為了緩和這種感受,他們選擇回歸,希望能從地方文化中尋找書寫資源并重建有機社群的精神品格,從而抗衡現代性危機給香港帶來的消極影響。然而,書寫的局限性也于此浮現,主要原因是缺失了大力弘揚東方文脈優勢這一維度,喪失了從中吸取精神能量和書寫經驗的有利契機,比如:香港兩位著名新生代作家韓麗珠和謝曉虹通過撰寫“城市異化”的小說延續了世紀末香港文學“無愛紀”的書寫,展示空間和權力如何與社會互動,敏銳捕捉人與空間割裂的異化感、人與人關系的疏離及各人內心的空虛感,用“陌生化”的寫作技巧反映人心的躁動,對不合理社會制度壓迫下走向“單一化”現象提出反思。可這種灰黑色調的書寫給人負面的排他效應感,不知道如何延續香港以往多元文化的活力,更不清楚如何結合東方文脈的傳統解決現實問題。實際上,西方一些智者對現代性的危機早有警惕。19世紀末,齊美爾(Georg Simmel),涂爾干(Emile Durkheim),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等人都曾敏銳地洞察到西方人文傳統與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發展失衡帶來的社會危機,并就此開出過補救的處方。到了20世紀50年代,傳統與現代二元互補的呼聲成為西方后現代主義的重要思潮。{60}因此,在現代語境中“重擷失落的傳統精神和東方美學”,并將它們做出創造性地轉化,可以成為接下來“重塑人文香港”的書寫方向。香港文學應是有精神的寫作,而不是避世的夢境。{61}
傳統東方美學的再造為本文所設想的書寫方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所謂“東方美學”(Oriental Aesthetics),據朱立元等學者的考察,一般指世界東部地域主要是亞洲地區各民族和國家的美學思想。東方美學同東方哲學傳統中重感受、重領悟、重直觀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與西方美學基于西方哲學中強大的理性主義傳統不同。現代東方美學也吸收了不少西方美學的內容{62}。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關于討論“文化中國”議題的研討會上,論文集編者在前言中指出,談文化不應從本位主義出發,又應兼重多元化、精致與通俗混融,并尋求傳統的轉化{63}。因此,透過香港經驗來參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行為,也不失為在現代語境下中國傳統文化為求“新變”的一次可操作性實踐。凌逾認為傳統文化的再造是可能的,需要從各類跨媒介創意的磨礪中實現中西文化的跨界變通。她以四部中國臺灣影響較大的戲劇和電影(戲劇《暗戀桃花源》、舞劇《水月》、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以及電影《刺客聶隱娘》)為例,考察它們如何相互吸取智慧,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邊界找到焊接點,通過活用各類媒介來復興和優化傳統,并強調這“需要跨媒介的精神,靈活的變通,融通的智慧”{64}。
以上就“香港書寫”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表現出來的限度做出反思。然而,這并不是說所有的“香港書寫”都忽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有一些中國香港作家,如董橋、鐘曉陽、辛其氏、李碧華、葛亮等都選擇書寫帶有古典情愫的文字來使“香港書寫”接續和傳承中華傳統文脈,并在“復古”的創作中求“新變”。其中,作為南來香港的新生代作家,葛亮的創作反撥了不少“香港書寫”過于西化的弊病,可以作為典型范例進行考察。《浣熊》是葛亮書寫“香港”的小說集。當思考城市的當下與歷史關系時,他是這樣闡釋的:“即使表達相關這座極具現代性的城市,我依然傾向于切入其文化傳統的部分進行表達。我相信這是這座城市的根基,比如,《浣熊》這部小說集,關注這城市中的節慶,如長洲的太平清醮,大澳的侯王誕。這些節慶關系著城市的淵源與其發展中重要的歷史節點。傳統凋落的過程中,它們的存在意味著,某種文化精神以儀典化的方式在進行傳遞。在現代情境里考察傳統的去向,主題會更為明晰。”{65}同時,這種接續和傳承并不是單純的“復古”。從近年的創作可知,葛亮追求更多的是在包括人文精神和審美話語范疇的“復古”基礎上求“新變”。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香港小說里,有兩部作品可以被視為“新古典主義”的典范之作:一部是鐘曉陽的《停車暫借問》,另一部就是葛亮被海外評論界譽為“新古典主義小說的定音之作”的《北鳶》。這兩部作品不完全屬于“香港書寫”范疇,但在復歸傳統精神和東方美學的理念中,其實也滲透著他們對香港文化、歷史和社會的思考,可以從不同側面為當下的“香港書寫”提供可資借鑒的書寫經驗和方法。尤其在“如何尋根、怎樣書寫?”的層面上,兩部作品是有延續性的。鐘曉陽的《停車暫借問》是在20世紀80年代感慨古典精神和東方美學在香港這片現代土地上面臨失傳的困境,而葛亮的《北鳶》則是在21世紀嘗試續接并彌合這種斷裂,通過創設融南北中國不同文化品性的多元共生空間“襄城”,來觀照傳統與現代、南方與北方如何于此地進行相互的對話、砥礪和融合的情形,讓古典精神和東方美學復活在這片現代土地之上。用葛亮的話來定義,新古典主義的歷程就是“常”與“變”,即“常是傳統的東西。在時代交接時,遭遇來自現代的考驗,而在這種情況下,怎么通過當代人的消化、體認、反芻,再把所謂的傳統通過你的方式表達出來”{66}。換言之,“新古典主義”就是“以現代的方式從古典文學傳統中汲取營養”{67}。凌逾將《北鳶》視為“新古韻小說”的代表,并提到:“新古韻小說的復古不是關鍵,而重在熔鑄當下文化,強調深度層次的新變,在文本哲思意蘊、符號敘事形式、文化轉型省思等層面的突破。”{68}
放在“香港書寫”的語境,“重擷失落的東方美學”指向的是既要從東方美學里吸取書寫的資源和方式,也要提取一種社群乃至民族的精神能量和氣質。《北鳶》匯集了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者合一的精髓,在香港這座具有典型商業化特征并融匯中西文化的大都市里,找到自身文化“異質同構”的立足點。從東方美學出發,《北鳶》將中國文學的東方氣質和古典精神與當下和西方的文化精神作了成功的對接,在形式和內容上為過于西化的“香港書寫”確立一個新坐標,相信往后的“香港書寫”會出現某種程度的創作轉向。
現有對“香港書寫”的研究,用王德威的說法來總結,就是“往往強調‘物理’、‘病理’層面”,而忽視了香港敘事的“倫理”層面,“除非我們對香港敘事的倫理層面多作思考,便不足以更理解香港敘事的物理和病理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學有別于其他華語文學的特色”{69}。也就是說,要想真正對作家眼中的“香港”做出觀察和解讀,就要從“倫理”的維度出發來考察敘述主體的寫作姿態和審美位格。“如何尋根”指向反觀自我主體(我是誰?),而“怎樣書寫”則牽涉到“及物”的問題,也就是為解答“我是誰”而選擇使用相匹配的語言、文體和表達風格。具體而言,用“如何尋根,怎樣書寫?”的理念來思考敘事主體文化心理在歷史和現實錯綜復雜的互動語境中的演變邏輯以及如何在漢語母語的表述及更新中重返審美及話語層面的原鄉,是當下切入反思研究“‘香港書寫’與傳統再造”這一問題的有效路徑。
① 需要強調的是,關于發生在香港“人文精神斷裂”的問題并不是屬于“九七”回歸以來的特有現象,而是英殖民統治時期就存在。
②④ 蔡益懷:《小說我城·魅影處處——香港小說二十年(1997-2017)批與評》,《香港文學》2017年7月號。
③{69} 王德威:《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香港文學》2007年7月號。
⑤ 本文定義“香港新生代作家”主要以出生年份、作品發表時間和地點、在中國境內外產生影響的時間和地點、作品內容是否多圍繞香港進行書寫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目前聚焦的范圍大致為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成長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九七”回歸后發表小說并產生影響的香港作家。(注:此處定義主要參考了伍家偉、鄒文律、陳慶妃等學者作家的觀點進行闡釋)
⑥ 陳慶妃:《香港折疊——論韓麗珠兼及香港新生代作家的書寫局限》,《文學評論》2020年第3期。
⑦{20} 陳智德:《論七十年代的都市文學》,見香港藝術中心及Kubrick編:《i-城志——我城05跨界創作》,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第12頁。
⑧{13}{19}{21}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59頁,第161頁,第234頁,第30-32頁。
⑨ 西西:《我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239頁。
⑩ 西西:《美麗大廈》,臺北:洪范書店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12頁。
{11} 也斯、陳智德:《文學對談:如何書寫一個城市?》,《文學世紀》2003年1月號。也斯在這個對談里把“Michel de Certeau”翻譯為“地·撒圖”,但鑒于內地學者普遍將其翻譯成“德·塞爾托”,所以此處使用內地學者翻譯的名稱。
{12} 西西:《照相館》,見陶然、蔡益懷主編:《香港文學》(增刊),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6頁。
{14} 《i-城志》編輯小組:《有關〈i-城志〉》,見香港藝術中心及Kubrick編:《i-城志——我城05跨界創作》,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15} 茹國烈:《給自己寫信》,見香港藝術中心及Kubrick編:《i-城志——我城05跨界創作》,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16} 鄒文律:《〈i-城志·我城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論“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人文中國學報》2017年第2期。
{17} 潘國靈:《我城05之版本零一》,見香港藝術中心及Kubrick編:《i-城志——我城05跨界創作》,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頁。
{18} 謝曉虹:《我城05之版本零二》,見香港藝術中心及Kubrick編:《i-城志——我城05跨界創作》,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
{22}{44} 葉舒憲:《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第1頁。
{23} 小思:《香港故事》,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頁。
{24}{30} 龍揚志:《香港回歸二十年的文學“本土”倫理》,見暨南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編:《粵港澳青年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未出版),會議時間:2017年5月20-21日,第72頁,第72頁。
{25} 蔡益懷:《港人故事,如何言說——香港文學的文化脈絡與獨特風貌》,《文學評論》(香港)2013年4月號。
{26} 關于香港學者和作家如何利用“第三空間”理論來探討香港文學與中國內地文學既融合又沖突的關系問題,筆者已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學文化身份認同研究批判——以本土性與中國性的內在矛盾為核心》(《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3期)一文做了詳盡探討,篇幅所限此處不作展開。
{27} 羅貴祥:《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66頁。
{28} 鐘曉毅:《香港文學:身份之中與身份之外》,《香港文學》2006年1月號。
{29} 有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小說中的“歷史敘事”問題,筆者已在《賡續歷史,重返原鄉——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小說的“歷史敘事”》(《文學評論》2020年第3期)一文加以論述,篇幅所限此處不作展開。
{31} 劉俊:《香港小說:中國“特區”文學中的小說形態——以〈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為論述對象》,《香港文學》2012年5月號。
{32} 草草:《書介:Metaxy:中間詩學的誕生》,《文匯報》(香港),2011年12月19日。
{33} 馮偉才:《評“香港文學本土化運動”》,引自楊匡漢:《學術語境中的香港文學研究》,見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0年版,第655頁。
{34} 張璐詩:《董啟章“寫本土是為了寫世界”》,《新京報》,2010年3月27日。
{35}{36} 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第22頁。
{37} 傅元峰:《新詩地理學:一種詩學啟示》,《文藝爭鳴》2017年第9期。
{38}{51}{52} 趙稀方:《〈小說星期刊〉與〈伴侶〉——香港早期文學新論》,《文學評論》2016年第4期。
{39}{53} 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序》,《香港文學》2014年11月號。
{40}{55}{57}{58} 葉維廉:《解讀現代·后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索》,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50頁,第150頁,第157頁,第157頁。
{41}{43} 趙一凡:《現代性》,見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頁,第647頁。
{42} 杜紅艷:《多元文化闡釋與文化現代性批判——布達佩斯學派文化理論研究》,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頁。
{45} 周憲:《從文學規訓到文化批判》,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頁。
{46} [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頁。
{47} 葛亮、馬季:《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葛亮、馬季文學對話錄》,《大家》2009年第3期。
{48} [德]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頁。
{49}{67} 張莉:《〈北鳶〉與想象文化中國的方法》,《文藝爭鳴》2017年第3期。
{50} 梁秉鈞:《嗜同嘗異——從食物看香港文化》,《香港文學》2004年3月號。
{54} 趙稀方:《小說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90頁。
{56} 黃傲云:《微弱的脈搏》,《香港文學》1985年第1期。
{59} 趙稀方:《香港:歷史、文學與認同》,《當代文壇》2021年第2期。
{60} 向懷林主編:《人文基礎》,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編寫說明第1頁。
{61} 此處根據行文需要對引文表述做了調整,特此說明。參見蔡益懷:《香港小說二十年:有精神的寫作,而不是避世的夢境》,《文藝報》,2017年6月30日。
{62} 關于“東方美學”一詞的理解,詳細可參見朱立元主編:《美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頁。
{63} 具體內容參見陳其南、周英雄主編:《文化中國:理念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10頁。
{64} 凌逾:《復興傳統的跨媒介創意》,《中國文藝評論》2018年第3期。
{65} 摘自筆者對葛亮的訪談《〈北鳶〉的歷史書寫與敘事營造——葛亮、徐詩穎文學訪談錄》,詳見葛亮:《由“飲食”而“歷史”——從〈北鳶〉談起》,《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66} 盧歡:《葛亮:尊重一個時代,讓它自己說話》,《長江文藝》2016年第12期。
{68} 凌逾:《開拓新古韻小說——論葛亮〈北鳶〉的復古與新變》,《南方文壇》2017年第1期。
(責任編輯:黃潔玲)
Abstract: A survey of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80s reveals an excessively internalized tendency and over-Westernized techniques that cause Hong Kong to face the self-imposed obstacle in its search for reshaping a humanitarian Hong Kong. To break through this restriction, one could engage in rethinking with the concept of a question, ‘How to seek roots and how to write’? On the level of roots, the focus needs to be on the thought of existence as to how to place oneself, to reexamine the values and limitations brought by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road on which the writers seek the roots and to re-excavate the cultural rootedness of oneself in the space of migratory culture. And on the level of writing, one ought to return from the over-Westernize form of writing to the insi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earch for artistic creation and breakthroughs, thus widening the scope of imagination for cultural Hong Kong. This concept has now becom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ut into the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 writing and the re-creation of tradition.
Keywords: The 1980s, Hong Kong fiction, Hong Kong writing, re-creation of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