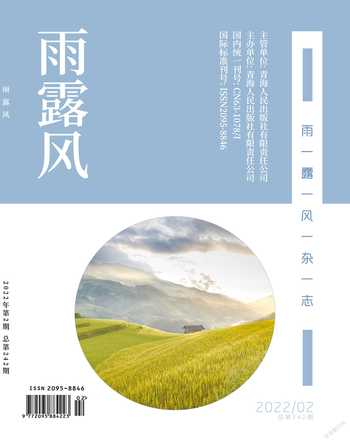沈從文小說《蕭蕭》意義懸置的原因探析
摘要:《蕭蕭》是沈從文小說中極有價值的作品,這篇小說注重呈現初始的人生境遇,作者極少介入個人的價值判斷,研究者們從不同的方向對作品進行了研究,對作品的表現內涵展示出千差萬別的思考。本文試圖從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敘述策略,分析造成小說意義懸置,主題不明的原因。
關鍵詞:意義懸置;人物形象 ;客觀化敘述
1929年沈從文創作的短篇小說《蕭蕭》,表現的是湘西落后的童養媳制度下人物命運的起伏,依舊保持了作者一如既往的牧歌式舒緩情調,將湘西世界的自然、人情、人性的美好,詩意地加以書寫。整個故事截取了主人公蕭蕭童養媳的生命歷程的瑣碎片段,自然地呈現出了湘西世界中的一個普通童養媳的生命和生活狀態。
讀完蕭蕭的閱讀感受,復雜而又奇妙,作者似乎為我們寫了一個故事,想要說些什么,但其實又什么都沒有表述清楚。從單一的文本中,我們很難對作者的態度做出準確的判斷。進行小說閱讀,概述小說內容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當我們試著進入小說的意味和氛圍,探尋小說的內涵時卻陷入了一種近乎無解的狀態。對作品的深度閱讀和習慣恰恰會妨礙對一個作品更深入的認識,悖論之所以會產生,原因在于對作品的深度模式的尋求最終獲得的不過是哲學層次上的抽象概念和圖式,而作品的具體而豐富的感性存在卻在這個過程中被肢解了。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一)蕭蕭的人物形象
小說呈現出一種沖淡平和的敘述特征。如果仔細閱讀,會發現發生在主人公蕭蕭身上的事,每一件都是生命際遇的重大轉折,稍有偏頗,蕭蕭都將萬劫不復。家庭是一個人成長的第一樂園,然而對十二歲之前蕭蕭的成長環境,作者進行了高度的概括:蕭蕭沒有母親,出嫁之前,寄養在伯父種田的莊上。[1]8這一語句簡要地交代了蕭蕭出嫁前的家庭環境,精煉到近乎沒有交代。蕭蕭以童養媳兼新嫁娘的身份出場,不同于大多數出嫁的姑娘,被抬在花轎上,笑著出場的,她既不害羞,又不害怕。蕭蕭亮相的方式與其出場身份存在著常識上的認知差距,這樣的差距使文本的張力漸次回蕩開來,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一個女人一生的兩個重要的生活狀態,在家,出嫁,就這樣在一個十二歲的少女身上結束,發展著。嫁到夫家的蕭蕭是幸運的,照顧小丈夫,承擔力所能及的農活,除此之外,就是自己找樂子。丈夫小自己九歲,蕭蕭只是小丈夫名義上的妻。鄉村生活中,生育是女子的重要人生課題,在蕭蕭這里,暫時還沒有到完成的時機。平靜無事的生活被成熟男性花狗和蕭蕭的自然人性打破——蕭蕭懷孕,孩子不是丈夫的,花狗恐懼潛逃,蕭蕭害怕,出逃失敗,面臨著重大的人生考驗,最終幾經周轉,蕭蕭的生活恢復平靜,生命安全危險解除,在夫家繼續生活著。在蕭蕭從十二歲到二十八歲,經歷了出嫁,懷胎,出軌,再嫁失敗,生子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蕭蕭這個人物的性格,形象,自我意識都給讀者一種模糊,不甚明朗的印象。
主人公作為小說的要素之一,應該是作者著力表現的對象,作者刻畫的主人公也應該有著屬于主人公獨特鮮明的特質。蕭蕭作為小說主人公,在閱讀之后,我們無法通過作者的表層文本對蕭蕭的外貌、性格、行為做斷言,慣常形容少女、少婦的形容詞,用來概括蕭蕭似乎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欠缺。加之作者刻畫人物用語的節制,對于判斷主人公對環境的能動反映,行為動機,意識情感都增加了難度。
(二)花狗的人物形象
花狗,這個引誘蕭蕭失身的關鍵人物,我們不能依靠常識來斷定這是一個壞人。真正進入小說的場域,我們也不能斷言花狗的善惡。文章對花狗的表述是這樣的:“花狗,面如其心,生長得不很正氣”;后文又說“花狗是‘起眼動眉毛,一打兩頭翹’會說會笑的一個人”以及“花狗是男子,凡是男子的美德惡德都不缺少,勞動力強,手腳又勤快,又會玩會說,所以一面使蕭蕭的丈夫非常歡喜同他玩,一面一有機會即纏在蕭蕭身邊,且總是想方設法把蕭蕭那點惶恐減去。”[1]16-19文本對花狗其人品的表述,似乎也不全面,但是從文本中我們至少可以獲取這樣幾個信息,花狗是身心發育成熟的男性,能逗蕭蕭開心,丟下蕭蕭一個人跑了,可以說沒有擔當。在他身上,人的缺點和優點并存。花狗引誘蕭蕭在先,不辭而行在后,花狗在蕭蕭身上得到了性欲的滿足,也險些為蕭蕭帶來禍端。花狗與蕭蕭的情事的始末,作者給了詳細的交代,其中對于花狗的引誘方式做了詳細的描寫,以及蕭蕭面對花狗引誘時內心微妙而又復雜的情緒變化。當花狗注意到心思單純的蕭蕭長到要聽歌的年紀時便給她唱“十歲娘子一歲夫”,蕭蕭隱約體會到這是罵人的歌便生氣地制止,她雖然隱約懂一點兒歌但對花狗的心思還不清楚。隨著花狗套路的加深,蕭蕭有點明白了花狗對她的心思。在花狗的多次誘惑下,最終蕭蕭讓花狗得逞。在讓花狗得逞之后,她才仿佛覺得做了一點不大好的糊涂事。這一段內心活動的變化推進著她與花狗的情事,是她從少女向少婦心思的轉變,這一描寫還原了蕭蕭自然人性中的一種極自然、合理、真切的心態。童養媳的身份,丈夫小蕭蕭九歲的現實,蕭蕭的自然人性只有在花狗的身上有實現的可能。花狗為引誘蕭蕭所做的努力,替蕭蕭的情欲提供了一個釋放的可能和途徑。在此意義上,有懵懂情欲的蕭蕭和成熟男子花狗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都有著對等的自然人性。因此,花狗的行為雖然與現實禮法相悖,也不能稱作惡。至于其行為讓蕭蕭陷入危機,也體現了作者對人生際遇和無常生命的思索。
要寫出一個人與物自在存在,拒絕任何主觀介入和闡釋的作品,并不容易,在沈從文的筆下,人物的情感和命運遵從一種合乎情理和事理的方向,在自在流逝的時間中,花狗與蕭蕭都有各自的悲喜,人性的需求,也有必須要面對的來自生存環境的各種桎梏,花狗逃走了,蕭蕭沒有來得及走,就被發現了。這種生命的不確定性必然引發作品主題的多義,對人物的客觀描寫也讓作品意義存在多重闡釋的空間。
二、敘述策略
(一)人物生活境遇的客觀化敘述
《蕭蕭》寫痛苦的歷程而無苦澀味道,在這篇小說中,外在現實淡化了,人物和情節都被奇特地中和了。現實世界尖銳的規則,利益,沖突都被回避了,讓人只憑借自然本性去行動,當平靜的現實被涌現的事件打破,悲劇可能不期而至,在人與環境的周折流轉后,變成一種順其自然,放任自流的生命哲學觀。
在我讀到蕭蕭這個小女子沒有母親,從小寄養在伯父種田的莊子上時,我曾疑惑作者為何將蕭蕭的身世寫得如此的省簡,蕭蕭在花轎上被平平穩穩地抬著以及蕭蕭身世后的那句,出嫁只是從這家轉到那家——這一切看似自在自然,我的疑惑是,隨遇而安的蕭蕭,真的如看上去的那般自在嗎?文中對蕭蕭生命意識的呈現表述為她什么事也不知道、懵懵懂懂、糊糊涂涂,作者似乎意在呈現蕭蕭沒有明晰的生命意識,所以她成長歷程中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她自主選擇的結果。可這是否是作者故意為之的呢?文章交代了蕭蕭沒有媽媽,寄養在伯父種田的莊子,在文章結局處交代了伯父是蕭蕭唯一的家長,且忠厚老實。不同于對蕭蕭性格塑造的吝嗇,作者在這里強調了伯父的忠厚老實和不忍。在處置蕭蕭這一事件上忠厚老實的伯父,不忍心蕭蕭沉潭,決定把蕭蕭嫁人,在做好這個決策之后,叔侄倆的會面作者有一段描述:“伯父把這事告給了蕭蕭,就要走路。蕭蕭拉著伯父衣角不放,只是幽幽地哭,伯父搖了一會頭,一句話不說,仍然走了。”[1]24伯父是夫家決定的唯一對蕭蕭的去向有決定權的人,他不是心狠手辣,而是忠厚老實,忠厚老實的他也不得不依照慣例,做出符合他本性的決定,除此之外,他也別無他法。十二歲的蕭蕭成為童養媳之前,伯父是外界看來唯一合法的監護人,所以,忠厚老實的伯父使得蕭蕭童養媳的命運帶有某種必然性。試想一下蕭蕭成為童養媳的過程:有人上門提親,依照伯父的自然本性,蕭蕭成為童養媳,蕭蕭被動。伯父只是個種田的農民,他的生活狀態也是被動的,他不能讓蕭蕭有更好的選擇,也不能在侄女犯錯后帶走她。可以說,蕭蕭和伯父以及文章中的所有人都存在被動性,他們的命運總是被別人或者一系列類似的偶然因素所把握。所有的這些偶然,都存在合理性,所有的偶然片段都存在于一個必然的日常的生活情景里。花狗與蕭蕭的相遇,讓花狗有引誘蕭蕭的可能,祖父的玩笑話對蕭蕭無意識的啟蒙,讓蕭蕭在走投無路之計,有了出逃的想法,帶丈夫上山打豬草,丈夫唱歌引來花狗。小說中,作者不著痕跡地在各種人事間創造了種種因果連屬關系。在理解各種事物之間的連屬關系后,我們追溯悲劇的源頭,卻無法分辨具有生活其中的人到底在哪里出了錯。每個人,只是安分守己地過著自己生活,也天然存在著苦難、不幸,無論如何掙扎,命運的手已經讓他們陷入被動。
事實上,日常生活是最無法掌控的東西,作者只不過呈現出了人物的自然際遇。可以說,對人物際遇高度客觀化的敘述,即是一種寫作技巧,也是一種生命姿態。人與人之間成長、階級、立場、性格的差異,交織在共同的事件中,其中的周折過程不可預知。對人物際遇的高度概括,沖淡平和的敘述,使故事呈現出不確定性。
(二)獨特的用詞與句式表達
著名學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于沈從文的《蕭蕭》有這樣的表述,他假借讀者的名義表達他對這篇作者的感受:“讀者看完這小說后,精神為之一爽,覺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應該這么自然似的。”[2]142事實上,在進入小說時,讀者個人的知識結構,會影響我們對作品的把握。只有一定程度摒棄我們已有的認知,真正進入小說的場域,通過文本去理解作者為我們建構的世界。在作者構建的文本中,一切人物的發展都顯得合情,合理,合乎人情。可這樣的自然而然仍然是通過作者努力營造出來的一種自然,讓人物在他文字營造的那個生活情境中自然而然,可他所努力營造的那個情境在文字的表達中留下了痕跡。
在蕭蕭這篇文章中,凡作者在敘述對象,描述生活片段時,總要為人物營造一個常態化、慣例化的背景,進而讓人物的表現看起來自然。文中存在很多表示常態、慣例的用詞和表述:“鄉下人吹嗩吶接媳婦,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會有的事情”“那丈夫本來晚上在自己母親身邊睡,有時吃多了,或因另外情形,起來放水拉稀是常有的事”“鄉下人的日子也如世上一般日子,時時不同。”[1]8-14“成天會有”“照例”“規矩如此”“習慣”“常有的事”,這些表示慣例、常態的詞語在小說中頻繁出現,對于人物出場的環境,事件發生的背景,人物行動的邏輯提供了合理而自然的鋪墊。這樣一般性的鋪墊之后,繼而引出人物,事件,描述個別。最大程度地對可能性進行概括之后,轉向對這一個,個別的描述。在文章中,慣例常態說明完之后,偶爾會用“也有”“有的”“或者”對事件的可能性進行補充,作者試圖概括整體圖景,囊括所有可能。對接下來發生的“這一個”的描寫有時與前面概括相似,有時卻偏離了概括。在文中蕭蕭的出場是湮沒在眾多做新娘子的小女人中,她的出嫁表現也被作者囊括在出嫁新娘子會有的表現之中。這種表述方式,造成個體特征不明顯,句子主語的承擔者變得不確定。使得讀者的注意力有所分散,不明確作者主要想表述的對象和重點,而其努力營造的自然,在讀者眼中,就稍顯刻意。當然這些有常態意味的表達,在不同的地方承擔不同的敘事功能和結構功能。但無可否認,這些表現常態的詞語,短語的使用,確實使小說的故事呈現出自然的特點。但從某種程度來說,將個別置于整體的背景之下的描寫,設置了閱讀障礙,一定程度影響我們對文本意義的把握。
三、結語
對主人公蕭蕭人物形象刻畫的不明晰性,對花狗這一人物存在的客觀闡釋,對文本中人物境遇的客觀化敘述以及作者獨特的用詞與句式表達,讓不同的讀者能從不同的角度對作品進行意義的闡發,文本的意義因此獲得了無限闡釋的可能,從另一個角度也造成了小說意義的懸置。好的文學文本永遠存在強大的沖動,就是對人的存在,人的生活和形象做出規約,同時以開放的心態,保存人類經驗的豐富性,探索人的行動和表述的無窮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品的意義懸置也正是作品生命力的來源。
作者簡介:鐘雯(1999—),女,漢族,云南昭通人,云南師范大學19級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參考文獻:
〔1〕沈從文.沈從文別集[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