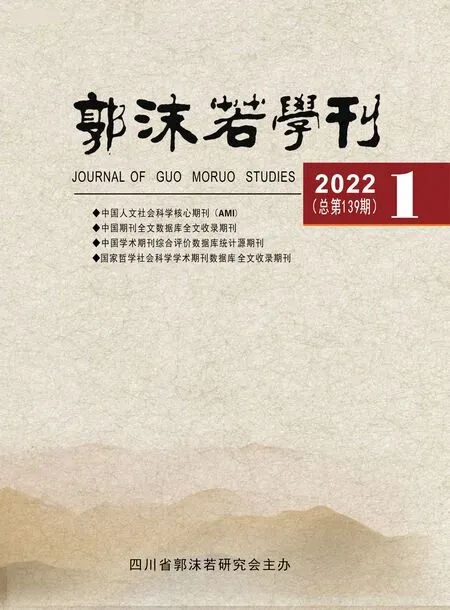重慶《時事新報》郭沫若研究資料綜述*
馮雨蕾 簡 憶
(樂山師范學院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一、有關郭沫若抗戰演講的報道
郭沫若擔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期間,積極發表演講宣傳抗戰,該報共發表相關報道7 篇,其中詳細報道4 篇。1938 年9 月5 日下午,郭沫若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介紹了栗本勇之助、中野正剛發表在《日本評論》8 月號的《大陸經營與日本產業》《大陸之長期經營》中的觀點,并結合天津4 日發的路透電內容告訴與會記者:“日本的野心是無止境的,她侵占了我們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同時她對各外國在華的權益也必定要排除凈盡,才告滿意。對付侵略者只有共同制裁,要在日本強盜的口中保全各國各自在遠東的利益,無論如何這是夢想。在國際聯盟行將開會的今天,希望諸位把這一點小小的意見傳給諸位的政府與人民,以供他們的參考。”該報9 月7 日以《敵國獨占遠東利益 竟明目張膽公開的發表言論——郭沫若招待外國記者之介紹》為題轉述了郭沫若的此次演講。1939 年1月8 日下午,郭沫若應《新民報》職工讀書會之請,在市商會作公開演講,題為《從近衛內閣總辭職后談到日本對內對外諸問題》,聽眾千余人。郭沫若在演講中告訴人們:“日之內閣改組,正表示其國內財閥與法西斯派對立之尖銳化。因法西斯之橫暴,在內促進其國內人民之厭戰心理,對外促進民主國家之密切聯系,國際間之和平更加容易實現,日帝國主義將成為短命的帝國主義。”該報1 月9日以《應〈新民報〉讀書會之請 郭沫若演講敵今后之困難》為題對演講情況進行了報道。該報1939年1 月12 日發表了澄之寫作的《郭沫若談日本崩潰的前奏》,該文主要介紹了作者1 月11 日在聯歡社聽郭沫若演講的情況。在郭沫若看來,“日本平沼內閣的上臺,是敵國崩潰的前奏”。1939 年1月28 日,郭沫若在中央電臺播講《世界新秩序的建設》時,從四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次日該報以《郭沫若講和平樹立在正義上》為題進行了報道。另外,該報1939 年9 月17 日第3 版、1940 年1 月14 日第3 版、1940 年2 月5 日第3 版分別以《郭沫若明晚播講》《郭沫若今晚廣播演講》《郭沫若播講全體勞軍與軍民合作》報道了郭沫若演講的消息。
二、有關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的文章
宗白華1941 年11 月10 日率先在該報第4版《學燈》發表《歡欣的回憶和祝賀》。該文回憶了自己當年在《學燈》發表郭沫若詩歌的原因:“他的詩——當年在《學燈》上發表的許多詩——篇篇都是創造一個有力的新形式以表現出這有力的新時代,新的生活意識。編者當年也秉著這意識,每接到他的詩,視同珍寶一樣地立刻刊布于《學燈》,而獲著當時一般青年的共鳴。”次日,時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發表《壽郭沫若先生》,稱贊郭沫若“是一面燦爛的大旗”。
郭沫若生日過后,該報還發表了三篇祝賀、紀念文章。羅蓀在11 月18 日發表的《偉大的“蘆笛”》稱郭沫若的詩歌為“偉大的‘蘆笛’”:“給人以鼓舞,喚人以覺醒,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族的奴隸的命運,被喚醒了,這只‘蘆笛’,正是民族的號角。”根據前面的說明文字可以知道,任鈞11 月18 日發表的《歡迎曲》為作者八一三事變前為歡迎郭沫若歸國而作的一首詩歌。作者認為:“這首詩,多少表現出了大家當日對于郭先生歸來的歡迎和崇敬之忱,而這種情感,時至今日,不但沒有變更,而且,與時俱進,越發來得強烈和深沉”。參加郭沫若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后,老舍寫作了《參加郭沫若先生創作廿五年紀念會感言》,并將其發表在11 月21 日出版的該報上。
三、有關郭沫若歷史劇的評論和報道
《棠棣之花》公演結束后,西夷于1942 年1 月21 日在該報發表了《〈棠棣之花〉觀后》。該文在高度評價整個劇本的同時,認為第五幕陳尸舞臺破壞了整臺戲的詩意,并且建議“充滿現代化的名詞,應該盡量避免”。在文章結尾前,作者還對演員們的演出情況進行了評價。據趙銘彝1942 年5 月21 日發表在該報的《我看川劇〈棠棣之花〉》可以知道,川劇版《棠棣之花》并非在郭沫若同名劇作基礎上改編而成,川劇版作者寫作該劇的目的和態度是:“他教訓著人們要‘為知己者死’,要報答人家的‘恩惠’,他(劇作者)顯然是站在士紳階級的立場向人們說話,維護著他們自己所用以存在的道德。”
在五部公演的劇作中,有關《屈原》的評價和報道最多,共有七篇。在《屈原》公演當天:1942 年4 月3 日,該報第4 版《青光》出版了《〈屈原〉公演特刊》,共發表三篇文章。南后扮演者白楊在文章中分析了南后的性格和形成原因,并認為“南后在全劇中的地位,造成了偉大的屈原底悲劇”。S·Y(劉盛亞)認為郭沫若是最適宜寫《屈原》的劇作者,其理由為:“他自己是文學家,也是有良心的從政者,他在異邦流亡過十年”。潘孑農在《〈屈原〉讀后》中,通過比較的方式認為“《屈原》這一劇本的演出價值,已較《棠棣之花》更見圓熟”。在接下來的時間里,重慶《時事新報》還發表了四篇有關《屈原》的評價和報道。黎寧遠從得失兩方面評價了《屈原》的劇本、配樂和演員,認為“布景設計沒有達到統一是顯著的缺點”。陳銘樞觀看《屈原》后作詩一首,郭沫若看見后,作《次賦韻答真如》,它們一起在4 月29 日第4 版《青光》發表。趙銘彝在《我看〈屈原〉》中發表了如何評價《屈原》的問題。聞郁在《北碚演劇通訊——第四函》介紹了郭沫若在北碚重師禮堂講演《屈原悲劇之意義》和《屈原》在北碚演出的情況。
民國時期,郭沫若的《孔雀膽》先后由中華劇藝社、西南劇藝社搬上重慶的舞臺。1943 年1、2 月第一次演出時,盡管廣告上不斷出現“客滿”字樣,該報卻只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1948 年4、5 月第二次演出時卻發表了四篇文章。1943 年2 月1、4日,顏翰彤在該報發表了《關于〈孔雀膽〉的劇本、導演與演員》。就劇本而言,該文認為《孔雀膽》沒有《屈原》寫得好;對應云衛導演的評價為:“他從大處著手,抓住了幾個緊要的關鍵和幾個緊張的場面,使它們有充分集中觀眾注意力的可能”;對演員的總體評價為:“若干過去在別的戲劇有著頗不壞的成績的演員,這次未能有更進一步的造詣,甚或留下了本來可以避免的弱點,主要的,我想還是由于時間的匆促”。墨雨1948 年4 月25 日在該報發表了《從〈孔雀膽〉看山城劇運——并向話劇藝術觀采進一言》,對導演、演員、服裝設計、燈光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48 年5 月9 日第4 版《六藝》共發表有關《孔雀膽》的文章三篇。在《與孟齊先生論〈孔雀膽〉》中,春鳴“站在愛護文藝教育的立場上”,不認可孟齊在《漫話〈孔雀膽〉》對該劇演出的評價。在《對〈孔雀膽〉劇本的一點意見》中,莎夫對《孔雀膽》的結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孔》劇的結構:以現實主義為基調,摻雜著若干份量的浪漫的彩色。所以增加了不少的艷麗,卻也失掉了不少的嚴整性。”在《談〈孔雀膽〉的演員們——敬獻給西南劇藝社諸兄》中,莎夫主要對導演,阿蓋公主、段功、楊淵海的扮演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虎符》演出時,該報僅在1943 年2 月3 日以《〈虎符〉明晚公演》為題發表了一則簡短的預告。《南冠草》演出時,王平陵1943 年11 月30 日在該報發表了《看〈金風剪玉衣〉》,高度評價了該劇的演出情況:“《金風剪玉衣》已經上演了,我第一次看到史劇演出的成功”,并對劇作與題材之間的關系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總之,作品的能否把握現實,與故事的選擇,沒有什么關系,全在劇作者是否已經認識到了現實,而有不得不寫的熱忱,是否具有剪裁故事的技術,能做到反映現實的效果?能夠如此,我以為是選用‘神話’來作題材,都不必詬病。”
四、有關郭沫若及其作品、言行的評價
重慶《時事新報》共發表評論郭沫若及其作品的文章五篇。由于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缺失了1938年6 月3 日的重慶《時事新報》,無從知道仲逵在《和郭沫若先生談幾個小問題》中還談了什么問題,單就發表在該報6 月4、6 日的該文而言,作者認為郭沫若“全廢茶館”的建議是“書生之見”。在該報1944 年1 月1 日發表的《我們所敬佩的作家——郭沫若》中,丘陵簡單介紹了郭沫若的生平、著述情況,并將自己佩服郭沫若的地方概況為以下五點:“一先生是中國的一個民族革命戰士”、“二先生是中國的一個天才詩人和文學家”、“三先生是中國的一個世界文學名著介紹者”、“四先生是中國的一個政治學家”、“五是中國的一個有偉大人格修養的文化戰士和革命戰士”。郭沫若的《鳳凰(沫若詩前集)》于1944 年6 月由重慶明天出版社出版后,楊塊在該報1944 年10 月3 日發表了《郭沫若的〈鳳凰〉》。作者認為“《鳳凰涅槃》足以代表作者當時做人對事的態度”、“在今天來讀這些作品似乎只好從技巧上著眼,然而卻又過于低劣。我們可以說:這部集子里能夠稱為‘詩’的實在太少了”。陳子展在該報1947 年5 月22 日發表《郭沫若與魯實先》,肯定郭沫若對魯實先研究的稱贊,批評一些人對魯實先“罵他反動,誣蔑他男女間事,而使用鬼蜮伎倆,散發匿名揭帖”,并對該種做法進行了批評。該報1948 年5 月24、31 日第4 版《時事文摘》第13、14 期轉載的《郭沫若先生的“恨”》原載昆明《中央日報》1948 年5 月8 日第6版、5 月9 日第5 版,該文還發表在臺南《中華日報》1948 年5 月9 日第5 版《論叢》、永安《中央日報》1948 年7 月12 日第3 版。該文是針對郭沫若發表在《現代華僑》上的《打破美帝扶日奴華計劃》寫作的,作者稱郭沫若為“第三國際的御用文人,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家”,認為美國扶持日本是“被世界共產黨的進攻迫出來的”,并將郭沫若的“恨”歸納為:“誰要拉住中國,使在民主自由世界而不進入鐵幕,郭先生就得恨誰,誰在設法阻止鐵幕擴大,郭先生就得恨誰……”
五、有關郭沫若的其他報道
重慶《時事新報》共發表有關郭沫若的其他報道十二篇。郭沫若、衛聚賢等人1940 年4 月7 日郊游過程中在重慶江北培善橋發現漢墓,略做準備后,于4 月14 日正式發掘,4 月20 日暫停發掘。4 月8、14、15、16、18、20、21 日出版的該報分別以《江北發現漢墓》《發掘漢墓 地點在江北培善橋》《發掘漢墓 又有新發現》《江北漢墓又發現九座》《第四座漢墓附近昨又掘出一墓》《漢墓發掘第六日發現鐵劍陶俑 古物攝影寄蘇聯發表》《漢墓發掘暫作結束 今日公開展覽》為題對整個過程進行了報道。1945 年6 月25 日至8 月15 日,郭沫若應邀訪問蘇聯。6 月10、28 日出版的該報分別以《郭沫若赴蘇聯》《郭沫若飛往列寧格勒》為題報道了6 月9 日由重慶啟程和6 月27 日從莫斯科飛列寧格勒的情況。另外,該報1940 年4 月1 日第3 版、1944 年11 月8 日第3 版、《時事新報》1946 年2月11 日第3 版分別以《中國萬歲劇團定期在國泰首次獻演》《蘇大使館茶會招待中外各界,郭沫若等演說》《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較場口一場紛擾——郭沫若李公樸等被毆傷 劉野樵負傷后自訴法院》為題報道了有關郭沫若的相關情況。
綜上所述,《時事新報》是民國時期一份非常重要的報紙,曾在上海、重慶出版。重慶《時事新報》發表的有關郭沫若的文章,是我們了解郭沫若抗戰以來的部分言行、作品及他人評價的重要資料。由于現在所有的數據庫都無法通過檢索方式查找《時事新報》上的文章,只能在抗戰文獻數據平臺上通過逐頁瀏覽的方式查找,因此,已經查找到的這些文章值得我們重視。
1、仲逵:《和郭沫若先生談幾個小問題》,1938 年6月4、6 日第4 版《青光》
2、《敵國獨占遠東利益 竟明目張膽公開的發表言論——郭沫若招待外國記者之介紹》,1938 年9 月7日第3 版
3、《郭沫若演講敵今后之困難》,1939 年1 月9 日第3 版
4、《郭沫若談日本崩潰的前奏》,1939 年1 月12 日第2 版
5、《郭沫若講和平樹立在正義上》,1939 年1 月29日第3 版
6、《郭沫若明晚播講》,1939 年9 月17 日第3 版
7、《郭沫若今晚廣播演講》,1940 年1 月14 日第3 版
8、《郭沫若播講全體勞軍與軍民合作》,1940 年2月5 日第3 版
9、《中國萬歲劇團定期在國泰首次獻演》,1940 年4 月1 日第3 版
10、《江北發現漢墓》,1940 年4 月8 日第3 版
11、《發掘漢墓 地點在江北培善橋》,1940 年4 月14 日第3 版
12、《發掘漢墓又有新發現》,1940年4月15日第3版
13、《江北漢墓又發現九座》,1940 年4 月16 日第2 版
14、《第四座漢墓附近昨又掘出一墓》,1940 年4月18 日第3 版
15、《漢墓發掘第六日發現鐵劍陶俑 古物攝影寄蘇聯發表》,1940 年4 月20 日第3 版
16、《漢墓發掘暫作結束 今日公開展覽》,1940 年4 月21 日第3 版
17、宗白華:《歡欣的回憶和祝賀:賀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1941 年11 月10 日第4 版《學燈》第151 期
18、馮玉祥:《壽郭沫若先生》,1941 年11 月11 日第4 版《青光》
19、崔萬秋:《八·一三前夕郭沫若先生歸國經過》,1941 年11 月16 日第5 版《青光》
20、柯靈:《遙祝——為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廿五年紀念作》,1941 年11 月16 日第5 版《青光》
21、許世英:《沫若先生》,1941 年11 月16 日第5版《青光》“壽郭沫若先生”欄
22、陳子展:《贈郭鼎堂先生》,1941 年11 月16 日第5 版《青光》“壽郭沫若先生”欄
23、黃芝岡:《步子展贈郭鼎堂先生原韻》,1941 年11 月16 日第5 版《青光》“壽郭沫若先生”欄
24、沈鈞儒:《沫若先生二十五年創作紀念》,1941年11 月16 日第5 版《青光》
25、《郭沫若五十誕辰 中蘇文協昨晚盛會 二千余人參加祝賀》,1941 年11 月17 日第3 版
26、羅蓀:《偉大的“蘆笛”》,1941 年11 月18 日第4 版《青光》
27、任鈞:《歡迎曲》,1941 年11 月18 日第4 版《青光》
28、老舍:《參加郭沫若先生創作廿五年紀念會感言》,1941 年11 月21 日第4 版《青光》
29、徐封:《香港通訊》,1941 年11 月28 日第4 版《青光》
30、西夷:《〈棠棣之花〉觀后》,1942 年1 月21 日第4 版《青光》
31、白楊:《理解“南后”的片斷》,1942 年4 月3 日第4 版《青光·〈屈原〉公演特刊》
32、S·Y:《最適宜寫〈屈原〉底劇作者》,1942 年4月3 日第4 版《青光·〈屈原〉公演特刊》
33、潘孑農:《〈屈原〉讀后》,1942 年4 月3 日第4版《青光·〈屈原〉公演特刊》
34、陳銘樞:《觀沫若所編〈屈原〉劇感賦》,1942 年4 月29 日第4 版《青光》
35、黎寧遠:《評〈屈原〉》,1942 年5 月6、9 日第4版《青光》
36、趙銘彝:《我看川劇〈棠棣之花〉》,1942 年5 月21 日第4 版《青光》
37、趙銘彝:《我看〈屈原〉》,1942 年5 月30 日第4版《青光》
38、聞郁:《北碚演劇通訊——第四函》,1942 年7月18 日第4 版《青光》
39、顏翰彤:《關于〈孔雀膽〉的劇本、導演與演員》,1943 年2 月1 日第5 版、2 月4 日第4 版《青光》
40、《〈虎符〉明晚公演》,1943 年2 月3 日第3 版
41、平陵:《看〈金風剪玉衣〉》,1943 年11 月30 日第6 版《青光》
42、丘陵:《我們所敬佩的作家——郭沫若》,1944年1 月1 日第20 版《青光》
43、楊塊:《郭沫若的〈鳳凰〉》,1944年10月3日第4版
44、《蘇大使館茶會招待中外各界,郭沫若等演說》,《時事新報》1944 年11 月8 日第3 版
45、《郭沫若赴蘇聯》,1945 年6 月10 日第3 版
46、《郭沫若飛往列寧格勒》,1945 年6 月28 日第3 版
47、《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較場口一場紛擾——郭沫若李公樸等被毆傷 劉野樵負傷后自訴法院》,《時事新報》1946 年2 月11 日第3 版
48、陳子展:《郭沫若與魯實先》,1947 年5 月22 日第4 版《青光》
49、墨雨:《從〈孔雀膽〉看山城劇運——并向話劇藝術觀采進一言》,1948 年4 月25 日第4 版《六藝》
50、春鳴:《與孟齊先生論〈孔雀膽〉》,1948 年5 月9 日第4 版《六藝》
51、莎夫:《談〈孔雀膽〉的演員們——敬獻給西南劇藝社諸兄》,1948 年5 月9 日第4 版《六藝》
52、莎夫:《對〈孔雀膽〉劇本的一點意見》,1948 年5 月9 日第4 版《六藝》
53、蔣君章:《郭沫若先生的“恨”》,1948 年5 月24、31 日第4 版《時事文摘》第13、1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