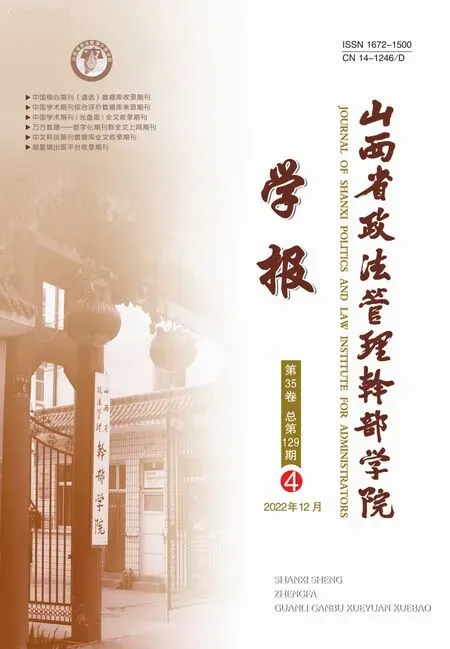冷凍胚胎的民法和刑法規制
楊坤鑫
(中國海洋大學 法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2021年6月,我國開始施行“三胎”政策。但鑒于“高房價”“高育兒成本”等現實問題使許多夫妻沒有養育多個孩子的條件,而具備相應經濟條件的夫妻中又有相當部分已超過最佳生育年齡,或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自然受孕。因此,這些特殊家庭就需要采用體外授精等輔助生殖技術來實現其生育目的。從目前研究來看,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嬰兒與自然受孕的嬰兒在身體與智力發育方面并無差異,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試管寶寶”出生。而在嬰兒出生之前,將配對成功的胚胎進行冷凍是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受精卵從細胞分裂成具備移植條件的胚胎,最后移植,這個過程中會有諸多不確定因素發生,如夫妻雙方或一方死亡、女方子宮突然喪失孕育能力乃至夫妻雙方離婚、失聯、遺棄胚胎等情況,此時,應當如何合法地處理冷凍胚胎?諸如此類問題在今后將愈發突出。因此,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以及其歸屬等法律問題成為法學界亟須解決的課題。
一、冷凍胚胎面臨的法律困境
衛生部于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輔助生育技術規范》等規范性文件規定了“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禁止實施胚胎贈送”“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等內容,但其規定所適用的范圍較為單一,并且未提及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及處置規則等關鍵問題。冷凍胚胎的法律地位、適用規則等方面,理論界尚未達成共識,仍存在巨大爭議。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相關案例也依然是法官對個案做出的解釋認定,衛生部對于特殊事件作出的回應批復,由此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法官無法可依,也不能拒絕裁判的困境。[1]2020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舉辦了第25期“案例大講壇”,專門就體外受精技術有關的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討。由此可見,由體外受精技術引發的倫理和法學問題已經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也可以看出這一技術也產生了極高的社會關注度。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已于2021年4月15日起正式施行,然而,僅有八十八條法律條文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只針對生命科學及生物技術發展過程中一些宏觀原則和制度進行了相關法律規范,而對于如體外受精等生物安全技術的具體法律問題并未做出明確規定,這也就導致了當前該領域司法實踐無法可依的困境。
法律需求決定法律供給,當前冷凍胚胎的法律困境決定了應當完善相關的法律供給。從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及協調性來看,生物安全法的有效實施不僅需要專門立法的明確規范及技術支撐,更需要與其他部門法的銜接及協調。[2]
二、冷凍胚胎的法律規制——民法角度
(一)明確界定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
對于冷凍胚胎相關問題的探討,民法界較為熱烈,尤其是針對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方面。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關于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界定主要有三種觀點,分別為權利主體、一般財產和特殊物體。我國民法采用的是嚴格的“人—物”二分體系,所以在界定冷凍胚胎時要么是人,要么是物,即對應上述的權利主體和一般財產。所謂的特殊物體有學者認為是介于權利主體和一般財產之間的一種特殊物。這里的特殊物體雖獨立于一般財產,但是與一般財產一樣都屬于民法中的“物”,即前者是倫理物,后者是一般物,前者擁有最高物格,對于它的保護和重視往往會高于其他的一般物。如楊立新教授認為:倫理物包含人體變異物,即脫離人體的器官、組織、尸體以及醫療廢物等,而胚胎作為脫離人體的組織,其法律屬性應為倫理物。此外,也有學者持“中介說”的觀點,如徐國棟教授在他的論文《體外受精胚胎的法律地位研究》中提出要“打破人—物二分體系,構建人—中介—物三級體系”的論斷。[3]
對于這三種學說,首先主體說是當然被否定的,因為主體說主張將冷凍胚胎作為權利主體,即人,而我國《民法典》第十三條規定: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可見,我國《民法典》對于權利主體的認定是以自然人的出生為起點的,而冷凍胚胎與這一標準相悖,故主體說首先被排除。針對“客體說”或是“中介說”的觀點,則認為將冷凍胚胎作為一種倫理物更為合理,原因如下:首先,對于“中介說”要打破我國傳統的民法“人—物”二分格局的觀點,筆者并不贊同,因為我國的民法體系整體都是以“人—物”二分格局為基礎的,要打破就意味著需要根本變革我國已有的民法體系,這并不是件易事,也并無必要;其次,冷凍胚胎作為一種帶有人格利益和人身屬性的物理形態上的有體物,冷凍胚胎到底應傾向于人多一些,還是物更多一些,這個問題本身就難以自洽,一旦定位不準,就會將立法引向虛無,并陷入形而上學的邏輯困境。[4]如果將其作為中介物,必然應該與左右兩種物有十分清晰的界限,而如何劃分這一界限是個非常棘手的難題,且就算解決了這一難題也會發現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其相協調。故筆者贊同將冷凍胚胎作為特殊物體的觀點,而對于楊立新教授和冷傳莉教授將冷凍胚胎認定為脫離人體組織的倫理物這一觀點還存在一些疑問:楊立新教授所認為的“脫離人體的器官、組織、尸體以及醫療廢物”的論述,筆者認為與冷凍胚胎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冷凍胚胎是具有生物學上的“活性”的,其具備發展成為人的潛力,而器官、組織、尸體以及醫療廢物可以說是不具備“活性”的,其與冷凍胚胎也許不能夠作為同一類物體。
(二)合理規范冷凍胚胎的處置歸屬
除明確法律屬性外,另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便是有關冷凍胚胎的歸屬和處置問題,目前存在較大爭議,主要包含:因夫妻雙方離婚引發的冷凍胚胎處置歸屬問題;因夫妻雙方有一方過世,而另一方是否能要求繼續實施冷凍胚胎技術的問題;因夫妻雙方皆過世而引發的夫妻雙方的繼承人之間、繼承人與醫療機構之間的處置歸屬問題。
首先,對于離婚引發冷凍胚胎的歸屬問題,以及所有者是否具有留存的冷凍胚胎進行生育的權利。針對歸屬問題,如果判決冷凍胚胎歸男方所有,就現有的科學技術來說,男方是無法單獨進行生育的,那么就意味著男方需要另找女性完成生育,這就成了“代孕”行為,而代孕行為在我國是非法的,故如果按照這種思路,那么冷凍胚胎的歸屬問題就已經迎刃而解了,即只能判給女方所有,但是這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呢?冷凍胚胎是由男方的精子和女方的卵子共同形成的,這兩者缺一不可,這就意味著男女雙方在冷凍胚胎的形成過程中是權利平等的兩方,而在判決中卻出現了僅能將冷凍胚胎判給女方的相悖結論,這顯然不夠合理。那么,無論判給誰,獲得冷凍胚胎的一方又是否擁有繼續使用留存胚胎進行生育的權利呢?在郭巍峰先生的研究生學位論文《夫妻離婚時冷凍胚胎處置的法律問題研究》一文中給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即在大多數情況下,法院會優先保護拒絕生育方的利益,因為生育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這就包含了權利人可以拒絕生育,即除非有特別規定,法律不能強制人做父母;對于保護要求生育方的利益比保護拒絕生育方的利益更容易,要求生育方完全可以再次結婚或再次進行新的胚胎移植來實現對其利益的保護,而對于拒絕方除了這一點好像別無他法;在夫妻未達成合意時貿然將冷凍胚胎孕育為子女,這顯然不符合該子女的利益。[5]
其次,夫妻雙方均死亡后其雙方繼承人之間及雙方繼承人與醫療機構之間應由哪一方獲得該冷凍胚胎的處置權呢?對此有一例典型案例,2014年發生在無錫市的“宜興冷凍胚胎案”,是全國首例冷凍胚胎繼承權屬糾紛,這個案例最突出的問題,就在于宜興市法院和無錫市中院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該案例的基本案情是:江蘇宜興的一對雙獨年輕夫婦不慎車禍遇難,而兩人生前在南京鼓樓醫院曾接受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并遺留下四枚冷凍胚胎,因此這對年輕夫婦去世后其各自的父母針對這四枚冷凍胚胎的處置與醫院產生了糾紛,男方父母作為原告將女方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將相關的繼承權判給自己,并且將拒絕交出冷凍胚胎的醫院也作為第三人追加到訴訟中。宜興市法院的一審判決認為冷凍胚胎作為一種具有未來發展成為人的潛能性的特殊物,不能被繼承,于是駁回了原告請求;而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則做出了與一審法院完全不同的判決,它繞開了冷凍胚胎能否被繼承的問題,而是從該胚胎對于雙方父母具有寄托哀思、緩解失獨之痛的人格利益入手,認為冷凍胚胎與受孕夫妻具有生命倫理上的密切聯系,理應不能歸醫療機構所有,故二審判決雙方父母享有對冷凍胚胎的監管權和處置權。
除此之外,還有夫妻雙方與醫療機構的糾紛,如徐靜、馬仲斌訴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院返還原物糾紛,張靜、郭強與南京鼓樓醫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筆者在對相關案例進行梳理后發現,各個法院在審判時和在最終判決時所遵循的原則和方法大多是相似的,即判決冷凍胚胎的處置權應歸屬于原受孕夫婦或者夫婦死亡后的繼承人,理由一是該冷凍胚胎含有受孕夫婦遺傳信息,其處置權當然歸屬于受孕夫婦;二是認為受孕夫婦與醫療機構簽署的對冷凍胚胎儲存的合同屬于保管合同,受孕夫婦作為寄存人當然有權處置自己的寄存物。
三、冷凍胚胎的法律規制——刑法角度
對于冷凍胚胎領域是否需要刑法的介入一直是學者們爭議的問題。刑法作為社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否有必要將這一剛剛興起的科學技術置于刑法的屏障下確實存在爭議。因為如果刑法對其過多介入,可能會阻礙這一技術的發展進程,但是完全摒棄刑法的介入也可能會造成該技術的畸形發展,這就需要尋找到一種干預與放松的平衡。與民法相比,相關問題的刑法討論則較為缺乏。2021年3月1日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非法植入基因編輯、克隆胚胎罪,這是針對2018年“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案”的刑法回應,但是對于冷凍胚胎方面的法律問題,似乎并沒有引起刑法學界的關注。
(一)冷凍胚胎不能“非法采集”和“走私”
202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七)》中規定了非法采集人類遺傳資源、走私人類遺傳資源材料罪罪名,那么冷凍胚胎能不能算是人類遺傳資源呢?人類遺傳資源是指含有人體基因組、基因等遺傳物質的器官、組織、細胞等遺傳材料,冷凍胚胎作為受孕父母雙方精子和卵子的合成體,當然具有父母雙方的遺傳信息。筆者認為這里的人類遺傳資源包含冷凍胚胎,所以這里的法條也就可以解釋為非法采集冷凍胚胎和走私冷凍胚胎。而“非法采集”和“走私”又應如何理解呢?筆者認為這里的“非法采集”是指通過違法手段獲得冷凍胚胎的方法,如醫療機構的醫療工作人員盜竊儲存的冷凍胚胎。在美國加州便出現過這樣的案例:一位32歲的女性起訴,稱自己體內的胚胎被盜并且被出售給他人,盜竊其胚胎的正是加州大學生殖健康中心的醫療工作人員,警方介入后發現有此遭遇的并不止她一人,這所醫院的醫療工作人員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經常盜取病人體內的卵子甚至胚胎,并出賣給他人。[6]“走私”的法律概念是違反海關法和國家其他法律、法規,逃避海關監管,非法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境的物品、國家限制進出境或者依法應當繳納關稅和其他進口環節代征稅的貨物、物品進出境,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行為。2019年3月15日,印度發生了首例走私胚胎案,一位名叫帕特班·杜萊的乘客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抵達印度孟買國際機場時被捕,因為他攜帶了一個裝有人類單胚胎的液氮罐。[7]雖然上述這些案件都發生在國外,但并不意味著我國未來就不會發生,我們也應該防患于未然,做好相關的法律規范。除此之外,還有買賣、非法銷毀、遺棄冷凍胚胎的行為,這里并不是絕對的禁止銷毀,因為“胚胎不但在人的發育過程中是一種重要的形態,在科學研究實驗中也是重要的實驗對象,科研人員可對符合條件的胚胎進行合法的實驗研究,且對那些可能孕育出先天性畸形、有先天性嚴重疾病、冷凍時間過長的胚胎是可以進行銷毀和丟棄的。”[8]
(二)冷凍胚胎不能買賣
關于冷凍胚胎的買賣行為,雖然我國刑法及其他部門法沒有明確禁止,但是通過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之前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可知,買賣冷凍胚胎的行為在我國是被絕對禁止的,因為其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針對如何對這一行為進行定罪的問題,已經有一些學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有學者認為應該另設新罪,比如非法買賣胚胎罪;有學者則主張以原有的非法經營罪來判定。對于“非法經營罪”,筆者認為還需進一步討論。非法經營罪,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買賣冷凍胚胎的行為確實違反了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所規定的一系列規章,同時也屬于非法限制買賣的物品,但是“非法經營罪”中規定的“擾亂市場秩序”,必須是已經存在市場,但在我國關于冷凍胚胎買賣的市場還不存在,所以將它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也許還不夠妥當。另設新罪也許更為適宜,如劉長秋研究員所認為的:可以專門設置非法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或胚胎的罪名。[9]對于非法買賣、銷毀、遺棄冷凍胚胎的,可以新設“非法買賣、銷毀、遺棄人類胚胎罪”。這是筆者的初步設想,還不夠成熟,將在今后的研究中繼續深入探討。
結語
筆者分別從民法和刑法角度對冷凍胚胎移植技術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或已經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初步分析,在新興技術不斷涌現的時代背景下,僅靠一門法律很難包含新技術發展領域下的所有法律問題。在考慮對一項足以影響到全社會的科學技術進行法律規制時,必然需要從法律的整體視角綜合規范。除了《生物安全法》這一基礎性法律外,還需要相關部門法與之相協調,甚至需要相關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相繼出臺與之相配套,方能為生物安全技術的發展提供相應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