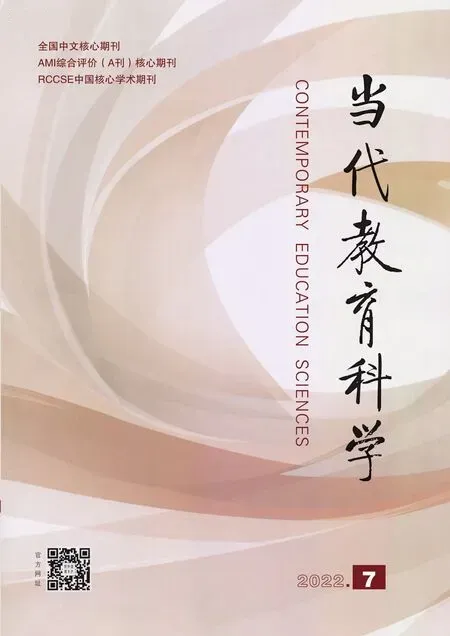論從“五育并舉”到“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范式轉(zhuǎn)型
● 馬 飛
“五育并舉、融合育人”是對新時代我國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整體回答,已然成為深化基礎(chǔ)教育教學(xué)改革的重點、難點和基本方向。當(dāng)前,從“五育并舉”到“五育融合”的嬗變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相互融合的過程,是將黨的教育方針政策轉(zhuǎn)化為教學(xué)實踐改革的內(nèi)在理念與外在行動的過程,這不僅是時代發(fā)展轉(zhuǎn)型在教育層面的變革,更是在哲學(xué)思維層面的反思,從而為教育教學(xué)實踐提供了一種新范式,表現(xiàn)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整體性、建構(gòu)性和生成性。理解“五育融合”教學(xué)范式的轉(zhuǎn)型與變革,是對教學(xué)理論與實踐創(chuàng)新的一種積極探索,同時也是指向”五育“本身的“連根拔起”式的剖析,最終為“五育融合”教學(xué)的實踐機理提供了方法論原則。
一、時代變革:“五育融合”是新時代教育變革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xí)近平總書記緊緊圍繞培養(yǎng)什么人、怎樣培養(yǎng)人、為誰培養(yǎng)人這一根本問題,旗幟鮮明地強調(diào)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事業(yè)的根本任務(wù),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這不僅是新時代教育工作目標(biāo)的重新闡釋與定位,同時也是對我國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整體回答,已經(jīng)成為深化基礎(chǔ)教育教學(xué)改革的重點、難點和基本方向。
(一)政策導(dǎo)向:“五育并舉”是新時代教育改革的國家方案
從時代發(fā)展戰(zhàn)略來看,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崇高使命和根本任務(wù)。2018 年9 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明確提出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并強調(diào)“要努力構(gòu)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的教育體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養(yǎng)體系”,[1]首次確立了“五育并舉”的全面發(fā)展教育體系和新時代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的具體要求。這是對黨的教育方針的新發(fā)展,對教育總要求的新認(rèn)識以及對教育工作目標(biāo)的新要求。[2]此后,黨和國家在全面貫徹全國教育大會精神的基礎(chǔ)上,通過頒布系列政策、文件構(gòu)建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培養(yǎng)體系。
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頒布了《關(guān)于深化教育教學(xué)改革全面提高義務(wù)教育質(zhì)量的意見》,提出“堅持五育并舉,全面發(fā)展素質(zhì)教育”的指導(dǎo)意見,并強調(diào)“突出德育實效”“提升智育水平”“強化體育鍛煉”“增強美育熏陶”“加強勞動教育”。[3]國務(wù)院辦公廳發(fā)布了《關(guān)于新時代推進(jìn)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dǎo)意見》,強調(diào)通過“突出德育時代性、強化綜合素質(zhì)培養(yǎng)、拓寬綜合實踐渠道、完善綜合素質(zhì)評價”來“構(gòu)建全面培養(yǎng)體系”。[4]同時,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的《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2035》強調(diào):“以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為根本任務(wù),加快推進(jìn)教育現(xiàn)代化……更加注重學(xué)生全面發(fā)展,大力發(fā)展素質(zhì)教育,促進(jìn)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的有機融合。”[5]2020 年,為構(gòu)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的教育體系,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關(guān)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xué)勞動教育的意見》,強調(diào)要把勞動教育納入人才培養(yǎng)全過程,貫通大中小學(xué)各學(xué)段,貫穿家庭、學(xué)校、社會各方面,與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相融合。[6]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全面加強和改進(jìn)新時代學(xué)校體育工作的意見》和《關(guān)于全面加強和改進(jìn)新時代學(xué)校美育工作的意見》,強調(diào)要把學(xué)校體育工作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進(jìn)一步強化學(xué)校美育育人功能,把美育納入各級各類學(xué)校人才培養(yǎng)全過程,貫穿學(xué)校教育各學(xué)段,構(gòu)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的教育體系,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7]如是,在頂層設(shè)計和政策的推動下,我國總體建構(gòu)了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的教育體系,以此表明既要堅持“五育并舉”,一個不能少,更要堅持“五育融合”,建構(gòu)一個有機整體,[8]從而為深化新時代基礎(chǔ)教育教學(xué)改革奠定了基礎(chǔ),指明了方向。
(二)實踐導(dǎo)向:“五育融合”是新時代教學(xué)改革的基本趨勢
在新時代的語境下,“五育并舉”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nèi)涵,它的提出不僅是對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學(xué)說與時俱進(jìn)的當(dāng)代闡釋,而且是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偉大實踐基礎(chǔ)上對教育改革發(fā)展規(guī)律良性互動的智慧結(jié)晶,進(jìn)一步豐富了黨的教育方針的內(nèi)涵。從實踐層面分析,如何將“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政策轉(zhuǎn)化為教學(xué)實踐改革的內(nèi)在理念與外在行動,已然成為當(dāng)前深化基礎(chǔ)教育改革的時代課題和基本趨勢。在“五育并舉”的政策背景之下,“五育融合”由此誕生,即“五育并舉,融合育人”,[9]并成為學(xué)界關(guān)注的熱點話題。眾多研究認(rèn)為,“學(xué)生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不僅需要確立‘五育并舉’的理念,更要確立‘五育整合’或‘五育融合’的理念”。“五育融合”的提出是對“五育并舉”的推進(jìn)、深化和發(fā)展。[10]換言之,“五育融合”的提出不僅是對“五育并舉”政策話語的理論提升,同時也是對我國教育改革實踐的反思,是回歸教育原點,邁向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融合育人的教育實踐之路。
循此而論,立足于我國基礎(chǔ)教育改革發(fā)展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從“五育”的基本內(nèi)涵出發(fā),“五育并舉”到“五育融合”的發(fā)展邏輯就是指德智體美勞從政策文本走向教育教學(xué)實踐的發(fā)展轉(zhuǎn)變過程,是將“五育”從政策理想轉(zhuǎn)變?yōu)榫唧w教育教學(xué)思維、理念和實踐的建構(gòu)性過程。因此在教育學(xué)的語境中如何理解“五育融合”的內(nèi)涵,亦即如何以“五育并舉,融合育人”深化教育教學(xué)改革,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wù)的新問題、新要求,尋求以課程教學(xué)、組織管理、學(xué)校文化的教育生態(tài)的整體變革,[11]已然成為新時期我國教育教學(xué)改革的基本方向。特別是,在人工智能賦能新時代的戰(zhàn)略背景下,伴隨著“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成為人才培養(yǎng)的新要求,以知識為導(dǎo)向的教學(xué)范式受到挑戰(zhàn),從知識立場走向生命立場儼然成為“智能時代”教育發(fā)展的需要,同時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現(xiàn)實訴求。因此,從德智體美勞的整體性出發(fā),“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改革不僅要在“五育”內(nèi)部進(jìn)行深度融合,而且要開闊視野在“五育”外部進(jìn)行跨域融合,精準(zhǔn)對接信息技術(shù)對人才培養(yǎng)的要求和挑戰(zhàn),準(zhǔn)確把握核心素養(yǎng)與德智體美勞的高效融合,創(chuàng)新基于“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改革所需要的“融合”,以此來夯實課程教學(xué)與“五育融合”的主渠道,轉(zhuǎn)變教學(xué)方法,瘦身教學(xué)內(nèi)容,改革教學(xué)評價,深化融合理念,在技術(shù)超越與生命發(fā)展之間探尋“五育融合”的平衡點。
二、思維轉(zhuǎn)向:從“五育并舉”到“五育融合”的嬗變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jìn)入新時代,從“五育并舉”到“五育融合”的嬗變,確證了我國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融合育人的教育發(fā)展實踐之路,已成為新時代基礎(chǔ)教育變革的基本方向。這不僅是時代發(fā)展轉(zhuǎn)型在教育層面的變革,更是對“五育并舉”思想認(rèn)識在哲學(xué)思維層面的反思,即從實體思維轉(zhuǎn)向?qū)嵺`思維。這既是深化教育教學(xué)改革的現(xiàn)實訴求,也是培養(yǎng)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要,為教育教學(xué)實踐提供了一種新范式。
(一)實體思維的承諾:“五育并舉”的理解依據(jù)
實體思維是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思維方式,亦稱“客體性思維”,是指把預(yù)設(shè)的某種存在或?qū)嶓w作為終極性的本原,并以此為前提解釋一切事物的思維方式,[12]相信世界上一切都有一個最終的、可靠的實體作基礎(chǔ),或一切現(xiàn)象、一切表現(xiàn)都一定是某個實體的存在,或它的屬性。[13]“五育并舉”更多是從名詞或副詞意義上的教育構(gòu)成要素層面來說的,[14]強調(diào)德智體美勞缺一不可,是對教育的整體性或完整性的倡導(dǎo),是一種理論抽象和育人假設(shè),主張以“實體”為寄托,試圖在教育之外預(yù)先設(shè)定某一邏輯基點來建構(gòu)人才培養(yǎng)模式,從而將“五育并舉”理解為德智體美勞等實體要素和基于“五育并舉”的人才培養(yǎng)理念。如是,這一理解觀念的思維基礎(chǔ)在于,將“五育并舉”視為獨立存在的實體或可行動的理念,并在本體論上承諾能夠?qū)@一實體的目標(biāo)、內(nèi)容、方式進(jìn)一步分解、解構(gòu),進(jìn)而確證出一條基于實體思維的理解思路。[15]從教育學(xué)的視角來分析,這是一種以本質(zhì)主義、理性主義哲學(xué)為基礎(chǔ)的教育發(fā)展觀,具有較強的邏輯性、抽象性、客觀性,它預(yù)設(shè)了與“五育”主體及其實踐絕對無涉的“事物本身”,理解和把握的最好方式在于將“五育并舉”的內(nèi)部構(gòu)成要素簡化、還原為具體的形式。
從教學(xué)范式來看,基于實體思維的預(yù)設(shè)將“五育并舉”視為一種獨立的實體,從而在教學(xué)實踐中以實體本體論的方式來理解和踐行“五育并舉”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即將實體本身等同于其教學(xué)內(nèi)容與形式。于是,基于“五育并舉”的教學(xué)變成超越時空且適用于任何“五育”主體的本質(zhì)規(guī)定活動,并按照預(yù)設(shè)的目標(biāo)、策略、方法開展教學(xué),以致造成“長于智、疏于德、弱于體、抑于美、缺于勞”的五育失衡和相互孤立現(xiàn)況,而“五育并舉”正是對這一問題的鄭重回應(yīng)。[16]但是,從“五育失衡”到“五育并舉”,無論從政策話語抑或理論抽象來理解其概念內(nèi)涵,人們都傾向于從“實體思維”出發(fā),按照一定的還原邏輯,預(yù)設(shè)相應(yīng)的知識、技能已達(dá)到特定的培養(yǎng)目標(biāo),把“五育并舉”的某一構(gòu)成要素視為其本身和關(guān)注的重點,從而導(dǎo)致“五育并舉”的教學(xué)范式的價值理性和人文屬性被遮蔽,育人價值在學(xué)科化和客觀的知識體系(德智體美勞)中被割裂,教學(xué)目標(biāo)和育人目標(biāo)被分裂的課程分解為孤立的五個子目標(biāo),整體的“五育并舉”人才培養(yǎng)模式被簡單化、線性化、靜止化,嚴(yán)重束縛著“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整體性培養(yǎng)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如是,以實體思維為基礎(chǔ)的“五育并舉”教學(xué)范式把本來相互聯(lián)系、相互過渡的對象離散化、割離化了,既不涉及對象內(nèi)部的任何結(jié)構(gòu)與關(guān)系,又不涉及對象之間的過渡和聯(lián)結(jié)”,[17]在實踐中易于忽視各育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聯(lián)和具體情境,使“五育”主體的思維陷入封閉、靜態(tài)、非此即彼的狀態(tài),不斷催生出新的教學(xué)問題。
當(dāng)然,實體思維下“五育并舉”的教學(xué)范式也承認(rèn)各育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但這種關(guān)聯(lián)是具有確定質(zhì)的兩個事物的外在關(guān)聯(lián),是與根本性質(zhì)無涉的情況下的相互作用,[18]如果把這種關(guān)系實體化,就會陷入結(jié)構(gòu)實在論。然而,德智體美勞中的任何“一育”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且任何教學(xué)活動都無法直截了當(dāng)?shù)貏澐譃槲逵心场耙挥薄嶋H上,教學(xué)活動作為培養(yǎng)人的實踐活動,德智體美勞之間相互融合、滲透,貫穿于個體生命發(fā)展的任何時間和空間,同時隨著時空的改變而變化。
(二)實踐思維的解釋:“五育融合”的邏輯支撐
實踐思維是把握屬人存在,理解、詮釋和評價一切哲學(xué)問題的根本思維方式,它不再抽象、孤立地考察物質(zhì)實體或精神實體,而是順著實踐能動性和具體歷史性進(jìn)行思維,以突出主體和實踐在“關(guān)系”中的主導(dǎo)地位,從而把“關(guān)系”理解為由主體能動的實踐不斷澄明的動態(tài)系列,即“用實踐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思維,從而把主觀和客觀、本質(zhì)和現(xiàn)象、關(guān)系和過程視為主客體互動中原本不可分割的動態(tài)整體的分別抽象,以強調(diào)主體因素并不是先驗的前提,而是實踐過程本身,是與實踐同步“成為”的。[19]“五育融合”的實踐邏輯是對“五育并舉”的推進(jìn)、深化和發(fā)展,側(cè)重于在五育實踐的貫通融合中實現(xiàn)“五育并舉”,所以說“五育并舉”和“五育融合”是理想與實踐、目標(biāo)與策略的關(guān)系,彰顯了一種實踐形式,即“融合實踐”。[20]如是,從實踐和關(guān)系的視角理解“五育融合”,它不僅是一種教育價值觀,也是一種教育創(chuàng)新思維方式,更是一種教育實踐新范式。[21]在新時代背景下,基于實踐思維的“五育融合”是一種有效平衡和解決“五育分離”的方法論原則。它立足于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復(fù)雜性、多樣性、系統(tǒng)性和動態(tài)性,直指實體思維下的“還原論”,并從“五育融合”的實踐、理念和思維出發(fā),致力于破除長期以來存在的“疏德、偏智、弱體、抑美、缺勞”,以及各育之間的“彼此分離”“相互割裂”“互不相關(guān)”等痼疾,[22]以構(gòu)建新時代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的新教育體系為歸依。
從教學(xué)范式來看,實踐思維下“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范式是對實體思維下“五育并舉”的教學(xué)范式的深化和超越,“而且是一種適應(yīng)我國教育特點的本土化跨領(lǐng)域融合教育教學(xué)范式”,[23]它根植于教學(xué)活動的實踐性、情境性、復(fù)雜性來理解“五育融合”的內(nèi)在特征和實踐規(guī)律,并強調(diào)基于“五育融合”的全面發(fā)展是“五育”主體間的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不僅各育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度、銜接度將有所提升,各育自身的推進(jìn)方式、運行方式和發(fā)展方式也會隨之發(fā)生革命性變化。因此,“用實踐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思維,擺脫了實體思維“見樹不見林”的弊端,為重構(gòu)“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范式提供了方法論原則。在教學(xué)中,整體的“五育融合”強調(diào)“五育”的融合性、均衡性以及關(guān)聯(lián)性,蘊含著整體的視野和實踐的立場,主張以回歸教育原點的思想方法,以整體促進(jìn)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價值旨趣,通過“實踐”“關(guān)系”的行動框架,以生命主體的發(fā)展需求,知識的融會貫通和育人方式的創(chuàng)新為邏輯起點,指向全面發(fā)展的育人目標(biāo)、整體性思維方式以及課程改革的深化,[24]表現(xiàn)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整體性、建構(gòu)性和生成性。
所以,教學(xué)從來就不是一種價值無涉的實體,而需通過實踐思維、系統(tǒng)思維、融合思維把“五育融合”置于交往實踐的教學(xué)關(guān)系和活動中,回歸育人原點,構(gòu)建多維互動、協(xié)作探究的生成性教學(xué)范式,重構(gòu)新時代基于“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目標(biāo)、理念、內(nèi)容、模式、方法、技術(shù)支持等,從而擺脫學(xué)科主義、知識主義、功利主義等傳統(tǒng)教學(xué)的弊端。這既是時代發(fā)展的現(xiàn)實訴求,也是智能時代發(fā)展的需要,更是教學(xué)實踐主動適應(yīng)社會變遷的必然反映。換言之,只有“五育”在實踐層面的有效、深度融合,才能在個體的生命發(fā)展中留下相應(yīng)的、可供回憶和喚醒的“五育情愫”,從而為人的終生發(fā)展奠定源源不斷的、意向性的、可資發(fā)展的綜合性素質(zhì)和緘默性知識,由此促使個體的教育自覺與時代精神達(dá)成內(nèi)在契合,形塑具有時代精神的獨特氣質(zhì)和品格,從而為新時代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wù),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提供內(nèi)在依據(jù)。
三、范式轉(zhuǎn)型:“五育融合”教學(xué)的實踐機理
教學(xué)范式的轉(zhuǎn)型是思維方式、價值理念、研究方法等的轉(zhuǎn)變在教學(xué)層面的闡釋與運用。實體思維的教學(xué)范式把“五育”視為教學(xué)內(nèi)容的組織要素,忽視了“五育并舉”的相對獨立性和整體性特征,使得“五育并舉”的教學(xué)范式走向“五育分割”,弱化了“五育”的整體育人功能。“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范式是對實體思維下“五育并舉”教學(xué)范式的超越,表現(xiàn)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整體性、建構(gòu)性和生成性。它不僅是教學(xué)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創(chuàng)新的一種積極探索,也是指向其五育本身的“連根拔起”式的剖析,最終形成“五育融合”教學(xué)的新生態(tài)。
(一)打破基于“加法式”的教學(xué)思維
教學(xué)思維是人們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釋教學(xué)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作方式。[25]教師作為教學(xué)變革的重要主體,其教學(xué)思維是認(rèn)識和實踐活動的內(nèi)在機制的重要內(nèi)容,規(guī)范著思維和實踐對象、主題、過程的運行方式以及結(jié)果的存在與表達(dá)方式。[26]由此論之,教學(xué)作為一種培養(yǎng)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對教學(xué)思維的追問是實踐教學(xué)論研究的一種實踐思維方式,對于探討“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范式來說,實踐思維更具特殊性和貼切性,其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否定論思維方式、一種現(xiàn)實批判的思維方式。[27]它針對實體思維的預(yù)設(shè)性、還原性和簡單性,追求擺脫唯科學(xué)主義思維方式和自然科學(xué)研究范式的束縛,打破教學(xué)思維重實體而輕關(guān)系、重預(yù)設(shè)輕生成,過于追求確定性、穩(wěn)定性、同一性的弊端。反觀現(xiàn)實,“五育分離”的根本就是這種實體思維和簡單性信念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方法、秩序經(jīng)由合法性的敘事后被誤認(rèn)為教學(xué)本身,教學(xué)的本真魅力與“五育”的真正意蘊卻被遮蔽在這一信念之內(nèi),而這種信念所堅守的就是“加法式”的教學(xué)思維。[28]它使得教學(xué)變成超越時空且適用于任何“五育”主體的本質(zhì)規(guī)定活動,即按照預(yù)設(shè)的目標(biāo)、策略、方法、內(nèi)容開展教學(xué),并把“五育”的某一育視為其本身和關(guān)注的重點,或者把課程教學(xué)分解為孤立的相關(guān)的內(nèi)容,以致造成“五育”的錯位、越位、搶位和不到位的現(xiàn)象。如是,“加法思維”的過渡盛行所產(chǎn)生的危害是教學(xué)內(nèi)容繁雜多變,結(jié)構(gòu)模糊,條理不清,難以統(tǒng)領(lǐng),質(zhì)量低下。“五育融合”教學(xué)實踐理性的邏輯前提在于“減法思維”的回歸,以打破原有事態(tài)的穩(wěn)定結(jié)構(gòu),并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將力量集中在一點之上,舍棄無用的累贅和不必要的成分,以最少的資源達(dá)到最好的效果。[29]回溯新課改的歷史走向,強調(diào)課程的整合從添加模式到融合模式是我國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的重要特點和趨勢。[30]在此過程中,為了切實減輕學(xué)生的負(fù)擔(dān),課程改革的融合模式不斷被深化,這種模式所堅守的信念就是“減法式”的教學(xué)思維。
所以,“五育融合”的課程教學(xué)與“減法式”的教學(xué)思維具有天然的契合度,即需要以“五育”的整體性和融合性為根本價值取向,打破根深蒂固的“加法思維”,在內(nèi)涵上避免將各育進(jìn)行簡單相加,在實踐中避免繁難偏舊的內(nèi)容堆積,也不宜厚此薄彼地在優(yōu)先級和重要性上排序,而應(yīng)以“五育融合”的思想方法提高“五育”之間的滲透度。所以,需要以核心素養(yǎng)為生命線和基點,圍繞學(xué)科核心概念構(gòu)建結(jié)構(gòu)簡單、線條清晰、簡明扼要的教學(xué)范式,即“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實踐要與核心素養(yǎng)精準(zhǔn)對接。[31]即圍繞核心素養(yǎng),化繁為簡、精簡教學(xué)內(nèi)容,化亂為明、明確教學(xué)目標(biāo),化粗為精、創(chuàng)新教學(xué)方法,化虛為實、提升育人質(zhì)量,去除煩瑣的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蒸餾掉花樣教學(xué)的水分。
(二)樹立基于“育人原點”的教學(xué)觀念
教學(xué)觀念是教學(xué)實踐變革的基礎(chǔ),建立“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范式,需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教學(xué)觀念,教學(xué)變革才可能真正發(fā)生。“五育融合”是新時代對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整體回答,從“五育不全”到“五育并舉”再到“五育融合”,就是回歸教育的初心,使教育真正站到人的立場上來,以人之生成、完善為基本出發(fā)點,將人的發(fā)展作為衡量的根本尺度,用人自我生成的邏輯去理解和運作教育。[32]這種立場是重塑“五育融合”教學(xué)觀念的前提,即教學(xué)要以現(xiàn)實生活中具體的人為基本出發(fā)點,真正圍繞人的社會存在而展開,從而把對教學(xué)主體的認(rèn)識由“抽象的人”轉(zhuǎn)向“具體個人”,將促進(jìn)個體生命自覺作為教學(xué)的根本任務(wù),[33]擺脫從人之外、之上的某種實體或抽象法則與規(guī)范為依據(jù)樹立違背“育人原點”的教學(xué)觀念。新時代語境下,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是“人的全面發(fā)展教育”的核心要素,是人類的共通理想。它的提出是對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學(xué)說”的當(dāng)代闡釋,體現(xiàn)了人類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生命理想與價值追求。[34]教學(xué)作為培養(yǎng)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必須以人的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為基本尺度,以人的生命和為了人的生命為基點,開展“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實踐。
由此論之,“五育融合”教學(xué)觀念的實質(zhì)就在于回歸教學(xué)的育人原點,以人的全面發(fā)展重塑教學(xué)價值觀念,彰顯“五育融合”的育人價值,以此促進(jìn)教學(xué)觀念、教學(xué)過程、方式、質(zhì)量的轉(zhuǎn)變與提升。換言之,“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過程將從知識化教學(xué)轉(zhuǎn)向生命化教學(xué),從知識授受轉(zhuǎn)向思維訓(xùn)練,轉(zhuǎn)向?qū)€體生命發(fā)展質(zhì)量的提升;教學(xué)方式將從單邊靜態(tài)、單向傳遞轉(zhuǎn)向多邊動態(tài)、交互生成,從教學(xué)獨白走向交往對話;學(xué)生學(xué)習(xí)方式將從被動、接受、符號的淺層學(xué)習(xí)轉(zhuǎn)向探究、合作、反思的深度學(xué)習(xí);教學(xué)質(zhì)量觀將從成績質(zhì)量觀轉(zhuǎn)向素養(yǎng)質(zhì)量觀,從知識質(zhì)量觀轉(zhuǎn)向生命質(zhì)量觀,以此將人的整體發(fā)展與“五育”教學(xué)的內(nèi)容、過程、方式進(jìn)行深度融合、轉(zhuǎn)化,從而形成整體的、動態(tài)的、融合的教學(xué)生態(tài)。
(三)構(gòu)建基于“時代變革”的教學(xué)空間
“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改革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相互融合、轉(zhuǎn)變的過程,是從理論的高度和政策依據(jù)走向并扎根于教學(xué)實踐的過程。在人工智能賦能新時代的戰(zhàn)略背景下,從空間向度理解和把握教學(xué)變革的實踐邏輯,可以促使教學(xué)空間變革成為深化課程教學(xué)改革的有益探索。[35]教學(xué)空間的變革是“五育融合”教學(xué)變革的基底,它與教學(xué)活動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而且只有教學(xué)空間與教學(xué)思維、教學(xué)觀念、教學(xué)方式等同步變革,重新發(fā)現(xiàn)教學(xué)空間之于教學(xué)內(nèi)容、方式方法以及教學(xué)質(zhì)量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才能從根本上促進(jìn)“五育融合”在教學(xué)實踐層面的落地生根。具體來說,“五育融合”教學(xué)范式的實踐邏輯在于彌合傳統(tǒng)教育發(fā)展中“五育分裂”的現(xiàn)實性問題,化解“應(yīng)試教育”學(xué)業(yè)負(fù)擔(dān)的根本性問題以及打破“五唯至上”的功利主義問題,促使信息時代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指向的素質(zhì)教育愿景——從“知識本位時代”走向“素養(yǎng)本位時代”。
從技術(shù)層面看,智能時代的知識圖景在生產(chǎn)、表征、傳播和呈現(xiàn)方面已然超越時空限制,促使虛擬環(huán)境和“增強現(xiàn)實”對發(fā)展學(xué)生核心素養(yǎng)提供了無限的學(xué)習(xí)空間,[36]為變革傳統(tǒng)的教學(xué)空間提供了現(xiàn)實基礎(chǔ)。從教學(xué)層面看,信息技術(shù)與教學(xué)的深度融合在促進(jìn)落實學(xué)生發(fā)展核心素養(yǎng)的同時,傳統(tǒng)“教室-鈴聲”的空間邊界被無限擴(kuò)張,深度學(xué)習(xí)、智慧教育、未來課堂已成為突破傳統(tǒng)課堂教學(xué)空間的良方,線上線下結(jié)合、虛實相融的教學(xué)空間在技術(shù)與生命的張力中逐漸成為新形態(tài)。如何在空間的轉(zhuǎn)換中發(fā)展學(xué)生核心素養(yǎng),落實“五育并舉”,成為深化教學(xué)變革的重點、難點和趨勢。因此,從教學(xué)空間變革的向度審視“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實踐邏輯,探尋教學(xué)空間的“在場”與“缺場”之于教學(xué)方法、內(nèi)容、組織形式、教學(xué)結(jié)果的影響,構(gòu)建基于“時代變革”的教學(xué)空間,是發(fā)展學(xué)生核心素養(yǎng),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人,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wù)的必然舉措。
(四)指向基于“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評價
教學(xué)評價是準(zhǔn)確把握和提升育人質(zhì)量的重要保證、完善教學(xué)過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和推動教學(xué)活動不斷增值的重要手段。[37]在具體的教學(xué)活動中,基于不同的教學(xué)思維、教學(xué)觀念就會產(chǎn)生不同的教學(xué)評價和評價結(jié)果。以實踐思維審視教學(xué)評價,它是人們對實踐活動的認(rèn)識和反思,具有強烈的實踐指向性,從而對人們的實踐活動具有鮮明的導(dǎo)向作用。“五育融合”的教學(xué)評價是基于教學(xué)實踐活動的價值判斷和診斷、激勵、調(diào)節(jié)教學(xué)的教育行為,指向于新時代學(xué)生的“整體發(fā)展”,其核心建立在“五育融合”的效果上,這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教學(xué)評價體系的確立。長期以來,我國教學(xué)評價鐘情于智育獨大的教育評價觀,存在評價主客體單一、方式傳統(tǒng)、內(nèi)容淺顯、作用甚微等不足,[38]以致造成疏德、偏智、弱體、抑美、缺勞的畸形現(xiàn)象。擺脫單一性評價,不再孤立地評價德育成效、智育成效、體育成效、美育成效和勞育成效,代之以“五育融合度”為評價單位,進(jìn)行整體評價,[39]是“五育融合”教學(xué)范式轉(zhuǎn)型的核心內(nèi)容,對提升育人質(zhì)量,促進(jìn)學(xué)生全面發(fā)展具有根本性的導(dǎo)向作用。
一是立足于學(xué)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價值基礎(chǔ),以“五育融合”的整體性、協(xié)調(diào)性和關(guān)聯(lián)性為根本根據(jù),從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整全視角系統(tǒng)推進(jìn)教學(xué)評價與“五育融合”課程體系、教學(xué)理念以及個體全面發(fā)展的深度融合。二是以提高“育人質(zhì)量”為核心,從成績質(zhì)量觀、知識質(zhì)量觀轉(zhuǎn)向素養(yǎng)質(zhì)量觀、生命質(zhì)量觀,將人的生命完善、內(nèi)在生成、整體發(fā)展與“五育融合”教學(xué)評價的內(nèi)容、過程、方式進(jìn)行深度融合。三是以“五育融合”教學(xué)評價的“有效性”和“標(biāo)準(zhǔn)”為歸依,深化和夯實五育之間的內(nèi)外部融合,不斷拓展五育邊界,明確教學(xué)目標(biāo)、內(nèi)容、方法、效果,厘清“五育融合”評價標(biāo)準(zhǔn),提高“五育融合”教學(xué)評價的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