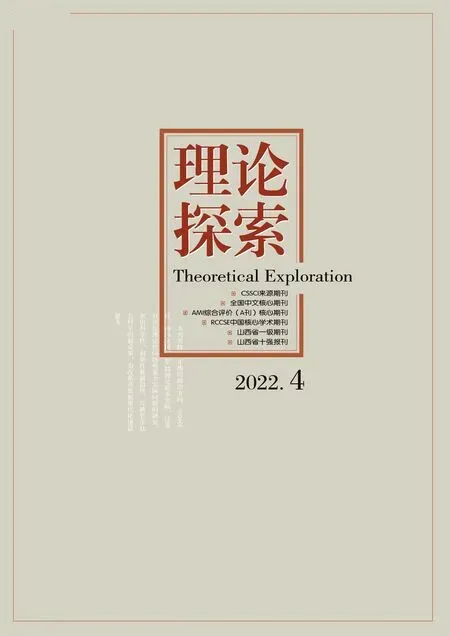全球空間正義對資本邏輯的否定與超越
李少霞 魏 莉
(新疆大學,烏魯木齊 830046)
正義是人類普遍的價值追求,人類生產生活實踐的全過程貫穿著正義原則。作為人類實踐的基本領域,空間與正義密切聯系,正義是空間的基本價值追求,全球空間正義是維持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原則和條件,內含政治空間正義、經濟空間正義、社會空間正義、文化空間正義和生態空間正義。其中,全球政治空間正義要求匯聚起空間變革的革命性力量,打破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空間區隔,使落后民族國家被束縛的主體力量得以彰顯,構建起共在共生共融的全球空間。全球經濟空間正義即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改革全球金融體系,為資本的運行制定合理有序的規范體系,加強對資本的引導和監管,界定資本運行的限度與域度,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防止資本野蠻生長操控,阻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一些落后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顛覆和霸權;并且,全球經濟空間正義內含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后發展中國家的線性對壘格局轉變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興經濟體與落后發展中國家互通的普惠格局這一要求,旨在縮小各國的經濟發展差距,維護全球經濟空間的安全穩健。全球文化空間正義就是要破除資本對文化的宰制,使文化的發展擺脫資本邏輯的控制,形成相互尊重、和諧共存的局面,構建適合全球文化多元發展和共生共榮的價值整合機制,使各國在文化交流互鑒中消除阻隔,加深世界各國對彼此文化的認知與了解。全球社會空間正義就是要倡導以自由人聯合的空間拓寬人的生活和生產空間,使人從受物質力量所遮蔽的深淵中解放出來,自覺構建起以和諧正義為主要特征的空間共享格局。全球生態空間正義就是在否定和超越資本邏輯的基礎上,秉持“兩個和解”的理念,堅持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構性原則,超越單個民族、國家的利益,以全人類整體利益和共同價值為引領,積極倡導和構建維護全球生態空間正義的國際機制,堅持權利與義務的同一性,引導各國參與全球生態空間合作治理,形塑全球生態空間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有效規避因全球生態空間價值缺失、正義理念缺乏、治理失衡等誘發的人類生存危機問題。
在全球命運一體化、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新態勢下,空間利益的合理分配和科學規劃已經成為影響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的重要因素。然而,資本的空間布展誘發了一系列空間斷裂和失衡問題,諸如:全球空間剝奪加劇、虛擬經濟空間的風險蔓延、文化霸權滋生、社會空間異化、生態空間生產正義缺乏,給人類帶來了危機,在此背景下,以全球空間正義理論否定和超越資本邏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全球政治空間正義遏制資本邏輯的空間擴張,營造公平正義的國際環境
全球政治空間正義是全球空間正義的首要前提,是對資本邏輯主宰的“空間剝奪”和“不平衡的世界體系”的摒棄和超越,在合理規制資本邏輯的前提下,倡導構建以平等和諧、開放公正、互通有無為準則的“共建共有共享”的規則體系,使各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能夠享有平等的國際話語權,團結協作、助力公平正義國際格局的構建,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首先,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內含空間生產的合理布局和公平正義,追問資本邏輯不平等的空間布展。資本雖然開創了人類社會空間發展的新階段,第一次打破了全球空間的各種壁壘,使全球空間成為一個整體。但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全球空間布展并不是一個利益均沾的過程,而是潛藏著更為深層的淵藪——加速了對落后民族國家的空間剝奪。全球空間正義倡導維護空間秩序,構筑公平正義的國際環境,保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空間權益。
大工業的普遍競爭孕育了現代資本,其不斷擴張的內在動力就決定了資本邏輯必然會不斷征服空間。馬克思指出:“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1〕88在資本增殖邏輯的內在驅動下,資本主義摧毀了原有的空間結構和空間系統,在對全球原有空間生產要素配置的基礎上構建起符合自身利益的空間系統,形塑了高度規矩化、秩序化和等級化的空間結構。伴隨這一等級化空間結構的形成,全球性的空間生產得以擴展和蔓延,資本也逐漸聚集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增殖和競爭的驅使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落后民族國家裹挾進不平等的國際分工秩序中,并逐漸將其邊緣化,成為國際政治體制的依附。資本積累的推進和殖民擴張的深入,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后殖民國家的空間剝奪也逐漸具有可持續性。馬克思認為:“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地跳躍式的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2〕519通過殖民擴張,資本主義國家在海外的原料基地不斷得以擴張,平等的貨幣交易只是形式的平等,其背后潛藏的則是政治權力對空間的形塑和占有,是國家利益主導下的利潤回流和資本增殖。全球政治空間正義理論主張整合一切反抗力量,顛覆“中心—邊緣”的等級性空間結構,推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后國家的剝削與壓迫,實現全球空間正義。馬克思曾以全球空間范圍內的階級斗爭統攝和反抗空間剝奪,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哈維也指出:“全球化實際上只是不平衡地理和歷史(時空)發展的過程,它為反資本主義斗爭創造了多樣性的地形,而那些斗爭則需要以這樣一種方式綜合起來。”〔3〕500因此,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就是要容納并整合空間,實施空間變革,破除空間不平衡的等級格局,阻斷空間的分隔和利益的分化,積極引導資本在全球空間范圍內的合理流動,重新構建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空間格局,助力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其次,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內含空間權力的合理規制和科學導向,揭示資本邏輯主導下空間的權力化。空間是支撐權力合法性的重要場域,但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空間被權力所操縱,淪為權力運行的工具。資本在全球的空間集聚加劇世界權力的不平等和財富分配的不均衡。空間位置總是具有某種壟斷的優勢,空間權力的排他性和唯一性強化了空間權力的壟斷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增殖邏輯的驅使下希冀占有更多的空間以保護他們的壟斷權力,獲取可預見性的超額壟斷利潤。但是這種壟斷勢力必然會將不同國家的文化結構與生活方式置于危險當中,把財富、權力和機遇集中于少數地區和少數人之手,形成空間交換中的非對稱性關系。當前,以利潤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體制不僅不能消除這一不平衡的非對稱關系,反而使這一不平衡的空間關系不斷凸顯出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賴對空間的高度壟斷權限制了地區間資本的空間流動,以一種不對等的空間交換方式榨取超額壟斷利潤,權力集聚的非對稱性必然會帶來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均衡。
在新的全球化時代,資本已經成為一種跨越區域的強大空間性權力,成為塑造全球空間形態的重要力量。在以“民族—國家”為主導的政治體系中,舊的全球秩序已經退出歷史舞臺,新的全球秩序還沒有建立,全球資本在這一斷裂期接管了舊秩序喪失的權力,依托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奪了落后國家獨立管理和發展本國政治經濟的職責,鮑曼曾指出:“在全球化這場卡巴萊歌舞表演中,國家就要跳脫衣舞。到節目結束時,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布:鎮壓權。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被摧毀了,主權和獨立被剝奪了,政治階級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門。”〔4〕63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就是要合理引導資本和權力的空間流動,破除資本邏輯對空間的超額壟斷勢力,實現財富分配的均衡性和利益分配的對稱性。
最后,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內含以共產主義空間革命為旨趣的空間解放,洞悉和否定資本邏輯的矛盾之源。資本邏輯主宰下的無產階級生活在“普遍的痛苦”和“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在資本全球空間流通中,資本以時間消滅空間的方式操縱著國際分工,將不同的民族國家拼接成同質性的復合體,但是,這種拼接“有時是偉大的,有時是通過哄騙,但在更多的時候是通過施加無情而粗野的強力”〔5〕4。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利益沖突表現在:第一,資產階級為追逐剩余價值的最大化,無限度地剝奪無產階級,突破了無產階級身體空間的限制,使無產階級的身體空間衰竭。他們“零敲碎打地偷竊”工人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沒有任何憐憫之心。麥克貝恩醫生曾指出:他在陶工中間行醫25年,發覺這個階級在身高和體重方面顯著退化——即“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2〕284。北斯塔福德郡醫院主任醫生阿利奇指出:“他們(指陶工)一般都是身材矮小,發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們未老先衰,壽命不長,遲鈍而又貧血,他們常患消化不良癥、肝臟病、腎臟病和風濕癥,表明體質極為虛弱。”〔2〕284-285。第二,如何規訓工人的身體空間是資產階級政治策略的重要一部分。資本的空間化運轉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工人生存空間的整體性、宰制了工人總體性的勞動空間,高度細化的社會分工使工人被局限于固定的勞動場所,成為一種可代替的機器部件和受局限的動物。資本的權威割裂了整體性的勞動空間,壓制和約束著工人的身體空間。馬克思曾明確提出舊式社會分工的局限性:“當分工一出現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6〕537第三,以物化邏輯為主導的資本空間運轉在與空間的雙向作用中秉持最大限度創造剩余價值的基本原則,只是以抽象的、自然的視角理解人的存在,片面地將人視為創造物質財富的機器和手段,而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和多樣化需求。資本以赤裸裸的金錢關系代替了人和人之間溫情脈脈的關系,以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系代替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褫奪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需求,加劇了人的身體空間的單向度化。
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強化對人的身體空間的解放,號召無產階級要以革命者的姿態抵制資本主導下的空間生產,消除空間中的異化和壓迫,構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空間。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身體空間“通過與資本積累動態之間常常是創傷性的、沖突性的關系而形成”〔7〕48,因此,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空間非正義就必須立足于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中的受壓迫的身體空間,將其作為空間革命的起點,破除枷鎖,打破工具理性化的“他者空間統治”,實現自由。以自由人聯合的空間將為無產階級提供政治革命的可能性空間,拓寬人的空間革命道路,使人不再被拘束于外在物質力量所控制的牢籠中,彰顯無產階級變革現實世界的革命主體力量。
二、全球經濟空間正義有助于解決資本邏輯的內在困境,有效規制資本邏輯的衍生
資本邏輯蘊含資本逐利和增殖過程中展現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伴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開辟,資本的虛擬化和金融化逐漸成為資本全球擴張的一種重要手段,資本邏輯衍生的內在困境在全球空間蔓延的主要表現是虛擬資本的惡性膨脹誘發虛擬經濟空間的風險問題。全球經濟空間正義就是以全球公正、安全和有序尺度追問資本邏輯的矛盾困境,有效規制資本邏輯的衍生。
首先,全球經濟空間正義以全球公正尺度介入全球經濟發展和利益分配,在抵制資本對全球經濟的盤剝中重塑經濟全球化樣態。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資本離開利潤便會死亡。為追求更大的利潤和價值,資本會在不同的行業中游走,并與利潤高的行業緊密相連。一旦某一行業的利潤下降,資本便迅速撤出這一行業。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為占有財富盲目投資生產,不斷壓榨和剝削無產階級,造成國內生產過剩,人民消費水平萎縮,貧富差距拉大。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生產過剩”并不是“絕對的生產過剩”,而是“相對的生產過剩”。資本的相對生產過剩與勞動人民的貧困總是存在于同一空間中,是相伴相隨、無法克服的矛盾。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8〕548全球化時代,資本不再局限于一國范圍之內,而是沖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游走,剝奪全世界人民的財富。全球財富被不斷地聚斂于少數國家之手,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愈來愈貧困,形成全球范圍內兩極分化的局面。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和布展使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在全球上演,誘發全球范圍內商品價格的波動。全球經濟空間正義秉持公正的原則推進全球經濟空間的重塑,旨在強調各國要秉持互利互惠的基本原則,共同推進普惠共享、健康可持續的全球化,積極規制和引導全球利益分配的公正化,將蛋糕做大的同時分好蛋糕,釋放全球化的正面效應,使各國在互通有無中共享全球發展的福祉,構建普惠、共贏、平衡的全球經濟發展空間。
其次,全球經濟空間正義以全球安全尺度介入虛擬經濟空間,揭示了貨幣資本金融化和資本空間虛擬化的潛在困境。虛擬資本的出現使得以前與空間相耦合的剩余價值的生產成為一種脫離空間的自行增殖的貨幣資本,將整個空間和社會總資本也納入虛擬的信用體系當中,抽象的空間成為滿足資本無限增殖的場域,與之相適應,剩余價值的積累也成為一種超越時空的虛擬數量化存在。由于虛擬資本的利潤是一種預期的收益,與現實資本總是處于一種不對等狀態,因此,因現實中社會總資本的短缺和剩余價值量的減少所引起的貨幣積累風險就必然地轉嫁至信用體系當中。資本的抽象空間被進一步虛擬化,喪失了其全部的構成性要件,成為一種只供貨幣資本無限增殖的虛擬化存在。這一系列后果均歸因于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內在不合理。信用資本占據資本主義體系的主導地位使虛擬經濟空間也完全被金融化的貨幣控制,金融資本成為肆意控制資本空間的決定力量。為保證剩余價值的實現,資本抽象空間的空間屬性和時間要素均被虛擬化。“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像倫敦那樣大的集中的貨幣市場就興起來了……因此,這幫賭棍就繁殖起來。”〔9〕570當空間被虛擬化以至退場后,以“物”的形式出現的社會空間也被虛擬化,全球經濟空間則演化為虛擬的、跨越空間界限的貨幣增殖空間。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使全球金融資本以跨國公司的形式在全球空間布展,通過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剝奪實施壟斷利潤的積累,占據全球金融霸權的主導位置。一方面,虛擬資本的不斷膨脹使那些本來就生產過剩的虛擬商品造成虛假需求,從而誘發實體經濟生產出更多的剩余產品,滋生社會的生產過剩。另一方面,金融資本的全球化使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資產階級的少數人手中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貧富差距,使勞動人民更加貧困,消費水平下降。全球經濟空間正義深入洞悉了資本金融化誘發的矛盾困境,旨在倡導要合理規制和引導虛擬資本的發展,在處理好總量控制與適當擴容的基礎上,合理推動全球實體經濟的融資,使全球資本市場充滿活力的同時積極穩妥地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實現全球經濟空間的安全穩健,不斷滿足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最后,全球經濟空間正義以全球有序尺度介入虛擬經濟空間,在批判貨幣體系的扭曲化和資本空間的危機化中改變資本的發展樣態。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和貨幣對于空間具有抽象化和虛擬化的作用,憑借這一能力,貨幣資本便可以將資本內部生產和交換的空間矛盾統攝于資本自身的周期運轉中,實施風險轉嫁。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機的時刻,支付差額對每個國家來說,至少對每個商業發達的國家來說,都是逆差,不過,這種情況,總是像排炮一樣,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這些國家里發生。”〔9〕557這就說明,不管是虛擬資本還是現實的貨幣資本,其承擔風險的能力是有限的,當經濟危機超越這一限度時,必然會衍生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力量。從虛擬資本的衍生機制來看,虛擬資本構建的虛擬經濟空間雖然根源于現實的經濟空間,但因其儲存規模與現實的社會財富不相符合,其本身的交換性和流通性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這就決定了虛擬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誘發經濟危機的直接導火線。隨著虛擬資本的發展,人們便滋生出一種錯覺,好像一些資本都會無窮地增加,因為,同一債券在不同人的手中會以不同的形式增加。這樣,賣空買空和投機交易成為資本主義市場交易中的普遍現象,也成為誘發經濟危機、導致虛擬經濟膨脹的主要風險因素。當現實的資本因其有限的空間生產能力不可能滿足虛擬資本無休止的投機活動時,虛擬資本潛在的風險便以空間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強大的破壞性力量從某一空間向全球空間擴散,推進貨幣資本的金融化效應在全球空間中掠奪,以填補財富缺口,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全球經濟空間正義倡導要深化全球金融體制改革,在完善全球金融體制的進程中,合理矯正金融市場的過度投機傾向和行為,使其趨于理性化,實現金融空間秩序的穩定。
三、全球文化空間正義廓清資本邏輯的文化宰制,破除文化霸權的掣肘
伴隨資本主義在全球空間的擴展,資本主義文化也不斷向其他民族和地區滲透,文化殖民與文化霸權、資本與文化的共謀等一系列負面效應成為制約全球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全球文化空間正義旨在堅持全球文化的多樣化,在尊重不同文化獨立發展空間的基礎上推進文化的交流互鑒和共通共榮,培植不同文化多元共存的全球空間環境。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寶貴結晶,體現該民族衡量真善美的價值標準和核心價值觀,對于形塑民族成員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具有重要的功能。因此,培植民族文化的發展空間對于維護世界和諧、促進全球文化多樣性均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全球文化空間正義有利于規避資本空間生產進程中的文化霸權現象,推進文化的多元發展。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不僅帶來了全球經濟危機,也加速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實施文化霸權和文化擴張的進程,不斷沖擊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本國與其集團利益的最大化,強行將本國的主流價值觀輸入其他地區,企圖排擠、打壓和侵襲異質文化,使本國文化在他國暢行,在文化上實現壓制他國的目的。冷戰結束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到單純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制裁已經難以滿足現實需求,必須采取綜合性的強權政治手段,突出以宗教信仰、道德規范、價值觀念為主要形式的文化滲透,將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理念、民主觀點、價值觀念植入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從而搭載全球化的快車,向全球實施文化擴張和文化霸權,維持和鞏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文化霸權和文化擴張泯滅和消弭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將對人類文化的長久發展產生嚴重威脅。全球文化空間正義秉持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與交融原則,在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文化發展自主權的基礎上倡導不同文化在交流互鑒中構筑全球文化發展的多元性,正確認識文化多樣性和單一性的對立統一關系,為不同文化的發展提供安全的國際空間,有效規避資本空間生產進程中的文化霸權現象。
其次,全球文化空間正義有利于破除資本駕馭文化而結成的共謀關系,肅清資本對文化的宰制。人不僅是一種物理性的存在,更是一種文化性的存在,人對現實世界的觀念把握和認知決定了人能以鮮明的實踐特性再現和重塑空間,人的文化創造活動一旦觸及任何實在的空間,便具有了文化的形塑力和審美性。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相伴相隨,伴隨物質生產性質、形式、規模的改變,精神生產的性質、形式、規模等也要相應變化。因此,要考察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的關系,就必須將物質生產本身作為一種范疇,從物質生產入手。世界市場的開辟使資本邏輯沖破民族國家的地域限制,資本主義大工業在資本主導下將觸角延伸至各民族國家,使其生產具有世界性。相應地,精神生產也具有了世界性,“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于是許多民族的文學成了世界的文學”〔10〕35。資本主義的空間擴張和地域滲透,也加劇了資本對文化的宰制,文化殖民成為資本推擠空間擴張的一種重要手段。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到之處,均將資本主義代表的價值理念、生活方式在空間中輻射,“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1〕404。伴隨資本全球空間擴張進程的推進,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受到資本邏輯的宰制。馬克思曾指出,“隨著資本的統治的發展,隨著那些和創造物質財富沒有關系的生產領域實際上也日益依附于資本”〔2〕239,于是,“一切職能都是為資本家服務,為資本家謀‘福利’”〔12〕298。一旦文化與資本結成共謀性關系,文化便體現出資本的權力和意志,維護和體現資本的階級關系。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文化與資本的共謀關系在城鄉關系中具有顯著的體現。伴隨資本的全球空間擴展,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社會空間關系發生深刻的重組與變遷,城市日益成為資本與空間生產要素的集聚地,呈現強大的空間輻射和聚集效應,是資本主義文明的載體,而鄉村則日益衰敗,原來充滿生機活力的鄉村蛻變為人口不斷流動、環境惡化加劇、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場所,資本將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系均已破壞,利己的物化關系和利益關系代替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社會關系。資本主義文明的空間輻射雖培植了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推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但其必然會造就文化的同質化空間,為資本拜物教和空間拜物教敞開通行的大門。全球文化空間正義倡導文化生產和分配的公平公正,尊重各國文化發展的獨立性和多樣性,深刻回應和解答了人類文化事業發展所面臨的資本宰制的困境,在遵循人類文化繁榮發展的致思理路的基礎上超越資本與文化共謀的全球發展樣態,為人類文明譜寫新的篇章。
最后,全球文化空間正義有利于消除逆全球化帶來的文化負面效應,保障各國在文化領域中分享全球利益。一段時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資本、技術等方面強勢推行逆全球化,加速了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政治運動的衍生,使全球化的公共價值觀和政策難以維持,為一系列閉關自守的思想觀念提供了更大的傳播空間,成為主導這些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逆全球化對文化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第一,逆全球化沖擊了全球文化的合作機制,使不同國家的文化存在誤解和敵視,加劇了西方國家在國際文化交往中的霸道和任性,擠壓和侵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文化領域中的利益空間,既支離了各國文化之間固有的聯系,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渠道和對話機制陷入停滯,也強化了文化格局中固有的權力支配關系。第二,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文化發展的不確定性,加速了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等社會思潮的興起,使西方發達國家以強硬的對抗政策捍衛自身的利益,強力抵制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破壞了全球文化多樣化、開放化、流動化的發展趨勢,長此以往,必然會帶來偏狹的種族主義、極端主義、文化的斷裂性分化、群體分裂在全球盛行,誘發不同國家的偏見和仇恨,形成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沖突和分歧,使文化權益的沖突和碰撞不再局限于某一個國家,而是從一個空間轉移向另外一個空間,與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矛盾和沖突糾纏在一起,導致文明沖突加劇。全球文化空間正義倡導在審視和把握區域和全球文化發展的復雜性和關聯性的基礎上,重建文化和諧發展的空間,為不同國家文化間的交流、合作和依賴創造更多的空間,整合文化發展的共識和經驗,使全球文化適應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的發展,推動全球文化秩序的重建和文化格局的協調發展,使不同國家相互差別、獨立的文化系統緊密聯系,開展有利于全球文化安全的積極行動。
四、全球社會空間正義根除資本邏輯的異化弊病,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資本邏輯開創了人類發展的新目標,但是,目標的無限性與資本的有限性使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競爭只能服務于少數人的需求。資本的逐利本性驅使人們無止境地追求剩余價值,“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6〕163為獲取更大的剩余價值,資本不斷重組和占有空間,人的生活空間和生產空間被高度壓榨,人的發展空間喪失。全球社會空間正義追溯資本邏輯對人的物化占有和精神吞噬,在揭露人的生存空間異化和人的發展空間喪失的基礎上,探求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與人自身、人與人的統一。
首先,全球社會空間正義內含人與自身的統一性,追究資本邏輯對人的物化占有和精神吞噬。“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13〕821資本的獲得建立在嚴重的階級剝削關系上,工人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財富卻最終歸資本家所有,工人依賴于資本和機器而活,成為資本和機器的附庸。當資本家占有絕大多數的勞動產品時,工人卻只能占有一小部分,“只得到他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工人維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為了繁衍人類而是為繁衍工人這個奴隸階級所必要的那一部分”〔6〕122。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生活空間便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對立,即無產階級一無所有,資產階級卻趾高氣昂;工人“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資本家“笑容滿面,雄心勃勃”,那些對于資本家來說是最富裕的狀態,對工人來說卻是赤貧。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社會化和分工協作是其主要特征,依靠雇傭勞動榨取剩余價值是其主要目的,與這一生產方式相適應,產生了特殊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宰制著精神空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6〕550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囊括了與之對應的資產階級的精神面貌,即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文化。以物化勞動和資本增殖為本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獲取更多的商品,實施精細化的分工,使工人隸屬于生產過程的某一環節,徹底改變了個體的勞動空間,壓制了工人多種多樣的生產才能,工人成為愚昧無知的片面性人,喪失了精神發展空間,商品、貨幣和資本的現實邏輯充斥了人與自身統一的基礎。全球社會空間正義就是要瓦解和超越資本邏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超越資本對人的奴役和壓制,拯救人的自由自覺的本性,通過勞動的解放實現人的解放。
其次,全球社會空間正義構建合理的空間秩序,揭示資本主導下人的生存空間的異化。資本的根本目的就是獲取剩余價值的最大化,資本的驅利本性在其現實性上表現為資本對于空間的無限占有和重組。為了更大程度地占有空間,從空間上奪回在時間上失去的東西,資本家將工人和生產資料集聚在同一空間,使工人的生活空間和生產空間分異。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工人的集聚使工人的生存狀況更加悲慘,這種悲慘狀況主要體現在:第一,工人的住宅短缺,居住狀況日益惡化。恩格斯曾指出:“今天所說的住宅短缺現象,是指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的居住條件因為人口突然涌進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14〕250住宅短缺不僅加劇了社會的矛盾,而且也使城市的治安狀況惡化,誘發了城市生態環境的污染。第二,工人的工作空間惡化、工作制度嚴苛。以女縫紉工為例,他們在工廠中面臨三種災難,即勞動過度、空氣不足、營養不夠或消化不良。工人住在低矮、擁擠、滿是塵土的或潮濕的工作室,骯臟而悶熱的空氣,累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資本家以最殘酷、最齷齪、最卑鄙的手段對工人實施剝奪。全球社會空間正義的本質就是要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生存空間異化,擺脫資本邏輯對工人生存空間的宰制,破除社會空間被擠壓、社會規則被遮蔽、社會功能受限的現象,構建合理的空間秩序,使人們能夠公平、公正地享受空間生產和空間資源配置中的權益,實現空間產品和空間資源的生產、占有、利用、交換、消費的正義,為人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空間。
最后,全球社會空間正義強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追溯資本主導下人的發展空間的喪失。作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勞動的本質就是主體客體化,即不斷滿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求;作為價值增值過程,其核心目的在于創造出成倍的、多于預付部分的結果,用于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因此,生產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唯一目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剩余價值均是由可變資本創造的,不變資本不能生產剩余價值,并且,可變資本所凝結的工人的勞動量的大小就決定了剩余價值的多少。工人工作的時間越多,生產出的剩余價值就越大,資本家要想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勞動時間。如何科學規劃和占有工人的勞動時間并使之服務于剩余價值的生產成為資本家的任務。伴隨剩余勞動時間的增多,工人消耗的體力越多,獲得的能夠維持自身生命需要的生活資料就越少,工人便沒有更多的機會從事科學、藝術等創造性的活動,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開展社會交往,發展自己的自由個性。工人被長期禁錮于片面的生產環節之中,體現出嚴重的片面化和貧瘠化,發展空間被剝奪。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悲慘境遇以及發展空間喪失的根源在于工人勞動時間的被剝奪,資本家精細謀劃和安排工人的時間,迫使工人要想維持自身的生存,就必須將自己的全部時間用于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工人淪為剩余價值生產的工具,喪失了發展自身的時間和空間。當資本家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勞動時間時,人的發展空間也就被壓縮;當個人沒有自由的時間去發展自己,被當作資本的奴隸和賺錢的機器時,人完全處于片面的、異化狀態,連一頭載重的牲口也不如。全球社會空間正義就是要將“異化的空間”轉為“正義的空間”,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為人騰出時間和空間,使個人在文藝、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五、全球生態空間正義揭示資本邏輯的反生態性,構建和諧的生命共同體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對于自然空間的全面利用成為一種新的可能。秉持工具理性的價值準則,資本主義將自然空間作為資本擴張和資本積累的重要載體。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空間生產雖然是一部文明演化史,但是,“文明是一個對抗的過程,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為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產生其最初的產品,并使氣候惡化”〔15〕311。全球生態空間正義聚焦人與自然的統一性原則,在深刻揭示資本邏輯反生態本性中追問資本邏輯的矛盾困境,有利于構建和諧的生命共同體。
首先,全球生態空間正義重塑人與自然之間的整體性價值,深層揭露資本的反生態本性。資本內含的反生態性決定了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矛盾,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探究必須要將其與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審視聯系在一起。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16〕147資本主義加速了人類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但卻衍生出一系列的社會性問題,資本主導下的工業革命雖然增強了人類對于自然的支配力,卻加劇了人類對于自然環境的破壞,使人與自然的關系走向異化。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其顯著的表現就是自然資源的嚴重短缺、生態環境的極端破壞、水流、空氣、土地等的嚴重污染。資本擴張的目的雖然是經濟增長,但是其背后潛在的本質是生態擴張。在經濟無限增長的驅動下,資本家依據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主宰著科技,實施生態擴張。資本積累的每一步總是以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這種積累一直要靠全球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自然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經常是有毒廢料)的下水道。”〔17〕127資本積累得越多、擴張得越深入,對于自然的宰制也就越嚴重。全球生態空間正義秉持正義和有序原則,在突出人與自然之間的整體性價值的基礎上,以同構性原則協調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合理引導和規制資本的邊界,構建共享的生態空間。
其次,全球生態空間正義強調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構建,深層揭露資本支配的現代性關系。資本支配的現代性關系體現的是資本邏輯對自然空間的主導,為追逐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加劇資本的運轉和集聚,資本家不斷地向自然索取更多的生產資料,將自然納入資本的有用體系中,“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和原有物體的新的使用屬性”〔1〕89,占有和全面攫取利潤。“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8〕390資本邏輯推動現代化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過度擠壓自然空間、挖掘自然資源和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嚴重惡化。全球生態空間正義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整體性價值和原則,突破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困境和人與自然二元分化的傳統思維,在堅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基礎上依據自然發展的根本規律,充分利用自然、保護自然和改造自然。全球生態空間正義并不是靠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的努力就能實現的,而是需要全人類整體的努力,需要各國的通力合作。當前,資本的高速運轉不僅加劇了本國空間內人對自然的攫取,而且也將人與自然的矛盾轉移向其他地區,使全球的生態空間嚴重惡化,人與自然處于兩極對立之中。全球生態空間正義秉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共同體理念,遵守自然發展的基本規律,以和諧性和包容性原則統籌應對資本邏輯對自然空間的宰制,以“共生共有共享”的價值理念和發展方式提升發展的內在動力,在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內在邏輯中重塑發展理念,推動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的構建,深刻揭示了資本主導環境和盤剝自然的驅利性和片面性。
最后,全球生態空間正義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科學揭示國際生態空間差序正義的困境。全球生態空間正義在其本質上就是全球資源環境配置的公平公正問題,是一種權利與義務、責任與利益的平衡,即資源享有的權利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應該平等分配。但是,就目前的全球現狀而言,利益的享有與全球生態責任的承擔處于不對等的地位。西方的一些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后,積累了強大的社會物質財富,占據國際生產、分工和貿易的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則處于被支配的地位。資本的全球擴展使發達國家不斷將資源消耗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不僅污染了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空間,而且從中獲得巨額利潤。相對于經濟實力和發展程度,發達國家應該比發展中國家投入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承擔更多的責任以保護全球生態空間。但是,發達國家掌握著國際規則的制定權,一方面,他們刻意忽略和回避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強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全球生態空間和保護全球生態環境方面要承擔同等重量的責任。另一方面,為維護發達國家自身的發展利益,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掌握的國際話語權,在享受權益的同時卻拒絕承擔保護國際生態的義務,退出全球生態公約。全球生態空間正義秉持享受生態權利與承擔生態義務對等的基本原則,強調要尊重歷史和各國發展的基本現狀,在堅持平等自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基礎上,合理構建全球生態空間的差序正義格局,號召世界各國要積極攜手應對全球的氣候變化,保護全球的生態環境,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良好的生態空間,滿足全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