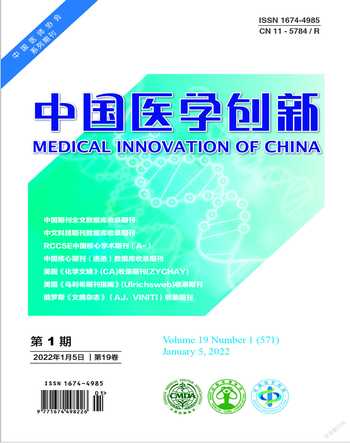抑郁癥與A其他系統之間關系的研究進展
姜巖琳
【摘要】 抑郁癥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精神疾病,但其治療效果卻大多不盡如人意且愈后易復發。近年來,大量研究表明抑郁癥不僅與神經精神有關,且受多系統影響,從而表現出不同的臨床癥狀。而其他疾病伴發抑郁癥更是病機復雜,治療難度較大。本文就抑郁癥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系做一綜述,幫助臨床對抑郁癥有更全面的認識與理解。
【關鍵詞】 抑郁癥 神經系統 循環系統 呼吸系統 消化系統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other Systems/JIANG Yanlin.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2022, 19(01): -183
[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relatively common mental illness, but its treatment effects are mostly unsatisfactory and tend to relapse after healing.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epress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neuropsychiatry, but also affected by multiple system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linical symptoms. The pathogenesis of other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o trea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other systems to help clinicians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Nervous system Circulatory system Respiratory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First-author’s address: Sheny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Shenyang 118304,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22.01.044
抑郁癥(MDD)是以患者精神狀態差,持續的心境低落,對外界刺激毫無興趣,自我評價有愧疚感甚則有自殺傾向等癥狀為臨床表現的一種精神類疾病。在社會飛速發展,生活節奏加快的背景下,抑郁癥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每年因抑郁癥而失去生命的人群逐漸擴大,已成為除身體器質性疾病以外致死率最高的精神疾病之一。抑郁癥的患病人群年齡跨度越來越大,這意味著青少年與老年人已逐漸成為本病主體,使本病不再是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中年人專屬,而成為全年齡性疾病,已嚴重威脅人類的身心健康。
多項研究證明,抑郁癥的發病與進展和多系統之間存在關系。人體本身即為一個為整體,每種疾病的發生與發展均不能孤立看待,而應注重多器官之間的內在聯系才能更全面的把握疾病,從而針對不同病情尋求更恰當的治療方法。抑郁癥更當如此。眾所周知,疾病的發展與轉歸往往與情緒及心理狀態密切相關;而持續低落消極的抑郁狀態更會導致多系統功能失調引起各種疾病。本文就抑郁癥與各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做一綜述,幫助臨床對抑郁癥有更全面的認識與理解。
1 抑郁癥的發病機制
抑郁癥發病機制較為復雜且無明確定論,通常被認為是遺傳、環境、心理、生物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導致的結果。目前有多種關于抑郁癥發病機制的說法已被廣泛接受,如血清5-羥色胺(5-HT)減少、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釋放下降、下丘腦-垂體-促腎上腺軸(HPA)亢進和炎癥反應影響等[1]。隨著抑郁癥相關研究的逐漸深入,近年來又發現了線粒體代謝障礙和水通道蛋白4(AQP4)表達減少等也參與了抑郁癥的發病過程。線粒體是能量代謝的主要場所,有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線粒體結構和功能有受損現象,線粒體復合體活性下降,輔酶Q10含量下降,而針對不同情況給予相應的恢復治療,可明顯改善抑郁狀態[2]。AQP4主要在星形膠質細胞(As)末端表達,不僅可以調節星形膠質細胞的生理功能,還參與了神經興奮和突觸可塑性[3]。動物實驗表明,敲除AQP4表達會誘發小鼠抑郁癥狀;尸檢結果發現,抑郁癥患者腦體積縮小,AQP4表達明顯下降。傳統抗抑郁藥物氟西汀治療抑郁癥的機制或與增加AQP4的表達有關。
2 抑郁癥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系
2.1 神經系統 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大腦初級運動皮層(M1)有受損傾向和可塑性下降的表現。M1區參與了軀體活動和肌肉控制,并在認知過程中同樣發揮作用。M1區的可塑性通過大腦皮層受刺激后的長時程增強(LTP)或長時程抑制(LTD)表現出來,且運動誘發電位(MEP)與M1區可塑性呈正相關。有學者在男性抑郁癥患者M1區可塑性情況的研究中,以重復經顱刺激(TMS)激發MEP變化。結果發現,男性抑郁癥患者在TMS后5、10、30 min后,與男性健康人群MEP值顯著增高的現象相比,均無明顯變化,并未引起M1區的LTP反應,表明男性抑郁癥人群M1區可塑性降低。但在旋轉運動學習能力的測試中卻發現M1區可塑性下降并未對男性抑郁癥人群旋轉運動學習能力有所影響,這一影響在健康男性人群中表現更為明顯,即M1區可塑性與旋轉運動學習能力呈正相關。分析其原因,可能受此試驗僅以男性作為研究對象和旋轉運動動作幅度過大不夠精細等因素影響[4]。
抑郁癥患者經常伴有軀體、內臟、關節等部位的慢性疼痛,這一癥狀的出現為治療抑郁癥提高了難度。黃朝陽等[5]在以雙脈沖體感誘發電位(P-SEPs)的方法,研究抑郁癥對中樞感覺神經系統的影響時發現,疼痛的產生可能與抑郁癥患者頂葉中央后回皮層興奮性減低和脊髓后角興奮性增高有關。研究時以刺激電極刺激患者左腕正中神經,分別行單脈沖電刺激和雙脈沖電刺激,以得到單脈沖體感誘發電位(S-SEPs)和P-SEPs。記錄電極分別置于Cv6點(第6棘突)、右側Shagas點(EEG國際10-20聯結系統C4后2 cm處)等,其中Cv6點記錄到的體感誘發電位成分為N13成分,為頸髓電位;Shagas點記錄到的體感誘發電位成分包括P25成分等,為皮層誘發電位。統計各測量點T-SEPs/S-SEPs波幅比值發現,抑郁癥患者的N13成分波幅比值明顯高于普通人群,呈興奮狀態;而P25成分波幅比值則明顯低于普通人群,呈抑制狀態。N13成分來源于脊髓灰質后角,說明該區興奮性有異常增高現象,其發生機制可能與后角抑制性中間神經元損傷有關。因此,抑郁癥患者存在疼痛刺激在脊髓水平處理失常,疼痛信號被異常放大地傳入大腦的情況[6]。P25成分來源于中央后回,其抑制狀態提示我們,抑郁癥人群頂葉中央后回皮層興奮性下降,疼痛信號處理功能紊亂,從而導致抑郁癥患者經常伴有疼痛癥狀且不易緩解的后果。
抑郁癥的關鍵癥狀快感缺失被認為與多巴胺能神經系統功能紊亂有關,因為此區掌握著與快感密切相關的獎賞系統。多巴胺能神經系統中的腹側背蓋區中腦-邊緣系統通路在大腦的獎賞環路中起關鍵作用,目前,中腦腹側被蓋區(VTA)-伏膈核(NAc)環路的多巴胺能神經元在獎賞刺激中的調節作用得到了廣泛認同。而抑郁癥患者該傳導通路通常有不同程度的損傷,VTA內多巴胺能神經元電活動異常,抑郁模型動物多巴胺能神經元放電頻率明顯升高,而降低該區神經元放電頻率則可以減輕動物的抑郁癥狀[7]。
多巴胺能神經系統功能紊亂與抑郁癥伴失眠現象也有密切的關系。抑郁癥患者的失眠情況通常表現為難以入睡、易醒和早醒等方面,其睡眠腦電圖通常顯示為慢波睡眠(SWS)降低和快動眼睡眠時間(REM)延長等方面。而多巴胺能神經系統的神經元、多巴胺轉運蛋白(DAT)和多巴胺受體等對睡眠-覺醒周期、睡眠深度、非快速動眼睡眠時間及SWS-覺醒時相轉換等涉及睡眠質量的關鍵因素起到調節作用。而通過藥物對紊亂的多巴胺能神經系統功能進行糾正,平衡多巴胺(DA)水平不僅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狀態,還能夠幫助患者重新獲得良好的睡眠[8]。
2.2 呼吸系統 研究發現,抑郁癥與呼吸系統疾病密切相關,不僅表現為呼吸系統疾病常可并發抑郁癥,而且抑郁癥的嚴重程度也在影響著呼吸系統疾病的預后與轉歸,為臨床診治帶來一定難度[9]。其原因不僅在于肺部疾病較為痛苦且纏綿難愈,為患者帶來心理壓力和經濟上的負擔,而且具有一定的分子理論基礎。例如,老年常見慢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已被多項研究證實與抑郁癥存在并發關系。COPD患者肺組織產生大量炎性因子如IL-8、IL-6、TNF-α等,不僅能夠激發炎癥反應,促使氣道發生改變,而且能夠穿過血腦屏障作用于神經系統,影響神經遞質的釋放及情緒調節失常,從而導致抑郁狀態[10]。COPD患者血清及肺泡灌洗液中IL-6水平較高,而IL-6的升高容易導致抑郁癥已得到多項實驗結果的證實。COPD并發抑郁癥人群中大多數有吸煙史或煙草暴露史,這可能與煙霧產生的尼古丁不僅能引起氣道上皮組織病變,而且能夠引起神經細胞炎癥反應有關[11]。也有研究發現,COPD患者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活性下降,導致血清皮質酮含量升高,而動物實驗發現,靜脈注射皮質酮會加重抑郁模型動物的抑郁癥狀,這表明呼吸系統疾病與抑郁癥之間也可能是通過HPA軸相互影響的[12]。
2.3 循環系統 抑郁癥患者常有自主神經功能紊亂,表現為交感神經異常興奮和副交感神經抑制現象。交感神經興奮性持續增高,血中兒茶酚胺含量增加,成為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循環系統疾病的危險因素。且動物實驗證明,抑郁模型大鼠左心室擴大,心室壁變薄,提示抑郁癥可以通過改變心室結構而引起心臟相關疾病[13]。抑郁癥患者HPA軸的異常能夠導致糖皮質激素等正性激素的釋放增加,從而導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縮力增強,心肌耗氧量增加,增加心臟前后負荷,提高心肌梗死、冠心病及高血壓等疾病的患病風險[14]。炎癥介質參與了抑郁癥病程的發生與進展,抑郁癥患者體內炎癥因子水平常呈失衡狀態,而過度敏感的炎癥反應也能夠導致血管內皮損傷,增加動脈粥樣硬化的患病風險[15]。此外,有研究證實,抑郁癥患者血小板活性增加,聚集力增強也是導致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之一。5-HT不僅存在于神經突觸之間,而且在血小板中也有較高含量,其作為神經遞質和血管活性物質不僅參與了神經沖動的傳導,而且參與了血小板凝血功能的發生。抑郁癥患者5-HT系統紊亂,如血小板5-HT2結合力增強等,能夠提高血小板聚集性,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16]。
2.4 消化系統 抑郁癥患者常伴有胃腸功能障礙,如胃食管反流病(GERD)、功能性消化不良(FD)、腸易激綜合征(IBS)和胃潰瘍等。很多抑郁癥患者常以胃腸道癥狀為首要原因去醫院就診,而對難治性胃腸疾病患者進行抑郁量表評估時發現,處于抑郁狀態者超半數以上,這提示我們抑郁癥對消化系統的功能有較大影響[17]。近年來,腦腸軸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漸漸認識到很多疾病的發展與轉歸都有腦腸軸的參與。腦腸軸是將腦神經與腸神經聯結在一起的神經網絡系統,溝通著情感中樞和胃腸感覺與功能以及內分泌免疫功能。腦腸肽作為神經遞質和胃腸激素在神經系統和胃腸道均有較為廣泛的分布,它由腦腸軸分泌并深刻影響其功能,主要包括胃泌素(GAS)、胃動素(MTL)、血管活性腸肽(VIP)和生長抑素(SS)等。研究顯示,抑郁癥患者血清MTL含量明顯下降;抑郁模型大鼠血清GAS、MTL含量下降,而SS含量升高,腦腸肽水平整體呈失衡狀態,而腦腸肽水平異常則會引起多種消化系統疾病[18]。眾所周知,腸道菌群對胃腸道功能有重要的調節作用。而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腸道菌群對宿主的應激反應、認知功能和抑郁情緒也有影響[19]。抑郁癥患者常有腸道微生態失衡的表現,如擬桿菌門、梭桿菌門增多,厚壁菌門降低等。此外,導致抑郁癥的主要原因5-HT降低也參與了消化系統疾病的發生[20]。5-HT作為神經遞質不僅廣泛存在于中樞神經系統,而且在腸神經系統中也有較高的含量。5-HT含量降低不僅能夠導致情緒調節障礙,引發抑郁癥狀,還能夠導致胃腸平滑肌收縮舒張失調,引起一系列胃腸道癥狀。
2.5 泌尿生殖系統 臨床診療中不難發現,很多抑郁癥患者伴有尿頻、尿急或漏尿的癥狀,最常見于老年女性,考慮與膀胱過度活動癥(OAB)有關。抑郁癥與OAB二者通常互為因果,抑郁癥患者因尿頻或漏尿的尷尬狀況減少社交,以致加重病情;OAB因患者態度消極,情緒低落而更加難以治愈。有學者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前額葉皮質(PFC)功能異常,削弱了其對應激時抑郁狀態發生的抑制作用,導致HPA軸過度激活,促使抑郁癥的發生[11]。另外,動物實驗表明,抑郁模型小鼠的PFC蛋白肌酸激酶B(CKB)等異常升高,提示抑郁模型小鼠的PFC能量代謝紊亂[21]。PFC對于泌尿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曾有學者對皮質額葉變性伴漏尿患者進行斷層掃描時發現[22],其葡萄糖相對代謝率(rCMRglc)顯著降低,提示PFC區能量代謝有下降趨勢。動物實驗發現,抑郁癥伴OAB大鼠PFC區CKB顯著升高。這些結果均證明了抑郁癥對泌尿系統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PFC區實現的[23]。
睪酮和雌二醇是人體重要的性激素,對男性和女性的生長發育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血清睪酮和雌二醇含量低于正常,其水平與抑郁程度呈負相關[24],而給予相關制劑治療則會使抑郁狀態明顯減輕[25]。其抗抑郁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但考慮與促進神經元修復生長和影響神經遞質的釋放有關[26]。另外,無論是因為抑郁本身較為沮喪的心態,還是抗抑郁藥物的不良反應,抑郁癥患者常伴有性功能減退的癥狀,影響家庭生活和諧,增加患者心理壓力而導致抑郁癥更加反復難以治愈[27]。抑郁癥伴性功能減退可能與抑郁癥患者中腦邊緣系統功能紊亂難以喚醒性欲和DA分泌失常難以獲得快感和高潮有關[28]。
2.6 運動系統 有數據統計顯示,大部分抑郁癥患者的骨密度(BMD)低于正常水平,常伴有骨質疏松癥;而在骨科就診的脆性骨折患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伴有抑郁癥狀,這提示我們抑郁癥也是導致骨密度降低發生骨折的危險因素。有學者對抑郁癥患者左側的股骨頸、股骨大轉子和Ward三角進行BMD測定,發現各部位BMD均低于正常,且女性更加低于男性,BMD水平與抑郁程度及病程呈負相關[29]。其原因可能為:抑郁癥患者睪酮和雌二醇等性激素含量下降,而二者直接參與了骨的形成和抑制破骨細胞的功能;HPA軸紊亂導致糖皮質激素釋放增加,抑制成骨細胞形成并促進骨細胞凋亡;抑郁癥患者瘦素(LEP)水平降低,而LEP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成骨細胞,促進其分化,而且可以作用于中樞神經和性腺,間接影響骨的形成[30]。此外,骨鈣素的表達也參與了抑郁癥的發展進程。動物實驗結果顯示,抑郁模型小鼠骨鈣素表達明顯降低,給予完全羧化骨鈣素后小鼠的抑郁樣行為快速逆轉,表明抑郁癥患者骨鈣素含量降低,而完全羧化骨鈣素卻有快速抗抑郁的作用[31]。
2.7 免疫系統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發現抑郁癥的發生發展與免疫炎癥反應的發生具有同步性,提示抑郁癥與免疫系統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的關系。大量臨床實驗表明,IL-1、IL-6、TNF-α、CRP等炎癥因子的激活是影響抑郁癥病程進展的關鍵因素。在重度抑郁患者體內和因抑郁而死亡患者的腦部標本中發現,炎性標志物明顯高于輕度抑郁患者和健康人群,而重度抑郁患者的炎性反應較輕度抑郁患者更加明顯,炎性表現更為突[32]。研究發現,炎癥因子對單胺類突觸的影響可能是發生抑郁情緒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干擾素、IL-1β和TNF等通過激活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降低四氫生物蝶呤(BH4)等輔酶水平,減少單胺類神經遞質如5-HT、DA和NE等的合成,而單胺類神經遞質在神經系統進行情緒調節時的作用不可或缺[33]。炎癥因子還能夠引起谷氨酸過量釋放,從而導致BDNF釋放下降;還可以干擾神經元的生長和修復,導致不可逆性損傷,最終影響患者的學習記憶能力和情緒調節能力[34]。由免疫細胞介導的炎癥反應也深刻影響著患者的抑郁情緒。動物實驗表明,調節性T細胞具有減輕炎癥反應,保護神經元免受損傷的作用,可降低實驗動物抑郁發生率[35]。而T細胞和白細胞活性下降,身體防御能力降低,會導致機體在遭受壓力及不良刺激后機體防御系統紊亂,情緒調節能力降低,這可能是抑郁癥發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臨床治療中,以炎癥因子為靶點的針對性治療能夠明顯改善患者的抑郁狀態,這更加證實了免疫炎癥反應與抑郁癥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36]。
3 小結
全球抑郁癥發病率正呈逐年上升趨勢,不僅摧殘人類的身心健康,且嚴重危及生命,已成為全球青年人自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其治療率低、復發率高,更容易導致患者失去治療的信心,情緒更加低落,造成惡性循環。大量實驗研究表明,抑郁癥的發生與全身各系統機能息息相關,抑郁癥與其他系統疾病的發生發展更是相互影響。在臨床診療中,把握整體觀念,跳出局限思維,從整個機體出發制定相應的診療方案,可能會收獲令人滿意的療效。
參考文獻
[1]常軍,章明星.抑郁癥的發病機制及治療研究進展[A].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身醫學專業委員會.第六屆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身醫學專業委員會換屆大會暨第十二次中國中西醫結合心身醫學學術交流會論文集[C].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身醫學專業委員會: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2019:21.
[2]劉少博,令狐婷,高耀,等.線粒體能量代謝障礙在抑郁癥發病機制中的關鍵作用[J].藥學學報,2020,55(2):195-200.
[3]劉諾,王真真,陳乃宏.水通道蛋白4參與抑郁癥發病機制研究進展[A].中國藥理學會.中國藥理學會第十五次全國學術大會論文摘要[C].中國藥理學會:中國藥理學會,2019:1.
[4]逄鋒.男性抑郁癥患者初級運動皮層可塑性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7.
[5]黃朝陽,詹淑琴,李寧,等.抑郁癥患者中樞感覺神經系統興奮性的變化研究[J].中國醫刊,2019,37(7):730-734.
[6] TIKàSZ A,TOURJMAN V,CHALAYE P,et al.Increased spinal pain sensitiz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A pilot study[J].Psychiatry Res,2016(246):756-761.
[7]王艷艷,黃莉莉,王鳳玲,等.多巴胺能神經系統在抑郁癥睡眠障礙中的作用[J/OL].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9,19(46):67-68,71.
[8]孫延娜,荊秦,李陽,等.滋陰養血安神方對失眠小鼠腦內多巴胺含量影響[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9,21(3):37-40.
[9]黃慶暉,胡銳寧,袁良.呼吸系統疾病并發抑郁癥的分子機制研究進展[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20,41(6):739-742,763.
[10] BARCZOK M.COPD—smoking is not the only risk factor[J].MMW Fortschr Med,2019,161(13):66-68.
[11] MATTE D L,PIZZICHINI M,HOEPERS A,et al.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COPD: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ntrolled studies[J].Respiratory medicine,2016:154-161.
[12] SKOLUDA N,STRAHLER J,SCHLOTZ W,et al.
Intra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acute laboratory stressors of different intensity[J].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5,51:227-236.
[13]李闖,石少波,楊波.抑郁癥和冠心病共病的機制及治療[J].醫學綜述,2020,26(18):3638-3642.
[14] HEADRICK J P,PEART J N,BUDIONO B P,et al.The heartbreak of depression:Psycho-cardiaccoupling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J].J Mol Cell Cardiol,2017,106:14-28.
[15] VACCARINO V,BADIMON L,BREMNER J D,et al.
Depress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2018 ESC position paper of the working group of coronary pathophysiology and microcirculation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ESC Committee for Practice Guidelines[J].Eur Heart J,2020,41(17):1696.
[16]王訓強,樓忠澤,張慶玉,等.血小板功能在抑郁癥與心血管疾病間作用的研究進展[J].浙江醫學,2016,38(6):440-442.
[17]杜曉娜,施學麗.抑郁癥伴功能性胃腸疾病發病機制研究進展[J].廣西醫學,2018,40(13):1469-1471.
[18]張濤,令狐婷,張瀟,等.抑郁癥共病胃腸疾病的神經生物學機制研究進展[J].生理學報,2018,70(1):71-78.
[19]田祖宏,聶勇戰.腸道微生物與腦-腸軸交互作用的研究進展[J].傳染病信息,2016,29(5):302-307.
[20]王深皓,董蕾,李路,等.5-HT4受體激動劑對腸易激綜合征患者消化間期運動及胃腸激素的影響[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4,35(2):254-257.
[21] WANG Z,LI W,CHEN J,et al.Proteomic analysis reveals energy metabolic dysfunction and neurogenesis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of a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mouse model of depression[J].Mol Med Rep,2016,13(2):1813-1820.
[22] PERNECZKY R,DIEHL-SCHMID J,F?RSTL H,et al.
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its functional anatomy in 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s[J].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2008,35(3):605-610.
[23]郝倩.大鼠膀胱過度活動癥和情緒障礙的關系及相關機制的研究[D].太原:山西醫科大學,2020.
[24]張巖,曹江,徐偉杰,等.老年首發抑郁癥患者臨床特點及認知功能受損程度與性激素水平的變化[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8,38(8):1894-1896.
[25]惠凌云,王亞文,張琳,等.血清睪酮水平與圍絕經期抑郁癥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婦幼衛生雜志,2016,7(4):1-4.
[26] MATTE D L,PIZZICHINI M M,HOEPERS A T,et al.
Hoepers,et al.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COPD: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ntrolled studies[J].Respiratory Medicine,2016,117:154-161.
[27]王肇軼.丁螺環酮對女性抑郁癥患者抑郁癥狀及性功能的作用探討[J].中國實用醫藥,2019,14(4):131-132.
[28]顧鳳華,張文躍,宋義勇,等.安非他酮與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對首發女性抑郁癥患者性功能的影響[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2019,29(3):201-203.
[29]許俊亭,謝守付.抑郁癥患者骨密度變化的臨床分析[J].中國醫藥指南,2017,15(36):7-8.
[30]關子易,薩日,劉丹妍.骨密度測定在青春期抑郁癥中的應用價值及進展[J].中國婦幼保健,2019,34(8):1930-1932.
[31]周嬋娟.骨鈣素與抑郁癥臨床及機制的初步研究[D].重慶:重慶醫科大學,2016.
[32] CHEN M H,LI C T,LIN W C,et al.Rapid inflammation modulation and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of a low-dose ketamine infusion in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A randomized,double-blind control study[J].Psychiatry Res,2018,269:207-211.
[33] MAES M,LEONARD B E,MYINT A M,et al.The new’5-HT’hypothesis of depression:cell-mediated immune activation induces 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which leads to lower plasma tryptophan and an increased synthesis of detrimental tryptophan catabolites(TRYCATs),both of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onset of depression[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1,35(3):702-771.
[34] STEINER J,WALTER M,GOS T,et al.Severe de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icroglial quinolinic acid in subregions of the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evidence for an immune-modulated glutamatergic neurotransmission?[J].J Neuroinflammation,2011,8:94.
[35] KIM S J,LEE H,LEE G,et al.CD4+CD25+ regulatory T cell depletion modulat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mice[J/OL].PLoS One,2012,7(7):e42054.
[36]黃曉幸,夏尊恩.免疫炎癥反應在抑郁癥中作用的研究進展[J].微循環學雜志,2020,30(4):78-81.
(收稿日期:2021-03-22) (本文編輯:田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