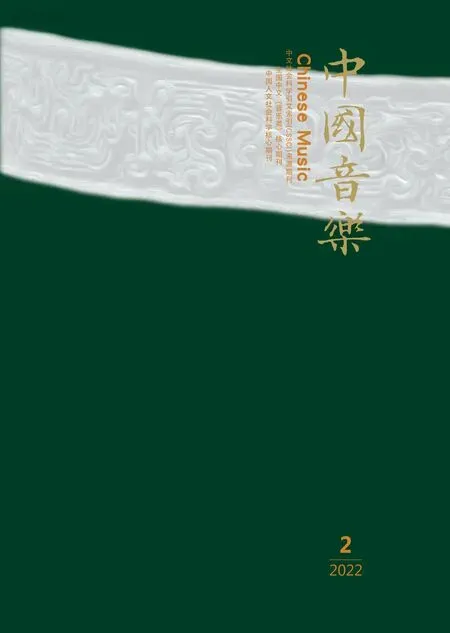摹寫·建構·復原
——音樂影像文本的生產方式與真實性
○ 劉桂騰
根據研究者與田野對象之間的關系及影像文本中主客觀因素的構成,可將音樂影像志知識生產分為摹寫、建構和復原三種基本方式。摹寫,是取觀察式民族志視角,由調查人主導、以“臨摹”方法書寫的一種“作壁觀世相”①語出“壁上觀世相”。黎小鋒:《壁上觀世相—“直接電影”在中國的嬗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43-47頁。該文修改于2018年2月,轉載于《電影作者》內部資料,2018年,第18輯。影像文本;建構,是取參與式民族志視角,由導演主導、以“創作”方法書寫的一種“真實的虛構”影像文本;復原,是取參與式民族志視角,由導演或調查人主導的一種“非虛構的搬演”影像文本。簡言之,摹寫是“臨摹”,建構是“創作”,復原是“搬演”。
作壁觀世相:摹寫法
創立了“電影眼”流派(cine-/kino-eye)的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1896—1954),用“移動的眼睛”將觀眾帶入現實世界并領略了民族志紀錄片的紀實美學魅力,對后來的觀察式民族志紀錄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紀錄片史中的“直接電影”和“真實電影”流派,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了“電影眼”理論的影響。1929年首映的《持攝影機的人》這部民族志紀錄片經典(見圖1),以“維爾托夫之眼”觀察并記錄了蘇聯烏克蘭敖德薩市普通人從早到晚的日常生計與行為。維爾托夫鐘情于“移動拍攝”的動機來源于他對紀錄片真實性的忠誠與信仰:“應是忠實、坦誠地展現他們的生活,記錄他們的思想,不虛假,不矯揉造作。”②〔法〕讓·魯什:《攝影機和人》,蔡家麒譯,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麒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9;79頁。如果你真的認真看了《持攝影機的人》,就會讀出被后現代新銳們質疑的“電影眼”里的真實性是多么難以撼動!難怪讓·魯什(Jean Rouch,1917—2004)感慨不已:“多少年之后,今天的一切電影技術、民族志電影、探索性影片以及我們今天用的‘逼真的拍攝’(living cameras)方面所碰到的一切問題,都在這些激昂的陳述中找到了解釋”③〔法〕讓·魯什:《攝影機和人》,蔡家麒譯,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麒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9;79頁。。維爾托夫在《持攝影機的人》片頭就開宗明義:“沒有字幕、沒有劇本、沒有布景和演員,這部試驗性作品旨在創造一種剝離于戲劇與文學的電影語言。”什么是“剝離于戲劇與文學的電影語言”?非虛構也。

圖1 《持攝影機的人》,吉加·維爾托夫,1929年
在攝制過程中,維爾托夫把拍攝行為也并入了電影“事件”,似乎是作為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把事件片段連接了起來。他在證明事件的真實性—持攝影機的人成為事件的見證人。但與魯什的“真實電影”不同,《持攝影機的人》的拍攝者并不與被攝對象進行互動,而是作為旁觀的記錄者入畫。作為一部“電影眼”理論實踐的經典作品,維爾托夫主張:“我是電影眼,我是機器眼;我以機器所特有的方式向你們展示這個世界。”④同注②,第79;79、86頁。這樣,攝像機就成了拍攝者身體的一部分:
我看(我用攝像機看)
我寫(我用攝像機記錄)
我組織(我編輯)⑤同注②,第79;79、86頁。
我觀察、我拍攝和我剪輯之“我”—人機合一,是非虛構民族志影像文本理想的書寫方式。對音樂影像志的田野作業來說,人機合一能夠使無生命的“機器眼”具有調查人的思維洞察力—鏡頭是學者的眼睛。⑥劉桂騰:《鏡頭是學者的眼睛—音樂影像志范疇與方法探索》,《中國音樂》,2020年,第2期,第12-22頁。雖然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人機合一,但它應該是民族志紀錄片拍攝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20世紀60年代紀錄電影形成了兩個重要的流派:濫觴于美國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和發軔于法國的“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這個局面,既推動了紀錄電影事業的發展,同時又給紀錄電影的“真實”打上了問號。“直接電影”是什么?是否有足夠的理由將其視為一個具有理論形態的概念?對此,電影史理論家們至今沒有達成共識。評論家與電影人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即使被冠以“直接電影”大師之名的當事人,有的也不以為然,如被譽為“直接電影”大師的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就從來未接受這頂桂冠。而“直接電影”的先驅者艾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1926—2015)則旗幟鮮明地在他個人網站上宣示:
1.遠離觀點;
2.愛你的被攝對象;
3.記錄事件、場景、過程,避免采訪、解說、主持;
4.與天才一起工作;
5.非搬演(unstaged),不控制(uncontrolled);
6.在現實和真理之間存在關聯。對二者都保持忠誠。⑦黎小鋒:《壁上觀世相—“直接電影”在中國的嬗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43-47頁。該文修改于2018年2月,轉載于《電影作者》,內部資料,2018年,第18輯,第121;121、124頁。
“直接電影”流派深受維爾托夫記錄電影風格的影響。其后期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不介入,不控制,如蒼蠅作壁上觀……”⑧黎小鋒:《壁上觀世相—“直接電影”在中國的嬗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43-47頁。該文修改于2018年2月,轉載于《電影作者》,內部資料,2018年,第18輯,第121;121、124頁。對此,雖然票房大多時并不買賬,但這種紀實美學風格還是吸引了眾多青睞“自然而然”紀錄片風格的追隨者。艾伯特·梅索斯晚年時曾語重心長地對青年紀錄片導演們說:“你不用控制現場,故事會自己呈現。……電影會自己向我講述生活故事。”⑨張同道、李勁穎:《直接電影是紀錄片最好的方式—阿爾伯特·梅索斯訪談》,《電影作者》,內部資料,2018年,第18輯,第20頁。我在想,如果我們的音樂影像志能夠放松下來—丟棄功利心來拍一部梅索斯式的片子該有多么愜意!現實是,“直接電影”的真實性主張只是在民族志電影理論之弦的一端震顫,卻從未達到真正的滿弦共鳴。有些人(包括專業的電影人)對“直接電影”的真實性不以為然,而“直接電影”的靈光卻一直在堅持以真實性為底線的民族志紀錄片作品中閃爍不已。作壁觀世相方法,是“直接電影”理念的精神棲息地。雖然不能將“直接電影”呈現的事實視為絕對客觀,但其努力追求民族志紀錄片真實性的理念是不容置疑的。應當承認,即使不介入、不控制—“如蒼蠅作壁上觀”也不意味著那里絕對沒有拍攝者的主觀性滲透其中。鑒此,我將“電影眼”和“直接電影”流派的民族志影像文本視為一種“摹寫”出來的事實。
對一個音樂現象的摹寫,猶如書法之“臨摹”—以逼真為要。盡管摹寫的音樂影像志知識不是事實本身,但它必須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實真相。摹寫出來的音樂現象,該是化妝鏡而非哈哈鏡之映像。所以,真實性是音樂影像志的立身之本。通過鏡頭所觀察、記錄的影像,是一個事實的映像—對事實的摹寫而非事實本身;并且,無論多么事無巨細,摹本都不可能囊括原本的全部;再經過案頭的非編,摹本中又融入了寫者更多的主觀因素。所以,把民族志影像文本視為事實的摹寫,就是承認寫者主觀因素的存在。這是當代民族志與傳統民族志在影像文本真實性問題認知上的理論分野。但是,這并不表明據此就可以任由主觀性的無限膨脹、任意揮發。摹寫,意味著必得縮小摹本與原本之間的距離,須要摹得更像—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實真相;并且,摹寫法還可有效避免文化主體權利關系的混淆:我在“摹寫”他者文化。
那么,究竟該如何理解民族志書寫的“真實”呢?沒有絕對的真實,但存在相對的客觀。摹寫的事實應該具有民族志知識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由生活的事實、學術的事實和審美的事實所構成。
生活的事實
所謂“生活的事實”,是指現實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即在文化持有人中流傳并真實存在的生活事件。“真實存在”,是指音樂現象的構成要素(時間、地點和人物)具有可驗證性。亦即事件的對象、地點和時序是非虛構的事實。在對象的選擇上,應該是現實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音樂事件,拒絕假非遺、偽民俗;在場所的選擇上,不能根據拍攝者的審美訴求而改變事件的空間關系。譬如,把音樂行為發生的特定生活場景置換為更為“好看”風景背景中;在時間的選擇上,保持事件發生和進程的時序,特別是那些具有周期性循環規律的節慶活動、民間信俗儀式,不能以拍攝方的時間、經費和氣候條件等因素而改變。時下流行的一些所謂的“傳統”之所以被目為假非遺、偽民俗,就是因為它們并非真的存在于現實生活之中,因而不具備生活的可驗證性。
學術的事實
學術的事實,是民族志書寫者的描述與闡釋。它以研究者(調查人)親身參加的田野調查為前置條件,是一種符合“生活的真實”要件并由研究者采錄、呈現出來的田野事實。由于“學術的事實”里也會帶入研究者的主觀因素,所以,田野人應該具備相應的學科訓練和符合田野倫理的職業操守,不能任意擺布田野對象,不能以“共謀”之名編造事實;尤其是田野作業拍攝的環節中,不能預設、操控田野事件發展的進程:
人類學家和觀察性電影制作人對參與觀察二者的重視程度都會有所不同,但不管如何融會二者,都有一個共識,即必須通過逐漸發現的進程,也即通過參與關心對象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把他們置于預先設定的模型中來獲得一種認識,不管這種預先設置的模型是電影制作人的腳本還是人類學家的調查表。⑩〔英〕保羅·休利:《民族志電影:技術、實踐和人類學理論》,呂卓紅譯,載莊孔韶主編:《人類學經典導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83頁。
調查人的田野行動,或多或少、自覺或不自覺都要受到本己文化觀念的影響。因為,調查人與文化持有者往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在那里,不同族群、性別、年齡、習俗和宗教信仰,以及裝束、工具、言談舉止等因素相互作用,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干擾和影響是難以避免的;并且,在最終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調查人往往使用本己文化的語言描述和闡釋異己文化中人們的行為。但是,調查人不能使用一個“預先設定的模式”來進行田野作業。
“預先設定模式”的形成,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音樂詮釋影響的結果。如大量經過“民族”型塑、審美提純以及商業化構建出來的族群音樂,通過公共媒介(演藝、廣播、電影、電視、大眾傳媒、音樂出版、印刷等)和專業音樂教育而成為“經典”。同時,那些因強化分類而形成的音樂知識體系也在影響著研究者的文化認知。于是,族群音樂中某些固化了的旋律、節奏等形態特征成了音樂審美判斷的標識,進而,成為“預先設定模式”的音樂觀念基礎。當“經典”成為一種辨識音樂文化的眼鏡,就產生了“他者凝視”效應:研究者在田野中有意無意地將這些“標識”投射到客體,而對象也從“他者凝視”中也看到了“自己”并自覺不自覺地迎合之。
2004年8月,我第四次踏上了科爾沁沙地。不巧,色仁欽薩滿外出行博不在家。我們追蹤到了庫倫旗的鄂勒順蘇木,準備一起返回色仁欽家—左翼中旗腰林毛都蘇木南塔嘎查。當我們行至舍伯吐的三岔口時,面臨一個選擇:向左走是珠日河,一個有奔馬和蒙古包的草原文化旅游區;往右走是腰林毛都,是一個居于沙地、楊樹林中的嫩科爾沁蒙古人的土坯房聚落。我選擇了向左—舍伯吐三岔口的這個一念之差,使我們來到了珠日河旅游區。我第一次見到了真正的草原:藍天白云、草原上的奔馬……當晚,就在這個“預設”的場景中心滿意足地展開了我的田野作業。
在田野現場,我有意安排了在牧場的氈房里進行采錄。這是一個“預先設定模式”,也就是說,從現場的一度作業(采集)中便是按照自己對那個文化的想象來搜集甚至制造“證據”。回到案頭,我將當年采錄的田野數據進行了整理,剪出了關于嫩科爾沁蒙古薩滿儀式音樂考察的第一部短片《離離原上草》(見圖2)。在非編中,我任意發揮著對“蒙古音樂”浪漫的田野想象,而這些想象則來源于被定義了的那些蒙古音樂“經典”。為了更加符合我的“蒙古音樂”想象,影片中,大量運用蒙古族典型的文化符號(草原、氈房、跑馬等)為背景,使用“標識”性的蒙古族音樂配樂(傳統馬頭琴音樂、騰格爾的創作音樂等)。在剪輯中,還特意剪掉了那些帶有當代元素的畫面。這個由“預先設定模式”制作的蒙古薩滿儀式音樂,是按照我對嫩科爾沁蒙古人生活方式的想象生產出來的。而當時真實的生活場景,卻是農耕、土坯房、沙地和楊樹林。

圖2 《離離原上草》,劉桂騰,2004年
2017年,我將當年采錄的田野數據重新進行了整理,又剪出了關于嫩科爾沁蒙古薩滿儀式音樂考察的第二部短片《絕響:色仁欽的塔拉亨格日各》。經過反思,為盡量克服“他者凝視”出來的東西,我剔除了那些特意安排的背景鏡頭(草原、蒙古包、跑馬等),放棄了典型化的蒙古族音樂配樂,并把被舍棄的一些具有當代生活元素的素材(如毛澤東畫像等)重新加以使用(見圖3)。

圖3 《絕響:色仁欽的塔拉亨格日各》,劉桂騰,2017年
同樣的素材,不同的理念,其結果大不相同。盡管片子呈現中依然有其不可避免的主觀因素,但還是糾正了由于違背“學術的真實”原則,放任因“他者凝視”而產生的造假問題,以及對文化權利人的不尊重甚至侵害的問題。所以,實現“學術的真實”,要求音樂人類學家必須自律,并有堅守音樂影像志真實性底線的理論自覺。
審美的事實
有時,音樂影像志成果也需要與普通觀眾分享—作為因應觀眾審美需求而產生的公共文化知識。因此,音樂影像志也不必完全排斥審美因素。但音樂影像志影片是從田野事實中產生出來并提供給公眾的一種民族志知識。音樂影像志的美學價值依然是要遵循“真實性”原則,以滿足人們對族群風習、社區音樂現象等人文景觀的好奇心、探索欲,以及對事實真相的渴求。
關于民族志紀錄片究竟是“學術的”還是“藝術的”—學術性與審美旨趣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個困擾電影理論家和影視人類學學者的問題,吵吵嚷嚷之中,至今亦無共識。影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里高利·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晚年的一次激辯,就是個典型的案例。這對影視人類學夫妻檔,他們最有名的影視人類學實踐成果是20世紀30年代后期在巴厘島的田野調查。其后,他們出版了《巴厘人的性格:一項攝影研究》(1942年)一書。這對搭檔最后為什么分道揚鑣不是我們的興趣點,而他們在視覺人類學上的學術理念分歧卻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民族志紀錄片的藝術屬性和科學價值。民族志紀錄片究竟是“藝術的”還是“學術的”?米德和貝特森的這場爭論,既是對民族志紀錄片屬性的反思,也反映了20世紀中葉以降影視人類學的時代風向。當貝特森回答為什么不喜歡使用三腳架時,直言影像紀錄應當是一門藝術。而米德則仍然堅持民族志紀錄片的學術性:一位藝術家能夠把他認為存在的東西呈現得十分漂亮,但你就無法對這些資料展開后續的任何分析了。米德批評“藝術論”者:“他們往往在追求藝術制作時忽略了對情節的忠實。這種過分的要求一直占據著電影界。而與此同時,很多文化沒有得到記錄便消亡了。”?〔美〕瑪格麗特·米德:《文字訓練中的影視人類學》,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麒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頁。她的“學術論”主張及其田野實踐有一個鮮明的學術指向—民族志影像文本是一種文化的“客觀記錄”。“學術論”和“藝術論”爭鳴的實質在于民族志紀錄片的客觀性。今天看來,雖然瑪格麗特·米德將民族志影像記錄視野定格為“正在消失的行為類型”有些狹隘,卻也道出了“客觀記錄”的文化典籍價值。與此同時,米德還指出了這種“客觀記錄”對于比較研究的重大意義。民族志的根基在其“志”上。志者,記也。因此,拋棄了“記錄”屬性的影片就不是民族志紀錄片。當然,民族志知識的傳播與闡釋可以有多元化的路徑,但其“客觀記錄”的基點不能動搖。其實,即使那些致力于超越科學證據功能的情感體驗的優秀影像文本,也是建立在“客觀記錄”的基礎之上,具有鮮明的紀錄美學風格特征。
真實的虛構:建構法
“你幸福嗎”?
如今,這個紀錄片經典的設問形式已經是個再尋常不過的訪談模式。而半個世紀前當“魯什之問”首現紀錄片中時(見圖4),?埃米莉·德·布里加德在《民族志電影史》中評論道:“在某種意義,魯什和莫蘭在1960年完成的拍攝的《夏日紀事》成了《美洲虎》拍攝過程的濃縮:略去了拍攝前的劇情表演設計,略去了拍攝后與演員的對話和解說詞的錄音。借助于Eclair攝像機、Nagra錄音機和‘你快樂嗎?’等問題,《夏日紀事》的人物在現場拍攝中被塑造了出來。”其中,采訪人的設問“你快樂嗎?”,就是我所說的“魯什之問”。埃米莉·德·布里加德:《民族志電影史》,楊靜、楊昆譯,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麒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第35頁。或許還沒人意識到它對后來紀錄片形式的影響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雖然“介入式”的紀錄片拍攝方式在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J.Flaherty,1884—1951)的《北方的納努克》中早已初露倪端,但讓·魯什明確主張并實施了將作者介入事件進程之中,這意味著“真實的虛構”成了參與式民族志紀錄片拍攝的新范式。從而,催生了“真實電影”流派的誕生并影響了一代民族志紀錄片的發展路向。
作為“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理論的代表性人物,魯什曾有人類學的學術背景,這就使他的電影觀察視角、拍攝方法和影像表達方式都具有民族志色彩。魯什的“介入事件”主張,也使紀錄片對社會事件的冷靜旁觀也多少沾染了政論式宣示真理的味道。《夏日紀事》誕生時的法國正處于與阿爾及利亞脫離屬地關系的陣痛中,魯什從文化沖突的角度反映了非洲移民在法國都市的文化差異問題。這種介入式的帶著政治意圖的文化接觸,顯然打破了傳統紀錄片強調價值中立和“客觀記錄”的要求。所以,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指出“真實電影”中蘊含著文化接觸并具有政治性功能。這是很中肯的評論。?埃米莉·德·布里加德:《民族志電影史》,楊靜、楊昆譯,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麒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第36頁。魯什在給民族志紀錄片帶來了新鮮感的同時,也帶來了至今仍然爭論不休的民族志紀錄片是否應該“虛構”和“介入”的問題。(見圖4)了弗拉哈迪的“參與”觀察,將前輩在拍攝現場的實戰經驗創造性地融合起來,納入了紀錄片理論的工具囊中。最具創新精神的是,魯什在《夏日紀事》(1961年)等一系列試驗性電影中將“虛構”引入了紀錄片,從而開創了“參與式”紀錄電影的先河。魯什把紀錄片與故事片的元素結合起來,力圖使電影成為人們真實生活的紀錄。這就產生了虛構。其目的,是為了追求一種更為強烈的“生活真實”。他首創了紀錄片的“訪談”模式,導演和采訪人等都入畫了—我們拍的,我們見證了事件的發生。拍攝者在場以及拍攝活動過程入畫,把拍攝活動并入電影“事件”,這在杰·魯比看來“有助于證實人類學研究結果的真實性”?〔丹麥〕彼特·伊恩·克勞福德、〔英〕大衛·特頓主編:《民族志電影》,高輝、郝躍駿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3頁。。

圖4 《夏日紀事》,讓·魯什,1961年
“直接電影”和“真實電影”流派以及大量的民族志紀錄片實踐者(諸如羅伯特·弗拉哈迪、吉加·維爾托夫和讓·魯什等)留下的紀錄片實踐和理論遺產,被電影理論家和評論家們總結為“觀察式”和“參與式”兩種民族志紀錄片創作方式。注意,民族志書寫的語境里“創作”一詞并非文學、戲劇意義上的那種“虛構”,而是一種必須遵守民族志真實性原則的作業方式。要謹慎使用“創作”一詞,因為它的常規意義會擾亂人們的視線,使人將其與文學、戲劇意義上的“虛構”等同起來。
真實與虛構,一直是民族志紀錄片理論紛爭中的焦點。事件,或真或假;而事實,則是一個真實
魯什堅守了維爾托夫的“移動拍攝”,又借鑒存在的事件;虛構的事件不是真實的存在,所以虛構的事件不是事實。但是,虛構的事件可能具有民族志意義上的某種“真實性”。譬如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件、回憶的事件等。這種虛構建立在事實的基本面上,事件中的人物是真實存在的。有的民族志作品為避某種忌諱而使用假名,但他依然是個真實存在的人物而非藝術創作中的所謂“人物原型”。以《夏日紀事》為例,“在魯什看來,《夏日紀事》絕不僅僅是一部紀錄片,因為影片中的人們都被激發表現出了他們的虛構部分;同時,它又絕不僅僅是一部故事片,因為它所展現的虛構部分是真實的”?鄧衛榮、劉靜:《影視人類學—思想與實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頁。。所以,民族志紀錄片并不完全排斥“虛構”,但這種虛構的事件應該是一種“真實的虛構”。
后現代思潮的新銳們把民族志視為一種“文化建構”?文化建構:“‘民族志’不是一個絕對的詞語,也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東西(今天人類學者做的許多事情,我們的先輩們不會認為屬于人類學的一部分或者甚至從未考慮過),而是一種文化建構,一種產生人類學學科的社會類型的產品。”馬庫斯·班克斯:《哪些電影是民族志電影?》,載〔丹麥〕彼特·伊恩·克勞福德、〔英〕大衛·特頓主編:《民族志電影》,高輝、郝躍駿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0頁。。這個頗具叛逆精神的理論揭開了民族志自命“客觀”的面紗,似乎擺脫了“真實”原則這個民族志紀錄片的符咒。與此同時,建構論也帶來了一場民族志的表述危機。人類學早期對影像手段的青睞,是看重影像文本的記錄功能。標榜民族志“客觀真實”的經典人類學時代,人們相信影像文本是以其“客觀真實”而優于文字文本。而今,已經沒有多少人會“像哈登、斯賓塞和博厄斯那樣,相信攝影機的價值在于它是一種客觀的圖像資料的記錄手段。一個世紀之后,絕大多數人類學家發現這個信念太過天真”?同注⑩,第578頁。。也就是說,盡管民族志書寫的客觀真實依然是其基本原則,但幾乎已經沒有人類學家再標榜這個“客觀真實”多么純粹,音樂影像志也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問題是,如今,虛構式民族志紀錄片走得越來越遠了。雖然有人聲稱這是與文化當事人“共謀”出來的事實,但在影像文本生產過程中導演居于主導地位的事實始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與文化持有者的合作并不意味著雙方的文化闡釋權是平等的,這種“合作”出來的民族志紀錄片是否已經失去了民族志的應有之義?在反思人類學思潮的影響下,民族志文本絕對“客觀”的神話被打破,卻陷入另一個極端—放棄民族志書寫對事實真相的追索,按照預設模式制造“事實”,譬如“非遺”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大量“申報片”。在我看來,民族志書寫雖然做不到絕對客觀,但也要努力呈現出一個相對客觀的事實,不能信馬由韁而無底線。具體說,就是尊重文化當事人的權利而不能任意編造事實。此外,在當下傳統復興運動出現功利化的情勢下,“建構”一詞所隱含的主觀意圖極易混淆,甚至顛倒文化主體的權利關系,為某些建構論者任由主觀性無限膨脹提供了說辭。與摹寫的事實不同,事實的建構,是一個文化再生產的過程。因而,它與事件的真實性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人們無法徹底擺脫從本己文化立場出發建構一種解釋體系的影響,即使貌似公平的“共謀”也難掩文化本位的侵入。學術話語權的強勢地位以及公眾影響力,或能夠為一個社會群體或個人帶來某種利益的誘惑,往往會使當事人屈從于這種虛偽的解釋而成為共謀者,從而為這類“建構”提供合法性的外衣。但是,這會導致文化當事人以及他所依托的族群或社團喪失自己的文化權利,最終異化自己的文化傳統甚至導致文化物種的消失。
如果我們從方法論的意義上將“建構”視為一種文化再生產的“創作”行為呢?
這種“創作”意義上的“建構”,可能由學者而為,也可能由文化持有者而為;或者,由雙方“合謀”而為。無論是哪一種,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作為人類知識生產的一種方式,創作應該是創作人的權利。生產者不同,其文化屬性就有所不同,不能因為有了當事人的合作就將其偽飾為當事人的傳統,更不能將局外學者的“建構”當作局內的文化事實。我們從不打算否定這種“建構”類型紀錄片存在的合理性,只是主張對其加以必要的界定。某些聲稱為“民族志電影”的影像創作作品充斥了大量由導演編排出來的故事和異文化想象,它們是否真的屬于民族志范疇的確令人生疑。在我看來,這頂多可算作“紀錄風格的故事片”。其實,故事片也不錯。為什么一定披上一件“民族志紀錄片”的外衣呢?所以,本文所言的“建構”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民族志影像文本寫作方法—采取參與式田野方法進行的一種“真實的虛構”。
如果把我們形成影像文本的過程分為獲取事實的素材拍攝和為呈現事實的案頭非編兩個階段的話,建構,首先必得以非虛構的方式獲取事實,在爾后的書寫過程中,以對事實的整體性把握為前提進行有限“虛構”。就此而言,是否以非虛構方式獲取數據(素材),就成了我們判斷影像文本的真實性的首要條件。所謂“真實的虛構”,是說音樂影像志在獲取影像素材時要遵循“一無三不”原則:無劇本,不擺拍,不置景,不使用專業演員,這就與一般的電影創作做了原則性的區隔。對于音樂影像志的實踐來說,堅守這個原則是田野影像文本建構的基本前提。同時,把“介入事件”作為獲取逼近事實真相的觸媒,亦具民族志意義上的合理性。不過,由于介入的“事件”中“包括拍攝人員到達某處、選取某些人生活的某個方面包含在電影中的活動,這樣,事件便是由意圖促使的一個范疇”?馬庫斯·班克斯:《哪些電影是民族志電影?》,載〔丹麥〕彼特·伊恩·克勞福德、〔英〕大衛·特頓主編:《民族志電影》,高輝、郝躍駿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3頁。。也就是說,把拍攝者的活動同時并入的“電影事件”具有某種“虛構”成分。畢竟,這個“事件”是由拍攝者選取的,它隱含了拍攝者的意圖。所以,拍攝者就必須盡力克服本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潛在影響,拒絕功利性目的誘惑,從而使由建構法書寫的影像文本具有民族志意義的真實性。
非虛構的搬演:復原法
羅伯特·弗拉哈迪的民族志紀錄片開山之作《北方的納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2)究竟是真實還是虛構的?這是紀錄電影史上的一個“弗拉哈迪之謎”。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它既不是“虛構”也不是“真實”,而是關于因紐特人祖輩生活的一場“表演”。用電影評論家的話來說,這是一種“非虛構的搬演”。?聶欣如:《認識弗拉哈迪—〈弗拉哈迪紀錄電影研究〉導讀》,載〔英〕保羅·羅沙:《弗拉哈迪紀錄電影研究》,賈愷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2-16頁。
《北方的納努克》這部紀錄片奠基之作誕生之后(見圖5),又涌現出大量仿效之作。普通觀眾視為關于因紐特人生活的“真人真事”,而電影評論界卻始終糾結于真實與否—紀錄片是否可以以虛構方式拍攝的討論之中,至今不絕于耳。其實,這是一種“歷史復原”方法。其合理性在于這個事件具有靠譜的歷史事實基礎,而且是文化持有者對祖先生活的真實記憶。就音樂影像志的學術使命而言,在文化當事人對祖輩歷史尚有記憶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復原式記錄,對保存瀕臨消失的音樂文化基因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圖5 《北方的納努克》,羅伯特·弗拉哈迪,1922年
盡管有人對弗拉哈迪的“非虛構搬演”是否有悖紀錄片真實性的質疑至今不斷,但這部紀錄片的里程碑意義至今無人撼動。在《北方的納努克》面世半個世紀后的20世紀70年代,因紐特人建立了自己的“因紐特廣播公司”(Inuit Broadcast Corporation,IBC)。導演薩克·庫努克(Sak Kunuk,因紐特人)還與當地人一起合作建立了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制作團隊,“創作極富戲劇性的故事,來呈現20世紀30年代定居點建立前伊格魯利克周邊的生活狀況”?關于因紐特廣播公司(Inuit Broadcast Corporation,IBC)和薩克·庫努克的情況介紹,可參見〔美〕費·金斯伯格、里拉·阿布-盧赫德、布萊恩·拉金編:《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丁惠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0-71頁。。薩克·庫努克拍攝的13集電視連續劇《我們的家園》(Nunavut,1993—1995),由依格魯利克居民自己飾演影片中的角色。這與弗拉哈迪在拍攝《北方的納努克》的方法何其相似乃爾!不過,當作為“真人”的納努克走紅歐美電影市場后,他的扮演者—阿拉卡利拉克就在北極死于饑餓。而薩克·庫努克等人的影像實踐卻為原住民帶來了福音:“他們的作品在一代熟諳傳統知識的人行將逝去的時候,記錄了此前不曾記錄過的文化遺產,而且通過讓年輕人參與歷史劇的拍攝,促使他們學習因紐特語及其他與文化遺產相關的技能,從而幫助減緩因紐特人生活的社會和文化再生產中存在的危機。”?〔美〕費·金斯伯格、里拉·阿布-盧赫德、布萊恩·拉金編:《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丁惠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2頁。這一點,正是復原法的價值所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從1957年至1976年,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托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以及國內最高水平的紀錄電影制片廠,在西藏、新疆、黑龍江、云南、四川、海南等邊疆地區,攝制了16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這批民族志紀錄片,使用了“歷史復原”方法進行拍攝,動員了大批當地少數民族擔任“演員”。自1957年開拍,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牽頭,八一電影制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等單位參與拍攝、制作,歷經20年(“文革”間斷了10年)陸續完成了16部民族志紀錄片,如《額爾古納河畔的鄂溫克人》(張大鳳,1959年)、《鄂倫春族》(楊光海,1963年)等。民族學家參與了當時的拍攝工作,并進行了大量前期民族學調查。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民主改革運動,這些地處邊疆和偏僻地區的少數民族的許多傳統生活方式、民間信仰風俗和原有的社會組織方式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甚至消失。因此,在許多場景中組織、使用了歷史復原法進行拍攝。這批民族志紀錄片,雖然帶有時代的意識形態印痕,卻也留下了相當數量的邊疆民族歷史文化資源,具有重要影像文獻價值。
楊光海導演的《鄂倫春族》,是其中一部大量復原了鄂倫春人歷史場景的民族志紀錄片(見圖6),作為一種民族志知識的記錄與傳播,社會公眾通過影片了解到鄂倫春人鮮為人知的社會形態、風俗、宗教信仰和勞動生活。《鄂倫春族》面世以來,曾參加過哥廷根、萊比錫、赫爾辛基、臺灣、云南等地舉辦的國際影視人類學電影節上展映,影響廣泛。

圖6 《鄂倫春族》,楊光海,1963年
以下,我們從復制法的運行機制、工作流程、拍攝方法,以及錄音、布光和剪輯等方面,結合當年直接參與復原拍攝的核心成員楊光海、滿都爾圖、蔡家麒諸先生的回憶和記述加以分析。
復原機制
《鄂倫春族》與《北方的納努克》一樣,都采用了復原法進行拍攝,導演沒有采用職業演員,而是由局內人來“表演祖輩的生活”。所不同的是,《鄂倫春族》沒有以某一人物為核心為敘事中心,而是圍繞一個族群整體社會生活、民族風俗、勞動生產方式展開民族志影像敘事。并且,與《北方的納努克》由商人資助、弗拉哈迪個人的拍攝行為不同,《鄂倫春族》是動用社會資源,由政府推動、電影攝制單位組織實施的“國家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秋浦、趙復興、呂光天、滿都爾圖先生都是著名的民族學、宗教學學者;八一電影制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都是國內頂級的電影制片廠。由此可見,這是一個由官方領導,以專家學者為主導,以電影攝制單位為主力,以地方政府為后援的運行機制。
以個人學術研究為旨歸和以完成國家科研課題任務為目標的拍攝項目,是在不同的運行機制中操作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在選題上應當取類似《北方的納努克》的“微觀視角”,而不宜做《鄂倫春族》這樣的重大題材。這是由調動社會資源的權利和設備技術條件等因素所決定的。
工作流程
《鄂倫春族》是按照事先撰寫的拍攝提綱進行拍攝的。據楊光海先生的記述:拍攝提綱“是以原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民族學研究員趙復興、呂光天、滿都爾圖三位學者提供有關鄂倫春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報告文字資料作參考,并聽取了他們口頭介紹有關鄂倫春人生產生活習俗。我又到納爾克氣、朝陽等鄂倫春獵民村觀察體驗,和獵民們座談,有了感性體驗和認識。然后返回鄂倫春旗阿里河,和三位學者共同討論拍攝提綱整體內容框架后,由我執筆編寫”?楊光海編著:《紀錄片檔案:鄂倫春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44頁。。其工作流程是,從專家學者的調查研究資料入手,再做進一步的田野調查、撰寫拍攝提綱,形成由“拍攝提綱”和“解說詞”構成的劇本。最后,導演再出分鏡頭劇本和“完成臺本”,進入拍攝現場。《鄂倫春族》的攝制,有劇本、有導演,由當地人“表演”其先民的生活。由此可見,復原什么、如何復原并不由文化事件本身所決定,而是局內外一系列權利相關方協調、平衡出來的結果。
據實復原
《鄂倫春族》紀錄片的拍攝,一開始就提出“據實復原”的原則。據滿都爾圖先生記述:“編劇和攝制人員的共識是,為了使影片內容具有完整性和科學性,對于已經消失或即將消失,而且有確切的文獻記載和人們尚在記憶的社會事物,據實加以復原是必要的。”?滿都爾圖:《民族科學紀錄片〈鄂倫春族〉的民族學特色》,轉引自楊光海編著:《紀錄片檔案:鄂倫春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56;156頁。影片中復原拍攝的內容主要有:弓箭、扎槍和滑雪板等在鄂倫春人當時已經不使用的勞動生活工具,以及樺樹皮和毛皮用品的制作及鐵器加工,夏秋季的采集、捕魚和“烏力楞”遷徙、婚禮和喪儀,“安達”制度中與外族的實物交換和氏族會議、田野耕種、薩滿跳神活動等。這些鏡頭,“都是經過必要的組織安排而復原拍攝的”?蔡家麒:《記民族志影片〈鄂倫春族〉的拍攝》,轉引自楊光海編著:《紀錄片檔案:鄂倫春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60;160頁。。即使是作為道具的弓箭、扎槍和滑雪板這些傳統生產工具,也是請鄂倫春匠人復制的。?在設計、復原拍攝這些鏡頭時,導演都充分聽取了當地鄂倫春人的意見,特別是老人們的看法,“同時強調了應該按照他們平時的習慣了的方式來行動。……只要將每個場景的主要內容交代清楚被他們領會之后,具體的演示活動則讓獵民們放手去做,不加干預,不做特別的要求”?。亦即,導演在拍攝過程中不對具體的“表演”行為加以干預;即使是“復原”,也應當尊重當事人的復原權利,以局內人的“記憶”而非局外人的“民族想象”為依據進行歷史復原。導演只掌握事件進程的總體框架和節奏,而不編排“演員”的具體動作。可以說,復原法的基本原則是“據實復原”。
拍攝與剪輯
紀錄片《鄂倫春族》的復原內容,首先是傳統狩獵活動。據蔡家麒先生的記述,影片中冬季獵狍子、黑熊和松鼠等鏡頭,都是跟隨獵人進入山林實地拍攝的。只是獵捕馬鹿場景的拍攝,由于拍攝團隊條件有限,沒有長焦鏡頭和變焦鏡頭,采取了“嫁接”方法進行拍攝:“在養鹿場內近距離拍馬鹿,躲過鹿場的圍欄等建筑,待剪輯時再接上獵民在獵場架槍射擊的鏡頭,作為一種補救。”?同注?,第160;159;159頁。這種“虛構的真實”,是通過后期剪輯運用蒙太奇手法完成的。另外,在實地拍攝的過程中,劇組也靈活地根據實際情況對某些內容做了某些更動,但總體上還是按照分鏡頭劇本來拍攝。“這就保證了基本內容邏輯性貫穿,避免了因隨機拍攝而浪費膠片。剪輯中的各種意見,以導演的為主。”?同注?,第160;159;159頁。當時,獵民們的游獵生活雖然已經結束了10年之久,但當年鄂倫春人族群生活、勞動的老年親歷者尚在,許多風俗習慣和逸聞軼事仍存于鄂倫春人的記憶之中。并且,鄂倫春人的狩獵生活方式和大部分服飾、生活用具等,還沒有因為下山定居而消失殆盡,這就為《鄂倫春族》的復原拍攝提供了符合“據實原則”的歷史依據。
布光與錄音
除了個別鏡頭(撮羅子中)使用了反光板補光外,《鄂倫春族》的拍攝現場沒有使用照明設備;當時沒有同步錄音條件,使用了半導體便攜式磁帶錄音機,在當地錄制了鄂倫春人演唱的民歌、氏族會議和薩滿跳神等場景的實況(后期將其編進影片中),音效也是后期剪輯時所做的擬音。?同注?,第160;159;159頁。這些設備條件和技術性問題,如今已不是什么難題了。對于音樂影像志的田野作業,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作為音樂影像文本真實性特征的同期聲必須予以保障。
以當代影視人類學的眼光來看,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局限,《鄂倫春族》滲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因素。但其拍攝流程和方法,還是為我們今天運用歷史復原法進行傳統文化的影像記錄、傳承與保護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以參與式民族志視角為基礎的復原法,雖然是以導演/調查人為主導并介入了事件進程,但以“據實復原”為原則的拍攝,還是為民族志紀錄片的真實性提供了保障。毋庸諱言,作為一種“非虛構的搬演”,復原式民族志紀錄片的真實性一直遭到學術界的質疑。然而,平心而論,這些質疑的產生并非完全由影片本身所致;而在于,你是把復原的影像文本偽飾為“現實的存在”抑或明示為一種“復原的歷史”。如果從方法論意義上理解復原法的價值,這種通過族群生活記憶來復原歷史的影像書寫方法至今仍具生命力和應用價值。在急劇變化的傳統社會中,依憑族群的個人或集體記憶來復原歷史生活、勞動和音樂活動情景,可以重構一段音樂文化歷史的斷層。
紀錄電影史表明:自《北方的納努克》以降,無論是“電影眼”理論,還是風靡于20世紀中葉的“直接電影”和“真實電影”,盡管人們對“真實”的理解與闡釋存在差異,但它始終都是紀錄片理論的核心命題,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民族志紀錄片先驅們的這些實踐和理念,對音樂影像志的理論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真實電影”的導演主動介入事件過程,希望創作更貼近現實卻不為“真實”所奴役的電影;而“直接電影”的拍攝者作壁觀世相,扮演不涉入的旁觀者;“真實電影主張觸媒而發的方式,獲取日常生活被遮蔽的真相;而直接電影主張采取伺機而動的方式,保持相對客觀,等候真相的浮現。”?同注⑦。但他們都恪守無劇本,不擺拍,不置景,不使用專業演員的“一無三不”原則;亦即追求民族志影像文本的真實性。而復原法雖然有劇本、有擺拍,但“據實復原”—非虛構的“搬演”,依然體現了對真實性的追求與堅守。對于音樂影像志知識生產的摹寫、建構和復原法來說,雖然“真實”的邊界從來就沒有一個無可爭議的尺度,但,民族志的真實性是一個不可逾越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