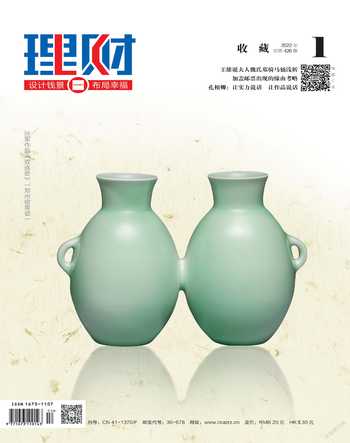河南博物院藏陶倉賞析
梁爽 李曉熒

陶倉是兩漢時期常見的喪葬明器,其出現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秦墓,漢時形成規制并走向興盛,魏晉后逐漸衰落。陶倉的造型源于古代存儲糧食的地面建筑,具體形狀和造型因時代、地域環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陶倉發展特點
墓葬中出土的陶倉明器分為圓形、方形等不同形狀,設計之繁簡各不相同。《呂氏春秋·仲秋紀》高誘注“圓曰囷,方曰倉”,簡單區分了不同形狀陶倉的名稱。如今學者們往往將圓形陶囷和方形陶倉統稱陶倉。圓形陶倉形制簡單,平面呈圓形,上有出檐或不出檐頂,分有蓋或無蓋,腹部呈筒狀,底部有足或無足。兩漢時期的陶倉多見倉頂,頂部多出檐,以懸山、歇山及四阿式形態為主。有的陶倉還設置天窗、氣孔等利于通風散熱、防潮防蟲的設施。為了適應南方潮熱的天氣,有些陶倉倉底還使用數根立柱支撐,形成干欄式結構。
方形陶倉主要指倉房與倉樓,平面呈方形,有較為規范的屋頂、瓦壟、房梁、門窗等。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陶倉的形態進一步復雜化和寫實化,陶倉房、倉樓由此出現。陶倉房是平面為方形的立方體儲糧明器,造型較陶倉更為繁復,不僅有屋頂、房脊、挑梁等細致真實的建筑構件,還時常繪有網格狀紋飾,用以竹篾編成的網格,抵御啄食糧食的飛鳥。隨著東漢時期莊園經濟的發展,形制更為復雜的陶倉樓出現。陶倉樓指帶倉的陶樓,一般有連閣和院落,樓層普遍高于兩層,上有屋頂,樓上開窗。
陶倉發展的歷史背景
陶倉的出現與時代的生產力、經濟發展水平及政治環境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陶倉的形制為研究其所在時代的政治經濟環境和文化思想意識提供了鮮明的證據。富足的農業生產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條件,五谷豐登一直是歷代人民的熱切企望。只有“吃得飽”,人們才有精力發展文化,制定法則,推動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自西漢初期始,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生產的措施以恢復連年戰亂所造成民生凋敝的慘景。輕徭薄賦的政策、鐵制農具的廣泛推廣以及大型水利設施的營建,都為農業經濟的復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史記·平準書》描繪西漢中后期的糧食豐收盛景,用“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加以形容,足見糧食之充沛、農業之發展。于是,人們開始廣泛地使用糧倉作為貯存糧食的場所,糧倉甚至成了家庭地位和財富的象征。相應地在墓葬中也逐漸出現了放置微縮版的倉、灶、井等用具這一“事死如事生”的現象。魏晉后,社會局勢動蕩,缺乏穩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薄葬之風遂起,繁復的喪葬明器隨之沒落。
河南博物院藏不同時期的陶倉
陶倉的地理分布及形制演變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西漢早中期的陶倉主要分布于以中原為中心的地區,多出現于高等級墓葬之中,是當時貴族們彰顯財富地位的工具。此時的陶倉造型簡單,平面多為圓形,折肩、筒腹、平底,倉蓋多為覆缽式。
“粱米萬石”帶蓋灰陶倉(圖1)
倉高41.6厘米,口徑10厘米。灰陶質,圓柱體,直口,平沿,圓肩,柱狀腹,平底附三蹲熊足。口上承覆缽式蓋,通體飾四組凸弦紋,腹側有朱彩隸書“粱米萬石”四字。
“小豆萬石”帶蓋灰陶倉(圖2)
倉高41.6厘米,口徑10.2厘米。整體呈圓柱形,直口,平沿,圓肩,柱狀腹,平底附三蹲熊足。口上承覆缽式蓋,下部一側有圓形鏤孔,通體飾四組凸弦紋。腹側有朱彩隸書“小豆萬石”與下部圓形鏤孔相應。
這兩件陶倉均出土于河南洛陽金谷園漢墓,形態類似,具有明顯的西漢中期的陶倉特征。這一時期的陶倉以圓形為主,繼承西漢早中期的覆缽蓋、筒狀身、平底等特點,但肩逐漸呈圓弧狀,倉腹繪有漢隸及四組平行分布的弦紋,底部有三只獸足。這種形態上的演變昭示著陶倉在造型上的美化和規范。“小豆萬石”及“粱米萬石”的隸書器銘剛勁挺拔、字體嚴整,是研究漢隸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同時,如此體形的陶倉不可能盛得下“萬石豆粱”,器銘所書只是一種美好而夸張的愿望,希望逝者在地下世界擁有取之不盡的食物。
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陶倉由皇室所在地區向外輻射,北方漢墓中常見陶倉,使用階級和地理范圍都有所擴大。此時陶倉的肩逐漸呈圓弧狀,三獸足多見,倉身紋飾也豐富起來。倉腹有紋飾或文字,以平行弦紋為常見。
紅綠釉桶式陶倉(圖3)
陶倉出土于河南濟源軹城泗澗溝墓地,倉身近圓柱體,圓肩,小口,口上置一復碟形圓蓋。蓋頂有柿蒂形紋飾,平底附三熊足。腹上有等距離的三條陽弦紋帶,肩以上施綠釉,肩以下施紅褐釉。在弦紋紋飾、三獸足、覆缽蓋的方面,此陶倉繼承了前期的陶倉形制,但在顏色方面顯得更加艷麗。這種復色釉的施釉方式主要見于西漢中晚期,在色彩搭配上具有較強的審美性。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更加低矮的陶倉形式,筒身更加渾圓、豐肩直口、肩部漸收,但制作工藝和施釉方式上都與此器物十分相近。
弦紋熊足帶蓋陶倉(圖4)
陶倉倉體為筒形,上豐下斂,口上有一博山蓋,下附三蹲熊足,倉身飾有四組凸弦紋帶,下部一側有一小圓洞。這一器物出現于東漢,繼承了西漢時期圓形陶倉的基本形制,在倉蓋制作上著墨更甚,狀似博山,但筒身下部出現了內斂的趨勢。由于后續喪葬明器的重點集中在方形倉房及倉樓上,圓形陶倉的形制逐漸趨向粗糙。
東漢中期以后,圓形陶倉逐漸被方形陶倉代替,陶倉房和倉樓成為喪葬明器的首選。墓葬中不僅隨葬陶倉樓,還配套置有灶、井、磨、豬圈等俗世農耕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這種精巧又寫實的明器標志著漢代糧倉建置走向精良,也代表著兩漢時期以陶倉為代表的喪葬明器逐步規范。除此之外,低溫鉛釉在西漢中晚期后逐步成了陶倉燒造的主要方式,陶倉多為綠釉或黃褐釉,更有黃綠結合的復色釉這樣具有獨特審美的藝術創造。而這時的陶倉也不再僅僅是上層階級的專屬明器,普通百姓也多用之祈愿往生富貴。
綠釉陶倉房(圖5)
倉房出土于靈寶張灣二號漢墓,倉身為扁立方體空心磚式,懸山頂,正脊兩端飾有翹首吻。前坡飾覆瓦壟9行,后坡溜滑,底部附四蹲熊足。倉身正面中部開有洞窗,窗兩旁立仿木式門頰直通上下。 除底部外通施褐綠釉。該倉房是民用倉房的模型。
黃綠釉陶倉房(圖6)
此倉房為泥質紅陶,懸山頂。正面中央有一長方形小孔。其上為四個斗拱和一圓柱橫梁,下有45度挑梁,底為前三后三蹲熊做支撐。通體施黃綠釉。該倉房設計精巧,結構復雜,檐下四組挑梁和斗拱的應用,具有實用性和裝飾性,為研究東漢時期建筑的發展、演變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兩件陶倉房極具寫實性,懸山頂的屋檐形態、翹首吻、斗拱、橫梁、挑梁等極具實用性的建筑構件一一出現,反映了當時對陶倉形態設計的真實、細致化追求,標志著東漢時期陶倉形態的重大變革。方形陶倉逐步代替了圓形陶倉成為普遍的喪葬明器。這一形式也為更加繁復巨大的陶倉樓的出現打下基礎。陶倉房的細致化從側面展現了穩定繁榮、經濟繁盛的社會局面,人們對喪葬水準的要求已經到了很高的地步。
魏晉之后陶倉的規范化形制逐步衰落,出現了頂為圓錐形、身為圓筒狀的陶倉形態。此時的陶倉較之兩漢顯得更為粗糙化、抽象化。
陶倉(圖7)
該陶倉為北齊器物,出土于河南省安陽縣洪河屯村范粹墓。倉身呈圓柱形,中空,下無底,圓尖頂。最頂端冠以小平面圓形屋脊。頂面斜坡起棱,以象征瓦或茅草的疊壓層次。此時的陶倉在形制上已發生較大改變,脫離了兩漢陶倉由簡入繁的演變規律,缺少了標志性的檐頂和足,且不施釉料,顯得更為簡約粗糙,不復兩漢時期陶倉之精巧寫實。這是由于魏晉之后社會大一統局面不復存在,分裂割據的社會環境破壞了積攢數百年的生產經濟,人民的生產生活受到約束,厚葬之風漸漸消弭。
河南博物院藏陶倉百余件,由以上選取的幾件具有代表性的陶倉可以看出,陶倉的形制演變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其發展離不開時代所賦予的政治經濟基礎。同時,陶倉的形制也為學者對當時社會經濟、工藝技術、審美思想、喪葬文化的認識提供了獨特的角度。陶倉是俗世糧倉的微縮版本,反映了因生產技術、政治生態等的改變所造就的農業生產形勢。兩漢時期作為政治經濟穩定、生產生活富裕的大一統時代,伴隨土地私有化,人們的剩余糧食變多,糧倉成了重要的儲糧工具。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人民的基本要求得到了滿足,關于死后尊榮和往生升仙的愿望便更加強烈。因此,厚葬之風漸起,包括陶倉在內的明器成了上層階級展現地位與財富的用具。陶倉由圓至方、由簡入繁、由小至大、逐漸寫實,至東漢時期出現了形制繁復的高大倉樓,又在魏晉時逐漸粗糙化。同時,陶倉的演變展現了漢代手工藝技巧的變化及真實糧倉的建置變化,也暗示了時代生產條件的變革之下人們樸素又誠摯的生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