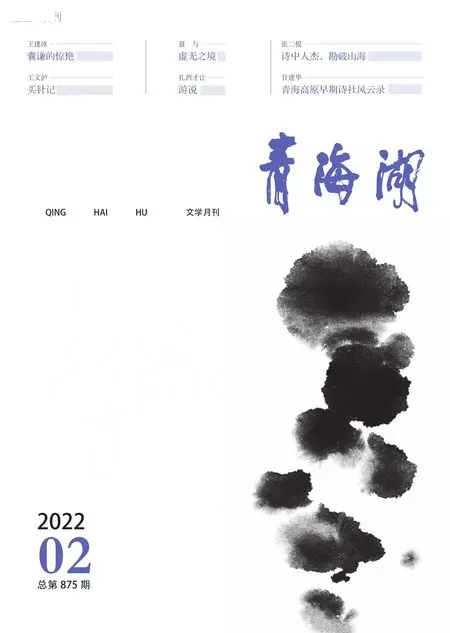用水中蒼穹擁抱天空(評論)
“……像老去的父親/它們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從不需要人類那樣的語言”(《凍紅的石頭》),當這些詩句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就像面對鏡像時的恍惚,這是我所熟悉的陳人杰嗎?在放棄優渥的生活狀態后,他以孤絕的姿態飛翔在高原之巔,這種修煉,對于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加速和催化。
但作為朋友,私下我們說起時,大抵并不能完全理解陳人杰的選擇:1968年出生的他,是浙江天臺人,大學畢業后回到杭州工作,然后就去援藏了,這一援就是三屆,之后索性調藏工作了。到底是什么讓他做出這樣的選擇?除了一些客觀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一定有發自內心的驅動,這種驅動或許是他這一行為的源泉,就像他在《何去何從》中所寫的:我為那走失的小羊在哭泣/你為在公路上撞死的阿爸在哭泣/我們在哭泣/在高高的雪原上/在低低的人世間。
我想一開始去援藏可能只是詩和遠方帶來的沖動,而沉浸于高原的風中時,陳人杰猶如蛻殼之蟬,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嬗變,到目前,它們就結晶在這部《山海間》的詩集中。
桃花從根柢飛出/能飛得更遠嗎,到哪兒算是抵達//所有的破繭開滿艷麗血跡/喚醒內心的戰栗//誰的盲目,或為盛名遮蔽/為漫山遍野的泛濫/其中的花瓣難作命運一辨 —— 選自《桃花吟》
這詩中的桃花,應該是他內心的寫照之一,在他離開江南多年,在高原上砥礪理想,他的心居然沒有被高原之狂風吹得粗糙。這桃花,我們可以讀到他對人世的溫柔一瞥,帶著對美好的眷顧,這或許是體現在他對題材的把握上,整冊詩集呈現出一種奇異的火焰,猶如祈禱,一種秘密的、充滿想象力的文字噴涌而出,它們在澄澈中又有沉甸甸的意蘊,對于南北這兩塊他所立足的土地,他為什么要去書寫,又怎么樣去表現出他的理解?
這種困惑和矛盾,在陳人杰的《與妻書》其實有所流露,詩很長,這里我摘錄幾段:“一只鳥滑過虛空/它是否摸到過天堂的門?//存在就是被選擇/我選擇了你,即選擇使徒、遠方/仿佛這一生都在蒼穹下,聽——/水聲無垠地與岸融合//溫柔之物將那山脊輕輕鎖住//只剩下你給我的香息/無任何花朵可以替代/你降臨的弧線/整個天空呈現古海的藍/只剩下蔚藍色的肺腑/吹送鷹笛,保留著浪花,一遍遍重新開始。”
這是陳人杰自己對自己的觀照,他的文字所呈現出的鏡像之一,在這種彷徨和堅定中,他有了自己的形象。
而地域的反差,同樣是一種鏡像,倒映著一種社會或人們內心的隱秘,陳人杰在《云》中,或多或少悟出了其中的真諦:“云在天上也站不住/石頭總能落地生根/多少年了,有人想給云一個懷抱/有人想給石頭一個家/——所有開始過的/都不曾結束//多少年了,云影從石頭上滑過/石頭被壓進心底。”
既羨慕于云之高蹈,又執著于石之堅韌,在詞與詞之間,在天籟般的旋律間,人生的細節被隱藏在文字之后,像是隱約的面龐,它所傳遞的一種精神張力:對于交流和溝通的需求,是輕和重有趣的對峙,是逃逸和留下之間的生活影像。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江南和西南作為兩種相對的地理,在陳人杰的肉體中糾葛斗爭,而讓他理解苦難和幸福之間的距離:對被忽視的命運的凝眸和對人世的憐憫。
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詩:“早晨,隱居在光線中的圣殿/朝露,黎明的銀耳環/
一頭母牦牛,熱吻這片刻溫存//雪山涌出,星月隱沒/你又在碧空下/多少淚水源于自身/我的左眼看不見右眼”(《譬如朝露》);我們也可以讀到這樣的字句:“苔蘚還原時間的地表/還我心中的荒蠻/孑立拉薩之肺/野徑,探出思想的蘆葦//我愛著紅蓼、水草/深陷的天空/被無數光影疏漏的時間/以及一條魚在泥水里吐泡泡//那個諳習水性的少年/迷幻地看著/自己的倒影,直至/肉身的濕地,一個神在晃動”(《拉魯濕地》)。
這些詩句中,有一種尖銳之音,帶著江南的溫柔之風和高原灼熱的陽光,在委婉的旋律中吹向我們,這是屬于陳人杰的世間情歌。而我們傾聽這些聲音,對于大地的凝視造就了這些詩意的匯聚,這使得詩得到一種高度和慰藉。
陳人杰是浙江天臺人,謝靈運和唐詩之路的潤澤對于他不可或缺,而山水詩是江南文化的一個傳統,從古典詩詞延續到新詩,從謝靈運以來,對于眾多的漢語寫作者而言,山水即抒情,從風物中提煉、發掘詩意,讓我們感覺到一種悸動和不可遏制的熱情。這種與山水交融的姿態成就了人與物相互為鏡,抵達靈犀一線,在《山海間》這冊詩集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傳統的隱約呈現。
“所有的葉片朝向星空/細小花,對接深邃幽暗里的萬古燈/從江南到萬圣之巔,行者的高原/以一己之力,將世界屋脊緩緩撬動/浪跡流螢,藏身綠度母的母體/大琴弦上,牧歌在日夜采集青銅”。
在這首致昌耀的《牧歌在日夜采集青銅》的詩中,彌漫出一種泛地域性的詩意:在人與物之間,文字找到了臨界點和結合點,并挖掘出一種精神里的寧靜之美,陳人杰是采集青銅的勞作者,也是對壯美山水的凝眸者,而山水詩一旦與高原相結合,便爆發出更加熾烈的光芒,在這冊詩集中,陳人杰寫了散布在高原上的多個峽谷和冰川,卻寫得搖曳生姿。在《伊日大峽谷》中,他的起句開明宗義:“靜謐在嘎那拉山和當扎拉山交會/兩片唇,幽閉峽道的靈脈。”這樣的詩句我們可以看作是一種隱喻,但更多的是自己對自己的一種深度認識:我們所看見的世界即是我們自己。
果然,在后續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精神的層層遞進:
“每一朵雪花活出自己的味道/你的芬芳從我的腳跟/一直沁到舌尖//喑啞言辭,遠,卻在我的心口/孤單的解脫,被一個個春天送回//……大隱,仍被天地所知/愛每一巉巖所纏綿的緋聞/與掩映的來路,讓花草孕育兒女/白云用位移重續枝條/飛行的信函,為大雁一字一句啄開”。
同樣寫峽谷的《加玉大峽谷》,卻又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風光,在第三到第五節中陳人杰這樣寫:
“有人窒息/有人拿懸念作喻/霹靂落下,一只鞋/顧不上另一只鞋//山水的小小分歧/影響了世界的旅程,和分裂”;
“一線天,以大峽谷之名/拱出絕壁/我,以家國之名/負裂而行,以小,見大光明”;
“流年如峽谷/而一個人攜帶著愛與恨/從中穿過/側著身”。
“胸臆萬世,此心悠悠,且把浪花當韻腳,在群星上散步”,這種天人合一的期待,或許是陳人杰在高原攬湖俯瞰時,蔚藍的湖水倒映著雪山和蒼穹,兩者之間無罅的擁抱能夠帶給他的啟示。
所謂的來路和歸途,這個哲學上的命題正是我們所苦苦追尋的人之答案。如果我的記憶沒有產生偏差的話,陳人杰正是學哲學出身,他的人文素養背景扎根于此。陳人杰的這些詩讓我想到行人這個意象,有意思的是,他所致敬的昌耀,生前在自己的名片上印著“行者”的自號。
蘇東坡的那闋《臨江仙·送錢穆父》一直是我所喜歡的,它道出了一種人生之旅中孤獨的況味,卻又有著世事洞明的通透:“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
行人。”
就是這樣的一個行人,從兩個相對的地域山水間他看到了自己的來路和去處,他在一派忙碌中依然保持著一顆不枯竭的詩心。這些詩,是他對自身的一種審視和期待,我們的閱讀大抵可以從這個切口去進入,他所看見,他所聽見,和他所思考的,在這些文字中糅合成一種聲音抵達我們的閱讀,或者幫我們推開了另外一扇門。
我把陳人杰的一首小詩放到結束之處,《朝思》之思是他對自身一個清晰的認識,而他文字的質地和輪廓,便這樣顯露出來,每一條岔路上,都能找到神明指引的方向:
玉宇,寧靜的廳堂/鐘聲中一輪紅
日/神是偶然/家譜,是驚奇的時間/三葉草的岔路口/三顆小精靈如生命的起點
李郁蔥 1971年6月出生于余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杭州。1990年前后開始創作,文字見于各類雜志,出版有詩集《此一時 彼一時》《浮世繪》《沙與樹》《山水相對論》,散文集《盛夏的低語》等多種。曾獲《人民文學》創刊45周年詩歌獎、《山花》文學獎、《安徽文學》年度詩歌獎、李杜詩歌獎等。
特約責編 馬海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