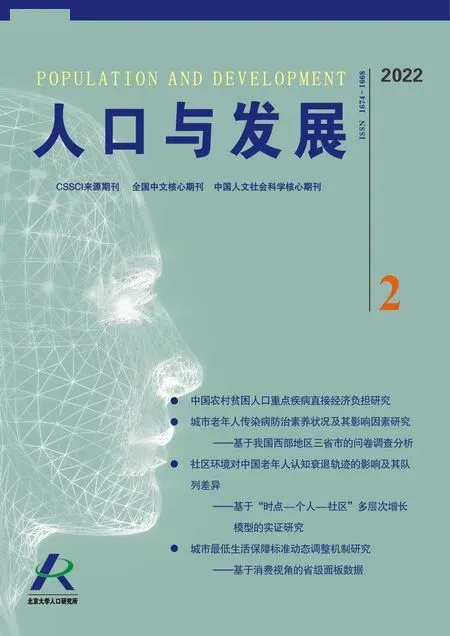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兼論教育的家校建構與個體特質的關系
高娟
(中南民族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1 問題的提出
地位獲得是社會學核心研究領域社會分層研究中的重要問題。通過教育獲得與職業獲得這兩個社會分層過程中的主要環節,社會成員在篩選機制下被分配安置于不同社會階層上,賦予了不同社會地位。從學校教育過渡到職業階段是大學生社會地位獲得的重要來源,也是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融合的結果。大學生就業不僅關系到大學生的地位獲得,而且關系到大學生家庭的未來社會階層歸屬。然而,經濟全球化發展時代,伴隨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涌入就業市場,使得中國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中面臨更加激烈的就業競爭,導致就業形勢日益嚴峻。近年來,在全球經濟形勢的影響下,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日益增長,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如何有效地促進大學生就業,實現大學生教育地位獲得或職業地位獲得,既是發揮高等教育的地位獲得功能的重要體現,也是營造公平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與平等的社會格局的重要手段。
關于地位獲得的研究,布勞與鄧肯綜合考慮個體的先賦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影響認為,以教育和工作經歷測度的人力資本因素作為后致性因素比從父母處獲取的先賦性因素對個體職業地位的獲得產生更重要的影響(Blau & Duncan,1967)。在個體地位獲得上,始終存在兩股主要力量在發揮作用。一是體現代際傳承的家庭因素,如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背景、家庭文化資本等。社會結構的自我復制無可避免地促使家庭背景對子代地位獲得產生重要影響。父母職業地位、文化程度和經濟收入越高,子女越能夠獲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和更具優勢地位的職業(文東茅,2005;李黎明、李衛東,2009;李春玲,2009;岳昌君、楊中超,2012;喬志宏等,2014)。家庭社會關系或社會資本對大學生的職業性質、崗位與起薪等也具有重要影響(閔維方等,2006;岳昌君、白一平,2018)。而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本也促進了子女獲得優勢教育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可能性(De Graaf、De Graaf & Kraaykamp,2000;Wu,2008;Scherger & Savage,2010;仇立平、肖日葵,2011;楊春華,2014;張文宏、蘇迪,2018)。二是體現后天努力的個人因素,如個體人力資本或可動用的社會資本、后天積累的文化資本等。個人也可以通過后天努力削弱先天資源的不平等,以緩解社會結構的固化效應和擺脫代際傳承的約束。人力資本更高的個體在尋找工作時可以有更高的收入和職位(Rotkowski,2003;González-Romá、Gamboa & Peiró,2018;岳昌君等,2004,2012,2018;閔維方等,2006;喬志宏等,2014)。個體社會網絡和所能動員的社會資本顯著影響其職業收入、職位等,促進了其職業地位的獲得(如Lin、Ensel & Vaughn,1981;Bian,1997;González-Romá、Gamboa & Peiró,2018;陳成文、鄺小軍,2004;康小明,2009;陳宏軍、李傳榮、陳洪安,2011;邊燕杰等,2012;薛在興,2014;李黎明、廖麗,2019),而通過后天所積累的文化資本也可以正向影響地位獲得以及劣勢階層的向上流動(如DiMaggio & Mohr,1985;仇立平、肖日葵,2011)。
對大學生地位獲得的研究已經從簡單因果機制研究過渡到多因素聯合的復雜因果機制研究,但相關研究更多地關注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及其對地位獲得的綜合效應(程誠,2012;賴德勝、孟大虎、蘇麗鋒,2012;黃敬寶,2014)。盡管有少數研究從廣義文化資本視角對社會地位獲得進行驗證,提示了文化資本是地位獲得的文化象征(如仇立平、肖日葵,2011)。然而,傳統文化資本的研究以父母文化資本和子女文化資本為主,很少推及學校文化資本。對具備一定教育程度的群體,文化資本如何實現教育成就的升級或職業地位的獲得?家庭文化資本與學校文化資本是否各自發揮作用,個體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其中又發揮何種作用?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也是本文將要探討的核心問題。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基于教育的家校建構(如家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與個體特質(大學生人力資本)的相互關系,在同時強調家庭文化資本和大學文化資本的雙重作用下,綜合考慮文化資本的多種形態和人力資本的不同方面,而非僅僅以某一個或幾個指標作為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替代變量,不僅關注文化資本對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后的職業地位獲得的作用,而且關注文化資本在大學生實現更高層次的教育獲得升級中的作用,重點探討家庭文化資本傳承、大學文化資本建構及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地位獲得的綜合互動效應。
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盡管大學生的地位獲得主要是通過職業獲得來體現的,但教育動機與職業收入之間通常具有一定相關性,大學畢業生通過個人努力實現教育獲得升級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具有優勢地位的職業,而更高層次的教育獲得通常也意味著更易獲得優勢社會地位,教育成就的升級也成為實現地位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大學生地位獲得可以通過教育地位獲得與職業地位獲得兩個環節實現。教育地位獲得可理解為通過大學生的努力實現繼續學習深造,以達到教育層級的上升或教育成就的升級。而職業地位獲得則可理解為通過大學生個體努力實現更好的就業,獲得社會經濟地位的更高回報。大學生地位獲得與其個體素質、原生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都息息相關,文化資本的家庭傳承、學校建構與大學生個體特質必然在大學生地位獲得上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2.1 文化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布迪厄認為,資本具有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形式,文化資本包括一群人之間具體化、客觀化、制度化的信仰、行為和品味,以表達一種超越經濟利益的等級制度(Bourdieu,1986)。Lamont和Lareau(1988)對文化資本給出了一個操作化定義,文化資本是制度化的,即廣泛共享的、高地位的文化信號(態度、偏好、正式知識、行為、商品和證書),這些文化被用于社會和文化排斥。 Winkle-Wagner(2010)表示,文化資本可能以通過社會出身(其中包括家庭階級特權)和通過教育兩種方式實現。可見,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是兩種主要的文化資本再生產方式。
2.1.1 家庭文化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家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承擔了重要角色(喬志宏等,2014),作為基于婚姻、血緣或其他合法關系而建立的社會基本生活單位,是最原始的、最基礎的和最重要的文化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場所。文化資本在子女教育獲得中具有積極作用(Wu,2008)。家庭文化資本的傳遞對教育水平也有直接的影響,文化社會化程度越高的個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越大(Scherger & Savage,2010)。Dumais和Ward(2010)的數據分析發現,家庭文化資本等對四年制大學入學和畢業表現均產生顯著影響。仇立平和肖日葵(2011)對上海市的實證研究發現,父母與子女的文化資本正向影響了子女教育地位與社會地位的獲得,同時文化資本的積累使社會地位較低家庭能夠實現子女的向上流動。楊春華(2014)基于理論與訪談分析發現,家庭文化資本中的“無形文化資本”與農村家庭達成教育目標和獲得社會地位具有密切關系。張文宏和蘇迪(2018)通過大型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顯示,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更大地促進了孩子流向優勢教育與階層地位的可能性,且家庭經濟資本通過家庭文化資本發揮作用。文化資本以其稀缺性和家庭差異化為不同家庭大學生帶來了分布不均的資源和特殊的優勢。大學生原生家庭所擁有的豐富的文化資本能夠以客觀文化環境條件支持和家庭交流互動關系等形式促進大學生文化習性的形成和獲得更多的教育優勢,以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成就,影響就業機會與職業意愿的選擇,進而實現向更高層級教育成就的升級和職業地位的獲得。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a: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升級具有顯著正向效應,即家庭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實現教育獲得的升級。
假設1b: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職業地位獲得具有顯著正向效應,即家庭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獲得更高地位的職業。
2.1.2 大學文化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由于大學生的主要生活場域是原生家庭與就讀大學,學校文化資本在大學生的地位獲得中也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多數研究發現,家庭文化資本與教育成就呈正相關,而很少有研究考察學校在決定文化資本和教育成就之間的關系時是否與家庭互動(Marteleto & Andrade,2014)。然而,學校文化資本也是不同學生獲得差異化的教育成就和職業成就的重要影響因素。有研究表明,學校聲譽(類型)或學校質量等對畢業生的就業結果與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Fox,1993;Zhang,2005;Long,2008;Hartog、Sun & Ding,2010;閔維方等,2006;胡永遠、馬霖、劉智勇,2007)。而王穎和李慧清(2015)基于廣州市20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學歷與就讀學校檔次等文化資本方面以及家庭創業史、高校創業教育活動、創業地政府的支持、志同道合的創業伙伴與創業資金支持等社會資本方面都顯著影響創業意愿的形成,而個體特質性別與應屆生身份也顯著影響了大學生的創業意愿。實際上,高等教育體制下不同大學文化資本的差異化強調了不同培養目標,對應著不同的職業需求和職業定位,大學教育通過不同的文化能力、文化產品和文化體制等傳遞不同的價值觀與行為方式,進而對大學生的教育成就、職業選擇和職業成就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a:大學文化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升級具有顯著正向效應,即大學生所就讀大學擁有的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實現教育獲得的升級。
假設2b:大學文化資本對大學生職業地位獲得具有顯著正向效應,即大學生所就讀大學擁有的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獲得更高地位的職業。
2.2 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明確對人力資本進行系統論述并將其引入經濟增長的分析中,使得“資本”內涵向廣義延續為產生增值的全部資源的總稱。人力資本是一組可能影響個人職業發展的個人因素,如教育、工作經驗、培訓、知識、技能和能力(Fugate、Kinicki & Ashforth,2004;McArdle et al.,2007)。大學生人力資本體現的是一種個體人力資本,代表了一種能產生收益的生產要素或資源。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如教育)增加了他們對組織的價值(Becker,1964),組織則通過更高的薪水和職業發展來承認這種更高的價值(Judge、Klinger & Simon,2010)。人力資本對大學生地位獲得的作用已經得到了證實(宛恬伊,2005;康小明,2009),而文化資本能夠解釋在擁有同等教育機會時卻依然存在著學業成績差異的原因。
2.2.1 家庭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在對個體教育獲得的解釋上應當予以結合,它們并非相互對立的(王志明,2008)。教育成就體現了個人努力的結果,但也與家庭背景之間密切相關,家庭背景是對學業成績影響最大的因素(Coleman,1966)。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家庭文化資本對學業成績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如Tramonte & Willms,2010;J?ger,2011;Huang & Liang,2016;Caprara,2016;Tan & Liu,2018)。文化資本影響個人教育表現,對于大學畢業生社會資源能力的提升、職業獲得機會的拓展和就業市場的發育成熟具有支持作用(汪衛平、葉忠,2015)。張艷、張雙月和張莉(2018)的實證調研結果顯示,學習成績在家庭文化資本對農科大學生農村基層就業意愿中發揮中介作用。大學生的教育成就或職業成就取決于個體的知識、能力等因素,但這些人力資本因素卻往往與家庭文化資本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父母教育程度較高、擁有更多文化物品、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圍和交流環境、父母教育支持與期望較高等家庭中的大學生可能受到家庭環境和父母的影響而具有更加優越的學習條件、更加強烈的上進心和更清晰的目標性,促進其更加努力學習和培養能力以提高學習成績和社會能力,進而更有希望進行更高層次的學習深造或獲得階層地位更高的職業。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a:大學生人力資本在家庭文化資本對其教育獲得升級的作用中發揮中介效應,即家庭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從而實現教育獲得的升級。
假設3b:大學生人力資本在家庭文化資本對其職業地位獲得的作用中發揮中介效應,即家庭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從而獲得更高地位的職業。
2.2.2 大學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
文化資本對大學生教育成就與職業成就的作用不僅僅表現在對家庭文化資本的繼承與運用上,也表現在學校為大學生所提供的文化資本是否充分與適當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在社會分層中的功能日益凸顯,習慣上而言,受教育者的學業成就或職業成就應當歸結為學校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學校品牌聲譽、環境氛圍、教師期望、師生關系、設施資源、教師學歷資格、規章制度等與學生的學業成績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如Win & Miller,2005;Rubie-Davies、Hattie & Hamilton,2006;Dube & Mlotshwa,2018;Arshad、Qamar & Gulzar,2018;Huang、Tse & Chu,2019;Rahim,2018;趙必華,2013)。而岳昌君、文東茅和丁小浩(2004)、閔維方等(2006)的分析表明,個人素質是高校畢業生求職成敗與收入水平的關鍵決定因素,學校提供的求職信息顯著影響了求職結果與起薪水平。我國高等教育在從“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化中經歷了不斷的分化,形成了具有不同類別或性質的高等院校并存的格局,也在教育內部表現出差異化的大學文化資本。不同的高校具有不同的社會聲譽、校風學風、文化氛圍、教師水平等文化資本特征,在學生培養上也具有差異性,大學生對這種文化資本的感知可能顯著影響其在專業知識或實踐技能等方面獲取的興趣與結果,進而對教育獲得的升級或職業地位的獲得產生顯著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a:大學生人力資本在大學文化資本對其教育獲得升級的作用中發揮中介效應,即大學生所就讀大學文化資本越豐富,其越有可能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從而實現教育獲得的升級。
假設4b:大學生人力資本在大學文化資本對其職業地位獲得的作用中發揮中介效應,即大學生所就讀大學文化資本越豐富,其越有可能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從而獲得更高地位的職業。
3 研究設計
3.1 思路與方法
基于理論假設分析,家庭文化資本與學校文化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升級或職業地位獲得具有顯著正效應,而大學生人力資本在其中發揮中介效應。以往研究中基本很少綜合探討家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大學生人力資本與地位獲得的綜合路徑,且在大多數研究中僅以部分指標作為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替代變量,而沒有結合文化資本的多種形態和人力資本的不同要素進行綜合衡量。為此,本研究綜合考慮觀測指標和變量的類型,運用SPSS和Mplus作為分析工具,首先對變量進行效度與信度檢驗、描述性統計分析等,然后分析家庭與大學文化資本、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職業獲得狀況(教育升級、就業或未就業)的路徑,并針對已就業大學畢業生檢驗家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職業地位獲得的路徑,最后納入性別、生源地與大學類型因素進一步探討相關路徑的變化。
3.2 數據與樣本
本研究以大學畢業生作為調查對象,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課題組于2019年進行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風險影響機制”問卷調查。2019年5月-7月,課題組通過問卷星和委托同學、朋友、親屬等社會網絡關系發放紙質問卷等形式對我國多所高校的畢業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參與調查的對象分布于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等不同區域,包括湖北、湖南、北京、河南、江蘇、四川、貴州、廣東、廣西等地部分高校的畢業生。調查分為預調查和正式調查兩個階段,預調查階段回收有效問卷312份,正式調查階段共計發放問卷2528份,其中有效問卷2384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4%。
3.3 變量設計
3.3.1 解釋變量:文化資本
Bourdieu(1986)認為,文化資本可表現為具體化、客觀化和制度化三種形態。本研究在衡量家庭文化資本與大學文化資本時依據這三種形態層面設計測量指標。
(1)家庭文化資本。借鑒Bourdieu(1986)、DiMaggio(1982,1985)、Tramonte和Willms(2010)、Dumais和Ward(2010)、Tan和Liu(2018)、郭叢斌和閔維方(2006)、孫遠太(2010)、仇立平和肖日葵(2011)、張文宏和蘇迪(2018)關于文化資本的測度,經過預調查階段的項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本研究從具體化形態(包括家庭文化習慣、文化氛圍、父母閱讀習慣、父母教育支持、親子交流)、客觀化形態(包括家庭文化物品、書籍雜志、高雅文化活動)和制度化形態(包括父母學歷、父母職業)形成了10個問卷題項作為家庭文化資本的測量指標,以定序變量或李克特五級量表反映。
(2)大學文化資本。考慮到大學生是大學文化資本的受眾群體,在研究中主要以大學生對就讀大學文化資本的感知來衡量大學文化資本。結合陳國民(2011)、羅生全(2010)、齊學紅(2007)關于學校文化資本的界定,借鑒王彬和崔玉平(2018)、蒙瑪琳(2016)、須圓(2013)、Lynn(2009)、廖慧宜(2006)對學校文化資本的測度,經過預調查分析,從具體化形態(包括大學建校歷史、社會聲譽、校風學風、師生關系、文化認同)、客觀化形態(包括教學設施、文化設施、校園環境、文體活動、學術科研成果)和制度化形態(包括規章制度、課程制度、就業制度等)形成了13個問卷題項作為大學文化資本的測量指標,以李克特五級量表反映。
3.3.2 中介變量:大學生人力資本
Schultz(1962)指出,人力資本是凝結于人身體之上的知識、能力與健康。Becker(1962,1964)認為,人力資本是員工或公司通過如教育或職業培訓等在技能上的投資。根據Schultz(1962)、Becker(1962,1964)等對人力資本的界定,考慮到大學生就業中健康要素的差異性較小,對大學生人力資本的測度中未列入健康要素。借鑒陳成文和汪希(2009)、喬志宏等(2011,2014)、賴德勝、孟大虎、蘇麗鋒(2012)、董克用和薛在興(2014)、黃敬寶(2014)、岳昌君和白一平(2018)等對大學生人力資本的測度,經過預調查分析,本研究形成了外顯性人力資本(政治面貌、學業成績、獎學金等榮譽證書獲得、其他學習經歷、實踐比賽獲獎、各種實踐經歷)和內隱性人力資本(道德品質素質、特殊文化能力、心理調適與承受能力、人際社交或溝通能力、工作與創新能力)層面的11個問卷題項作為大學生人力資本的測量指標,以定序變量或李克特五級量表反映。
3.3.3 被解釋變量:大學生地位獲得
關于地位獲得的測量,布勞-鄧肯模型以教育獲得和職業獲得作為衡量指標,威斯康星模型則主要從教育獲得、職業獲得和經濟收入進行綜合測度(王衛東,2013)。本研究從教育獲得、職業獲得和職業地位獲得綜合考慮大學生地位獲得。
(1)大學生教育獲得和職業獲得。依據職業狀況將大學畢業生分為未就業、職業獲得和教育獲得三類,分別賦值為0、1、2,進行綜合路徑分析,在此基礎上再細分為教育獲得和職業獲得兩組進行路徑分析。大學生教育獲得升級以大學畢業生畢業后是否成功實現繼續升學深造轉換來衡量,若成功實現升學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大學生職業獲得以大學畢業生畢業后是否順利簽訂就業協議或合同實現就業來衡量,若成功就業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2)大學生職業地位獲得。關于職業地位的測度,有些學者以職業階層作為衡量指標(如仇立平、肖日葵,2011;李黎明、廖麗,2019),也有些學者以職業收入和單位性質為衡量指標(如程誠,2012;高玉玲,2014)。本研究對大學生職業地位獲得以初職作為切入點,考慮到畢業生初職獲得時的職業階層差異性較小,對職業地位獲得以大學畢業生初職職業薪酬和單位性質進行綜合測度。初職職業薪酬根據初職單位的月收入進行分層,以1-5級定序變量衡量;初職單位性質則根據是否體制內為標準,將就職于政府部門或國有企事業單位賦值為1,就職于其他性質單位賦值為0。
3.3.4 控制變量
為了進一步分析在其他變量影響下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地位獲得之間的作用路徑是否發生變化,本文引入以下控制變量:
(1)性別。以虛擬變量反映,男生賦值為1,女生賦值為0。
(2)生源地。根據大學畢業生的生源地分為“農村或鄉鎮”、“縣或縣級市”、“市或地級市”、“直轄市或省會城市”四個層級,分別以1-4進行賦值。
(3)大學類型。許多研究中將大學類型作為大學生人力資本的衡量指標之一,而大學類型理論上符合大學文化資本的操作化指標,本研究為了在不低估學校類型的作用下更加清晰地分析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地位獲得的路徑,將大學類型獨立作為大學生人力資本和地位獲得的控制變量考慮。根據大學畢業生所就讀的大學類型分為“高職高專”、“民辦本科高校或獨立學院”、“國內外普通本科院校”、“211高校(非985)”、“985高校(非211)或國外知名高校”五個層級,分別以1-5進行賦值。
4 調查數據分析
4.1 樣本特征分析
參與調查的2384名大學畢業生中,男性和女性畢業生分別占比44.6%和55.4%;漢族和少數民族畢業生分別占比76.3%和23.7%;畢業于高職高專、民辦本科高校或獨立學院、國內外普通本科院校、211(非985)高校以及985高校或國外知名高校的畢業生分別占比約0.8%、7.4%、82.4%、7.2%和2.1%;所學專業分布于13個學科門類,其中工學39.3%、管理學20.4%、經濟學11.9%、理學11%、其他文科類13.5%、農學醫學和軍事學3.9%;生源地來自農村或鄉鎮、縣或縣級市、市或市地級城市、直轄市或省會城市的畢業生分別占比56.5%、18.6%、18.5%和6.4%。
4.2 問卷的效度檢驗
對家庭與大學文化資本、大學生人力資本問卷是基于理論分析與文獻研究并吸收借鑒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問卷所設計的,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鑒于理論分析已經確定了各個潛在因子所對應的觀測指標,本研究采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驗問卷的結構效度。運用Mplus軟件對相關變量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修正后的模型擬合指標匯總如表1所示(1)由于家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和大學生人力資本變量的觀測變量均以定序變量或李克特五點量表形式反映,根據王孟成(2014)的分析,盡管當選項數目在5個以上時將其作為連續變量可以獲得可靠估計結果(Johnson & Creech,1983),但這種數據實質仍然是類別數據。因此,本文在分析過程中將觀測變量作為類別變量采用WLSMV估計法進行分析。使用WLSMV估計類別變量模型時,推薦使用WRMR作為評價模型的擬合指標(Yu,2002)。。

表1 相關變量問卷的修正后CFA模型擬合指數表
表1中的數據顯示,修正后相關變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的χ2顯著性概率p值均大于0.05,達到顯著性水平,且WRMR<1,RMSEA<0.05,CFI和TLI值均大于0.95,表明模型均具有良好的適配度。同時,標準化參數估計結果也顯示,家庭與大學文化資本的三個構面、大學生人力資本的兩個層面的參數估計均具有統計顯著性,標準化因子值分別介于0.483-0.954、0.735-0.958、0.585-0.934之間,表明相關問卷測量指標具有合理或較好的效度。
4.3 問卷的信度分析
為檢驗相關變量測試問卷的信度,運用SPSS對相關變量及其結構層面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相關變量調查問卷的信度分析結果表
表2中的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和大學生人力資本潛變量的α系數分別為0.880、0.971和0.745,均在0.7以上,而這三個潛變量的因素結構面α系數也均在0.7以上,表明這三個變量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合理。
5 模型結果分析
根據地位獲得理論,盡管地位獲得主要通過職業獲得實現,但教育在地位獲得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此,采用均值法對相關潛變量進行賦值后,分別構建模型分析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與職業獲得狀況以及職業地位獲得的路徑。
5.1 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職業狀況的路徑分析
大學畢業生畢業后面臨著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實現就業或繼續升學實現教育升級兩種選擇,為檢驗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對大學生教育升級或職業獲得的作用路徑與效果,構建相關路徑分析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職業狀況的路徑模型
根據圖1的模型,采用Mplus軟件的類別變量估計法進行路徑分析,分析顯示,在職業狀況上,實現就業的大學畢業生1054名,占比44.2%,實現繼續升學深造的大學畢業生701名,占比29.4%,而未就業的大學生有629名,占比26.4%。路徑分析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職業狀況的路徑分析結果
表3中的數據顯示,對總體職業狀況和教育獲得組、職業獲得組的路徑分析模型擬合值WRMR分別為0.001、0.000和0.000,刪除不顯著路徑后的WRMR值分別為0.290、0.156和0.626,模型均擬合合理。分析結果表明:(1)家庭文化資本和大學文化資本均對大學生人力資本具有非常顯著的正效應,它們可以聯合解釋教育獲得組和職業獲得組的大學生人力資本變量的14.2%的變異量。(2)大學生人力資本狀況對大學生教育獲得和職業獲得均具有顯著正效應,且對教育獲得的影響(0.375***)比對職業獲得的影響(0.256***)更大一些。家庭、大學文化資本與大學生人力資本三個變量共同解釋了大學生教育獲得的16.1%的變異量和職業獲得的6.4%的變異量。(3)家庭文化資本在大學生總體職業狀況上具有一定顯著的直接正效應(0.063**),主要體現在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升級的直接正效應(0.072*)上,但其對大學生職業獲得卻具有較弱顯著性的直接負面影響。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資本豐富的大學生更傾向于選擇教育成就升級,而升學深造未成功的大學生通常也沒有選擇就業而是選擇再次備考。同時家庭文化資本還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教育升級和職業獲得均產生非常顯著的間接正效應(0.066***),其中對教育獲得的間接正效應(0.112***)比對職業獲得的間接正效應(0.059***)更強。總體而言,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的總效應為0.184,其中約60.9%是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發揮的作用,而對大學生職業獲得則基本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發揮間接正效應。(4)大學文化資本對大學生的教育獲得和職業獲得均未發揮顯著直接效應,但卻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教育獲得(0.056***)和職業獲得(0.063***)發揮顯著間接正效應,但這種效應均較小。
5.2 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職業地位的路徑分析
運用Mplus軟件對已就業大學畢業生家庭和大學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職業地位的分析顯示,初職職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3001-5000元、5001-7000元、7001-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的畢業生分別占19.8%、47.1%、22.8%、7.5%和2.8%,而就職于政府機構或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畢業生占41.3%,民營、外資和其他單位的畢業生占58.7%。路徑模型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

圖2 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職業地位的綜合路徑圖
根據圖2的分析結果,文化資本、人力資本與大學生職業地位的路徑模型擬合指數WRMR值為0.001,模型擬合較好。分析顯示:(1)家庭文化資本與大學文化資本對大學生人力資本均具有非常顯著的正效應,大學文化資本(0.265***)比家庭文化資本(0.221***)對大學生人力資本具有略強的正向影響。它們聯合解釋了已就業大學生人力資本變量的14.4%的變異量。(2)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職業薪酬產生非常顯著的正效應(0.215***),而對其職業單位性質的效應呈現弱正向顯著性(0.105*)。家庭、大學文化資本與大學生人力資本三個變量可以共同解釋大學生職業薪酬的7%的變異量和職業單位性質的2.9%的變異量。(3)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均是既產生直接正效應,又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產生間接正效應,但在對大學生職業薪酬的影響上,其直接正效應呈現弱顯著性(0.077*),而間接正效應則呈現強顯著性(0.048***=0.221×0.215),在對大學生職業單位性質的影響上,其直接正效應(0.097*)和間接正效應均呈現弱顯著性(0.023*=0.221×0.105)。總體而言,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總效應分別為0.125和0.12,表明其對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影響中分別有約38.4%和19.2%是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發揮的作用。(4)大學文化資本對大學生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直接效應均不顯著,但卻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發揮間接正效應。其中,大學文化資本對職業薪酬的間接效應(0.057***)比其對職業單位性質的間接效應(0.028*)更顯著,且這種效應更大。
基于綜合路徑模型分析結果,剔除兩條不顯著路徑之后的模型標準化效應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剔除不顯著路徑后的模型標準化效應分析結果表
表4中,模型擬合指標結果顯示,剔除兩條不顯著路徑后路徑模型擬合WRMR值為0.325,模型擬合依
然良好。復回歸分析決定系數結果顯示,剔除不顯著路徑后,家庭文化資本和大學文化資本對人力資本變量的聯合解釋變異量略有增強,而家庭、大學文化資本和大學生人力資本對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聯合解釋變異量則略微減弱。標準化路徑結果顯示,家庭文化資本對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總效應、直接正效應和間接正效應均無較大變化,而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其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影響有所提升,大學文化資本對其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的間接效應也略有增長。
5.3 進一步研究
基于對教育獲得、職業獲得和職業地位獲得路徑模型的分析,繼續納入控制變量分析相關路徑的變化,并探討對因變量解釋變異量的影響。納入控制變量的路徑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引入控制變量的路徑分析結果表
表5的結果顯示,(1)性別對大學生實現就業和職業單位性質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對初職薪酬也具有較顯著的影響,但對教育獲得并未產生顯著影響,這意味著男生在實現就業和就業單位性質、薪酬上都比女生更具有優勢;生源地主要對大學生職業單位性質具有較顯著的影響,表明來自于城市的大學生更易獲得體制內的職業,而生源地對大學生是否實現升學、就業或初職薪酬都不產生顯著影響;學校類型對大學生人力資本具有積極影響,而其對教育獲得、初職單位薪酬和單位性質不僅產生積極的直接影響,還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它們形成不同程度的間接影響,尤其是在大學生教育升級和初職單位薪酬方面的影響更加顯著,但其對大學生是否實現就業卻不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僅僅通過對大學生人力資本的作用產生一定間接效應。(2)在對教育獲得的作用路徑上,引入三個控制變量后,家庭文化資本的直接效應減弱,不具有顯著性,而家庭文化資本和大學文化資本通過大學生人力資本的中介作用所產生的間接效應依然顯著,但影響程度有所下降,這主要是由于學校類型在其中所發揮的顯著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所導致的,說明在大學階段所就讀高校的品牌質量對能否實現教育升級比家庭所發揮的作用更大。學校類型的引入使得相關變量對大學生人力資本變異量的聯合解釋從14.2%上升至16.4%,而對教育獲得的聯合解釋變異量從16.1%上升至24.1%。(3)在對職業獲得的作用路徑上,納入控制變量后家庭文化資本和大學文化資本對其依然不產生顯著的直接效應,而主要通過人力資本的中介作用發揮間接效應,但由于性別的影響和學校類型的間接效應,它們對大學生職業獲得的間接效應程度略微增強和減弱。性別和學校類型的影響使得相關變量對大學生人力資本的聯合解釋變異量從14.2%上升至15.8%,而對教育獲得的聯合解釋變異量從6.4%上升至7.8%。(4)在職業地位的作用路徑上,納入控制變量后,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生職業薪酬依然同時發揮直接和間接效應,但其對大學生職業單位性質卻不再具有顯著直接效應,這主要是由于生源地對大學生職業單位性質的顯著效應弱化了家庭文化資本的直接效應,性別的強顯著效應和學校類型的弱顯著效應也同樣產生了一定影響。而大學文化資本對職業薪酬和職業單位性質依然僅產生顯著間接效應。性別、生源地和學校類型的影響使得相關變量對人力資本的解釋變異量從14.4%上升至15.9%,對大學生職業薪酬的聯合解釋變異量從7%上升至12.8%,對大學生職業單位性質的聯合解釋變異量從2.9%上升至7.6%。總體而言,盡管受到控制變量的影響,家庭、大學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對大學生教育獲得、職業獲得和職業地位的影響產生了少許變化,但相關路徑依然較穩定。
6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了家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與大學生人力資本對大學畢業生地位獲得的作用路徑,研究發現:
第一,家庭文化資本對大學畢業生實現教育升級、獲得更高薪酬和體制內的職業均具有弱顯著的直接正效應,但在性別、生源地和學校類型等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它對大學畢業生的教育升級和初職單位性質不再產生顯著的直接正效應。而大學文化資本對大學畢業生教育獲得升級、職業獲得或獲取更高薪酬和體制內的職業均不產生顯著的直接效應。
第二,家庭文化資本越豐富、所就讀的大學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所積累的人力資本也會越多,而大學生所積累的人力資本越豐厚,則其畢業后更有可能實現教育升級和就業,也更有可能獲得薪資報酬更高和體制內的職業。即家庭文化資本和所就讀大學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大學生越有可能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實現教育獲得的升級、順利就業和獲得地位更高的職業。
第三,男性大學生比女性大學生更容易實現就業和獲取薪酬更高或體制內的職業,但在實現繼續升學深造上卻不具有優勢;來自于城市的大學生更可能獲得政府機構或國有企事業單位等體制內的職業;就讀大學的品牌越強的大學生越有可能實現教育升級、獲得更高薪酬和體制內的職業,而來自品牌更強大學的大學生所積累的人力資本也可能更多,進而使他們更易實現升學深造、順利就業和獲得更高地位的職業。
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兩因素對大學生地位獲得具有雙重驅動作用,在大學生地位獲得上,除了家庭代際傳承和個體后天努力兩股力量始終發揮作用,學校過程建構也在其中發揮著間接作用。大學生人力資本是大學生經由教育所獲得的個體特質,文化資本雖側重于教育的家校建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一種特質。一方面,家庭教育通過文化資本的代際傳承發揮教育的家庭建構意義。家庭是文化資本代際傳遞的重要場所,大學生受到家庭場域父母文化資本形式的浸染,塑造他們獨特的慣習,對于他們接受或適應學校和社會場域主流文化產生顯著影響,進而影響大學生在個體特質培養和職業行為選擇方面的成效。另一方面,大學教育通過建構與主流社會相適應的文化資本,促進大學生個體特質的獲得,發揮學校在教育中的作用。盡管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強調,所有的“教育行為”客觀上都是“符號暴力”,因為它是通過一種強權所強加的文化專斷,使得具有文化資本優勢的精英階層的子女更能在學校教育中占據優勢。但大學學校教育不僅為大學生學習知識和掌握技能創造受教育的條件,同時也在向大學生傳遞它們的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通過師生之間的傳遞與繼承實現校內代際傳遞,進一步對處于大學場域的大學生人力資本積累發揮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大學生地位獲得。因此,大學生家庭與大學文化資本的傳承與建構不僅僅作用于教育過程中,也通過對人力資本積累發揮作用而與個體特質同時呈現于教育的結果之中。
本研究對于在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框架下,發揮教育的家校建構與個體特質的相互關系,促進大學生保持優勢階層地位或實現階層地位向上流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基于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家庭應當適當且有效地利用文化資本傳承實施干預,充分發揮教育的家庭建構作用。本研究顯示,家庭文化資本因素能夠直接或間接潛移默化地影響大學生的地位獲得。父母自身提升教育程度、秉持開明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觀念、注重營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和開放的親子交流溝通環境,有效利用制度化、客觀化與具體化家庭文化資本,能夠為子女創造良好的客觀文化條件和引導子女恰當利用文化產品,促進大學生子女積累人力資本,發揮家庭文化資本在教育獲得上的作用。
第二,大學應當建構與主流社會相適應的文化資本,發揮學校過程建構在大學生地位獲得中的間接作用。大學需要建立良好的人文環境、良好的校風學風、和諧的師生關系、完善的人文設施、多樣的文化活動、合理的規章制度、適宜的課程結構等,形成符合主流背景的制度化、客觀化與具體化學校文化資本,充分發揮全體教師和大學生群體的共同作用,實現大學文化的資本化,并進一步將大學文化資本與大學生家庭或社會文化資本相結合,促使大學文化資本的提升,使之價值內化至教師和大學生群體。
第三,大學生應當全方位多維度積蓄人力資本,獲得在就業市場上更具優勢的個體特質。根據本文的研究,大學生家庭文化資本與大學文化資本主要是通過人力資本來影響其地位獲得,人力資本依然是大學生在教育升級、職業獲得與職業地位獲得中的關鍵直接因素。人力資本是由外顯性人力資本和內隱性人力資本構成的有機整體,這就需要大學生從顯性與隱性人力資本兩方面積累多種性質形態的人力資本,獲取具有競爭優勢的知識與技能,促進在就業市場上實現地位的向上流動。
第四,依托政府與社會力量規范高等教育就業市場,營造公平公正的教育與職業環境。本文的分析顯示,性別、生源地等因素對大學生教育獲得、職業獲得和職業地位具有一定影響,打破這種客觀差異化,需要政府通過適當的政策干預強化勞動力市場建設與管理,也需要用人單位、就業服務機構和社會媒體機構等多種社會力量共同努力營造良好的勞動力市場環境。
雖然本研究在某些方面擴展了以往關于這一領域的研究,所采用的調查數據涵蓋了多個區域不同家庭不同類型高校的大學生樣本,且本研究中的路徑分析受調查樣本地域的直接影響較小,其影響更多地反映在家庭與學校特征的影響中,故而樣本數據與研究結論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由于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樣本量有限,數據主要通過半隨機發放獲取,并非絕對完全的隨機調查,且調查數據的地域分布并非完全均衡,可能導致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后續研究還需要繼續擴大樣本量,囊括所有地區全部高校的大學生樣本進行分析,以期避免研究結論可能存在的地域局限性,進一步提升研究結論的準確性與普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