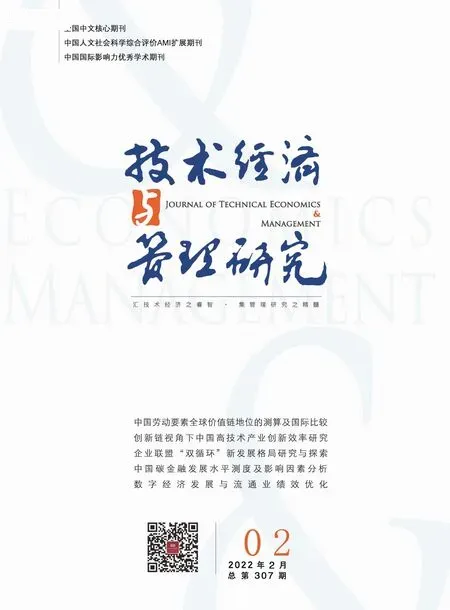經濟波動、社會性財政支出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
何柯樺,梁 微,葛宏翔
(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廣東 廣州 510900)
一、引言
經濟波動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一直是經濟學家們十分熱衷研究的問題。但到目前為止,經濟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依然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認為經濟波動促進了經濟發展(Canton,2002;Oikawa,2010),也有一些研究認為經濟波動阻礙了經濟發展(Badinger,2010;Wang&Wen,2011;Annicchiarico等,2016),還有一些研究認為經濟波動與經濟發展沒有明確的聯系(Solow,1997;Dawson &Stephenson,1997;Posch &Walde,2011)。雖然學者們對于經濟波動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的觀點不一致,但他們都認為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中國經濟波動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國內學者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內學者有盧二坡、王澤填(2007),盧二坡、曾五一(2008)以及陳昆亭等(2012)。然而,這些學者的研究并沒有清晰地揭示出經濟波動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渠道。從理論角度來看,經濟波動影響經濟發展的渠道是多方面的,但政府支出可能是其中最為重要和最易忽視的(Jetter,2014)。如果經濟波動是通過一定的渠道影響經濟發展,那么單獨考察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就不全面,將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分離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可能更有價值。文章利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省際層面的面板數據,檢驗了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并揭示出了一個傳遞渠道:社會性財政支出。通過研究發現,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為負,間接效應為正,總體效應取決于兩者的強弱對比。間接效應主要通過社會性支出發揮作用,即經濟波動增加了社會性支出,而社會性支出對經濟發展存在積極作用。根據估計結果,在樣本期內,經濟波動影響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強化,但是經濟波動對社會性支出的影響隨著時間推移在下降,與此同時,社會性支出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導致經濟波動通過社會性支出間接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在弱化,使得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不斷強化。文章的主要貢獻是為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提供了更為精細的經驗證據。
二、文獻綜述
經濟周期與經濟發展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研究領域,在很長時間內被作為兩個獨立的問題進行研究。經濟周期理論往往只關注經濟波動的特征、規律以及誘因。經濟發展理論則集中討論長期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宏觀經濟學新提出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將經濟波動與經濟發展納入了同一個分析框架(Kydl&Prescott,1982)。Lucas(1987)研究指出,相對于經濟發展,經濟波動不值得深入探討。然而,Ramey&Ramey(1995)的一項實證研究顯示,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負面作用,而且這種負面作用是持久的。這一研究結論引起了廣泛關注,隨后涌現出大量關于經濟波動與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證文獻,試圖尋找經濟波動影響經濟發展的理論根基與經驗證據。
關于經濟波動與長期經濟發展理論根基的探究,學術界主要基于內生增長理論(AK model)和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兩種分析框架展開。在內生增長分析框架下,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是不確定的。這是由于經濟波動引發的不確定使得消費者對未來充滿擔憂,從而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較高的儲蓄意味著較高的投資和較快的經濟發展。然而,經濟波動同時又降低了調整后的風險投資回報,使得企業投資動力不足,進而不利于經濟發展。因此,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效應取決于二者的強弱對比(Aghion&Banerjee,2005)。在熊彼特范式下,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原因在于其存在機會成本效應(Opportunity-cost Effect)和清洗效應(Cleansing Effect)。一方面,機會成本效應的存在使得企業面臨較低的短期投資回報時,長期投資反而變得相對有利,因此,在經濟波動增加時,企業傾向于增加R&D投入,通過技術進步促進了長期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經濟波動會迫使低效率企業淘汰出局,奠定了長期經濟發展的基礎(Schumpeter &Fels,1939;Saint-Paul,1993;Caballero & Hammour,1994;Aghion &Saint-Paul,1998)。
從理論角度考量,上述兩種觀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要弄清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實證研究很有必要。Ramey&Ramey(1995)、Kneller&Young(2001)、Rafferty(2005)以及Cerra&Saxena(2008)的實證研究均顯示,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然而,Caporale&Mckiernan(1996,1998)、Grier等(2004)以及Stastny&Zagler(2007)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Imbs(2007)的研究得出,關于經濟發展與經濟波動的研究,僅從總量層面檢驗二者的關系可能會遺漏許多重要結論。Jetter(2014)的研究也發現,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政府支出。
如果說政府支出是影響經濟波動與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那么對于中國而言,可能就更加值得重視,因為中國的政府支出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經濟波動的情況下,政府會增加何種類型的支出,這種政府支出的增加對長期經濟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由預防性儲蓄理論可知,經濟波動引發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對未來充滿擔憂,進而會增加儲蓄減少當期消費,基于政府層面,應該增加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穩定社會公眾的消費信心。如果這一理論假設成立,則得出的邏輯線條可能為:經濟波動引發社會性支出增加,社會性支出增加推動長期經濟發展。文章接下來的部分將試圖對這一假設進行驗證。
三、計量模型及數據
1.計量模型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文章建立如下計量模型,識別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被解釋變量經濟發展率y取五年移動平均值作為長期經濟發展的測量指標,為消除聯立性內生問題,模型中的解釋變量相對于被解釋變量滯后了一期:

其中,i和t分別表示地區和年份,τ為時期數,y為人均經濟發展率,volit為經濟波動,X為一組控制變量,包括固定資產投資、私營投資占比、存貨投資、對外開放以及城鄉差距。μi為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νt為時間效應,εij是隨機擾動項。α為回歸系數。
為檢驗社會性支出是否為一個傳遞渠道,間接的作用于長期經濟發展,在回歸方程(1)中引入社會性支出(sclit),構建回歸方程(2),方程(2)中的控制變量與方程(1)完全相同。

2.經濟波動的度量
目前比較常用的度量經濟波動的方法采用經濟發展率的滾動標準差,然而,Mallick&Debdulal(2015)指出這種做法存在一個潛在問題,即沒有分離經濟發展中的潛在長期成分和周期成分,導致直接用水平值測得的標準差并不能度量真實的經濟波動。借鑒Mallick&Debdulal(2015)的做法,首先對經濟發展率進行HP濾波處理,并利用HP濾波分離出來的周期成分的五年滾動標準差作為經濟波動的度量指標。在采用HP濾波時,平滑參數λ的取值十分關鍵,文章采用的是年度數據,參考大多數文獻的做法,取λ=100,同時,根據Ravn&Uhlig(2002)的建議取λ=6.25進行HP濾波,并將其作為穩健性檢驗。
3.其他變量說明
經濟發展率:為剔除規模效應,更加客觀地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此采用地區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作為經濟發展的測量指標。具體做法為,首先以各地區1978年為基期的GDP平減指數將各地區GDP的名義值調整為實際值,再取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差分得到地區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社會性支出:借鑒郭慶旺和賈俊雪(2009)以及呂冰洋和毛捷(2014)的做法,將財政支出科目中的科教文衛支出定義為社會性支出,并以各地區實際社會性支出占地區實際GDP的比重來衡量。由于在2007年后政府支出科目做了改革,因此,政府社會性支出的數據區間為1978—2006年,對于這期間部分數據存在缺失的情況,采用插值法進行補齊。人均收入:采用各地區1978年為基期的人均實際GDP衡量。固定資產投資:采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衡量。私營投資占比:以私營個體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來衡量。存貨投資:采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中存貨增加額占GDP的比重衡量。對外開放: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由于進出口貿易以美元計價,采用當年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匯率進行轉換。城鄉差距: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來衡量。以上數據來自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以及各省區市的統計年鑒。
4.數據的統計性描述
根據以上說明,進一步將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結果報告在表1中。

表1 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四、實證結果及穩健性分析
1.基本回歸結果
采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法(LSDV)對回歸方程(1)和(2)進行估計,同時控制了不可觀測的地區個體效應和年份效應,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及組內自相關,對回歸中的標準誤以地區聚類(Clusters)進行校正,并將結果報告在表2中。
首先不考慮社會性支出,只考慮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見表2中的模型1~模型4以及模型6。模型1~模型3為經濟波動與經濟發展的兩變量回歸,雖然經濟波動的估計系數為負,但在同時控制地區和年份效應后,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遺漏變量的緣故所致。因此,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入人均收入、固定資產投資、私營投資占比、存貨投資、對外開放以及城鄉差距等控制變量,見模型4與模型6,結果顯示,引入這些控制變量后,經濟波動的估計系數依然為負,但不顯著。進一步地引入政府社會性支出,見表2中的模型5與模型7。結果顯示,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與此同時,模型7中經濟波動的估計系數變得顯著。上述回歸結果表明,經濟波動作用于長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性支出是一個關鍵因素,經濟波動直接降低了長期經濟發展,但通過社會性支出間接促進了長期經濟發展。

表2 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五年平均經濟發展率)
2.進一步討論
在上述回歸分析中,對被解釋變量(長期經濟發展)的取值為經濟發展的五年均值,進一步對被解釋變量取七年和十年均值,以考察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效果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改變,結果見表3,其中,模型8~模型9顯示的是被解釋變量取七年均值的回歸結果,模型10~模型11顯示的是被解釋變量取十年均值的回歸結果。對比表3中的模型8~模型11與表2中的模型6~模型7,各主要變量的估計系數符號未發生變化,經濟波動的系數變得更加顯著。同時,還表現出兩種情形:第一,經濟波動的系數估計值不僅更加顯著,而且絕對值在逐漸增大,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得到了強化。第二,社會性支出的系數雖然依然顯著為正,但其絕對值在逐漸的衰減。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不但沒有衰減,反而得到了強化,但間接效應卻在不斷減弱。

表3 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七年和十年平均經濟發展率)
3.經濟波動與社會性支出
以上回歸分析得出的經濟波動通過增加社會性支出渠道間接地促進了長期經濟發展的結論是否成立,還需要進一步檢驗,即需要檢驗經濟波動是否顯著地增加了政府在社會性支出的投入。為此,建立如下的回歸方程。
其中,i和t分別為地區和年份,τ為時期數,sclit為社會性支出,volit為經濟波動,Z為一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收入、人口規模、對外開放以及經濟發展率。μi為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νt為時間效應,εij是隨機擾動項。β為回歸系數。
對此,分別取社會性支出的五年、七年和十年均值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法(LSDV)對回歸方程(3)進行估計,結果見表4。可以看出經濟波動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經濟波動的確促使了政府增加社會性支出投入。進一步觀察模型12~模型14中經濟波動的系數估計值,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波動的系數估計值在減小,而且顯著性水平也在降低,即經濟波動促進政府增加社會性支出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減弱。

表4 經濟波動對社會性支出的影響(五年、七年以及十年社會性支出均值)
4.經濟波動、社會性支出與長期經濟發展——3SLS估計
前述分析表明經濟波動直接地降低了長期經濟發展,但通過社會性支出渠道間接地促進了長期經濟發展,然而,如果經濟波動同時決定了長期經濟發展和社會性支出,就存在內生性問題。針對這一問題,進一步建立回歸方程(4)與(5)組成一個方程系統,并借助3SLS方法對方程組進行估計:

表5列出了3SLS的估計結果,模型15a~模型17a顯示的是回歸方程(4)的估計結果,對應的長期經濟發展分別為五年、七年和十年經濟發展率的均值,模型15b~模型17b顯示的是回歸方程(5)的估計結果。觀察表5的估計結果,發現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作用顯著為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還在不斷強化。社會性支出對長期經濟發展的作用顯著為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性支出對長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在降低。與此同時,經濟波動對社會性支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的結論依然成立。這與前述分析一致,即經濟波動直接降低了長期經濟發展,但其促使社會性支出的增加又顯著地促進了長期經濟發展。為觀察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其強弱對比,進一步計算出了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總效應,結果見表6。據此發現,對于以五年、七年和十年平均經濟發展率衡量的長期經濟發展而言,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分別為-0.50%、-0.51%和-0.55%,間接效應分別為0.03%、0.02%和0.02%,總效應分別為-0.47%、-0.49%和-0.53%,平均來看,當經濟波動每增加一個標準差,長期經濟發展將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

表5 3SLS估計結果

表6 直接效應、間接效應與總效應
5.穩健性檢驗
(1)改變經濟波動測量方法
在基準模型中,利用HP濾波后的周期成分的標準差度量經濟波動,但在利用HP濾波時,不同的平滑參數λ取值對應著趨勢項與波動項的不同權重,因此,λ的取值不同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在基準模型中,設定的λ值為100。Ravn&Uhlig(2002)建議年度數據的平滑參數λ取6.25,因此也取λ值為6.25進行濾波處理。在得到經濟波動的標準差后,對模型7、模型9和模型11進行重新估計,結果見表7中的模型18~模型20中,結果顯示,經濟波動和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估計結果與基準模型一致。參考以往文獻研究,文章直接利用經濟增長率的五年滾動標準差度量經濟波動,對模型7、模型9和模型11進行重新估計,估計結果見表7中的模型21~模型23。結果顯示,經濟波動和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估計結果也與基準模型一致。
(2)以金融危機前的數據作為樣本
鑒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為此,文章只選取金融危機前的觀測值對模型7、模型9和模型11進行重新估計,估計結果見表7中的模型24~模型26。結果顯示,經濟波動和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估計結果也與基準模型一致。
(3)控制技術進步(TFP)因素
考慮到技術進步對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一步在模型7、模型9和模型11中引入TFP增長率作為控制變量,對其進行重新估計,估計結果見表7中的模型27~模型29。結果顯示,經濟波動和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估計結果也與基準模型一致。

表7 穩健性檢驗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文章通過省際面板數據檢驗了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顯示:經濟波動直接降低了長期經濟發展,但經濟波動會促使政府增加社會性財政支出間接地促進長期經濟發展,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總效應取決于二者的強弱對比。根據估計結果,在樣本期內,經濟波動影響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強化,但是,經濟波動對社會性支出的影響隨著時間推移有所下降,與此同時,社會性支出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由此導致經濟波動通過社會性支出間接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在弱化,使得經濟波動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不斷得到強化。根據測算,經濟波動對長期經濟發展的總效應大約為-0.5%,也就是說經濟波動每增加1個標準差,將導致長期經濟發展降低約0.5個百分點。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是:一方面,應該提高宏觀調控能力,降低經濟波動;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適當加大社會性支出的投入,以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