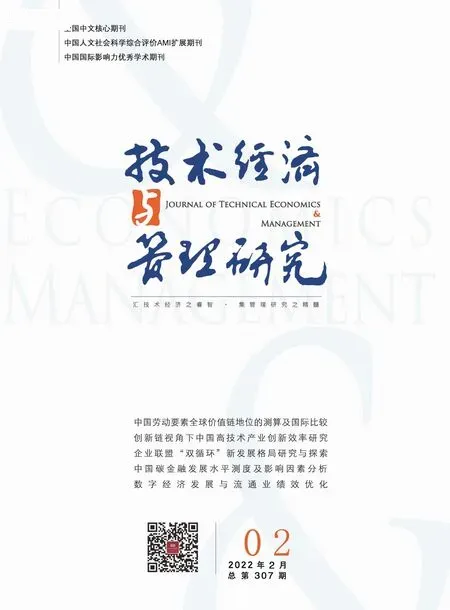數字創新模式、知識場活性與企業創新效率
——來自經驗取樣法的調查
夏天添
(1.江西科技學院學術委員會,江西 南昌 330000;2.江西省區域發展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00;3.江西科技學院 財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一、引言
數字技術與中國實體經濟的不斷深化融合,既推動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的發展,也對中國企業創新帶來了一系列變革[1]。“十三五”以來,數字技術成為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的新動能,而且隨著數字技術在新產品研發與技術創新過程中的深度應用,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相融合的意義得到了業界和學界的廣泛關注[1],更有學者從戰略融合角度出發[2],討論了數字技術和企業創新之間的深層內涵。故而,“數字技術和企業創新的融合效果,將如何影響企業創新效率”成為了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各大企業亟待解決的新問題。為此,通過對以往研究展開分析后,發現了以下不足之處:
1.忽視了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體系的融合機制
現有研究主要從“戰略匹配”和“戰略融合”兩個方面展開了研究:其一,戰略匹配強調企業創新戰略與數字化轉型戰略之間的匹配性[4],是否有利于企業高質量發展[5];其二,戰略融合強調數字化轉型戰略在企業創新戰略中的聯合作用[6]、協調作用與集成作用。如Vinit等的研究證實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升開放式創新效率與組織績效[7],但從戰略融合角度展開討論的研究則較為匱乏。然而,在新一輪數字革命浪潮的沖擊下,數字技術亦將廣泛應用于企業經營與創新過程中,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應被視作一個有機整體性企業行為[8,9],即需要從戰略融合角度,探究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及其對創新效率的影響機制。故而,文章參考Chesbrough的觀點[9],并結合企業創新的本質(即跨組織邊界的知識流動)[10-12],提出了“數字創新模式”的概念。數字創新模式是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實現高目的性的跨組織知識流動,并進行高度辨識與高效轉化(吸收)的現代化企業創新模式。該模式是一種集合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的融合性創新戰略,其功能含括創新需求驅動、跨組織邊界、平臺化、高效率等數字化優勢,能夠賦予企業全新的創新動力。
2.缺少過程機制與情境機制的討論
由于文章提出的數字創新模式,立足知識基礎觀視角,并強調企業數字創新模式中的知識資源流動與管控[13,14]。故而,文章力圖從知識基礎觀層面,討論數字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效率的過程影響機制。根據知識基礎觀理論,知識場活性作為一個極具代表性和效力的過程變量[15];一方面,體現了企業的知識活躍度管理實力[16],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企業知識資源儲備當量[17]。鑒于各種企業創新行為(模式)均需要調用知識儲備,而數字創新模式能否提高企業創新效率,亦取決于對企業內部的各類沉睡知識的喚醒效率與質量[18-20]。同時,在企業創新研究中,組織韌性被視作干擾企業創新戰略與實施的關鍵性調節因素[21]。按照組織韌性的強度差異,高組織韌性的企業在創新投入、過程管理、風險把控等方面,有較好的基礎與實力[22],能夠以較高的創新容錯性,保障創新戰略的正常實施[23];而低組織韌性的企業則在各項管理能力與機制保障體系方面較弱,難以抵御企業創新過程中的突發事件沖擊[24]。因此,本研究將一并討論知識場活性與組織韌性的有調節的中介作用,以探討數字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的過程機制與情境機制。
3.研究設計存在局限
鑒于以往研究多采用微觀靜態(截面)取樣、個案研究或宏觀面板取樣的研究設計,忽視了企業的多元性、市場的動態性,以及來自微觀層面的情境解釋,文章結論及建議對策亦存在一定的局限與不足[25]。為此,文章將采用經驗取樣法的動態取樣范式,突破以往研究靜態取樣與微觀層面研究不足的局限。
綜上所述,文章立足知識基礎觀視角,圍繞“數字技術和企業創新的融合效果,將如何影響企業創新效率”這一關鍵問題,以中國知識密集型企業為樣本,通過連續15周的經驗取樣調查,揭示數字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的深層影響“黑箱”,以及知識場活性與組織韌性的有調節的中介作用。
文章的理論模型圖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圖
二、研究假設
1.數字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
新時代背景下,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的戰略性融合,不僅蘊含著高效重組與配置企業知識資源的潛力,更能夠實現企業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數字化管理,打破創新戰略的預設框架。同時,立足知識創造視角,數字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來源于以下兩個方面[26]:
(1)知識搜尋方面
數字創新模式的本質在于突破企業傳統封閉式創新思維界限,通過不斷吸收外部異質性知識以實現高質量創新[27]。根據知識基礎觀理論,異質性知識將開拓企業創新思維,有助于激發企業創新靈感,提升企業創新效率與成效[28]。而隨著互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與企業(產業)的深化融合,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得到了突破,企業能夠利用各種形式的數字化知識交互機制,如企業社區、在線平臺等,推動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高效互動,并利用數字技術手段,主動搜尋企業創新所需的高價值的異質性知識,以豐富自身知識資源儲備[29]。
(2)知識利用方面
Teece認為提高企業創新效率的關鍵因素,不僅取決于創新本身的難度系數,還取決于企業實力的強弱[30]。一方面,數字創新模式多構筑于開放式數字平臺或技術工具之上,為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數字化創新,提供了虛擬化與規模化的跨組織知識交互渠道,為企業提供了大量知識資源,讓知識再造成為可能,并同時推動了企業的跨組織戰略協同[31];另一方面,數字創新模式需要企業具備相應成熟度的數字化水平,高數字化成熟度的企業,普遍采用系統化管理模式(如ERP系統、CRM系統等),以實現知識資源的高效調用與配置;因此,對于知識利用程度較高的企業,其在數字化創新過程中,能夠實現精準的成本與風險控制,進而保障預期的創新進度與效率[32]。
綜合上述,文章認為數字創新模式所實現的知識搜尋與知識利用的有機互動,推動了企業知識資源價值提升的良性循環,進而加快企業創新效率。故而,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創新模式正向顯著影響企業創新效率。
2.知識場活性的中介作用
“知識場”的概念,最早由野中郁次郎受電磁場理論啟發所提出,其認為知識場是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如大學、用戶、供應商、研究機構等)之間,通過跨組織的知識流動、交互、搜尋及再造產生的理論空間[15];各知識交互主體在該空間內,形成了無形的社會網絡聯結[16]。而知識場活性則是指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在知識場中所開展的各種知識流動與交互過程[17]。金珺等認為數字創新模式能夠優化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交互頻次、形式與質量,進而改善或優化企業創新效率。具體而言:
首先,數字創新模式加快了知識場中的知識流動機制。知識再造的過程是知識在顯性與隱性之間相互碰撞的交互過程。企業利用數字創新模式與其他創新主體所構建的創新戰略合作,一方面通過數據共享模式,拓寬了企業的創新知識供給渠道,并透過數字化創新平臺的協同機制與交易機制,拓展了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交互深度[31];另一方面,該模式加快了跨組織知識流動,隨著知識流動提速,知識場內的各類知識資源加速碰撞,推動了高模仿成本的隱性知識資源增長。同時,數字創新模式促進了企業的異質性知識增長。因此,數字創新模式可以讓企業通過精準高效的數字化程序,實現知識場中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精準知識交互,從而激發了知識場中的異質性知識活躍度。由此可知,數字創新模式的實施,不僅豐富了企業的知識儲備,更能夠通過異質性知識資源增加提高知識場活性。因此,文章認為數字創新模式將提升知識場活性。
其次,根據知識基礎觀理論,知識場活性促成了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氛圍與交互渠道,可以對企業現有知識資源進行深度挖掘,從而發揮知識重組的潛在價值,優化創新過程與環節,加快創新效率與成效。加之,根據SECI模型的觀點,隱性知識顯性化是知識場中各主體的初衷,即通過注冊專利、發布新產品等方式,實現知識的創新轉化。由此而言,知識場活性是決定企業創新效率的前因變量,通過刺激或催化知識場內的知識流動與知識碰撞,將加快知識資源的顯性化進程,企業創新效率亦隨之優化與提升。因此,文章認為知識場活性將加快企業創新效率。
綜合上述,文章認為企業可以通過數字創新模式,激發其所構建的創新知識場中的知識交互潛力,從而擴大企業知識儲備和創造更多異質性資源,強化知識場活性;而知識場活性的強化亦促進了企業與各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關系,能夠更好地推動隱性知識的顯性催化進度,從而加快企業創新效率。故而,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H2:知識場活性會在數字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的正向顯著影響之間,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
3.組織韌性的調節作用
縱觀以往研究發現,組織韌性的差異將影響企業在創新戰略上做出不同的規劃、部署與決策。路江涌等人發現高組織韌性的企業,多熱衷于低成本的創新模式,如開放式創新模式、迭代創新模式等。這是源于一方面,組織韌性能夠優化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強化企業風險應對能力,以降低由突發事件沖擊,所造成的創新風險;另一方面,組織韌性能夠加速企業知識資源的顯性化進程,以加快產品研發效率,降低產品替代風險。因此,在數字革命浪潮下,高組織韌性的企業更加注重數字化轉型,以及通過構建數字創新模式,實現市場動態性的精準掌控,加快企業創新效率,以快速填補市場需求。
張秀娥等人認為企業若要通過實施數字創新模式,來激發知識場活性,以加快企業創新效率,其核心問題在于“企業如何在知識場中吸收高匹配度的異質性知識資源,并將其順利轉化”[22]。當企業的組織韌性較高時,企業對內部知識體系的弱點、不足及局限之處便越了解,便可在知識場中,進行有目的性的知識汲取;并且,高組織韌性將幫助企業高效、科學與精準的配置(內化)外部異質性知識資源,以用于完善新產品研發流程與提升企業創新效率。反之,當企業不具備高組織韌性時,其在風險應對、資源配置及經營戰略等方面,或居于劣勢,或缺乏預案及應對措施;即便通過數字創新模式在知識場中,獲得了大量異質性知識資源,也可能會因缺乏資源調配能力或重組轉化能力,或是在突發事件沖擊的干擾下,導致企業內部知識資源“沉睡化”[24];加之,在以往研究中,雖未形成沉睡知識必然提升企業創新效率或成效之觀點,但多數學者的觀點均證實,沉睡知識的“喚醒”成本頗高。故而,對于低組織韌性的企業而言,知識資源的過量儲備,未必能夠改善企業的創新效率[20]。
綜合上述,文章認為在企業實施數字創新模式的過程中,組織韌性能夠充分發揮數字化的優勢,進而提高在知識場中的知識流動速度,以及提升異質性知識資源獲取的精準度,進而以低風險與低成本的優勢,高效推動異質性知識資源的顯性轉化,以加快企業創新效率。故而,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H3:組織韌性能夠調節數字創新模式對知識場活性的正向顯著影響,并進一步間接影響企業創新效率。
三、研究設計
1.研究計劃
文章將中國知識密集型企業為樣本,并借助MBA聯盟等渠道,得到83家企業的支持,突破了以往研究設計中,靜態取樣或單一案例之局限,文章采用經驗取樣法的動態研究范式展開調查。具體調查計劃包括兩個步驟:
步驟一:向樣本企業的管理者及其所屬研發團隊的相關員工,告知調查計劃的全部內容、流程及要求,并收集相關資料信息(含企業及被試者的人口統計學信息,以及由管理者所填答的組織韌性量表)。
步驟二:在正式調查的連續15周內,要求被試者(研發員工)于每周周末下午18點(時限為15分鐘),依照本周的實際工作情況,填寫“數字創新模式”和“知識場活性”量表,并同時要求被試者(管理者)提供可用于核算研發團隊創新效率的有關數據。
在經過連續15周的經驗取樣調查后,文章按照未開展數字化創新、未連續完成調查、重復回答等標準剔除無效樣本后,共得到了71家企業的管理者及372名研發員工的配對數據,樣本回收率為85.54%。從樣本所屬行業來看,制造業、現代服務業與IT業的樣本分布為19.7%、67.6%和12.6%,且大中型企業占比50.7%,具備5年及以上經營年限的樣本高達81.53%;同時,從被試者方面來看,具備3年及以上現職工作經歷的高管占比為70.76%,而員工占比則為80.10%,且二者的本科率高達86%。由此說明,本次調查所回收的樣本數據呈均衡分布,達到了開展相關檢驗的基本門檻。
2.測量工具
數字創新模式。鑒于以往研究中尚未開發有關數字化創新的相關量表,故文章參考Chesbrough等的研究觀點與建議[33],從知識流動的過程機制角度,結合數字技術與開放式創新的戰略融合視角,在原有的開放式創新量表基礎上,融合了在中國企業創新實踐中,最為常用的數字技術,并構建了如“本公司可以通過數字化平臺,完成與其他合作方的協同創新”等在內的5題項量表,由研發員工填答,并采用Likert 7點量表進行觀測,再按照團隊人數取均值計算(Cronbach's α=0.879)。
企業創新效率。鑒于以往研究中尚未開發有關企業創新效率的相關量表,故文章借鑒Ganesan等的做法[34],基于被試者(管理者)提供的企業創新投入產出數據,利用DEAP 2.1軟件,分別從“提前完成時長”“專利授權進度”“計劃完成度”及“過程管控”四個方面核算企業創新效率。并依照對應樣本企業的實際創新效率轉化為分類變量(Cronbach's α=0.834)。分類依據為“1~7”,分別對應創新效率提升“10%及以下”“11%~0%”“21%~40%”“41%~70%”“71%~100%”“100%~200%”“200%以上”。
知識場活性。借鑒Senoo等開發的4題項量表[35],由研發員工填答,并采用Likert 7點量表進行觀測,再按照團隊人數取均值計算(Cronbach's α=0.912)。
組織韌性。借鑒Kantur&Iseri開發的9題項量表[36],并采用Likert 7點量表進行觀測(Cronbach's α=0.871)。
四、數據分析
1.描述性分析
由于數字創新模式、知識場活性及企業創新效率均為管理者與研發員工的填答結果聚合,故需要對組間層次變量進行數據聚合分析。本研究參考相關學者的做法展開分析[37],結果顯示各主要變量的數據聚合結果滿足數據聚合的相關標準。
依據描述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說明各主要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干擾。

表1 描述性檢驗結果
2.區分效度分析
根據CMV分析的結果顯示,首因子方差率為36.42%,小于50%的閾值,說明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擾較小;同時,MCFA分析的結果證實,四因子模型的擬合度最優,說明文章提出的假設模型具備一定水平的區分效度。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結果
3.假設檢驗
文章按照方杰、溫忠麟的做法[38],采用多層嵌套模型進行假設檢驗,具體結果如下:
第一,直接作用檢驗。根據表3的M1列的結果,數字創新模式正向顯著影響企業創新效率(γ=0.394,p<0.001)。故H1的假設得到了檢驗。
第二,中介作用檢驗。文章借鑒溫忠麟等人的做法,在H1的假設得到驗證的基礎上,同時,分別檢驗了數字創新模式與知識場活性,以及知識場活性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的直接作用,并在三者均顯著的前提下,將知識場活性納入M1的模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如表3的M2列):知識場活性能夠在數字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γ=0.360,p<0.001,γ間接=0.190,p<0.001,95%,CI=[0.153,0.231])。故H2的假設得到了檢驗。
第三,調節作用檢驗。文章借鑒Edwards&Lambert的做法[39],將組織韌性、數字創新模式及二者的交互項作為自變量,將知識場活性作為因變量,進行調節作用檢驗。結果顯示(表3的M3列和圖2)組織韌性能夠顯著調節數字化創新對知識場活性的提升作用(γ交互項=0.184,p<0.001)。同時,為進一步檢視組織韌性的調節作用,文章按照“拔靴法”的做法,將組織韌性以增減一個標準差的方式,拆分為高低兩個組別并分別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在高水平(γ高=0.236,p<0.001,95%,CI=[0.193,0.284])、低水平(γ低=0.128,p<0.001,95%,C=[0.090,0.169])與差異水平下(Δγ=0.108,p<0.001,95%,CI=[0.147,0.219]),組織韌性均可顯著調節數字化創新對知識場活性的提升作用,并進一步間接提升企業創新效率。故H3的假設得到了檢驗。

表3 假設檢驗結果

圖2 組織韌性的調節作用圖
五、結論與啟示
1.研究結論
在新一輪經濟變革與數字技術深化融合的背景下,市場競爭與需求的變化詭譎難測,企業須在時刻做好應對突發市場(事件)沖擊的準備與條件的前提下,持續推動產品研發與技術創新,方可謀得未來的生存空間。而在此過程中,數字創新模式無疑成為了深化與拓展企業創新邊界的關鍵。本研究基于知識基礎管理論,以中國71家知識密集型企業為樣本,展開了連續15周的經驗取樣調查,結果顯示:數字創新模式能夠顯著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知識場活性能夠在數字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發揮顯著的中介作用;組織韌性能夠顯著調節數字創新模式與知識場活性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進而間接影響企業創新效率。
2.理論貢獻
基于研究結論,文章的理論貢獻包括:
第一,開拓了企業創新的研究邊界。在以往研究中,企業創新領域的相關學者主要聚焦討論了數字技術在現代企業創新中的必然性與必要性,卻忽視了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之間的融合關系與成效。故而,文章基于知識基礎觀理論與信息系統管理理論,從戰略融合角度提出了數字創新模式,呼應了前人在數字化轉型趨勢下開辟新型企業創新模式的呼吁。同時,鑒于以往研究仍未就開放式創新與創新之間的影響關系,形成較為統一的觀點,文章立足微觀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剖析了數字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深層影響“黑箱”,證明了數字創新模式作為典型的開放式創新,能夠顯著提升企業創新效率與成效,這一結論響應了劉洋等的呼吁[1],更支持了本研究的核心觀點,即數字創新模式為加快企業創新進程,加快新產品市場投入進度,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該觀點的證實亦開拓了企業開放式創新的研究邊界,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與方向。
第二,闡明了數字創新模式的過程機制。縱觀以往研究,有關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效率或績效的研究,多為討論其二者間的直接影響機制,忽視了對過程機制的關注;尤其在數字經濟時代,創新的本質是知識的流動與交互,而以往研究卻鮮有學者從知識場角度展開實證檢驗。為此,文章的結論證實了知識場活性的完善與強化,能夠成為數字創新模式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的關鍵橋梁;該結論的得出亦得到了實踐的充分檢驗,也就是說在數字創新模式下,在知識場中的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有序流動與交互碰撞,可以增加知識傳導,提高隱性知識的顯性轉換進度,從而加快企業的新產品研發速度。該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詮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經營效率與質量的內在機理,更進一步厘清了數字創新模式的部分過程機制。
第三,揭示了組織韌性在數字創新模式的影響過程中的情境機制。文章檢視了組織韌性的下行效應,即組織韌性能夠強化數字創新模式對知識場活性的提升作用,進而間接提高企業創新效率。由此而言,高組織韌性的企業可以憑借強勁的企業實力與高創新容錯率,開展數字化創新,并激發知識場活性,實現更多異質性隱性知識的顯性轉化,以加快新產品研發進度與效率。該機制揭示了動態環境背景下,實現企業高效率創新與低風險創新的關鍵,亦是對張秀娥、滕新宇呼吁的響應,這對進一步探索現代企業知識管理有著重要的理論貢獻。
3.管理對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文章提出以下管理對策與建議:
(1)構建企業數字化基礎,逐步推進數字化創新
企業須打破傳統經營理念,采用現代化管理思維,開展企業數字化轉型,以完善企業運行機制與效率。具體而言:首先,企業須根據自身運行情況、市場競爭強度等因素,進行數字化轉型規劃,并按照業務關鍵性順序,逐步建設或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含設備、條件、軟件等);其次,在具備相關數字基礎的前提下,通過信息管理系統、在線平臺等數字化手段,將企業相關業務流程全面數字化,以推動企業精準化管理;最后,企業可通過云計算、在線社區、網絡平臺等數字化知識交互平臺,推進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知識融合,吸引各類創新主體參與,以進一步擴大知識場的規模與活躍度,實現企業高效率創新資源的“云供給”。此外,企業還可以通過深度開發數字孿生、AI、邊緣計算等先進算法(技術),開拓企業數字創新模式的2.0版本,從而實現“線上、高效、精準”的“人-機”協同創新。
(2)重視知識場活性管理,充分發揮知識轉化功能
企業須重視知識場活性,尤其是在跨組織知識流動時,企業亦需要根據自身組織韌性水平,選擇科學的知識管理策略。具體而言:首先,企業可以利用云端、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構建第一方知識庫系統,或是融入第二方或第三方知識庫系統,以作為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流動渠道,即構建知識場;其次,企業可在知識庫系統的原始功能上,添加社交、媒體、CRM、供應鏈等跨組織信息交互功能,以構建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信任與品牌印象,從而進一步激發知識場活性;最后,企業需重視知識場的日常管理,要做好制定知識場管理的運行規劃與應急預案,關注知識場活性的變化與趨勢,以寄期在知識場中攫取更多異質性知識資源,并促進其隱性知識的顯性轉化進程。
(3)加強組織韌性規劃,實現高容錯率數字化創新
“十三五”以來,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組織韌性的價值與功能,逐步受到了業界的關注與重視。文章的結論亦證實企業的組織韌性差異,亦決定了其數字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實際提升效果。故而,文章建議相關企業:首先,全面性審視企業資源配置,逐步優化完善現行企業資源配置局限與漏洞,并適時調整組織結構,以及業務流程機制;其次,綜合性評估業務流程與項目實施風險,逐一排查業務流程中可能出現的隱性風險,或可采用數字化風險模擬評估等手段,綜合評價其業務流程的風險強度,并通過數字化模擬,調整業務流程方案,以降低風險沖擊概率與傷害;最后,通過數字創新模式剖析出企業創新及創新進程改善所需的異質性知識類別,進而在有充分應急預案規劃下投入創新資源,實現高目的性知識流動與交互,從而精準獲取高契合度的異質性資源,或是戰略性知識資源,以降低沉睡知識成本,減少來自成本及風險方面的企業創新壓力。
4.研究局限與啟示
文章立足知識基礎觀理論,從戰略融合角度,提出了數字創新模式,并以企業的實際創新活動來觀測企業的數字創新模式開展程度,但該方式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檢驗與討論,未來可依照實際研究情境,采用如物聯網、PLM系統等不同技術的融合模式進行研究,或是以更加深入的融合性觀測方式加以分類,從而更好地解釋數字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效率及成效的作用機理。同時,文章僅從知識管理角度,討論了數字創新模式的過程機制,未來亦可從其他層面或角度,拓寬其過程機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