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包法利夫人》
李慶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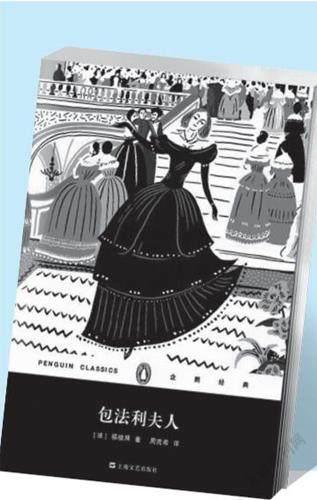
重讀《包法利夫人》,是想找回過去的閱讀記憶,福樓拜這部名著以前只讀過兩遍,許多情節都已淡忘。以前讀的是李健吾譯本,自己書架上找不到了,上網向圖書館借了一本,是周克希譯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因為兩個譯本并未同時在手,未做文字對比,僅憑閱讀印象不覺有高低之分,畢竟兩位譯者都是名家。據網上信息,如今中譯本已逾二十種,其中孰優孰劣,自有行內人士去評判。
周克希譯本有些人物譯名跟李健吾不同,如包法利先生的名字,李譯作“查理”,周譯是“夏爾”。愛瑪的兩個情人,李譯是“賴昂”和“羅道耳弗”,周譯為“萊昂”和“羅多爾夫”。對讀者來說,譯名最易先入為主,如永鎮那個藥劑師,留在腦子里的記憶還是“郝麥”,現在周譯作“奧梅”,一眼看去感到陌生。
考慮到李健吾的舊譯名較為讀者熟悉,本文依然沿用郝麥、羅道耳弗這些人名。引述原著則取自周克希譯文,因為手頭只有這個本子。作為非專業讀者,我只談閱讀感受,主要從故事本身來討論作家的敘事意圖和文本意涵。
福樓拜的現實主義或曰自然主義敘事歷來為人稱道,但納博科夫認為《包法利夫人》的現實主義只是一種“相對概念”。他的《文學講稿》(申慧輝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本文以下引述的內容為龔文庠所譯)專有一章講這部小說,舉述書中若干情節和細節,表明福樓拜的故事不乏違背生活真實的臆造。比如,羅道耳弗夜里招呼愛瑪去幽會,朝她臥室窗口擲砂石,包法利醫生居然毫無察覺。不但他從未發現妻子出軌的蛛絲馬跡,就連鎮上最愛管閑事的郝麥亦從未聽說愛瑪的風流韻事。就常理而言這不大可能。還有關于愛瑪騎馬的描述,以及馬車夫的過于老實天真,等等,似乎也不能令人信服。
愛瑪不是那種特別審慎謹細的性格,在她與查理的八年婚姻生活中,穿插著與賴昂、羅道耳弗的長期婚外情史,要瞞住自己老公實非易事,而福樓拜的手法就是一個“瞞”字。瞞得了一時誰說瞞不了一世,現實主義不排除這種可能,小說敘事本身緣從假定的邏輯。不過,在我看來,撇開納博科夫提出的那些疑問,女主人公性格的變化(成長史)卻是更值得質疑。
愛瑪,包法利夫人,一個被浪漫幻想和虛榮心引入歧途的少婦,以出軌偷情來擺脫庸常而乏味的人生,最終因債臺高筑而破產自殺。福樓拜詳盡地描述了女主人公自我毀滅的整個過程,這是中國人老話所說“自作孽”的故事。但起初這是一個純情少女,后來怎么變成一心追求榮華富貴的淺陋婦人(照納博科夫說來,她性格中有一種“冷酷的粗俗”),書中盡管給出種種鋪墊,依然不能勾連人物性格邏輯的草蛇灰線。
愛瑪出身于富裕農戶,她父親盧歐老爹被納博科夫認為是書中少數幾個“好人”之一,可以說她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她出場時,母親已經去世,她在家中服侍父親和料理農莊事務。之前她在修道院的寄宿學校“受過良好的教育”。據查理前妻打聽來的消息,我們知道愛瑪“會跳舞,懂地理,會畫畫,會繡掛毯和彈鋼琴”,頗有才藝。查理最初去農莊給老爹治腿時,就注意到廳堂上掛著一幅炭筆畫的密涅瓦頭像,是愛瑪獻給父親的作品。
書中第一部第六章是一個重要關節,這里以回敘手法介紹愛瑪在修道院的讀書經歷,但這一段除了善意的撒謊,未見有品性污點。她讀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諦》,讀司各特的歷史小說和中世紀行吟詩人的作品,她想象著“自己能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里,像那些身穿長腰緊身胸衣的城堡主人一樣,整天待在有三葉飾的尖頂拱門下面,雙肘撐著石欄,手托下巴,眺望遠處平野上一位騎黑馬戴白翎飾的騎士疾馳而來”。她就讀的寄宿學校雖說也是一種苦修教育,卻沒有多少禁錮心靈的清規戒律,反倒培養了她的浪漫情懷。音樂課上學到的那些恬靜的浪漫曲,打開了“情感世界的誘人幻景”,有些同學將各種畫冊帶入學校,女生們在寢室里偷看那些帶有異國情調或東方色彩的圖畫,這給她帶來遠方的想象……
這一章在于敷設初始化的浪漫底色,作者考慮到女主人公日后的變化,不忘記提示她村俗的一面—“她的性格,在熱情浪漫中間透出一股講求實際的意味。”世俗的欲念使她逐漸遠離信仰的奧義,使得修道院嬤嬤們對她備感失望。可是,她回到家里又懷念起修道院了,覺得鄉間生活令人生厭。作為敘事鋪墊,福樓拜在愛瑪性格中著意植入一種耽于想象又搖擺不定的特征。不過,這不足以提供她走向毀滅之途的動因,性格搖擺在常人身上亦常見,像愛瑪那種飛蛾撲火似的瘋狂卻不是常人所有。

渥畢薩爾城堡侯爵府的舞會,電影《包法利夫人》(1991)劇照
追溯愛瑪性格養成之思想來源,似乎主要在于文學閱讀。寄宿學校使她養成了閱讀習慣,婚后依然捧讀不輟,查理也跟別人說起,她就愛待在房間里看書。納博科夫認為,她接受的是“浪漫主義的陳腔濫調”和“淺俗的意象”,這未免責之過甚。其實,她經眼之書大多是經典作品,讀的是巴爾扎克、喬治桑、雨果的小說,像歐仁·蘇之類已屬等而下之。至于她是否真正理解原著的精義,那是另一回事,自然不能以學者標準去要求她。想必成千上萬的法國少女的閱讀書目也跟愛瑪相仿,如果說是讀書有害,而為什么偏偏是她成為被浪漫文學戕害的“這一個”?將閨中閱讀作為緣由,是以類型化經驗捏塑人物,非走向極致不可。
納博科夫那本書里說:“三種因素造就一個人:遺傳因素、環境因素,還有未知因素X。這三種因素相比,環境因素的影響力遠遠弱于另兩種因素,而未知因素X的力量則大大超過其他因素。”在愛瑪的故事里,很難說家庭遺傳因素給她帶來負面影響,此項姑且不論。納博科夫不認為環境因素有多重要,他說:“像包法利夫人這個人物一樣,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也是福樓拜精心創造出來的。所以,說福樓拜式的社會影響了福樓拜式的人物,就是在作無意義的循環論證。”好吧,這一項也暫且撇開,那么剩下就是未知因素X了。
未知因素X,應該就是某種不可預期的偶發事件,但納博科夫忙于分析“多層蛋糕”式的小說結構,并未說起愛瑪的那個X是什么。其實,小說第一部第八章的故事可以說就是那個X,這一章講述包法利夫婦應邀去渥畢薩爾城堡侯爵府上做客。因為查理給侯爵做過一個小手術,侯爵舉辦宴會那天作為答謝也邀請了他們夫婦。這是愛瑪平生唯一見識上層社會生活的一次機會,在那兒她與一幫貴族男女共度良宵,筵席的場面和各種美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還有餐后的舞會—從開場的四組舞到夜宵后的沙龍舞,他們徹夜狂歡。侯爵府上的排場和諸項吃喝玩樂,這里不便詳盡復述,總之對于愛瑪來說,這短暫的奢華生活著實讓她大開眼界。過去是現實境遇限制了她的想象,現在她有了人生的目標—
天蒙蒙亮了。她望著城堡的扇扇窗戶,目光久久在上面流連,一心想猜出昨晚見到的那些人都待在哪些房間。她向往了解他們的生活,渴望置身其間,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從這一刻起,愛瑪就不是原先那個愛瑪了。城堡的貴族生活顛覆她的三觀,原本對婚姻生活心滿意足的包法利夫人,開始對查理嘖有煩言,“她愈看他愈覺著不順眼”。其實,那天回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掉了家中的女傭。書中只說她頂嘴,難道不是嫌那女傭不順眼了?書中記下了城堡之夜給她帶來的持久影響。
……沃比薩爾(渥畢薩爾)之行,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一個窟窿,猶如暴風雨一夜之間在崇山峻嶺劈出了長長的罅隙。但她還是忍了:她把那身盛裝,連同鞋底被舞廳地板蠟染黃的緞鞋,小心翼翼珍藏在衣柜里。她的心宛如這緞鞋;一旦擦著華貴而過,便留下了無從拭去的痕跡。
回憶那次舞會,成了愛瑪的必修課。每逢星期三,她醒來便想:“哦!一星期前……兩星期前……三星期前,我還在那兒來著!”漸漸的,容貌在記憶中模糊了,四組舞的情景淡忘了;號服,府邸,不再那么清晰可見了;細節已不復可辨,悵惘卻留在了心間。
縱觀全書,這個事件是鑄成愛瑪悲劇的唯一的X因素。城堡之夜“細節已不復可辨,悵惘卻留在了心間”,此后愛瑪期待著侯爵還會在渥畢薩爾重開舞會,可是一直沒能等來侯爵府來人召喚。城堡的聲色娛樂將她帶入不可想象的愉悅之境,亦將其心中朦朧的浪漫之念轉化為明晰的物質之欲。福樓拜在書中寫道:“一次偶然事件,有時會引發一連串的波折,會帶來風云突變的結局。”愛瑪沉入黑暗之際,開始徒勞地叩擊鎖閉的命運之門。
細細梳理愛瑪性格發展的敘事邏輯,大致就是這樣兩點:一是文學閱讀,啟發了她那種詩和遠方的浪漫想象;二是渥畢薩爾城堡之行,向她展示了金錢與地位構筑的另一種生活。福樓拜的敘述筆墨委婉有致,同時也提供比較多的能夠說明人物心理特點的細節(這些我就不復述了,免得文章過長),但是其內在脈絡還是過于簡單,歸納起來,無非是這樣一種因果關系:一個沉湎于文學的女人,偶爾見識了某種奢華生活場景,就足以變壞。
關于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勃蘭兌斯有一個簡明的概括:“在巴爾扎克時代以前,小說幾乎專用一個題材—愛情;巴爾扎克同時代人的上帝是金錢,因而在他的小說里金錢成了社會運轉的樞紐……”(《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第十三章)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巴爾扎克已經離世,但福樓拜依然要面對愛情主題,就像塞萬提斯依然要拿騎士精神做文章。只不過在福樓拜的故事里,愛情只能與金錢聯姻,呈示二者并駕齊驅的雙重主題。
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并不像納博科夫所說完全是作者的“精心創造”,因為并不是福樓拜讓金錢成為社會運轉的樞紐,當時社會本身已經是這個樣子。就在福樓拜創作《包法利夫人》期間,馬克思寫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托克維爾寫了他的《回憶錄》,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法國當日的社會狀況,雖然二者得出不同的政治結論(一者遺憾革命不徹底,一者因革命而感到恐懼),但他們都發現是資本的權力關系造成了社會危機。馬克思進而指出,當時掌握統治權的并不是法國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集團,他將這個集團稱為“金融貴族”(包括銀行家、交易所大王,以及鐵路、煤礦、鐵礦、森林和大土地所有者,亦即托克維爾所說的“大業主”),正是資本運作和資源壟斷扼住了社會的命脈。《包法利夫人》寫的是一八四○年前后的事情,這一輪革命尚未到來,但資本與寡頭已經掌控大局,即便在外省鄉鎮,亦有稅務員和公證人事務所作為體制的配套,以資本為樞紐的經濟體制已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精神趣味。福樓拜的現實主義與其說表現在刻畫人物形象方面,不如說是將這樣的社會環境再現于自己虛構的故事。
至于愛瑪,既然已將浪漫融入奢華的夢境,其情感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與金錢扯上關系。在福樓拜這個外省故事里,也有一個鄉鎮微縮版的“金融貴族”,那就是永鎮賣服飾的商人勒樂(周譯本作勒侯)。其實,他的鋪子不只出售時裝和家紡用品,實際上主業是放高利貸(據說他過去是開錢莊的)。這個人物出現在小說第二部,愛瑪和查理從道特遷居永鎮后,勒樂來登門拜訪,借著推銷商品來招攬他放貸的客戶。他對愛瑪說:“(我)是想讓您知道,錢我是不放在心上的……要是您手頭緊,我可以借給您。”話里話外透出的意思是,他手里資金充足,可承攬閨中貸、私情貸、抵押貸和轉移支付等各種金融業務。
愛瑪用錢之處,都在那兩個情人身上。她先是與永鎮公證處書記員賴昂發生了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這一段時間不長。當賴昂去了巴黎以后,她在農展會上結識了鄉紳羅道耳弗,很快就直入主題,甚至打算要一起私奔。愛瑪偷情的勁頭太大,讓羅道耳弗扛不住。他這頭撤火了,正好賴昂從巴黎回到永鎮附近城市盧昂,于是兩人舊情復燃,愛瑪每星期進城一次去幽會。他們一起聽歌劇,參加化裝舞會,在豪華旅館做愛……美食,肉欲,愛瑪永無饜足。賴昂這人膽小乏味,愛瑪用自己的方式改造他,照納博科夫的話來說,“他倆的戀愛以怪誕而又哀婉的方式實現了她所有的浪漫幻想”。
她以為這就是“愛情”,其實不過是林林總總的風花雪月而已,需要不斷用金錢去維護。于是,她不得不在勒樂那兒賒賬和借貸,不斷地從勒樂手里簽出借據,她不但賣了盧歐老爹留給自己的遺產,甚至將包法利家的祖宅都抵押了出去。小說第三部不斷出現這類情景,叫人看了心驚肉跳,她自己竟是債多不愁。最后,她稀里糊涂欠下八千法郎巨債,讓債權人告上了法庭。她破產了,法庭限定二十四小時之內償還,否則要查封她和查理的全部動產及日常用品。走投無路的愛瑪急得到處找人借錢,找她的情人賴昂,找公證人居由曼,找稅務員畢耐,都不成。公證人還想乘人之危占她便宜,此時感受到被侮辱的憤懣喚起她最后的自尊,恨不得把那男人狠揍一頓。最讓她傷心的是那個羅道耳弗,當初兩人說好一起私奔,這家伙事到臨頭卻變卦了,弄得她大病一場。現在他說他還是愛著她,卻是不肯掏腰包,這無疑將她逼上了死路。結果愛瑪只得服毒自盡,在神甫的禱告聲里,她離開了這個金錢世界。離開了金錢,愛瑪的情愛世界就徹底崩塌。
一個無所顧忌的浪漫女子,適配一個窩囊、麻木、死心眼的丈夫,福樓拜正是按照這種模式來配置包法利夫婦的婚姻關系(難免讓我們想到潘金蓮和武大郎的夫妻配)。在包法利醫生眼里,愛瑪永遠是那個目光悵惘而率真的少女,他每天帶著滿滿的幸福感出門行醫。不管愛瑪如何折騰,他從未心生疑竇,甚至勒樂討賬都討上門了,還是渾然不覺。為了完成愛瑪那種無邊的浪漫主義,查理這般死心眼的現實主義就必須傻缺到底,直到她死后,直到他自己也要死了,憂傷的心頭依然充滿百合花一樣“朦朧的愛的氣息”。
查理情商是太差,但智商應該沒有大礙,就其從業經歷來看算是合格的醫生。他行醫中也出過紕漏,那回聽了郝麥忽悠,貿然給人矯正畸形足搞出醫療事故。但總的來說,他的醫術乃至醫德還是受到更多的認可。在整個故事中,這位查理·包法利先生,除了羅道耳弗所稱“失之寬厚”的老實人性格,沒有給人留下太多印象,故事情節很少聚焦在他身上。
然而,從小說敘事結構來看,從頭到尾卻是依據查理的人生框架,他是書中唯一貫穿始終的人物。小說第一章,從查理作為盧昂中學插班新生說起,那頂寒愴的帽子,他姓名的別扭的發音,惹得全班哄堂大笑。這一章濃縮了他整個青少年時期,捎帶介紹他的原生家庭,以及他如何通過醫師資格會考,開始到道特行醫,并娶了一位號稱富有的遺孀。第一位包法利夫人其實并沒有什么錢財,當查理心里有了愛瑪之后,那女人就死了(純然出于故事安排需要)。于是,后邊的主角就換成了第二位包法利夫人,查理一直在場,卻沒有多少戲碼。而愛瑪死后,福樓拜又回過頭來寫他,寫他處理愛瑪的后事,傷心欲絕中對愛瑪的思念,失魂落魄地變賣家產抵債,最后他也死了。福樓拜將愛瑪的故事整個嵌入查理主題的元敘事,而故事原本的主人查理·包法利卻成了一個不甚重要的配角。
納博科夫注意到,小說開頭一章是用第一人稱“我們”(查理班上同學的口吻)來講述,但很快便由主觀敘述轉換為客觀敘述(周譯本正文第七頁開始,敘述人“我們”就消失了),直到結尾都是全知視角的第三人稱敘事。在現代小說中,換用敘事人和敘述人稱的手法并不少見,但福樓拜是在讀者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敘述轉換,這就比較特別。納博科夫僅僅從敘事結構方面歸納其技巧意義,稱之為“柔和的波浪式運動”。但他未能意識到,這種本末倒置的敘事結構所具有的顛覆性意義。小說將次生的愛瑪故事作為主題敘事,正是意味著查理所代表的那種從傳統社會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已黯淡無光,正當行業和一板一眼的正經人不再成為人們的話題,這儼然表明,現實的布爾喬亞生活已被浪漫主義文化所遮蔽。
對于沿循啟蒙色彩的浪漫主義,作家表現出一種復雜的審美態度,借由查理對愛瑪的寬容,亦表達了他自己對新思潮的理解之同情。但其中無疑帶有悲觀主義的審視,愛瑪的命運則是他對那種偏離正常生活趣味的批判。從這個意義上說,福樓拜可謂反浪漫派的現代派。
這部小說里有一個無關大局的重要人物,就是藥劑師郝麥。在永鎮這地方,此人算是有頭有臉的社會達人。包法利夫婦一來到永鎮,郝麥就黏上來了。作為鄰居(也算是查理的半個同行),他似乎無處不在。幾乎所有的場合,郝麥都要發表言論,還經常給報紙寫文章,他關注時事和科學,屬于比較新潮的一路。在納博科夫看來,這人是一個“成功的庸人”,還是一個“無賴”,因為“他的科學知識來自各種小冊子,他的文化修養來自報紙,他的文學趣味低劣得可怕……”納博科夫打心眼里瞧不起這類鄉鎮知識分子。
關于郝麥這個人物,歷來評論者有不同看法。福樓拜的傳記作者杰夫里·沃爾(Geoffrey Wall)則是正反兩面出擊,一方面認為,“郝麥是福樓拜所諷刺的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代表了鄉鎮生活中最強大的散漫力量”“他還是一個滑稽的偏執狂,狡詐的偽君子,江湖騙子,庸醫,就像莫里哀或本·瓊生筆下的人文,不外乎多了些似是而非的專家的外表”;而另一方面又說,“郝麥代表了他所屬階級的進步,對現代性的追求,還有自身要忍受的歷史矛盾……”同時他還提示,郝麥的反教會態度使他轉向對科學的信仰,因而成為鄉鎮知識分子中的空想家(企鵝版《包法利夫人》導讀)。
郝麥看上去只是場面上插科打諢的陪襯人物,并非構成故事行動元的角色。愛瑪的一切行為,永鎮的大小事件,基本上跟他沒有關系(只是忽悠矯正畸形足讓醫生閃了個跟斗)。我所說的“無關大局”,就是這個意思。福樓拜何故在他身上花費那么多筆墨,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這樣一個并不依附故事主干而存在的形象,活躍在永鎮的日常生活中,自然有著映襯效果,照納博科夫的說法是表現了那個時代的“庸人風氣”。但客觀地說,郝麥那些淺薄而與時俱進的思想言行,反映了浪漫主義文化的某個側面、某些精神特征。
從某種意義上說,郝麥是愛瑪的社會倒影。愛瑪是憂郁的,郝麥是快樂的。他們是印刷物開啟心智的一代人,愛瑪耽于浪漫小說,郝麥卻不止是喜歡大眾科學讀物,雜七雜八的文學作品也瀏覽過不少。他在本堂神甫面前為文學辯護,槍槍戳到要害,他還勸說查理陪夫人去盧昂城里看戲……走出中世紀的鄉鎮知識分子一時目迷五色,惘然之中首先抓住的是精神愉悅。郝麥的沒心沒肺,在愛瑪身上體現為冷酷。同樣的浪漫主義文化,在郝麥身上呈現為兼收并蓄的雜色,而愛瑪卻是一心一意追逐自己的目標。
納博科夫對郝麥這個人物全然否定的看法未免有些偏頗,他沒有理解福樓拜設置這樣一個人物的真正用意。實際上郝麥是我們從歷史和社會角度去認識愛瑪的一把鑰匙。
愛瑪是一個壞女人嗎?也許不一定要從現實的角度去理解這個女性。波德萊爾就認為“她是一個很崇高的女人”,而且將她視為那個時代的英雄。詩人之言不免有些夸張。
波德萊爾是福樓拜同時代人(兩人都生于1821年),他寫過一篇《論〈包法利夫人〉》的論文(收入《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年),其中逐條分析愛瑪所具有的“英雄的種種風度”,想象力,行動力,十足的男性品格,擅于享受生活,以及富于追求理想的勇氣,等等。他認為,包法利夫人的不幸只是嫁給了一個笨蛋老公,她身處那個狹小的環境,只能以幻想填補心靈空缺,所以將公證處的書記員理想化了,又將穿著獵裝坎肩的鄉紳當成了司各特小說里的英雄好漢。到頭來,她發現自己“就像是麥克白夫人搞上了一個不稱意的統帥”,這是她理想失落的根本,亦是悲劇的根源。
波德萊爾是將愛瑪視為一種寓言性人物,并不計較其現實的罪愆,這跟納博科夫和許多論者的評價大相徑庭。詩人不難想象那種沉悶而瑣屑的鄉鎮生活(其實他感到巴黎比外省更加憂郁),庸人風氣鎖閉了一切,任何彷徨猶豫無濟于事。福樓拜的故事打開一個奇異的窗口,他瞥見驛車上閃過愛瑪的倩影,帶著朦朧的目光急急奔向虛無之域,這讓他激動不已。作為對比,他明顯地發現,永鎮的那些男人總是表現為各式各樣的無能。

電影《包法利夫人》(1991)劇照
不能說愛瑪本身是多么復雜的性格,只是這一形象投射在接受層面產生了過于復雜的意蘊。對于這個通奸女人,波德萊爾不作道德評價,卻是肯定了她一心要擺脫平庸人生的正當性。這樣來看待愛瑪這個人物,是否更接近福樓拜的本意呢?當然,不必在意作者究竟想說什么,關鍵是我們從這里看到了什么,是嘲諷中產階級的空虛無聊,還是表現某種欲求與苦難相偕而來的悲情人生?在波德萊爾看來,人性的追求往往帶有自身的污點,也就是叔本華所謂“有罪的無辜者”的意思。對于愛瑪的憐憫與同情,或許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思路。
福樓拜或是以愛瑪的道德污點作為一種原罪的隱喻,悲憫是出于同情,寬宥是期待救贖。現代性本身是否攜帶道德進步,文明與進化如何一再遭遇困境,這是大革命以來困擾法國知識界的大問題。舊制度的崩潰也許是天意所愿,貴族思想家德·邁斯特就是這么想的(如果撇開啟蒙主義和共濟會的陰謀),他將人心墮落作為每一次進步的報應。在《論法國》(魯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書中,他對社會變革作出了這樣一種反面理解。不過他提出“懲罰以便再生”的觀點,無疑是一個有趣的辯證命題。
追尋浪漫主義的原罪,不妨視為更高層次上的現實主義。波德萊爾在一篇談論雨果作品的文章里表示了這樣的感慨:“唉!經過了這么多許諾了如此之久的進步,原罪依然留下了足夠的痕跡,讓人們看到了它數不清的現實!”(《評〈悲慘世界〉》,收入《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不必介意,福樓拜懷著何種動機將愛瑪作為“數不清的現實”中的一例,故事本身并沒有標準的解讀方案。我想,他既然這么講述,也許是真的看到了希望的再生。
二0二二年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