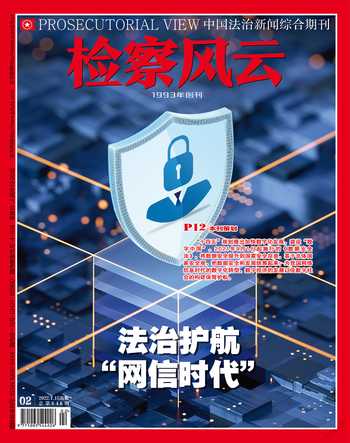“高考”的故事
翻翻民國大師們的回憶,會發現他們在“高考”時發生了不少有趣而難忘的故事,讓人讀起來忍俊不禁。
不同于現在統一時間、統一命題的高考形式,民國時期大學招考在相當長的時段中(1912—1937)都是各校自主命題、自主招生的。1938年,民國教育部設立全國統一招生委員會,實行全國統一高考。然而統一考試僅實行3年,就因抗日戰爭而被迫中斷了。
在自主招生的年代,各大學根據自身情況,獨立組織招生、命題和錄取等工作;對于學生來說,考大學的首要任務就是選定目標學校。
民國時的大學,有公立(國立、省立等)、私立和教會辦學等。知名的國立大學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私立大學中聞名的有南開大學;教會大學中頗負盛名的有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對于中學畢業后立志升學的學子們來說,提前做好功課,研究各校的招生條件和考試時間就很重要。
一般來說,各大學會在報紙上刊登招生廣告,如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申報》的廣告欄上就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學或高等學校招生的廣告。作家茅盾回憶,當時他母親訂閱了《申報》,上面登載著北京大學在上海招考預科一年級新生的廣告。1913年夏天,北京大學由京師大學堂改名后第一次招收預科生,而且當年第一次到上海來招生,這對于長江以南各省想考北京大學的中學畢業生,著實是一大方便。當年茅盾只有17歲,獨自出遠門求學讓人有些不放心,他母親考慮到家里表叔在北京財政部工作,兒子去北京讀書也好有個照應,便讓茅盾去報考北京大學。

amG75Tw6d0zuANb+vstdSZdeOehKXTcX33PQw0D6VLA=季羨林
各校獨立招生,招考時間不同,考期一般會錯開。為了增加考上大學的概率,許多考生選擇多校投考。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立志升學的他在考前做足了功課:翻閱了當時差不多所有全國有名氣的高等院校的章程和招生簡章,選定了北京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等作為投考的對象。他選擇學校主要從學校的聲望來考慮,在他選擇的學校中就涵蓋了國立、私立和教會學校。
據季羨林回憶,當時的北平(今北京)有十幾所大學,還有若干所專科學校。到北平來趕考的學子,總共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考生心目中列在大學榜首的當然是北大和清華,當時全國到北平的學子幾乎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即使自知庸陋,也無不想僥幸一試,畢竟這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事。但是,兩校錄取的人數畢竟是有限的,在五六千名報名的學子中,清華錄取了約兩百人,北大不及其半。
幸運的是,季羨林當年被北大、清華同時錄取了,兩所學校都是名校,究竟該如何取舍呢?“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據說這是北平每一位學生所熟知的話,也顯示出同為名校的北大、清華等學校風格的差異。
北京大學的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它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始。初期學校的監督及以后的校長,均為當時官僚充任或兼任,不少學生也把進大學堂念書看作仕途晉升的捷徑,因此學生中也多有官僚氣和暮氣。
清華大學的背景則相當不同。清華的前身是留美預備學堂,當時美國出于種種考慮,號稱“退還”清政府一部分“庚子賠款”,指明用于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于是才建有這所學堂,專門培養青年到海外留學。晚清時,不少保守官僚家庭對于送自家子弟出國留洋尚有一絲顧慮,擔心受到所謂西方思想熏陶的青年回來成了“剪辮子”的革命黨。隨著民國建立,社會風氣逐漸轉變,政界、學界、工商業界渴望一批有新知識、新理念的青年來服務和建設,于是早年那批青年學生留美若干年回國后多為大學教授、科學家、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樣的情況下,出國留洋成為不少青年向往的目標,清華也變得相當熱門。
季羨林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學習,因為他看到出國“鍍金”以后方便回來搶到一只穩穩當當的“飯碗”。于是,被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同時錄取的他,在權衡利弊后,選擇了更容易出國的清華。
除了這些國立名校,幾所教會大學也頗為搶手。如北平的燕京大學、上海的圣約翰大學等,這些學校歷史較久且設施完善、校園環境優美。學校主要采用英文授課的教學方式,對于學生的英文訓練很有助益,他們畢業后無論出國留洋還是謀職都更為便利,因此這類學校頗受一些沿海地區學生家庭的歡迎。不過,這些學校往往收費不菲,一年一兩百大洋的學費,對于普通人家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因此一般老百姓家的學生是不敢輕叩其門的。語言學家周有光回憶,當時他曾同時考取上海圣約翰大學和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由于圣約翰大學費用昂貴(一個學期就要200多大洋),他考慮家庭實際情況,已準備放棄而轉去南京求學。結果她姐姐同事聽聞這情況,勸她姐姐:“考圣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圣約翰大學又不讀,太可惜了。”最后借錢給他上了圣約翰。

北京大學秋景
當時上大學的學費、生活費對于一般家庭來說是一筆相當昂貴的開支,囊中羞澀的學子們如果想繼續升學,還有什么法子呢?其中一個就是入師范學校讀書,有些師范學校不僅能免除學費,還解決學生食宿,也不失為清貧學生的一條升學之路。
確定了投考學校,就要按照學校的招考時間和條件去趕考。雖然民國考大學不像古代考科舉那么辛苦,不過就當時的交通條件來說,趕考也是件折騰人的“體力活”。
語言學家趙元任剛開始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學堂讀書。他家住在常州,南京與常州兩地雖不遠,但他第一次去南京時,得水陸換乘,整個行程頗為周折。他先是乘小火輪東行至蘇州,然后換乘較大輪船到上海,在旅館住一夜,最后再換乘揚子江大輪船前往南京。
因為大多數學校除了在本校設考場之外,還會在上海、北平這樣交通方便的大城市設考點,對于大多數非本省的趕考學生來說,趕考路就顯得更為漫長了。當時,季羨林從老家山東到北平投考學校,他記得到北平趕考的學子,幾乎全國各省的都有,連偏遠的云南和貴州也不例外。北京大學早年的畢業生楊亮功(后為知名教育學家)回憶,他從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后,便計劃北上作升學準備。由于他是初次出遠門,父親伴他由鄉間到縣城。他們與同行趕考的4位同學搭伴,一路由巢縣搭小輪,經蕪湖,乘大輪,到南京,轉津浦鐵路北上。路上大家相互照料,克服了很多困難。對他來說,有個曾進京參加過殿試的父親對于沿途情形給予指示,也是相當幸運的。
(筆者介紹:張寧芳,華東政法大學博士,主要研究近代人物與文化等)
投稿郵箱: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