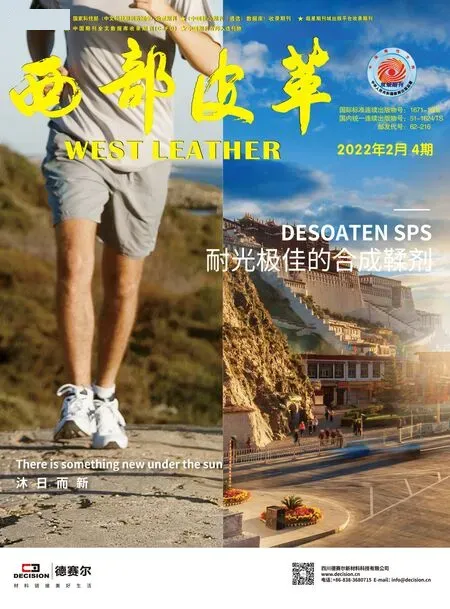從成都博物館陶俑看我國古代服飾的特征與變化
陳曉娟,武嬋娟
(四川師范大學,四川 成都 610100)
我國服飾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古典書籍和史料中留下了種種傳說。服飾文化可以追溯至原始社會,從“襲葉為衣裳”“有巢始衣皮”可以看出人類最早用樹葉、動物毛皮做成衣服。人類在蒙昧之初就開始穿衣著服,其目的主要是抵御嚴寒。隨著社會的發展,羞恥心的萌發和對美的追求使得人們對服飾越來越重視。經過千百年的文化沉淀,服飾逐漸有了如今的新潮模樣。本文以成都博物館陶俑為考察對象,從成都博物館館藏的不同時期的陶俑中重點選擇東漢時期和后蜀時期的陶俑為例,分析其背后的喪葬文化、社會生活及服飾風格的成因等問題。
1 東漢陶俑及其服飾文化
秦朝已有關于服飾的嚴格規定,漢承秦制,所以漢代在服制上亦有相當嚴格的規制。成都是蜀文化的中心,有著極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漢代的成都是自由的都市,繁榮昌盛,一方面古樸至善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激情昂揚的荊楚文化,那時候以俑代替人殉,是一種有著強烈寄托的厚葬文化。漢代婦女服飾上承戰秦、下啟魏晉,體現出長期以來人們對女性美和女性服飾美的審美。西漢前期陶俑集中出土于都城及封國的高等級墓葬中,陶俑多加彩繪,有的身穿衣物。西漢中后期開始,表現日常生活的勞作俑、伎樂俑增多,且伎樂俑多以呈組的形式出現,至東漢中后期,以侍從俑、伎樂俑和庖廚俑為主的陶俑組合在全國各類型墓葬中流行開來。東漢成都地區“說唱俑”,是漢朝陶俑經典的代表之作(如圖1 所示)。
東漢時期“說唱俑”大體分為坐式、立式兩大類,從圖1 中我們可以明顯地觀察到人物身體的比例塑造并不符合實際真實人物比例,人體塑造也較為夸張。陶俑上身袒露,雙乳下垂,其身體部分的簡單粗獷的雕刻與面部的仔細雕刻形成鮮明的虛實對比,且陶俑的服飾也相當簡陋。東漢“說唱俑”不僅有著楚文化的浪漫激情,還特別注重寫意的表達,為突出其神韻,在造型上簡潔概括,衣紋處理方面,上半身袒露,下半身大刀闊斧,沒有特別的細節刻畫,衣服和紋理大為簡練概括,但整體塑造的非常生動活潑,吸引住了觀者的眼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從簡要的陶俑服飾無法獲取太多服飾信息,館藏東漢陶俑中有赤裸上身的俳優俑、說唱俑,但絕大部分陶俑都是穿著上衣的,沒有穿單層衣的陶俑。但我們可以從糯、裙、褲、半袖等簡練服飾中明顯感受到東漢清新活潑的服飾風格。
東漢時期執物俑(見圖2)中有抱囊俑、持瓢俑、持箕俑等,與中下層百姓生活息息相關。觀察發現,執物俑的衣領襟口都開得較低,領口依次露出,服裝上口呈圓臺狀與頸貼合,外衣多為交接領口,衣領處多為左側蓋于右側之上的結構,內層右側比左側多一條領緣。從大量陶俑形制可以推測出這種領口在當時非常流行,而館藏的博物館陶俑更多的是反映平民以及奴仆的衣著情況。漢初規定,百姓一律不得穿雜彩之衣,只能穿本色麻布,到西漢末年平民只能穿青、綠兩種顏色的衣服,禁止穿紅色、紫色。在服裝的式樣上似沒有嚴格的制度,但從出土的陶俑來看,漢代勞動者多穿窄袖長至膝的長糯,或短糯配褲或身著長袍。抱囊俑(見圖2左側)體型均較大,多為男俑,呈站姿,頭戴巾幘,身著長袍,左手抱囊,有的頭梳高髻或帶巾幘。此類生活勞作俑負責衣食住行,如備置飲食的庖廚俑和提罐俑等,還有負責出行的牽馬俑等。執鍤鋤俑(見圖2 右側)大多數頭戴平頂笠帽,身著短褐,衣不過膝,衣領多為敞口,腳穿草鞋,腳趾外露,有的俑身著長袍,腳穿翹頭履,有的一手執鍤,一手執箕,腰間配環首刀、簸箕等勞作物件。這些生產勞作俑多總角束發,身著短褐,衣服寬松,體態輕盈。服飾的設計與生產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另一方面再提到陶吹笛俑、撫琴俑等伎樂俑(見圖3),這些陶俑頭戴巾幘平頂立帽或梳高髻簪花,著長袍,袖口寬大,撫琴俑(見圖3 右側)均為坐姿,頭戴巾幘或冠,著長袍,盤腿而坐琴置于兩膝之上,雙手按于琴弦之上或揮舞或仰頭作吟唱狀。擊鼓俑多與伎樂俑成組出現,而俳優俑則體型更大,腹部圓滾且上身赤裸,褲子多滑落于腹下或盤旋于腰間。吹笛撫琴俑多為坐姿,琴置于膝上。舞俑則頭梳高髻簪花,著寬袖長袍,一手側舉或一手握巾,有的單手提袍作舞蹈狀,巴蜀地區舞俑衣飾與動作基本相同。長袖舞在西漢初期盛行于宮廷,隨著時代的變遷,漢代樂府的設立使得宮廷與民間音樂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東漢時期的音樂呈現世俗化的特征,這也就是為什么民間音樂盛行的主要因素,東漢時期的舞俑舞姿散漫且服飾隨意,民間舞者從著裝到形體都呈現出自娛灑脫的精神風貌。
從史料中發現,影響漢代蜀地服飾文化的因素有主要幾個。其一是受陰陽五行說的影響,當時,青、紅、黑、白、黃作為五行的色彩象征廣泛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與生活,另一方面是受楚文化的影響,崇尚赤色,紅色對服飾的影響深遠。漢代服飾以寬衣廣袖為美,深衣還是襦服都是如此,漢代服飾袖子長且寬大,漢代深衣衣裳相連,使身體深藏于內,他們的衣領最具特色,通常為交領,領口低便于露出領子。工匠們花費更多的精力表現陶俑外貌、服飾、發型、裝飾等細部,女性服飾更為復雜,男性服飾簡單。東漢時期蜀地莊園繁榮,俑的增加是莊園經濟發展的結果,東漢末期至蜀漢前期,陶俑種類和數量呈衰落趨勢。
2 后蜀陶俑及其服飾文化
從成都博物館館藏后蜀時期陶俑來看,女俑造型精巧別致,極具代表性。五代時期,后蜀定都于成都,其樂舞俑的服飾有紅、綠、黃、白等顏色。服飾方面,相較于東漢時期的闊布剪裁,后蜀時期的蜀錦織物美輪美奐,造型樣式都更為豐富。眾所周知唐代服飾雍容華麗,而到五代十國時期,人們逐漸追求舒適,這一點從陶俑造型上就能直觀看出。后蜀陶俑的服飾大小合體,修身剪裁,精巧簡約。如圖4 所示的女俑面部被塑造得溫和,身材纖細消瘦,服飾盡可能地貼合人物。這一時期女俑的發髻多為高髻,其上或裹巾或簪花,神態生動,表情豐富。女俑身穿長褙,正面為對開直領門襟,門襟自然地自上而下,對稱且樣式多為雙層,從頸部到褙子下擺呈現出整體自然下垂的樣貌,隨著其擺臂或舉手揮舞動作而產生的褶皺都清晰自然。
成都龍泉驛區趙廷隱墓出土的彩繪陶花冠女舞俑(圖5)整體形象刻畫精巧細致,服飾紋路清晰可見,質地的厚薄程度與褶皺也非常直觀。舞蹈者面露微笑,神態祥和可愛,身材纖細,雙手上舉,頭戴紅色高帽,帽子的紅色絲帶自然垂搭于兩側胸前,帽子樣式精巧別致,引人注目。雙側帽檐向上翻折,前身領口為交領右衽,腰部圍紅色系帶系帶盤節看似繁瑣卻能最好地展現其腰身比例。裙擺飄逸張揚,敝膝作云紋狀搭于裙內,大口褲中露出黃底紅面尖頭鞋,鞋頭有金色云紋作裝飾。整體服飾刻畫細致入微,最好地呈現出舞者當時的狀態。
成都博物館館藏彩繪陶樂俑(圖6)樣式多樣,均為站立姿勢,其動作和所執之物各不相同,其中一部分為歌俑一部分為舞俑。樂俑裝束造型十分講究層次,清晰可見外衣里面的內衫與裙,衣邊以金邊進行裝飾。她們使用的樂器多種多樣,如笛子、篳篥、笙等,每一個陶俑儀態端莊身材纖細,頭部裝飾豐富,頭戴金簪等配飾,其上衣服飾多為直領對襟,服飾左右開叉,衣服著褙,內部搭配系帶長裙,裙擺露出之處造型不一且各帶裝飾,衣邊裝飾簡介大塊紋路,從其腳踝部分可以直觀看到其大口褲腳,褲腿部分也清晰可見,整體裝飾層次分明,簡約舒適。褙子在隋唐時就已經被列入了婦女冠服中,褙子兩側高開衩是便于勞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戰亂時期社會動蕩所致使曾的華服變得素雅便于人們行動自如。短至腰間長至膝蓋各不相同,長袖短袖層次疊加,可以看出短袖為半臂,半臂袖能夠襯托出長袖的樣式和紋理,裙擺內部為三襜造型,有豎直有圓弧,而衣邊花紋多為云紋、蓮花紋等等。褙子的袖子形狀有長短寬窄之分,而女性多為長袖,窄袖更方便于日常勞作生活穿,長袖是為了適應舞者的需要更加顯得自然靈動。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陶俑造型結構清晰,服飾簡約而不簡單,和自身的貼合也趨向完美和舒適。在五代十國時期,戰亂頻繁,相較于唐代的雍容服飾造型,這時期的服飾明顯更加輕便簡潔,部分圖像直接可以看出半身長裙為百褶裙,蔽膝算得上是其特色之一,而蔽膝上的云紋、蓮花紋、波浪紋增加其形式美。五代后蜀趙墓出土的彩繪陶俑年代久遠,供我們參考也相對有限,但也能讓我們體會到那個時代的服飾智慧。
3 結語
服飾文化是人類社會不斷探索發展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歷史性時代性以及社會性,從四川成都市出土的較多總類的東漢陶俑以及后蜀時期的不同陶俑,成都龍泉驛區趙廷隱墓出土的二十余件彩繪陶伎樂俑最為精巧別致,時隔多年依舊能直觀看出其色彩別致,極具代表性與特殊性。從服飾上看來,漢代服飾文化相對典雅,雖然比不上唐朝服飾的發達與制度的完善,卻也獨具特色,我們從傳統服飾中找到與當代社會的新融合義不容辭,探索出新的方式跨時代兼容并蓄,為現代社會的服飾與發展探索出新的方向,在繁與簡的生活里讓著裝持續地合理地舒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