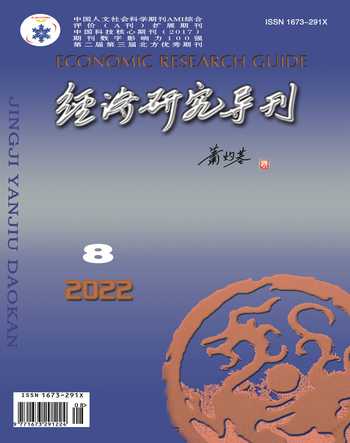關于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思考
鄂明月
摘? ?要:低齡的未成年人犯罪一次次挑戰社會大眾所能容忍的底線,為了順應社會期許、適應社會發展現狀,我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由14周歲降至12周歲,加強了對未成年人的控制,為未成年人進行違法犯罪敲響了警鐘,使其明白,在使用合法武器為自己辯護的同時,他們也必須遵守法律。未成年這個詞,也不再是避免法律后果的借口。這一修訂對我國立法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通過對我國有關規定進行梳理以及對國外立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借鑒,對我國此次新的法律條文的出臺存在的不足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并且提出了相關的完善建議,希望能夠對解決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有所助益。
關鍵詞: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刑法修正案
中圖分類號:DF62?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08-0156-03
一、刑事責任年齡的內涵
(一)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概念
我國《刑法》規定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是刑事責任年齡的概念表述[1],也是進行違法犯罪的行為人是否需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觀要件之一。刑事責任年齡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心理,身體成熟度和社會的發展。行為人辨別和規范其行為的能力會影響刑事責任年齡。
(二)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發展
1.萌芽期
《周禮》中提到的三赦制度是中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體現,它始于西周時期的個人生活。到這個時期,人們逐漸發現不同年齡段的人具有不同的刑事責任能力。由于當時法律的落后和人們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認識程度有限,這一時期我國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并不是特別精確和完備。
2.發展期
到秦漢時,刑事責任年齡制度與西周時期相比較,可以說具有相當快速的發展。秦朝時期,犯罪人的身高與年齡掛鉤,以身高作為刑事有罪的衡量標準。但是這種判斷標準是非常不科學的,有很大的漏洞。西漢時期的立法并沒有規定刑事罪責的年齡制度,漢文帝首先確立了不需要負刑事責任年齡的階段,并在皇帝的諭旨中有所體現。
3.完善期
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在唐代達到頂峰并開始發展。 唐代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了細致的界定,將其劃分為三級,作為刑事責任的界限。在清末以前,刑事責任的年齡制度使用的一直是唐代制度,但到了清末,與以前的法律相比,更加強調了無刑事責任能力。
(三)國內學者的不同觀點
我國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目前在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2],一種贊同刑事責任年齡下調,另一種反對刑事責任年齡下調。
1.贊同的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低齡化、廣泛化的特征,基于此,其危害不容忽視,不能過度縱容。適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降低兒童犯罪率,也可以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起到警示作用。
2.反對的學者則認為,14周歲是目前各國普遍采用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起點,我國的相關規定是符合國際趨勢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是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最佳方法,這對青少年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的犯罪原因是家庭、學校和社會等變量復雜相互作用的結果,魯莽地懲罰12歲以下未成年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可能對其身心健康產生重大影響,不利于其重新融入社會。
二、域外刑事責任年齡相關規定
(一)美國
美國與英國同樣作為英美法系的國家,在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上一直根據普通法規則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由于美國是一個聯邦共和國,因此沒有一致的刑事責任年齡法規,不同州的法律同樣對刑事責任年齡有不同的規定,有些需要7歲,有些需要8歲,還有一些需要12歲和14歲。雖然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各不相同,但都是從比較早的年齡開始的,這與美國的刑事責任年齡是一樣的。它與國家的社會發展密不可分。
(二)英國
英國在最初時期并沒有將年齡作為刑事責任的免責事由。英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更側重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懲罰,其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低于其他國家,十分嚴厲。直至21世紀,對于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問題,英國逐漸意識到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重要性。自此,英國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逐漸實現了均衡發展,既注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懲罰,又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三)中國香港地區
中國香港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是根據英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相關法律制定的,其限制沒有內地那么嚴格。此外,無罪推定在香港完全適用。香港法律假定已年滿10周歲但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沒有犯罪能力,但如果有充分證據表明該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理解和規范其犯罪能力的行為,則該未成年人可以被起訴。因為其明知自身的行為的可能產生一定的危害結果仍然實施該行為,說明其主觀惡性較大,那么該行為人就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三、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的必要性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必要的[3]。第一,隨著文明的進步和人們生活環境的改善,青少年性早熟現象日益普遍。處于信息時代背景下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接觸到未加篩選的各種良莠不齊的信息,這些信息對正在塑造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未成年人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經調查顯示,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開始回升,其犯罪實際領域十分廣泛、犯罪手段多樣,且有些手段極其殘忍。比如,2021年3月13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巴彥縣一名14歲的小女孩因抵觸母親的管教,將其母親殺害,并將其尸體藏在家中的冷庫中。如果其家人出具諒解書可能會對其從輕處罰。如此惡劣行徑最后的處罰如果非常輕微,甚至有些案件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對受害者及其家屬極為不公平,也不利于社會關系的恢復。此外,它也并不會懲罰到未成年人本身,無法彰顯我國的司法公正,無法保障社會安全。第二,避免“未成年”成為行為人違法犯罪的保護傘。有些犯罪行為人利用未成年人的身份故意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如果不對刑事責任年齡予以適當程度的降低,最后的處罰結果可能會讓普通民眾無法接受。第三,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案件無一不在觸動著社會大眾敏感的神經。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和社會準則理應適應社會的發展現狀、順應社會期許。此次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下調,改變了過去“一刀切”的規定方式,對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正面意義。它對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產生了有利的影響。
《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責任年齡條款的不足。任何一項新的法律條文的變動和出臺,都需要理論與實務的雙重檢驗。我國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相關規定已經沿用了40多年,且符合國際立法慣例,然而,我們目前生活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和對事物的認知能力,都與當初制定法律時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可以說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下調,順應了民眾的期待,但是其在司法實務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4]。
第一,《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那么如果本條款中的“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指的僅僅是罪名還是指具體的犯罪行為,我們對其所產生的理解不同,那么在司法實務中處理相關案件時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甚至可能會導致擴大或者縮小此條款所保護的范圍。第二,在該條款并中沒有明確的界限或標準來確定何種程度屬于“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第三,《刑法修正案(十一)》在規定了主體等條件外,還規定了“情節惡劣”的限定標準。對于本條款中關于犯罪危害程度的“情節惡劣”的條件與前面的“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條件具有什么樣的關系,值得我們反復斟酌適用,因為理解的差異會直接導致產生的處理結果的不同。最后,本條款除了對主體要件、罪行要件、情節要件等實體要件進行了相應規定,它還規定了程序標準。雖然此項規定體現了我國立法機關對于懲罰未成年人所持的審慎態度和立場。但是由于對“情節惡劣”等要件目前尚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判斷標準,這將會導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工作人員在核準時將會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將會具有一些主觀色彩,不同的司法人員處理相應問題時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處理結果。這將會使人們對我國的司法的權威性產生一定程度的質疑,不利于實現我國的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
四、關于刑事責任年齡條款的完善建議
(一)依法規范自由裁量權
未成年人代表著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的未來,他們是祖國的希望。因此便要求我們的司法工作人員在處理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的案件時,應當秉持如履薄冰、慎之又慎的態度。我們既要對得起在困難中與我們相遇的受害者,也要合理地利用我們手中緊握著的權利。盡管要懲罰違法者,但還必須保護他們的權利仍不受侵犯。首先,我們應該構建監督機制。如果司法工作人員有任何違法行為,濫用其自由裁量權,監察機關有權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釋。其次,我們應當加強社會監督。社會監督雖然具有一定的弊端,但是只要我們合理利用大眾和網絡媒體的力量,就不僅會讓我國的司法工作人員審慎使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權,也將會對我國的司法建設具有一定的積極推進作用。最后,我們應當從我國司法工作人員的精神層面入手,加強檢查工作隊伍的職業道德建設,使其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
(二)構建前科消滅制度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檔案封存機制作了相應規定,但沒有為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提供類似“重新開始”的選擇。由于刑事前科消滅制度可以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禁止有刑事定罪的人再犯罪,因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和日本,都對前科消滅制度制定了必要的立法。而我們的國家則相反,我國不但沒有相應的規定[5],反而規定了前科報告義務。這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將會給他們從此貼上“犯罪的標簽”,極易使他們喪失重新融入社會的信心和機會,從而以濫為濫、自暴自棄,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6]。未成年犯罪記錄清除制度極其重要,它是根據當今社會發展趨勢而建立的。對于未成年人這樣的一個十分特殊的群體,我們應該給予其一定的寬容,給予其一個改過自新、重返社會過正常人生活的機會。我們應該避免使其因為一次的過錯用自己的整個人生來承擔責任的慘痛代價,這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一旦前科消滅制度得以構建和完善,將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首先,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歷史,不要求在戶籍或人事檔案中登記。這樣能夠讓未成年人毫無顧忌地以一個正常人的身份重回社會,重新生活。其次,在與未成年人相關的犯罪前科消滅之后,如果其再重新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不得對該未成年人適用有關累犯的規定。最后,應取消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對民事和行政權利的限制,使未成年人在求學以及就業方面不會受到其他人的歧視,遭到不公平待遇。總之,我們應該保護未成年免受犯罪記錄帶來的任何和所有負面影響。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們在構建消滅系統時必須謹慎,不要過度擴張。既要維護未成年人的權益,也不要過分放松對有一定的識別和控制自己活動能力的未成年的要求,以免其利用未成年人的身份故意犯罪。他們有責任避免法律的后果。寬容并不意味著要縱容,我們必須要構建“和諧司法,減少社會對立的”刑事標準。
五、結論
在我國,未成年犯罪的低齡化和暴力化將是未來不可避免的現象。據統計,我國近些年犯罪率已經有所降低,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卻有抬頭的趨勢。其中引起輿論嘩然的有昆明市的14歲少女與男友殺人拋尸案、貴州省的17歲少年14天連害九命、重慶市的10歲女孩摔嬰案等。此次我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下調,一方面體現了每一條法律的改動和出臺都是與社會發展具有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也昭示著我國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的趨勢已經不容樂觀。此次修訂的條例存在一定的不足,也仍需從多方面對其進行加強和完善。繼續對“犯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究竟是指具體的犯罪行為還是僅僅是指罪名,以及對“手段特別殘忍”、“情節惡劣”等情節條件和限定條件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認定,以便于在司法實務中我們的司法工作者能夠用統一的判斷標準,準確無誤地對案件作出合理合法的判斷,避免其濫用自由裁量權。另外,未成年人犯罪雖然具有一定的個人因素,但是學校、家庭、社會因素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在未成年人犯罪后,學校、社會、家庭應當共同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使該未成年人能夠再次重新融入社會,使其能夠正常生活,從而避免其再次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國歷來遵循“教育第一,懲罰第二”的理念。我國此次對刑事責任年齡的下調,并不是為了以暴制暴,而是為了讓受害者及其家屬得以一定的寬慰,讓所謂的“小惡魔”受到一定的懲罰。但終究如前面所說“刑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只是我們作為最后的底線保障,在處理青少年犯罪時,我們也必須確保這些青少年的最大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決更復雜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42.
[2]? ?高園.中國古代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探析——以“矜老恤幼”思想為切入點[J].社會科學動態,2021,(9):97-100.
[3]? ?李丹陽,馬建全.對《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合理性分析[J].西部學刊,2021,(16):76-79.
[4]? ?滿濤.未成年人利益最佳與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兼評《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一條[J].河北法學,2021,(7):91-110.
[5]? ?朱明慧.論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滅制度的構建[J].法制與社會,2020,(28):180-181.
[6]? ?于光明.試論我國前科消滅制度構建的必要性[J].法制與社會,2019,(29):19,27.
[責任編輯? ?興?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