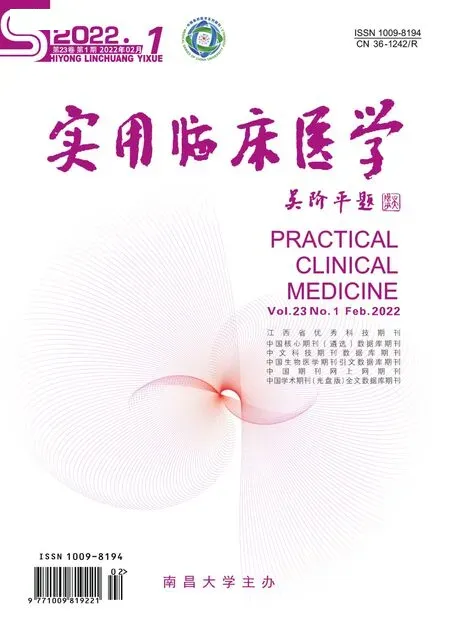精準麻醉策略對乳腺癌術后疼痛及炎性因子的影響
付輝凡,徐 鳴,周 斌,于福平,羅振中
(1.南昌市第三醫院麻醉科,南昌330009;2.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麻醉科,南昌 330006)
目前,手術仍然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療方法,但患者常伴發乳腺切除術后疼痛綜合征(postmastectomy pain syndrome,PMPS),通常表現為術后胸部、腋窩、上臂及肩部出現慢性疼痛[1]。目前,PMPS的病因和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有研究[2]表明,術后急性疼痛管理以及持續的炎性反應不佳是PMPS發生發展的重要危險因素。因此,術后急性疼痛的精準化管理可預防慢性疼痛。
精準醫療的核心策略是以恢復病患的生理、心理、社會完整性為宗旨,實現最佳疾病控制,最小醫源損害和最低醫療耗費的多目標優化[3]。精準麻醉是精準醫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系列的麻醉處理策略,囊括整個圍術期的處理細節[4]。本研究擬采用精準化麻醉策略優化圍術期管理,并評價其對乳腺癌患者術后疼痛及炎性因子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招募2019年7—12月于南昌市第三醫院行全麻下單側乳腺癌改良根治術的女性患者70例,因高血壓及鎮痛藥物服用史排除6例,最終納入64例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精準麻醉組(P組)和傳統麻醉組(R組),每組32例。本研究通過南昌市第三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并與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
納入標準:年齡30~70歲,體重指數(BMI)18~25 kg·m-2,ASA分級Ⅰ—Ⅱ級。排除標準:慢性疼痛病史及長期服用鎮痛藥物者;穿刺部位存在感染;酰胺類局麻藥過敏史;重要臟器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礙;精神和神經系統疾患;術后發生感染及二次手術者。
1.2 麻醉方法
P組:患者術前半小時在病房內予以咪達唑侖0.05 mg·kg-1肌內注射,入手術室后快速泵注右美托咪定1 μg·kg-1,由同一名麻醉醫師行超聲引導下胸壁神經阻滯:在前鋸肌和胸小肌筋膜間,注入0.375%羅哌卡因15 mL,胸大肌和胸小肌筋膜間再注入0.375%羅哌卡因10 mL。確認阻滯平面后,行麻醉誘導:地塞米松0.2 mg·kg-1+依托咪酯0.3 mg·kg-1+舒芬太尼0.2~0.4 μg·kg-1+順式阿曲庫銨0.2 mg·kg-1,麻醉維持采用右美托咪定、丙泊酚和瑞芬太尼靶控輸注(TCI)+順式阿曲庫銨。術中根據腦電雙頻指數(BIS)值調整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切皮前及手術結束前分別予氟比洛芬酯50 mg靜脈滴注,術畢采用PCIA(舒芬太尼2 μg·kg-1+昂丹司瓊12 mg,均稀釋至100 mL,設定2 mL·h-1,自控0.5 mL·次-1)。返回病房后行非藥物方法進行干預,包括手臂運動、局部理療、按摩及心理護理等。
R組:患者入手術室后常規麻醉誘導:咪達唑侖0.05 mg·kg-1+依托咪酯0.3 mg·kg-1+舒芬太尼0.2~0.4 μg·kg-1+順式阿曲庫銨0.2 mg·kg-1,麻醉維持采用丙泊酚、瑞芬太尼及順式阿曲庫銨,術中根據血壓及心率變化及經驗調整劑量,手術結束行PCIA,選用配方與P組相同。
1.3 觀察指標
記錄術中瑞芬太尼和丙泊酚的用量、術后48 h鎮痛泵有效按壓次數及住院總費用;記錄2組患者術后1 h(T1)、6 h(T2)、12 h(T3)、1 d(T4)、2 d(T5)、3 d(T6)時靜息及咳嗽的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評分);測量術前(T0)及T1、T4、T5及T6時靜脈血IL-6及TNF-α質量濃度;記錄術后嗜睡、惡心嘔吐、穿刺并發癥等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基線資料、術中及術后情況
2組患者年齡、BMI、ASA分級、手術部位、手術時間、失血量及住院總費用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R組比較,P組患者術中瑞芬太尼、丙泊酚用量及術后PCA自控次數明顯減少(P<0.05),見表1。

表1 2組一般資料、術中及術后情況
2.2 術后不同時點靜息及咳嗽時VAS評分
與R組比較,P組在T1-5時點VAS評分明顯降低(P<0.05),T6時點VA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術后不同時點靜息及咳嗽時VAS評分的比較 分
2.3 不同時點血清IL-6、TNF-a水平
與R組比較,P組在T1、T4及T5時點IL-6及TNF-α質量濃度下降(P<0.05),T6時點IL-6及TNF-α質量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T0比較,R組在T1、T4及T5時點IL-6及TNF-α質量濃度升高(P<0.05),P組在T1及T4時點IL-6及TNF-α質量濃度升高(P<0.05),見表3。

表3 2組不同時點血清IL-6、TNF-a水平的比較
2.4 不良反應
術后R組有6例患者出現惡心嘔吐,P組未見麻醉相關不良反應。2組穿刺均未見感染、氣胸、血腫等穿刺并發癥。
3 討論
臨床調查顯示,乳腺癌患者術后合并慢性疼痛的發生率達13%~53%[5-6]。術后慢性疼痛的危險因素包括手術類型、術前焦慮、放化療、年齡及術后急性疼痛的管理等[2]。慢性疼痛的病因及機制復雜,一旦發生再進行治療往往效果不佳。因此,圍術期早期干預急性疼痛對預防術后慢性疼痛有著重要意義。
疼痛治療與精準麻醉密切相關,且也朝著精準醫療的方向發展[7]。本研究納入的麻醉精準化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1)抗焦慮:心理學因素特別是術前的焦慮狀態在慢性疼痛發展過程中起一定作用[8-9]。此外,全身麻醉患者術前口服咪達唑侖具有顯著的抗焦慮作用,同時咪達唑侖聯合右美托咪定可增強術后鎮痛效果[10-11];因此,術前肌注咪達唑侖+麻醉前靜脈輸注右美托咪定以緩解術前焦慮。2)抗炎:圍術期單劑量全身應用激素可通過抑制炎性介質釋放有效緩解術后早、晚期疼痛,并能減少阿片類藥物的用量[12],圍術期系統應用地塞米松可作為多模式疼痛策略的一部分。本研究采用靜脈輸注地塞米松抑制炎癥因子。3)多模式鎮痛:區域阻滯可以有效降低乳腺癌的術后疼痛,其中胸壁神經阻滯(pectoralnerves block)且僅有1個穿刺進針點,具有操作簡單、效果確切、安全性高等特點[13]。此外,非甾體類抗炎藥物可通過抑制COX從而抑制前列腺素E的釋放,并通過抑制痛覺敏化進而達到超前鎮痛的效果[14]。本研究采用超聲引導下胸壁神經阻滯+靜脈鎮痛(阿片類藥物聯合非甾體類抗炎藥物)進行多模式鎮痛。4)非藥物干預:有研究[15]顯示,手臂運動、局部理療、按摩及心理護理等均有助于改善患者術后疼痛。本研究患者術后均早期進行康復及心理治療。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傳統的經驗式麻醉管理比較,精準化麻醉策略使得患者術中瑞芬太尼和丙泊酚用量及術后疼痛評分明顯降低,術后48 h內鎮痛泵按壓次數顯著減少,且術后2 d內各時點IL-6及TNF-α質量濃度下降。
綜上所述,圍術期精準麻醉策略可有效緩解乳腺癌患者的術后疼痛,并抑制炎性因子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