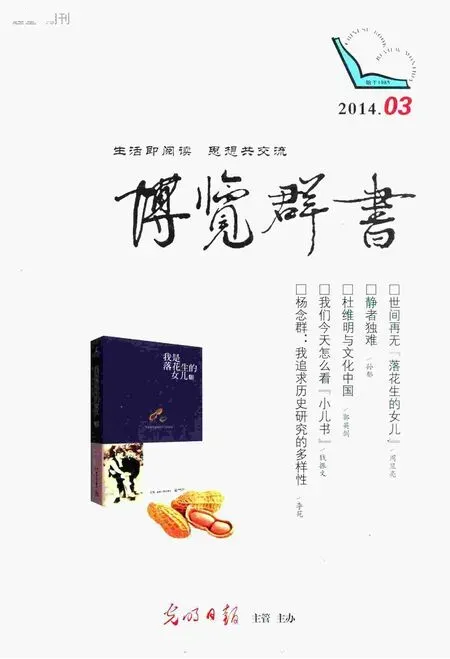這三十萬字散文有一種命運共同體意識
周紀鴻

“愛”是不能忘記的。愛是文學的主題,更是散文家心中永恒的話題。在中國現當代散文界,在眾多散文家的筆下,“愛”是一直存在的、不可替代的主旨。冰心是現代散文女作家中,秉持“愛”心的杰出代表。她的大愛之心、博愛之情,百余年來,滋潤著億萬幾代老少讀者的心靈。近日,我捧讀了廈門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著名散文家陳慧瑛的散文集《有一種愛叫永遠》。這部30萬字的散文集,精選了陳慧瑛的47篇散文和34首散文詩。文字晶瑩剔透,感情赤誠真摯,愛意緩緩流露,暖意融融會心,真的是叫人無論如何也不想放下手中這部厚厚的散文集。
在碎片化閱讀、手機劃屏當道的眼下,一部散文集能讓讀者達到如此地步,委實不易。女作家陳慧瑛系民族英雄陳化成將軍嫡系五代孫女。她祖籍廈門,是1946年出生于新加坡的歸國華僑。陳慧瑛1962年16歲考入廈門大學中文系,1967年畢業。曾連任五屆廈門市作家協會主席、福建省文聯委員、省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四屆廈門市人大常委、人大僑臺外事委員會主任,并擔任廈門市陳化成研究會會長、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散文詩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和廈門大學兼職教授、廈大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英國劍橋、美國ABI名人傳記中心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地方人大機關的工作,眾多的社會兼職、學會職務并沒有影響她的散文和散文詩的創作。她曾當過10年記者。在基層采訪中,她仔細地追問,認真地思索,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激勵她勤奮地寫作。有300余篇作品入選大、中學教材和150余種文集。《梅花魂》《無名的星》等獲國內外文學獎。憑借著一顆愛國華僑的赤子之心,為神州華胄捧出火紅的青春真情畢現,為創作不惜東奔西走一路追求,歸國華僑的愛國情懷在陳慧瑛的筆下散發出沁人心脾的芳馨。
《有一種愛叫永遠》全書分“鄉緣”“鄉魂”“鄉愁”三部分,其中“鄉緣”分量最重。陳慧瑛緬懷師長、憶說文友的散文,大多數寫于20世紀80年代。閱讀那個激情燃燒歲月里的文字,給人以情真意切、赤誠相見的感覺。特別是由于陳慧瑛具有愛國名將后裔、歸國華僑、記者、一級作家等多重身份,她接觸到的很多人物大都是蜚聲海內外的名宿大咖,包括《社會主義好》的作曲、著名音樂家李煥之;著名指揮家陳佐湟;著名因明學家、書法家、詩人虞愚;著名畫家張人希;著名漫畫家、國畫家葉淺予;著名版畫家、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古元先生;一代名師——畢業于清華,留學于劍橋,執教于廈門大學的資深教授鄭朝宗先生;授業恩師陳汝惠,即指揮家陳佐湟的父親;臺灣當代著名散文家、哈佛碩士、芝加哥大學博士、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許達然;著名作家、美籍華人陳若曦女士;旅美著名詩人;畫家秦松先生;菲律賓華僑詩人、攝影家云鶴等,通過與名宿專家們的采訪接觸和當事人的言談舉止,著意探悉名宿大咖的性格特征與精神世界,這些人都有各自的思想光亮與性格異彩。鄭朝宗先生的博學謙遜,古元的率直真誠,許達然的智慧與警覺,陳汝惠老師的坦然與寬容,陳佐湟的天才帥氣等,都是形神畢肖,躍然紙上。陳慧瑛的散文寫的是個人角度與這些名家的深層交往,如對歷史問題的探究,師友相互信函的往來,看法意見的推心置腹的交流,運用的素材都是真材實料,細節的真實,大都帶有“獨家”采訪和披露的性質,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陳惠瑛的散文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與文獻意義。
陳慧瑛真情講述了自己心底藏著的“梅花魂”的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陳慧瑛雖然出生在異國他鄉,但是受外祖父的影響,對祖國愛之深情。她的媽媽是外祖父的獨生女,她又是母親的獨生女。外祖父是為抗日戰爭、為家鄉作出突出貢獻的愛國僑領和國學素養深厚的儒商。老人家能書善畫,是星島文壇頗負盛名的文化人。古玩墨寶不在話下——書房中一幅老干虬枝的墨梅,是老人真愛的寶物。新中國成立之初,陳慧瑛和母親回到祖國的懷抱,外祖父因為年事已高,留在了新加坡。臨行前,外祖父把心愛的墨梅國畫傳給陳慧瑛,交代她一定要保存好。母女上船前,外公又送給她一包雪白的細亞麻布,繡著血色梅花……一幅丹青,幾朵血梅,既是外祖父給陳慧瑛的圖騰般的寶物,更是寄寓著異國華僑華人的赤子之心!
歲月如梭,外祖父一直在經濟上支持她。但是,在陳慧瑛上大三的時候,外祖父遺憾離世。星島一別,竟成永訣。重洋萬里,母女二人,悲慟欲絕。老人逝后次年初春,陳慧瑛在老家種下了兩株梅樹:一株蠟梅,一株紅梅……用梅樹寄托對老人的思念。而外祖父的墨梅,則成為陳慧瑛行走奮斗,陪伴她多年的“護身符”!無論是她在太行山深處勞動鍛煉,還是在艱辛跋涉的人生路上,冰清玉潔的墨梅,凜冽正氣,像火,給了她溫暖;像血,給了她活力。墨梅浸透了幾代海外赤子對祖國圣潔的情感;在祖國苦難的時光,給了她不尋常的熱能和可貴的信念。整篇散文寫人述情,如泣如訴;如詩如畫,如歌如賦,講的是家事,何嘗不是講國事?墨梅成了賡續親人血脈的見證,成了愛國華僑傳遞骨肉親情的魂靈。往事如煙,不囿流俗。這樣一篇借物抒情的散文,表達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熱愛眷戀之情,多年來成為語文教材中的精品。
陳慧瑛的《有一種愛叫永遠》真情再現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血肉之親和炎黃子孫的手足之情。著名作家、美籍華人陳若曦女士;旅美著名詩人、畫家秦松先生;菲律賓華僑詩人、攝影家云鶴;廈大菲華校友佘明培先生、杜妮絲小姐等,這些外籍華裔——廈門家鄉人,在陳慧瑛的筆下,流淌著赤子情懷。她說,“我來自海外,我是中國的女兒,我所有的愛與溫情,都為祖國虔誠奉獻;所有的悲歡離合,都與故鄉休戚相關。”
由于家世淵源和個人豐富的生活閱歷,她的作品包含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大量文章反映華僑、華人、港澳臺同胞的生活和故鄉廈門的人文風貌,情真意摯、細膩不失豪放,委婉而又豁達,傳統文學底蘊深厚,深受海內外讀者喜愛,在當代文壇、特別是僑、港、澳、臺各界享有盛譽。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壇上流行所謂文化大散文。這種散文大量涉及歷史事件掌故,企圖通過對歷史上的舊式人物、古老事件的緬懷和追蹤,挖掘當代人較少了解的史實,建構起比較高端莊嚴、如出土文物般的新散文路數。這種寫法也確實取得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但是這種散文寫作者的心靈和精神觸角比較隱蔽,往往求助于歷史資料和時代背景,掉書袋和轉抄史實就比較常見。這樣的書寫給讀者帶來的思考和啟迪很有限,自由想象和心靈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明顯的局限。散文寫作方式毫無疑問是自由的、豐富的,單純的文化挖掘和史實追尋,很難令人感同身受。陳慧瑛的散文真實誠懇,帶有明顯的記者身份特征和歸僑知識分子的實誠特點。這與她不到16歲就接受正規高等教育有關,及至1967年畢業時,陳慧瑛基本上學完了大學中文系本科課程,這使她成為“老五屆”散文家中的佼佼者。當時,這些學子深受新中國初期“散文四大家”——吳伯簫、楊朔、劉白羽、秦牧以及方紀、魏巍等人的影響,這些散文家大多是從戰火中成長起來的“記者散文家”。其特點就是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下,一個人民的記者必須是有情懷的,家國情懷,秉持正義,為人民的利益鼓與呼,所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陳慧瑛也是這樣一位記者型散文家。她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華北太行山基層鍛煉6年,深切地認識底層現實社會,后回故鄉《廈門日報》從事文藝副刊主任編輯10年。在當記者的時候,陳慧瑛就埋下了文學的種子,她的散文有些是在新聞基礎上,或者由新聞線索所引發的深度創作,因而更生動,更傳神,更接地氣,也更容易抓住讀者。
如《“很風景”的人——記旅美著名詩人、畫家秦松先生廈門行》《萍蹤俊影——記下達菲華校友佘明培先生》《威姆先生》《杜妮絲小姐》等。陳慧瑛以平等的視角,專注地接近所采訪的國內外名宿專家,抓住被采訪人物的特征,其愛國的情懷,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對祖國故土的鄉愁思念等。秦松先生祖籍江蘇,1949年15歲時隨家人去臺灣,1969年在美國各地舉行個人畫展及參加國際集體畫展后,定居紐約,1949年離開大陸赴臺之前,曾在廈門小住數月。這次故土重游來到廈門,“日光巖上望金臺,聊借一水慰相思呵!”從對家鄉的思念,到對“文化感”的認同,再到“又見老鄉”及至“詩魂·畫魂·中國魂”的交織,最后到“愛的歸宿”和“行內話”的文化人的交流,從素昧平生到一見如故,她與秦松先生的和對話,都是掏心窩的真心話。索爾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一個真實的細節比整個虛構的世界的分量還重。陳慧瑛的記者采訪和散文家創作渾然一體。她的散文不是“紙上的文學”,而是“生活中的文學,”也是現實中真實的美學。
陳慧瑛的散文創作,是感念故鄉,將深沉的愛通過感官的知覺放大的寫作。感官、記憶、在場感,作為寫作的母體和源泉,都是她的散文語言的質感、真實感和存在感的來源和依據。所以我們看到,陳惠英的散文沒有那種空泛的抒情,也不是那種無根浮萍,而是扎根在現實生活和事實基礎上的活生生的文學,她與生活的現場、大地的細節、故土的記憶緊密相連。記者型散文家會看、會聽、會嗅、會聞、會問、會感受,這些本來就很正常寫作才能,在陳慧瑛的筆下得以一一實現,因而具有了異乎尋常的價值和意義。
陳慧瑛的《有一種愛叫永遠》,不僅有47篇真情實感的散文,還有34首散文詩。這本散文和散文詩的合集,在全國也是不多見的。眾所周知,福建,特別是廈門不但出小說家、散文家、詩人,還出了不少散文詩作家。這與廈門美麗的自然環境和鼓浪嶼這塊浪漫的“琴島”有密切的關系吧。我也曾在廈門鼓浪嶼島上的海上花園酒店小住,島上游人如織,琴聲悠揚,海風習習,流光溢彩。劉再復先生也曾寫過不少精美深沉的散文和散文詩。從世界文學的范疇看,印度詩人泰戈爾憑散文詩《吉檀迦利》獲得諾獎,法國詩人圣瓊·佩斯憑他的散文詩《阿納巴斯》獲得諾獎。謝冕認為,“散文詩與其說是散文的詩化,不如說是詩的變體。”陳慧瑛的34首散文詩收錄在第三部分“鄉愁”中。集中體現出陳慧瑛的愛國、愛家鄉、愛父老鄉親的拳拳之心。這種情懷令人感動。家鄉的海色、潮涌、山水、黃昏、落日、古寺……都讓她流連忘返,熱淚漣漣。她為故鄉奮筆疾書,為家國縱情高歌,廈門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她的眼里都是創作的題材和謳歌的對象——“相思花謝了,合歡花開;合歡花謝了,鳳凰花開……終年不斷的花兒,連名字也充滿愛情色彩。”“該不是這兒的陽光特別富足,愛,才顯得這般旖旎?萬物,才分外充滿生機?啊,故鄉,一冊彩色的童話,一片滋潤生命洋溢愛情的土地!”這些流淌著詩情畫意的文字,似乎只有陳慧瑛這樣的出身經歷和身在廈門的人才會脫口而出!她說,“因為故鄉,我才有了絢彩的夢、清麗的詩,才有了百靈鳥一般的歌唱!”
她的散文詩,其實甚至不用評論家來解讀,只要讀者靜靜地閱讀,慢慢地欣賞,自然會與她情相通,心相知,同頻共振,愛意相融……
早在1985年,散文大師冰心在給陳慧瑛的信中寫道:
你的《無名的星》拜領并已拜讀,可謂文情并茂,我尤其喜歡祖國和故鄉那一段,希望你再多寫下去,我為故鄉多一個女作家而高興!
在1991年10月5日給陳慧瑛的信中又寫道:
你的大著《芳草天涯》收到并已拜讀,……你的散文,我很喜歡,特別是抒情中都有敘事,不是空泛地傷春悲秋、風花雪月,這種文字,我看膩了。希望你照此再寫下去,你不是“小冰心”,你有自己的風格。
陳慧瑛的散文,從內容上是與眾不同的,在形式上既能繼承古典散文直抒胸臆的表達方式吐納風云之志;又能嫻熟地借鑒古詩詞中的比興手法,巧妙自如地開篇布局,點燃她的散文和散文詩的鳳頭,發散出生命的綻放和靈魂的顫音!雖然,陳慧瑛是一個女散文家,但是她的散文具有豪邁的氣勢、豪爽的風格和豪放的情韻,充盈著對生活、對未來的歌唱和思考。
她的《梅花魂》《竹葉三君》《舊鄰》《鐘情》等散文,飽含著家人、友人和自己的親密感情,更流淌著濃郁的愛國之情。與書名同名的那篇散文《有一種愛叫“永遠”》,寫的是2010年第八屆世界同安聯誼會在古城同安舉行。來自30幾個國家和地區的92個代表團1500多名嘉賓,集聚故土,共敘鄉情,同襄盛舉。在廈門同安是著名的僑鄉之一。陳慧瑛作為歸僑中的一員,對數百萬福建籍的僑胞,特別是廈門同安籍的僑胞飽含深意,講述起同安的僑界名人,言之鑿鑿,情之拳拳。陳慧瑛追憶歷史上的同安人杰地靈,彪炳史冊——她的祖先、著名抗擊外侮的民族英雄陳化成;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凡有海水處,無人不知名”的陳嘉庚先生;著名鋼琴家、教育家,曾培養出顧圣嬰、殷承宗等鋼琴大師的李嘉祿先生和著名婦產科專家林巧稚先生等等,都是同安的僑胞,可謂群星璀璨,萬人敬仰。當代同安僑胞百里、千里、萬里歸來,投資建廠,振興中華,或投資興醫辦學,或扶貧濟困、修橋造路、或引資引智,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無數華僑和歸僑,他們在海外奮斗生存,把錢捐贈給國內,支持國內建設,立下了不朽功勛。海外華僑不但支持了國內的經濟發展,而且為國內的政治、文化、外交、社會等方方面面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這些僑胞鄉音難改,鄉情纏綿,心中永遠有一個愛的牽掛——中國是千萬海外僑胞的永不忘懷的“根”與“魂”。
陳慧瑛的散文有一種英雄豪邁之氣,有故土純樸天然地氣,華夏兒女骨肉同胞的血脈基因在字里行間流淌,炎黃子孫的文化基因在文中凝聚。她的《有一種愛叫“永遠”》,是連接大陸與海外華僑溝通情感的橋梁,是情系全球華僑歸僑的溫暖紐帶……這樣的散文寫作在國內獨樹一幟。特別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下,首先建設好全球華人命運共同體乃當務之急。從這個角度看,陳慧瑛的散文寫作具有一種示范和引領的意義。
(作者系廊坊師范學院文學創作與評論中心研究員,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