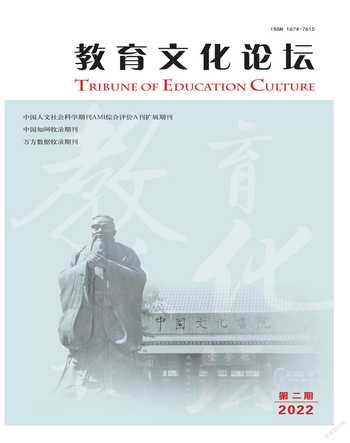梁啟超辦報研究芻議
葉思博
摘要:梁啟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當時著名的報人,他的政治思想貫穿于他的辦報活動。政治上幾經沉浮,他的思想亦在不停流變。其思想流變,不僅體現在他的政見上,也體現在他的報刊活動中。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和邏輯分析法,分別基于政治、文學和新聞專業主義的視角,對梁啟超的辦報活動進行梳理。
關鍵詞:梁啟超;辦報;政治;文學;新聞專業主義
中圖分類號:G21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7615(2022)02-0087-04
梁啟超的一生曾與多份報紙結緣:與志同道合之士合辦了《外交報》《選報》,于港澳創辦了《實報》《澳報》,“戊戌變法”失敗后東渡日本創辦了《清議報》《新民叢報》……梁啟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報人。因此,其創辦報刊的主旨、內容,常常伴隨著其政治思想的流變而發生變化。本文結合目前研究梁啟超的系列研究成果,基于政治、文學、新聞三個視角進行梳理。
一、基于政治的視角:流變與堅守的交織
在梁啟超的辦報生涯中,數《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這三份報紙影響最大,而這三份報紙也可以被看作是他政治思想的縮影,因為在短短十余年里,他完成了由“維新”到革命,再從革命到立憲的思想轉變。縱使千變萬化,他辦報的落腳點始終圍繞著救國思想。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與康有為逃往日本,同年12月創辦《清議報》。由于對晚清政府的失望,加之不得志的躊躇之情,令《清議報》一開始便喊出“明目張膽,以攻政府”[1]的主張。在日期間,由于梁啟超與革命派人往來密切,以及對日本社會的切身考察,使其逐漸與康有為分道揚鑣,思想開始轉向共和。1901年,梁氏甚至創建《新小說報》來專門鼓吹革命。兩年后,他赴美洲考察,再一次轉變了思想。在美洲,梁啟超意識到中國與美洲之間的不同,因此,放棄了以革命手段求得共和的想法,回歸了立憲陣營。同樣,這樣的轉變也體現在他的報刊中,《新民叢報》開始成為與革命派爭論的陣地。
我們可以說梁啟超的思想善變,但恰好說明他無時無刻不在為國家存亡和民族復興而思考。在不停的流變中,他仍在試圖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而從中體現的憲政理想從未改變。
“政本之本”的觀點最早見于《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這是梁啟超對報刊的政治定位,他始終堅守之。在古代社會中,報刊與君主之間是“臣屬”關系。梁啟超東渡日本后,將西方的社會契約論引入報刊與政府的關系,重新定義了報刊、政府和國民之間的關系:報刊不僅是政府的顧問,還對政府有監督之義;政府則是國民的“雇傭”。在日期間,他受學者松本君平的思想影響較大,并在其思想中提煉出了“政本之本”的觀點;后又在此基礎之上結合盧梭的“公意觀”,強調了報刊創辦的“公意”目的,并將這一責任歸咎于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上[2]。
其實,在梁啟超提出“政本之本”的報刊角色觀之前,他的系列辦報活動也體現了這一觀點,他的活動皆以“救國”為導向,以政治為基準。故而在他不斷流變的思想下,亦有堅守的信念與之交織。
二、基于文學的視角:詩風轉變下的宣泄
在梁啟超的辦報研究中,關于其詩詞的研究亦引人注目。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在文學史論中鮮有提及,直到學者夏曉虹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出版后,人們才開始逐漸考究梁啟超的詩詞。而他的詩詞風格,也如他的政治思想一般在不斷流變。從戊戌時期到民國時期,他的詩詞也走過了一條從打破傳統到回歸傳統的長路。
據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亡友夏穗卿先生》記載,在戊戌前夕,他曾與友人一同私下創造過“新詩學”,然直到1898年11月在《亞東時報》上發表《去國行》后,他的詩詞生涯才正式開始。在《去國行》中,他采取了詩、賦、文結合的形式,在保留了傳統詩文風格的基礎上引進了新名詞,縱橫恣肆,長歌當哭。與此前私下創作晦澀難懂的“新詩學”相比,《去國行》不乏新名詞且易懂、磅礴,短短數段便借助日本之國情表達了作者對維新的看法,這一作品被研究者視為其詩詞之路的開端。
1900年2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中發表的《汗漫錄》拉開了“詩界革命”的帷幕。在《汗漫錄》中,梁啟超認為數千年來,中國古典詩壇已形成一種既有的固定風格,雖風格成熟但卻喪失活力,故而他也提出倘若不進行“詩界革命”,那么中國將會面臨“詩運殆將絕”的境地。同樣,他也提出新詩歌應當具有“新意境”“新語句”和“古人風格”這三長兼備的改革總綱領,這亦是他對新詩歌奠定的理論基礎。在《汗漫錄》所著的31首詩中,無一例外地體現了梁啟超在詩界改革中的良苦用心,詩中大量運用“共和”“女權”“平等”等新名詞,祈盼通過引進新事物的方式解放國民思想,但同時也對古典詩歌的行文風格小心保留。《汗漫錄》是梁啟超對“詩界革命”的一次偉大嘗試,被視為揭橥“詩界革命”旗幟的“領頭雁”,其中所錄作品,皆為其親自嘗試變革的偉大實踐內容。但遺憾的是,在《冰飲室合集》中,《汗漫錄》被改名為《夏威夷游記》,其中的詩歌被全部剔除,這也直接導致后人在研究梁啟超辦報活動時常常遺漏其詩詞創作的部分,實為惋惜[3]。
在《清議報》中,梁啟超特開專欄“詩文辭隨錄”以志詩文,他曾用這樣一句話定位此欄: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為斯道別辟新土。在創刊的幾年中,梁啟超在“詩文辭隨錄”上發表了21題54首詩,且這些詩大致為留別詩、紀事詩、感興詩和自勵詩,詩中內容多為當時國情,飽含作者心中愛國情懷與救國抱負,體現了作者渴盼革命(特別是詩界革命)的愿景[2]。如《太平洋遇雨》中說道,作者在乘船過太平洋時偶然遇雨,這雨絲連貫了亞洲和美洲,已經離開的亞洲此時不知怎樣,但即將到達的美洲卻是令人向往。這首詩在當時被詩人用作聯絡暗號,詩中的“風雷”體現出其愿創出一番事業的志氣,但后又提及戊戌的傷痛與前段相對比,以此引人扼腕。同時,梁啟超在留別詩《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中暗示了其想在畫界進行革命,其全面改革之心可見一斑。
在《清議報》后,梁啟超創辦了《新民叢報》,先后在該報開辦了“詩界潮音集”和“飲冰室詩話”兩個詩詞專欄——前者是作者的創作實驗之地,后者是理論探究之田,二者相輔相成,一同形成了《新民叢報》的詩詞園地。拉開這一園地序幕的是《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這一作品后來也被稱為最能體現詩界革命精神的詩歌。這首詩歌全文一千五百余字,與古體詩歌不同的是,其篇幅較長,且長短句不一,行文論述已不再沿用古代表達方式,而是采用“半白半古”的風格行文。在這首詩中,亦不乏許多新名詞,如第一次提出了河流文明時代的“四大古文明祖國”(中國、印度、埃及和小亞細亞),這也是“四大文明古國”之說所可考究的最早雛形。總體來說,《新民叢報》前四號中刊出的詩詞,風格比較溫和,旨在開發民智,引導公德,與梁啟超此前對報館的認知較為接近;從第五號開始,其詩文風格大變,由溫和轉為激進,這同樣和他當時政治思想由保守轉向革命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梁啟超在創辦《新民叢報》時期大力提倡“詩界革命”,但他在評議古體詩歌時卻能做到公正客觀。例如,在評價舊派詩人陳三立時,他說“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在評價與自己詩風不同的章太炎等人時,他也毫不吝嗇贊美之詞。總的來說,《新民叢報》是梁啟超辦報生涯中影響力最為深遠的一份報紙,無論是從發行量、發行時間還是刊物現代化上看,這份報紙都是近代中國報刊事業的一座高峰。
梁啟超創辦了《新小說》雜志,在該刊創辦了“雜歌謠”專欄,該專欄陸續發表多首旨在振興國家的學堂樂歌,代表作有《愛國歌四章》等;他創作的《新未來中國記》《世界末日記》等多篇政治小說及翻譯的西方詩文也在該刊發表,啟發了民智。遺憾的是,梁啟超在報刊發表的詩文主要集中在1903年之前,此后創作減少,且后期詩歌也不再有此前“詩界革命”時的風姿。例如,《秋風斷藤歌》中充斥著舊名詞,《朝鮮哀辭五律二十四首》中充滿著舊風格和舊說辭。在1910年創辦《國風報》之前,他便已經開始思考詩歌的新體式,并同京城士大夫群體來往密切,詩風逐漸向“同光體派”轉變。
雖然梁啟超的文風歷經多次變化,其辦報思想、宗旨也在隨時而變,但在轉變之下,我們也可看見其情感的宣泄,不僅僅是每一次文風轉變時對國家安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見他對突破舊制枷鎖、突破其師康有為束縛的決心。在從《清議報》向《新民叢報》過渡的過程中,雖說《清議報》因火災停刊,但顯然這只是一個較為體面的推托之詞。現許多學者在研究《清議報》停刊原因時也認為,《新民叢報》的誕生,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對《清議報》之打壓、保皇會聲譽之損、經費緊缺等客觀原因造成[4],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梁啟超與康有為之間思想發生分歧且矛盾激化而產生[5]。因此,創建刊物的過程是梁啟超追求自我的過程,刊中創作也是其長期受制于康有為、保皇會后的宣泄。
三、基于新聞的視角:專業主義下的辦報
(一)報館定位:去塞求通
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梁啟超提出了著名的“去塞求通”之說,且認為報館應起到“耳目喉舌”之用。他曾借用西方諺語把報館喻為“文壇之王”,把報紙喻為國家的“耳目喉舌”,視為“現在之糧,未來之燈”[6]。學者黃旦認為,梁啟超式的報館橫跨于國與國之間,相交于君與民之界,在內與外、上與下的位置上來回運動[7]。但梁氏“去塞求通”之意并非糾結于它一成不變的形態,而是更注重其順勢而變的流動形態。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不同的國情之下,報館可以是一人之報,也可以是一黨之報,自然也可是一國之報、世界之報。但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報館都是去塞求通的功能性場所,且在當時社會中已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將報館視為“第四種族”,與君同級。
(二)超前的新聞思想:法制、自由與價值
1.新聞法制
梁啟超的新聞法制思想主要源自對誹謗、思想淺陋的治理。維新派人曾多次在發刊詞中站在法律角度辯證論述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梁啟超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頒布了限制報館不當行為的法令,是因為許多報館存在閉門造車、混淆視聽、意氣用事、道聽途說、斷章取義的弊病[8]。毫無疑問,周游西方世界的梁啟超早已受到這類思想的影響,認為誹謗不僅對政府、黨派、領導人的聲譽有重大損害,同樣對報館自身的威嚴有所消損。而一旦報館不再贏得國民的信任時,報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更不必說它去塞求通的價值了。而面對千篇一律、抄襲等思想陋習時,梁啟超則更是深惡痛絕,這也和他對報人提出的較高素養要求相吻合。
2.新聞自由
學者肖燕雄曾總結梁啟超的新聞自由思想:報館是自由言論與自由思想的集散地[9]。梁啟超認為,報館的言論自由和社會風氣的開放是相輔相成的:報館應盡監督權力之天職,因此,報刊上的言辭可以稍微偏激,但必須真實;意見相左的言論可在報刊上公開激辯,引起全民討論的熱潮,這樣一來,國民的思想就活躍了。
梁啟超的新聞自由思想建立在中國國情基礎之上,政治論、工具論的色彩較為濃重,他的新聞自由主義十分重視“中學為體”。因此,基于當時的國情,梁啟超以為言論當自由,但不可過度,這亦與傳統“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梁啟超的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希望言論過于開放,只需前進一小步即可[10]。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他曾自貶“五種弊病”以向清政府表示自己的忠誠,向清廷示好以求支持,因此,他的新聞自由還不是完全的現代化自由,這份“自由”還具有封建專制色彩。
3.新聞價值
梁啟超認為,許多報館存在閉門造車、混淆視聽、意氣用事、道聽途說、斷章取義的問題。可以發現,梁啟超之新聞是真實的事實,而且是重要的、新鮮的事實[9]。這說明,他認為新聞應當具有重要性和時效性。梁啟超說,《時務報》的報道應該“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同時“文甫脫稿,電已飛馳”[11]。這些皆體現其對重要性和時效性的嚴格把控。而這兩大新聞價值,現在也被視為當代新聞五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從哪一方面看,梁啟超能在百余年前提出此類想法,都是超前且積極的。
(三)新聞素養:基于“五本”“八德”的延伸
梁啟超對報館最出名的要求當數他在《〈國風報〉敘例》中的“五本”“八德”之說。實際上,除了“五本”“八德”外,他還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報道客觀性的要求,對報刊編輯提出了精英主義的鞭策,在編輯實踐中也有自己的創新之處。
首先是報館的客觀性要求。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中,梁啟超曾借用史家思想來論述報館的客觀性,認為報館要對歷史負責,撰寫之人要有獨立的思想與見解,不畏強權而敢于說真話。其次是對編輯精英主義的鞭策,這與史家精神中對編輯的要求是一脈相承的。關于精英主義,梁啟超在《論私德》和《論政治能力》中均表達出他對“中等社會”階級的期盼,認為“中等社會”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精英),而辦報人則屬于這一階級,報刊不僅要勸導政府,還要引導國民[2],這也和他的政治立場緊密相關。
在編輯實踐中,梁啟超在“五本”“八德”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在欄目設定、文體風格上都有自己的見解。欄目設定上,他曾對《時務報》中的“論說”和“紀事”作出了不同規定,“論說”以“公要周適”為主,“紀事”以“博速確直正”為主。除此之外,他還學習西方報社,在《中外紀聞》開創“一事一議”短評欄目,在《新民叢報》開辟“國聞短評”欄目,這些欄目都成為后來中國報刊編排的重要模板。文體改革方面,他以簡單通俗、鼓動性強的新文體為主,對傳統文體造成極大沖擊[12]。
參考文獻:
[1]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71.
[2]李濱.立憲目標下的報刊政治角色設想——戊戌后梁啟超的“政本之本”觀點探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19(5):95-101+112.
[3]胡全章.從“才氣橫厲”到“唐神宋貌”——近代報刊視野中的梁啟超詩歌[J].文學遺產,2013(4):144-152.
[4]張煒.從《清議報》到《新民叢報》——梁啟超棄舊圖新另辦報刊原因探析[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7,27(1):36-42.
[5]焦寶.梁啟超的思想變動與晚清報刊詩詞演進——以梁啟超及其主持的報刊為中心[J].浙江社會科學,2016(11):130-136+155+160.
[6]周帥.政治與文化的交融:梁啟超的編輯出版發行思想[J].教育文化論壇,2015,7(2):29-32.
[7]黃旦.報紙和報館:考察中國報刊歷史的視野——以戈公振和梁啟超為例[J].學術月刊,2020,52(10):165-178.
[8]陳力丹.恩格斯論黨中央對黨報的領導方式[J].新聞界,2016(1):67-68.
[9]肖燕雄,盧曉.近現代不同立場辦報之人的身份認同——以梁啟超、于右任、李大釗、史量才等人撰寫的報刊發刊詞為主的考察[J].新聞界,2017(3):24-32+106.
[10]朱清河,時瀟銳.彌爾頓與梁啟超自由主義報刊思想之比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31(4):223-227.
[11]梁啟超.論報館有益于國事[N].時務報,1896-08-09(1).
[12]巢小倩.梁啟超報刊編輯出版思想及其啟示[J].出版參考,2020(6):49-53+57.
Abstract:Liang Qichao, a famous politician, thinker, as well as famous newspaper m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is political thoughts ran through his newspaper publishing activities. Through political ups and downs, his ideas kept constantly changing, which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political views, but his newspaper publis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analyzes Liang's newspaper publishing activities
Key words:Liang Qichao; newspaper publication; politics; literatur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責任編輯: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