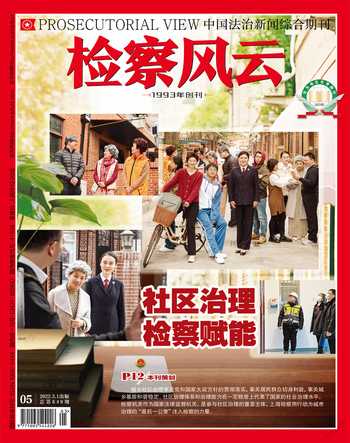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和刑法保護
顧偉 翁音韻 龔笑婷
從本質來看,虛擬財產是存在于網絡空間、具有一定價值的數據。稱其為財產,是因為部分數據的表現形式是現實的貨幣,具有獨立的價值。另有部分虛擬財產雖不以貨幣為表現形式,但能夠與現實世界的財產利益實現交互。因此,討論虛擬財產的法律保護具有現實意義。
基于虛擬財產的本質屬性,我國現行刑法框架下對侵犯虛擬財產的法律規制可循兩條路徑:一是基于其虛擬屬性,其存在方式依托于計算機系統。這一路徑著眼于維護計算機信息系統管理秩序,從而保護虛擬財產;二是隨著現代網絡社會的發展,虛擬財產除了本質上為電子數據之外,其被賦予的經濟價值日益突出。這一路徑認可虛擬財產具有刑法中財產的本質屬性,將虛擬財產納入傳統財產的保護范疇。
廣義的虛擬財產所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一切有價值的、存在于網絡空間的數據均可稱之為虛擬財產。“虛擬性”與“價值性”是其共性,但其使用目的、方式、存在形態等各不相同,在法律屬性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
一是金融資產類,如銀行賬戶、股票賬戶、基金賬戶中對應的金融資產。此類資產雖然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但它們是現實經濟利益的直接體現,可以在一定的交易規則下完成與現實貨幣的直接轉換,其財產屬性不存在爭議。
二是電子卡券類,是可以直接換取實物、進行消費,甚至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流通、交易的電子數據,包括可以兌換實物或當作現金抵扣的各類消費券、代金券、信用積分等等。這類電子卡券與實體經濟利益具有直接對應關系,有完整的交易機制,符合財產的基本屬性。
三是虛擬貨幣類。與人們普遍認知和廣為流通的金融資產不同,虛擬貨幣主要指數字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以比特幣為例,它是一種虛擬的加密數字貨幣,依據特定算法,通過大量的計算生成,在一定范圍內可以購買虛擬物品,甚至與現實貨幣進行兌換,經濟價值不言而喻。早在2013年,五部委在《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中指出,比特幣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應當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這雖然否定了其貨幣屬性,但客觀上承認了其財產屬性。
四是身份賬號類,即用戶通過注冊獲取的身份認證信息。驗證此類身份信息后,用戶可以從網絡服務商處獲取各類網絡服務,如QQ賬號、微信賬號、郵箱賬號、游戲賬號、股票賬號等。筆者認為,此類身份認證賬號不具有財產的基本屬性。首先,身份賬號存在的意義在于,讓用戶通過一連串特定的數字認證信息,實現身份的確認,或根據付費情況的不同,在相應的范圍內獲取網絡服務。身份賬號扮演的角色是媒介,是工具。雖然賬號作為身份認證工具具有一定使用價值,甚至部分賬號可以出售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但其價值不完全符合刑法對財產客觀經濟價值的要求。其次,賬號本身的價值性難以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同。雖然出現了“QQ靚號”可以一定價格出售的現象,但其價值并不符合大眾的認知,無法以穩定的市場關系體現出來,物價部門也無法給出人們普遍接受的估價結果。
五是虛擬物品類,普遍出現在網絡游戲中,包括游戲中的裝備、道具、角色等。此類虛擬物品有些是玩家在游戲商城購買的,有些則是通過在游戲中完成既定任務等方式獲得的,伴隨著玩家的經濟、勞動力投入。運用此類道具可使玩家在游戲中獲得精神愉悅,可以體現其在網絡空間的使用價值。
綜上,虛擬財產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其具有使用價值,其客觀經濟價值如何體現則各不相同,需要結合不同的情境具體考量。從大的分類上看,金融資產、電子卡券、數字貨幣等,均能夠與現實貨幣發生直接交換關系,其經濟屬性已成為本質特征;身份賬號、虛擬物品等更多體現的是用戶與網絡運營商之間的服務關系,與傳統的財物有所區別,其數據屬性仍然處于突出地位。
當行為人侵犯的虛擬財產主要以數據形式表現,其財產屬性相對弱化時,只須循保護數據這一法律適用路徑即可,該類行為一般應作為計算機類犯罪處置;當行為人侵犯的虛擬財產主要體現財產屬性時,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存在一定的爭議。
有一種觀點認為,侵犯虛擬財產可以作為牽連犯處理,如行為人實施盜竊虛擬財產的行為,必然要侵入計算機網絡系統,同時觸犯盜竊罪、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屬于牽連犯,應從一重罪處罰;另一種觀點認為,這屬于想象競合,盜竊虛擬財產的行為同時觸犯盜竊罪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可擇一重罪論處;亦有觀點認為,盜竊罪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之間不是想象競合,而是法條競合;還有觀點認為,應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關于利用計算機實施有關犯罪的規定處罰。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虛擬財產的保護是值得探討的法律問題
有觀點認為,該法條系法律擬制條文,通過計算機實施了上述行為的,應當依照刑法有關金融詐騙犯罪、盜竊犯罪、貪污犯罪、挪用公款犯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犯罪的規定以及其他犯罪的規定處罰,而不是按照關于計算機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例如,行為人利用計算機進行盜竊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處罰。
然而,筆者認為,這一法條文并非法律擬制條文,而是注意性規定。法律擬制條文,是指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特定法條的規定,但在特殊條件下刑法將該類行為擬制為特定犯罪加以處置。
注意性規定,是在刑法已作出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忽略的規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詐騙、盜竊等犯罪的,依有關規定定罪處罰,其提示性在于:一是突出利用計算機作為工具、手段或者載體的違法性,其目的是強調打擊日益猖獗的利用計算機實施犯罪的行為,將之作入罪化處理;二是明確利用計算機實施財產類犯罪,并非一概以計算機犯罪或盜竊等普通罪名認定,而應視具體情況認定。
當虛擬財產具有刑法中規定的財產屬性時,對其侵犯的行為有可能既屬于計算機類犯罪,又屬于侵財類犯罪。以盜竊虛擬財產的行為為例,行為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入計算機系統,刪改系統存儲的數據,進而實現對虛擬財產的占有,對其應如何定罪處罰?
進入計算機系統的方式可能有多種,當身份未被授權,或手段不合法時,就涉及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對此類犯罪評判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侵入行為。
通常,牽連犯實質上是評價數罪,科刑一罪。只有當某種手段常用于實施某種犯罪,或者某種原因行為導致某種結果行為時,才宜認定為牽連犯。如果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是一種獨立的構成要件行為,構成獨立犯罪,則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與盜竊屬于兩種犯罪行為,確實存在牽連關系。
此處的牽連關系指的是以侵入系統為手段,以修改數據為目的。如果行為人實施了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一款列出的違反國家規定,侵入國家事務、國防建設、尖端科學技術領域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同時有修改數據從而占有虛擬財產的行為,那么可以以牽連犯論處。
反之,如果行為人僅僅實施了侵入普通的計算機信息系統的行為,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二款的表述,侵入只是作為與其他技術手段并列的、獲取該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的一種方法,而非獨立的構成要件行為,則不涉及牽連犯的問題。如果對虛擬財產的占有是通過獲取數據的方式實現的,那么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本身就包含了得到這一結果的行為,應該考慮該罪名與盜竊罪之間的競合關系。
編輯:姚志剛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