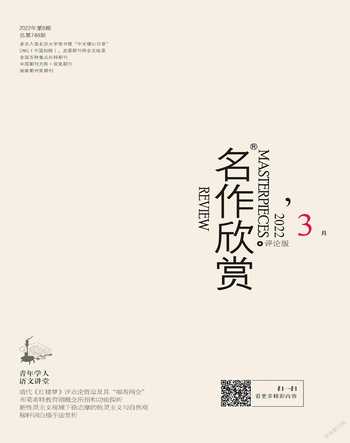后殖民主義視閾下的《弗蘭肯斯坦》
孫曉沖
摘要:英國女作家瑪麗·雪萊的作品《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因為外形丑陋,在誕生之初就遭遇了無情拋棄,并在數次嘗試融入人類社會失敗后,踏上了復仇之路。他從被拋棄、被孤立的邊緣人逐漸變成以牙還牙的復仇者,其所經歷的心路歷程就是被壓榨、被奴役的奴隸和被殖民者的真實寫照。本文將從后殖民主義視角出發,從“話語霸權”“邊緣化”和“混雜性”幾個方面論述怪物所處的邊緣人狀態和他反抗的必然性。
關鍵詞:《弗蘭肯斯坦》??? 后殖民主義
《弗蘭肯斯坦》是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夫人瑪麗·雪萊的處女作和代表作,被后世公認為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也是哥特小說的杰作。作品一經問世便聲名鵲起,成為很多戲劇和電影的底本。作品中的維克多·弗蘭肯斯坦博士和他創造的怪物,兩百多年來更是受到讀者不斷推敲和琢磨,從各個角度進行解讀和闡釋,諸如人類學、倫理學、社會學、女性主義、敘事學等方面,不斷給這部經典之作注入新的活力和時代氣息,后殖民主義理論更是為分析和解讀這部小說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后殖民主義思潮的理論化和系統化以薩義德《東方主義》的出版為標志,先后涌現出如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斯圖亞特·霍爾等優秀的理論家。他們的理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講后殖民主義“主要針對前宗主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帝國遺毒的對抗性話語,反對現代西方的文化霸權以及帝國主義的知識結構,強調文化的多元性,關注邊緣化、差異性和混雜性,維護前被殖民人民的身份認同”①。巴巴認為個體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與他者的差異中形成和確立的,通過與他者文化的協商,從而形成具有自身獨有特點的混雜性文化身份。《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就是被殖民者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極力想要融入人類社會,但因為缺乏該文化所能接納的最基本的外部特征而被拋棄、被孤立。本文將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結合作者的真實經歷和薩義德、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義,從“話語霸權”“邊緣化”和“混雜性”出發,探討怪物所處的孤立無援的邊緣人狀態和他追求自我的努力。
一、作者經歷
瑪麗·雪萊生長在一個思想開放、崇尚自由的家庭。她的父親威廉·戈德溫、母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丈夫珀西·比希·雪萊都是思想激進的英國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筆耕不輟,針砭時弊,其中奴隸制和對印度的殖民侵略就是他們關注的社會問題。長期以來英國都是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他們在北美殖民地驅使奴隸為他們種植煙草、棉花、蔗糖等經濟作物并從中攫取巨額利潤,可以說奴隸貿易為后期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資本積累和強勁的推動力②。直到1807年,英國政府才迫于政治壓力禁止了橫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但是殖民地的種植園主依舊可以合法蓄奴。從18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就對印度發動了侵略戰爭,不斷蠶食其領土,建立和擴大殖民地,進而瘋狂掠奪印度的財富。雪萊夫婦奔走呼號,為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終結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雪萊更是傾注心血寫成了《麥布女王》,其中的詩句更是表達了他對奴隸制的痛恨以及對平等自由的不懈追求:
要知道,權力好比猖獗的瘟疫,
凡是被它碰到的都被它玷污;
服從,滅絕了天才、道德、自由和真理,
使人一個個變成奴隸,
把人類的肉體變成了一架機器。③
除了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們還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們所屬的時代。就瑪麗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歷而言,也可以看出她創作《弗蘭肯斯坦》的深意。“她反對英國為了自身利益剝削和踐踏其他國家,批評英國人的妄自尊大……試圖扭轉歐洲中心主義的殖民話語。”④因此,在一定意義上,瑪麗在她的作品中含蓄、迂回地表達了對殖民地國家和人民與倍受驅使和排擠的他者的人道主義關懷,而作品中的怪物就是他者形象的藝術再現。
二、維克多的話語和文化霸權
在《弗蘭肯斯坦》里,最具寓意性的人物就是造物主維克多,他出身顯赫,祖先和他父親都是市政要員,政績斐然。他理性、求知欲極強,崇尚自然哲學,是科學奇跡和先進技術的化身。他掌握著創造生命的能力,是上帝一般的存在,同時也掌握著絕對的話語主宰權。在他的敘述中,總是不經意地流露出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感。當他媽媽帶著他去窮人家里走訪,“她看到一個農民和他的妻子在干著苦活兒……最引起媽媽注意的是其中一個孩子,那孩子似乎屬于另一個種族。其他四個孩子都是結實的小流浪兒,黑眼睛。而這個孩子卻很瘦弱,是明顯的金發碧眼。衣服雖然襤褸,那頭非常耀眼的金發卻似乎給她戴上了一頂輝煌的王冠……她的容貌特征帶了天堂的印記”⑤。他在頌揚一個種族的同時也在貶低另外一個種族,這無形中暴露了他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只有金發碧眼的白人才配得到他們的幫助和拯救,而黑眼睛無疑代表著亞洲,代表著少數派和不被白人所接受的“他者”。可以說維克多是以“凝視”的方式制造出來“被凝視”的東方,塑造出亞洲人的“他者”形象。在故事的一開始,讀者就可以感知到維克多敘述中東/西二元對立的權利關系,符合西方審美的伊麗莎白成為他母親優先救助的對象。相比之下,有著亞洲人特點的孩子則顯得黯然失色,這也為后面的故事走向埋下了伏筆。
隨著故事的發展,當他夜以繼日地創造出怪物之后,他對亞洲人的偏見或者是歧視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偉大的上帝呀!他那黃色的皮膚幾乎覆蓋不住下面的肌肉和血管。他有一頭飄動的有光澤的黑發、一口貝殼般的牙齒……”⑥黃皮膚、黑頭發明顯是東方人的相貌特征,再跟怪物的長相聯系起來就具有隱喻的意味。聯系歷史,當時英帝國在全球擴張殖民地,印度正處于英國的占領和奴役中,駱謀貝認為將“怪物理解為受英國奴役的東方國家的隱喻亦無不可”。維克多把他的創造物始終定義為“可怕的妖怪”,“木乃伊也沒有他猙獰……是但丁也設想不出的奇丑的怪物”。⑦眾所周知,人們對種族差異的感知首先是相貌上的差異,而維克多在沒有給予怪物任何相處關愛的機會的情況下,僅僅因為外形差異就直接把他的創造物等同于邪惡,為拋棄他尋找理由,這更像是殖民者和原住民的關系。齊亞烏丁·薩達爾指出,在西方人眼里,“東方是未開化的,是異教徒的,是處于基督教世界的傳統法令和約束之外的……也是偏僻、屈從和劣等的”⑧。從這個角度來看,怪物和他的造物主之間存在著種族上的鴻溝,無論他丑陋與否,在維克多的眼里他都是劣等的、邪惡的。在怪物沒有學會人類的語言之前,在他沒有能力反擊的情況下,維克多以自己的審美、價值觀把他直接定義為惡魔,本質上是他給怪物施加話語霸權,使他處于失語的狀態,從而加強了他的“他者”身份。因此,怪物本身并不奇怪,他天性溫良,崇尚美德,厭棄人類的邪惡,而維克多卻把他假象成了怪物。
李應志在《后殖民人物與思想》中說:“薩義德指出霸權不是通過暴力的形式強加的,而是通過知識等形式的‘說服’、通過積極的‘贊同’來實現的”。在小說里,維克多并沒有強制怪物接受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思想歷史,而他背后的西方文化卻無時無刻不在對怪物施加著它滲透性的力量。當躲在棚舍里的怪物看到“菲利克斯給莎菲上課用的課本是沃爾涅的《帝國的滅亡》時……我聽到了亞洲人的懶散,希臘人驚人的智慧和思想,早期羅馬人的戰爭,他們驚人的美德、之后的墮落”⑨,怪物所習得的所有知識都表明,西方的歷史是充滿智慧的、光輝的,而相比之下,非西方的文明都是野蠻的、落后的和無秩序的。正如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所指出的:“這種區別表現為天然的西方人的優越性和東方人的低劣性這一等級秩序……東方人思維上的缺陷、性格上對謊言的癖好、生活上的渾渾噩噩,在任何方面都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貴形成鮮明的對比。”“我想起了自己的處境……我沒有錢,沒有朋友,也沒有財產,只有一副奇怪形狀,令人厭惡的外表……我是魔鬼嗎?是世上的污點嗎?”⑩聯系歷史我們發現文明、科學、進步一直以來都是殖民主義最為有力的辯護詞,使得他們的殖民征服合法化。在強大的文化霸權施加的壓力下,殖民地人民被收編吸納,站在了“文明”的一邊,喪失了文化上的自我主體性。怪物也不例外,他的知識越多,他對自己就越厭惡,內心就越痛苦。面對強大的西方文化,自我主體性的缺失使得怪物無法真正坦然地面對自己,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中無法自拔。
三、怪物的邊緣性和混雜性
怪物在被創造出來之后就遭遇了維克多的拋棄,饑寒交迫的他受到恐慌的村民的追趕和攻擊,最后在村莊附近的一個廢棄的茅舍里棲身,并偷偷觀察一家人的生活,慢慢地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因為“只有掌握了他們的語言,我才可能使他們不在意我這奇怪形狀”。他企圖通過語言走進他們的世界,得到他們的認可和接納。“我想象他們會厭惡我,但我可以用溫和的態度與和解的言辭先獲得他們的歡心,再贏得他們的喜愛。”?在一定意義上,他放棄了自我,任由自己被他人掌控卻不自知,他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法農在他的代表作《黑皮膚,白面具》里一針見血地指出:被殖民者尤其因為把宗主國的文化價值變為自己的而更要逃離他的窮鄉僻壤了。他越是拋棄自己的黑皮膚、自己的窮鄉僻壤,便越是白人。這種邏輯使得怪物認為只要接受人類的文化,使用他們的語言,他自身的缺點就會被遮蔽,從而贏得人們的歡喜。當他鼓起勇氣想要打破沉默,靠近盲人德拉賽,向他吐露心聲并憧憬獲得一家人真摯的友情的時候,現實卻給了他沉重的打擊,“我為痛苦和悲傷壓倒,見他第二棍就要打來……趁著混亂偷偷躲進了我的棚屋”?。怪物抑郁苦悶的直接原因是他從維克多和德拉賽一家那里得知自己的粗糙、丑陋、卑微和低賤,“我的長相猙獰,身材龐大”?,他的自我厭棄越強烈,想要融入人類世界的愿望也就越強烈,而正是這種愿望慢慢地吞噬了他。殊不知被他描繪得知書達理、溫文爾雅的德拉賽一家和理性、才華橫溢的維克多到頭來面目可憎、偽善且言行不一。
“混雜性”是怪物身上另外一個重要的特點,也是后殖民主義的關鍵詞之一。所謂“混雜性”是指當各種文化交叉融合在一起時,處在文化雜交中的個體會在建構身份時表現出身份困境和雙重的文化身份建構。“可我的樣子卻是最丑陋的人的形象——因為像人,所以才顯得特別恐怖。”?怪物的困境是他介于人和怪物之間,只是長得“像人”,這種特點使他也無法成為真正的怪物,自我和他者在他的內心不斷博弈,使他表現出強烈的身份困境。這種混雜的身份困境是一種劣勢,但同時也是一種優勢。游離于怪物和人類兩種身份之間,使怪物可以取用不同的身份,從而超越身份二元對立的僵局,以一種混雜性的身份重構自己的主體地位,這是怪物的唯一出路,而他卻執意要建立單一的、非此即彼的身份,這必然會失敗。
四、怪物反抗的必然性
在經歷種種磨難后,怪物對待自己身份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起初他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自己掌握了對方的語言,真心實意地跟人類交往,就能夠獲得他們的青睞。彼時,他的自我是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只能甘于接受人類的評判,并將自己定格為丑陋可怕的怪物。接踵而至的打擊使他敢于面對真正的自己,是怪物的自己。他的自我意識逐漸被喚醒,開始對自己的造物主宣戰,殺了維克多的弟弟并且不無得意地說:“我也能制造不幸了!我的敵人并不是不能征服的。這孩子的死能讓我的敵人絕望……”?。他進而向維克多提出讓對方再制造一個跟他同樣奇形怪狀的可怕女人,因為只有同類才不會嫌棄他,他才能建立自身平衡穩定的身份。他還表示自己“永遠不會卑躬屈膝,像個下賤的奴隸。受到了傷害我就要報復。我既然不能怕人,就得讓人怕……”?融入人類社會的希望破滅后,他對自己身份做了反思和調整。在維克多拒絕為他制造同類后,怪物憤怒地說:“是你制造了我,可我是你的主人。服從命令吧。”?從被動的、盲目的崇拜者變成了主動的破壞者和復仇者,怪物最終完成了自我主體性的確定。在殺了維克多好友克萊瓦爾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后,他選擇了自我毀滅。
五、結語
怪物學會了感知、生火、閱讀、寫作和理性思考,最后才學會了復仇,他并非誕生之初就會謀殺。如果說他真的是怪物,那也是人類社會造就的產物。作為造物主,維克多拋棄了怪物,他自己的“孩子”。與“父親”的疏離迫使怪物在其他人身上尋求愛與溫暖,換回的只是躲避和恐懼。冷漠、孤獨占據著怪物的生活,使他無法喘息,報復的種子慢慢開始發芽。這表明即使被殖民者愿意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去融入殖民者的傳統,沖突也會產生,因為殖民者的文化無法接受缺乏共同文化記憶的“他者”。要構建自己的主體性必須通過反抗才能實現,即使這是一條充滿暴力和血腥的不歸路,因此怪物的反抗具有必然性。瑪麗·雪萊在小說中間接表達了自己對殖民地人民的理解和同情,為他者發聲,這種難能可貴的人道主義情懷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也依然有著重要的思想價值和文化意義。
①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
②楊瑛:《英國奴隸貿易的興衰》,《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4期。
③〔英〕珀西·比希·雪萊:《麥布女王》,邵洵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頁。
④原玉薇:《瑪麗·雪萊在殖民時代的普世關懷》,《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⑤⑥⑦⑧⑨⑩???????〔英〕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孫法理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頁,第52頁,第54頁,第22頁,第130頁,第47頁,第30頁,第123頁,第125頁,第149頁,第140頁,第142頁,第120頁。
參考文獻:
[1]駱謀貝.“他者”的幻象——《弗蘭肯斯坦》東方主義批評[J].外國語言文學,2015,32(4).
[2]齊亞烏丁·薩達爾.東方主義[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弗朗茲·法農.黑皮膚,白面具[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4]李應志,羅剛后殖民主義人物與思想[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