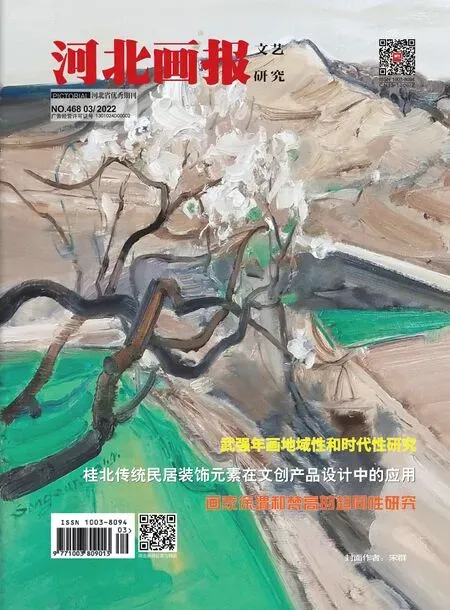中西文化比較
——徐渭與梵高
李美娟
(澳門城市大學)
一、徐渭與梵高身世經歷的“相似性”
(一)徐渭的人生經歷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為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演戲時用的帳頭木偶,只是在戲中用,并非是真實的世界,而他畫這“玩偶”的世界,亦不是真實的世界,借“戲帳”來喻宇宙之天地,每個人皆是戲中人。采用戲謔的態度看待世界,這與徐渭的人生經歷有重要的關系,天才縱逸卻命運多舛,悲慘的人生經歷是其性格形成的重要成因,而個性又深深影響著他的藝術風格。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出生于紹興府山陰縣觀橋大乘庵東(今屬浙江紹興),出生百日后,其父去世。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在十歲時,生母被苗氏趕出家門,骨肉分離,與長兄年齡相差三十多歲,缺乏手足之情,青少年時未得到親生父母的疼愛,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故而有寄人籬下之感。但他從小聰穎異常,文思敏捷。六歲讀書,九歲便能文,十多歲時仿楊雄的《解嘲》作《釋毀》,當地紳士們稱其為“神童”。自幼以才著稱,卻在科舉屢遭挫折,二十歲考中了秀才,但到其四十一歲時,已經經歷八次考試卻未能中舉。在其二十五歲時,家產又被豪紳無賴霸占。二十六歲時,妻子因病早逝。家破人亡,功名不第。嘉慶三十三年,由于倭寇進犯浙閩沿海,徐渭先后參加多地戰役,出謀劃策。嘉慶三十七年,升任浙閩總督的胡宗憲而后被招入幕府,充當幕僚。嘉慶四十四年,胡宗憲死于獄中,原先幕僚也有少數人受牽連。徐渭生性偏激,連年應試未中,精神上不愉快,且擔心自己受到迫害,因此,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后因狂病發作中,懷疑妻子不貞,將其殺死而后入獄。出獄后,應好友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關系惡化。張元忭個性嚴峻、恪守禮教,而徐渭生性放縱,不愿為傳統禮法所束縛。晚年潦倒,貧病交加常至斷飲。不肯見富家貴室,低首乞食。一生反復自殺九次之多,患有狂病,將心中之情揮灑在文學、書法、戲曲、畫作之上。去世時,身邊唯有一狗陪伴,連一鋪席子都沒有。享年七十三歲。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正是徐渭這跌宕顛沛的人生,奠定了其有著不同的人生觀,對于生命也是有著不同的感悟。將其性情融注于筆端,創造驚世駭俗的杰作之品。徐渭的朋友離浙去北京,送別詩云:“不但別離才苦惱,時時悲喜戲場中。”離別之感,對于人生的體悟。他的詩常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之氣。他筆下的戲謔揮灑,宣泄內心無盡的憂傷,何嘗不是心靈的悲歌?
(二)梵高的人生經歷
“我的悲傷將永遠留存”梵高的曲折人生,享年三十七歲,割耳一次,自殺一次,在世時是鄰居口中的瘋子,家人中的失敗者,作品從一文不值到千金難買,作為荷蘭后印象派畫家,是后印象主義的先驅,并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的藝術,尤其是野獸派與表現主義。他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色彩世界,呈現唯他特有的一種表現力量。
梵高出生于1853年3月30日荷蘭鄉村津德爾特的一個新教牧師家庭,“發芽的種子絕不會裸露在凝霜的寒風中,而那正是我的人生一開始就面臨的狀況”。梵高,在幼年時是缺少母愛的。早期畫風寫實,受到荷蘭傳統繪畫及法國寫實主義畫派的影響。1886年,他來到巴黎,結識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畫家,并接觸日本浮世繪的作品,視野的擴展使其畫風巨變。1888年,來到法國南部小鎮阿爾,與高更交往,創作《向日葵》系列等。此時,梵高的瘋病已經時常發作。同年12月,梵高與高更的關系逐漸惡化,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梵高生了幾場大病,經常出現幻覺。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割掉了一只耳朵。后被送于療養院,在1888年12月到1890年7月他去世前的這段時間里,共完成了450幅作品。1890年7月,梵高在精神錯亂中開槍自殺。
“我感覺到內心有一股力量……一團熊熊燃燒、無法熄滅的火焰”,這體現了他對于繪畫的熱情。人生經歷影響了其創作風格,不被陳法所拘,而是用獨特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例如,1887年的《向日葵》,梵高重新建構自己的繪畫方式,顛覆已有的審美觀,1888年以后,梵高的藝術又出現了新的風貌,以螺旋形和波浪形的筆觸來表現對象,色彩鮮艷強烈,筆法大膽,畫面上常有象征性的想象,如《黃色的麥田與絲衫》《阿爾女郎》及《自畫像》等。但梵高的黃金時期是短暫的,不久之后就患上了精神病。1890年,弟弟提奧把梵高接回了巴黎,梵高仍繼續作畫。但以前瘋狂的熱情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畫面是寧靜的、強烈的、無望的痛苦,例如,《暴風雨后的麥田》《有烏鴉的麥田》。
二、東方文化之徐渭
東方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以下從語言上進而分析。在語境中,去解讀并比較各自的文化與思想。語境,顧名思義就是語言形式產生的環境。狹義而通俗地說,語境指口頭說話交流中的前言后語,或書面寫作表達中的上下文聯系。所謂語境,實際上可看作語言的文化背景、歷史傳承、時空環境、心理訴求以及情緒景象等。“一個詞對于中國人則是表達一個理念,西方的詞則是必須顯示的是聲音。”例如,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以蓮花象征著君子的品德,比喻從污俗的環境中走出來,卻能保持純真的品質而不沾染壞習氣。而徐渭的《畫荷壽某君》:“若個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為,況直雙槽琥珀黃。”將滿池荷香匯于紙墨中,透過這虛虛實實的墨色當中,看到的是玲瓏剔透的琥珀黃,縷縷不盡的香意,憂淡而感傷。沉醉于墨海之中,需配備百年之飲。借荷花的品德喻此詩祝壽,呈現心中痛快淋漓的俠氣,表一番生命狂舞的衷曲,滿篇淋漓……所呈現的則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以小見大,從一朵花中感悟宇宙的奧秘,去體味人生,表現中國文學的不可窮盡性和朦朧性的美。
對于中國繪畫發展的認識源于文化與思想,以下從思想層面進行分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出自老子的《道德經》,中國的宇宙觀中,從宏觀的整體看待事物,而不是片面地進行分析。這樣的觀察方式造就了中國的思考方式的獨特性。“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指人與道合而“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乃是講述中國文化的特點,普遍聯系之整體概念。例如,王羲之的《蘭亭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便說明中國的觀察方式并非西方的“焦點透視”,而是采用“景外鳥瞰”的觀察方式進而“經營位置”于畫紙上。徐渭的《四時花卉圖》:“老夫游戲墨淋漓,花草都將雜四時。莫怪畫圖差兩筆,近來天道夠差池。”或許有差池、殘缺的作品可能反而是更加生機勃勃的,更有生命力的一種渲染,例如,西方米洛斯的《斷臂的維納斯》,渲染的則是不完美之美,這種殘缺的美表現的反而是更真實更有味道的美。并且一切都是在生命流轉之中,一切事物都在變化發展中,畫家筆下花草的呈現也并非客觀物質存在的花草,而是賦予花草生命力,包含創作者的主觀情感以及事物的本質特征。
基于以上東方文化在語言層面與思想層面的解讀,進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繪畫的獨特的造型表現方式即“意象造型觀”。“意象”作為一種美學概念,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從古至今,創作者一直把意象作為審美核心要素之一來對待。顧愷之的“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蘇軾的“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齊白石的“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徐渭的《魚蟹圖》中,“逸筆草草”的揮灑水墨淋漓之感,墨暈翻飛,妙在收放控制,極有章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同時,使觀者能夠解讀作者筆下更深層的意義,包含客體象征的真正內涵以及蘊含著的審美觀,從而也通過某些蘊含深意的客體象征著人生價值觀,以及情感的表達等。因此,只有理解中國繪畫獨特的觀察方式,才能理解中國畫的“造型觀”,才可以使觀者更好地解讀中國畫之美。
三、西方文化之梵高
十九世紀是藝術發生重大發展變革的時期,學院派的純粹理性化創作方式不再占據權威地位,從而出現了眾多特點迥異的藝術潮流。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流派包括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印象主義。在西方繪畫大發展的過程中,梵高到巴黎遇見了印象派與新印象派,融入鮮艷色彩和畫風,創造獨特的個人畫風。
1887年的《唐居老人》標志著梵高正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畫面色彩明艷、線條滯拙有力、用筆粗獷奔放,帶有深深的情感。同年的《向日葵》,用“折枝”的方式,以靜物為表現對象來對待,此作品風格并非主流審美,而是表現自己感受的狀態,重新建構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顛覆當時已有的審美觀,具有獨特性。
約1889年,梵高的藝術又出現了新的風貌,常以螺旋形和波浪形的筆觸來表現對象,色彩對比極端強烈,筆法更為大膽,畫面常帶有象征性的想象。“想象力的發展走向超越物質的世界,走向無拘束、無邊無垠的精神世界”,這也正是對梵高狀態的描述,例如,《金色的麥田與絲衫》《星夜》《自畫像》等。
《自畫像》梵高一生創作多幅自畫像,1885-1889年完成了40余幅不同神態的自畫像。其呈現畫家觀察自己并顯露深層心理的表達方式,通過筆觸、色彩的表達,感受畫家的內心情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梵高不被陳法所拘,而是推陳出新,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其情感的力量。
四、徐渭與梵高繪畫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徐渭與梵高同樣有著悲劇的人生經歷,卻也都在繪畫史上書寫了傳奇,既有獨特性又有共通性。徐渭患“狂病”,梵高患“精神病”,二人都有自殺的經歷,同樣有著對于現實生活的憤懣之情,并且都創造了一代新畫風,對后世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打破文化差異性,二人皆在畫作中盡情抒發強烈的情感。不為陳法所拘,而是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通過藝術創作來實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徐渭與梵高同樣有著強烈的個性,都在極其自我與個性的表達之中,表現與身世相關聯而創造的“繪畫語言”,皆具有“狂放”的特質,呈現強烈的情感力量。徐渭的繪畫風格反傳統文人畫的恬雅閑適,開創大寫意的手法,其畫作具有強烈的生動之美。梵高的作品呈現唯他特有的一種表現力量,將自己的感受化為強烈的色彩與筆觸。
徐渭用中國的水墨在畫紙上揮灑,梵高用油畫顏料在畫布上盡情繪畫,使用不同的繪畫工具表達心境、抒發情感。而對于當代的人們在欣賞畫作時,能夠在《墨葡萄圖》《星夜》中感受到特別的情感。《墨葡萄圖》中,畫作以淡墨鋪出大片葡萄葉,生動的葡萄粒仿佛隨風搖曳,墨色淋漓揮灑抒之,畫面以濃破淡,葡萄的晶瑩剔透、隨風搖曳,仿佛訴說著無盡的寂寞孤傲之情。《星夜》中,畫中如空氣流動的漩渦造型,將空氣的流動與旋轉的星體融入湛藍夜空中,松柏、村莊也同樣在運動著,宇宙之間仿佛是“渾然一體”的至極狀態。“燦爛的青玉與藍玉嵌成的天空,地獄一般的熱灼而腐爛的天空,熔金噴出一般的天空,其中懸著火輪一般的旭日。”這是當時巴黎的雜志《法國水星》上刊登的一篇贊美梵高繪畫的文章。這兩幅作品都給人以至深的感動,產生情感共鳴,這便是偉大藝術作品的共通性,深深感動內心。一個用毛筆水墨來進行繪畫,一個用色彩顏料來繪畫,用不同的工具去塑造心中的意境……
以自由意識抒發性靈,用心靈去建構理想的世界,去領會生活中的觀察之美,去揮灑心中之情。因此,我們在畫中能夠產生共鳴,充滿快樂與痛苦,充滿狂躁與平靜,充滿渴望與厭惡,矛盾的情感糾纏在一起,畫家所揮灑的每一筆的濃淡干濕,都是充滿著運動之感,暗示了心中之想,動之以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王國維的這句話讓我們每每賞畫之時,都環繞于耳邊。欣賞徐渭《墨葡萄圖》中的畫與詩,對于作者的身世以及心中之情一遍又一遍感嘆可惜。經過400多年的時間,畫作讓我們與古人仿佛隔空對話,以畫作為媒介,產生共鳴之感。欣賞梵高的《向日葵》,昂首挺胸的向日葵的金黃色,仿佛與太陽在對話,捕捉瞬間的美,感受到梵高繪畫的速度,像火焰似旋轉的筆觸,而色彩也是一點也不吝嗇地描繪,一層一層渲染向日葵的情感,梵高在畫中抒發著不盡的熱情。在距今約130年的時間,讓賞畫的人們可以感受到他對于繪畫的熱愛,感受到炫耀奪目的向日葵永遠追逐陽光,永遠充滿著生機與熱情。
五、結語
中國畫作為藝術中獨特的畫種,隨著逐步發展,影響力的提升,而廣為人知,與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使中國畫蘊涵了獨特的智慧與哲學思想。本文探析徐渭與梵高同樣的悲劇人生經歷,并且在藝術上取得了非凡的藝術成就,解讀其受個性影響的藝術創作風格,以及中西文化比較中的獨特性,并打破文化差異,探究二人的共通性,通過作品實現個人價值,表達其心境以及對于藝術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