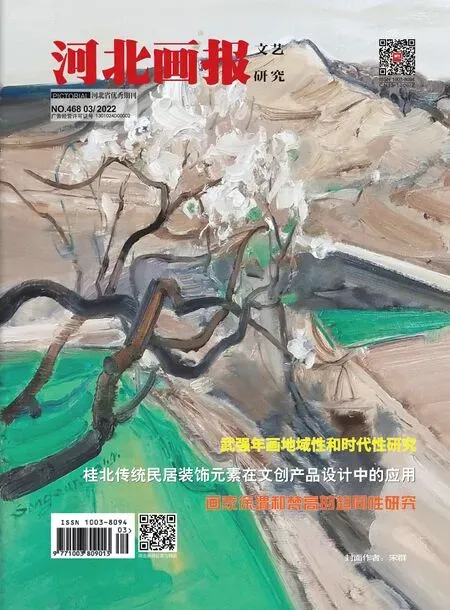澄懷味象
——論中國山水畫的寫意性
黨志斌
(西北民族大學)
中國人對于意象和意境的追求是自古有之的,無論是文章、詩詞、歌曲、繪畫等,藝術創作者所想表達的思想往往深深隱藏在作品形象之中,通過藝術手法的修飾將獨特的精神與作品形象相融合。山水畫是中國的主流繪畫題材之一,對于美好事物的描述、對于山水美景的追求,都是山水畫得以發展的動力。對于山水寫意的優化其實從未停止,新時代下對于如何將情感寄托于山水,以及如何利用情感豐富山水畫的意境,都是山水畫家在不斷研討的課題。
一、中國山水畫發展概述
縱觀中國文化藝術史不難發現,時代背景的變化才是促發藝術理念改變的主要動力,尤其是在社會矛盾尖銳的動蕩時期,對于封建朝廷的無奈、對世俗現狀的失望,都會讓文人雅士希望逃避現實、去追求虛無縹緲的天地之景,對于山水畫的發展歷程同樣如此,贊揚自然美景、將情感與希望寄托于山水畫像之中,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尤其是在由“盛世”轉變到“亂世”的過程中,藝術創作者的內心道德體系崩潰,社會整體的審美偏好也開始變化,對于山水意象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這種愈受外力擠壓,愈以退守為反抗的獨特心態,是受到中國封建社會特征以及中國獨特審美理念的影響,就是在感到現實無望的情況下,將自身際遇、希望、志向、思維觀念等都寄托在山水之中,用山水意象來宣泄情感,追求化實為虛、虛中求韻的創作意境,從審美角度避開社會現實,在失望與希望中渴望得到解脫。所以山水畫的發展歷程是我國傳統社會不斷在安定與動蕩之間徘徊的象征之一,山水意象將天地之景與人文情感相互交融,畫家的過往前塵通過筆鋒滲透入顏墨之中,構成了山水之畫的獨特魅力。
在中國的藝術形式中,其實一直都不倡導直抒胸臆式的情感表達方式。一方面是因為封建統治者的控制,一些特有的詞匯和句子不能直接展現出來;另一方面則是藝術習慣使然,無論是詩文、小說、繪畫、歌曲等,真正受到追捧的作品一般都是將作者思想內涵暗藏于作品之中,或是側面影射社會現實。但是我國傳統藝術中又不喜歡使用抽象的創作方式,也就形成了以具體的形象,隱晦地表達作品目的的創作習慣,形成了越是需要鑒賞才能感悟出思想內涵的作品,就越會受到文人追捧的藝術潮流。所以根據對史料的研究,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史基本是以下面幾個時期為主: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畫以獨立面貌登上歷史舞臺。此時對于山水景色的感悟、對于山水之景的描繪和表達,已經突破了漢代“比德”傳統,不再認為山水之美是由其影射的人之德行決定,而是注重山水之物本身的美感,重視挖掘山水之間原本的韻味。宗炳的《畫山水序》是中國最早的一篇山水畫論,對于如何構造基礎的山水形象、如何賦予山水獨特的意境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除了展現直觀、簡單的美感外,生物與生物之間的交匯、環境對環境的彼此影響等,都暗含著天地間最基礎的道理,世間之法往往便存在于一花一草一木一石之間。“暢神”則是心靈與自然相呼應的玄理之境,在這種境界中,個人的經歷與過往通過感官與外界共鳴,從而感悟自然之道、宇宙之理,這也就是為何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景會感受到不同的精神。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山水畫家更注重如何表現山水本來的面貌,以及如何將情感寄托于天地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時期的山水理念或許是對“天人合一”之理的傳承。
隋唐五代是山水畫迅速發展的時代。由于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朝代不斷在“盛世”與“亂世”之間“反復橫跳”,時常出現以人力扭轉乾坤的事件,所以“無法無天”的世道下對于“自然”的敬畏、對于“天地真理”的追求自然是有所減弱,此時的繪畫美學理論重心轉移到強調畫家創造力、張揚畫家的創造精神層面上來。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一時代的藝術創作并非完全執著于藝術形象本身,山水更像是畫家抒發志向情感、逃避現實的一種手段。其中張璪認為山水不應當是簡單的景物,情感也不是單一的人物情感,而是山水通過情感的加持而更有意義,畫家也是在看到了美妙的山水景物之后才情感迸發。可以說張璪所強調的主客、心物的交互融合,是對山水畫題材的集體升華,原本簡單的借景抒情,升級為在山水之物間營造意境,簡單來說,就是將情感通過意境表達出來,而不是直接將情感寄托于山水景色之中。
宋代是中國山水畫發展的高峰,這一階段的社會情況更加復雜,藝術創作者更希望借用文化來“粉飾太平”。在這一時期,郭若虛于《圖畫見聞志》中明確點明的“意象”的概念,對張璪的藝術理念深表認同。他認為“意象造型”的前提是畫家要有一個審美心胸,就是畫家本身就要對自然有憧憬的心理,要有追求天地之理的心胸,對于任何山水景象都要包容學習。他主張山要包括對原本山水景色之美的展現,又要營造出合適的意象,將情感寄托于意象之中。對于山水畫“象”的營造,宋代山水畫總體上呈現出“意”“象”兼備的山水面貌,既要展現出天地之間原本遼闊、雄偉、壯麗、豐富的美感,又要對景物做出藝術改動,讓景不是景,但細看之下“景還是景”。
元代是寫意山水畫成熟階段,和宋畫相比,元代的山水畫并不追求形態與精神上的復刻和展現,而突出的是“意趣”,重視山水畫意境之中體現的趣味,在當時四方平安的時代背景下,中原的藝術理念自然更偏向于享受和觀賞性。趙孟頫提出不能僅僅追捧繪畫技巧和所蘊含志向的高低,而是注重在畫的意象中體現文人的儒雅之氣,重視“畫”與“文”的結合。元代的寫意山水畫與現代的山水畫風格更加相似,減少了對山水之美的展現以及高遠意象的營造,轉而更重視創作者精神的展現,也是從這一時代開始,山水畫家更重視追尋自我畫風。
總的來說,相較于外國抽象畫的藝術形式,由于我國古代的藝術作品更專注于具體的形象展示,所以為了抒發對世俗的不滿,山水畫的藝術理念與現實生活相違背,對于世俗欲望的厭惡,體現到山水畫中就象征著文人墨客對社會現實的反抗,對于統治者的失望,就會轉變為對天地美景的向往。古典藝術追求物我合一,所以在隋唐以前,山水畫家謀求神游天地的審美畫境。到了隋唐以后,山水畫家不斷追求“托物寄情”的深度優化,注重抒發個人的生活之趣。到了如今,畫家的作品偏離了山水,雖然以山水為畫,卻突破了山水的束縛,最終形成自我的山水寫意手法。
二、意象類型特征分析
所謂寫意,自然不能是簡單的山水構造,單純的繪畫手法修飾也很難表達出作者的創作思想,很多時候山水畫的意象是需要與批注相配合。在魏晉時期,由于社會風氣更加自由,各種藝術理念、世界觀點層出不窮,政治對于人心的控制依然十分微弱,所以這一時期繪畫的功能從政治教化中解脫出來,更重視繪畫觀賞者的觀賞體驗,或是畫家本身思想意志的宣泄,開始真正誕生山水畫的審美意識,中國藝術特有的“意境”創作觀,也開始和山水畫相融合,“寄情于景”的抒情方式開始成為主流的藝術理念之一。不過由于時代所限,雖然這一時期已經開始有文人參與繪事,但對于如何營造“意象”、如何將精神與山水畫像相融合,還沒有比較成熟的理論指導。
直到唐代,自由、繁榮的社會背景下,藝術發展更加多樣豐富,也開始有文人嘗試將文字與繪畫相結合,賦予山水畫像更獨特的韻味。山水畫的“詩畫交融”最早由唐代的王維實現,王維本身就是出色的詩人,善于在文字描寫中勾勒出山水意境,王維在寫景詩上有其獨到的見解,能細致入微地刻畫自然事物的動態,天地在他的筆下被賦予獨特的人文意義;而于畫,其筆下山水一變勾斫之法,始用渲淡、皴法,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在詩與畫兩個領域都有所建樹,刺激了王維新藝術理念的形成,他開始思考詩詞的意境是否能與繪畫的意象相結合,文字能否賦予畫像更深刻的精神韻味。不過王維并未完成“詩畫交融”的理論建構,單純的“寄情于景”并不能讓他找尋到畫與文融合的真實路徑。真正明確提出“詩畫交融”主張的是宋代的蘇軾,他將詩之“緣情言志”的特性賦予畫上,為畫家如何將情感與精神體現到作品之中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指導。換言之,就是不糾結于山水本身,而是要以山水為載體,但畫的精神又要超脫于山水的限制,突出主觀之“意”的主導作用,從而使繪畫具有“詩意”。山水畫的“詩意”彰顯出山水畫家達到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一方面追求美妙、遼闊的天地景色;另一方面又不會因為這些景色而限制了畫家本身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在繪畫中以山水為形,但以畫家的主觀精神為骨,寄托于天地,又超脫于天地。由此,蘇軾將山水畫的寫意性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縱覽中國山水畫之發展,歷來強調“線”的審美地位,在中國的審美印象中,“追本溯源”的理念根深蒂固,所以對于線條的設計更加執著,形成諸多線描風格。但隨著“意象”理論的發展,畫家開始不再執著于對山水景物形象本身的復刻,而是根據自我經歷提煉出獨特的畫風意象,對山水之景進行藝術加工,彰顯出對天地自然的向往,以此來逃避世俗生活。這一時期的山水畫像,已經初步進入“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象外之意。因此,線描技法也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唐以后,詩詞的蓬勃發展賦予了山水畫另外的發展路徑,“文”與“畫”的結合讓畫家的思想精神開始融于天地之間。“以書入畫”自然不是簡單地將文字與繪畫相結合,而是在充分感受山水情懷的基礎上,利用畫家自身的文學底蘊賦予山水形象更多的精神意義,造型依于物象而不黏于物。
三、現代山水畫意象營造
一個山水畫家有三種寶貴的能力:第一種是鑒賞與賞析能力,要在經典和過往的山水作品中追溯到原作者的畫風畫意,從而回饋到自我的繪畫意識;第二種能力是審美能力,山水畫家要有最基礎的審美意識,要明白“美”的概念;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能力是在前兩個基本能力的基礎上,明白如何將“美”通過繪畫手法展現出來,要形成自我的獨特畫風。
真正的好畫里面存在著共同的藝術規律。對于繪畫作品的欣賞,一定是觀賞者對某一幅作品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對于山水畫而言,除了山水形象本身要刺激觀賞者的審美欲望外,營造出的意象也要暗含作者獨特的思維理念。所以在山水繪畫時,針對不同的景象要選擇相應的創造手法。當我們在寫生之前往往要花很大的精力、用很多的時間,去向古代優秀作品探求不同山水景色之中共同的藝術規律,所以優秀的山水畫家必須具備欣賞的能力,要對優秀的古典山水畫作進行感悟和學習,從先人的藝術理念中提煉出獨特的自我風格。
寫生和寫實是有區別的,這個“生”就是一種生命狀態,生動、活潑的形式,而不是實實在在的外形。所以山水畫中的“美”需要提煉,其實只要山水景本身足夠壯麗秀美,那么只要寫實就能賦予作品足夠的審美價值,但要是想將作品上升到一種概括性的高度凝練的形式,必須在山水形象之間營造意象,將作者的思維精神暗含于意象之中,賦予單調的山水景物更豐富的精神意義。天地自然生長的東西首先是雜亂的,但雜亂里面就隱藏著變化,天地的規律浩瀚復雜,不同的景物搭配又會帶來不同的觀賞效果,所以山水畫家要懂得找到“美”,理解天地自然所構造出的獨特美感。
例如,畫一個石頭,外在的輪廓一根線條下來,充滿了一種曲折變化,這里面就有很大的信息量。在山水畫中,線條不是簡單的線條,粗細濃淡干濕剛柔等手法與具體的繪畫形象進行搭配,所體現的思維也是不同,所以山水畫家需要思考如何將天地自然的美感通過繪畫手法表現出來。
中國山水畫的歷史并不是空中樓閣,是由各種各樣的朝代特征和社會現實所決定、推動的,山水畫家在不同的世俗欲望中對同一片天地產生不同的理解。與世界范圍內的山水畫發展相比,中國山水畫更加特立獨行,即使在山水寫意概念誕生的初期,我國傳統畫家也不會僅僅局限于對山水形象的復刻,而是根據畫家的個人過往與所受待遇,提煉出不同的繪畫意志,賦予山水之景更加豐富的欣賞價值。隨著繪畫材料的進步和山水意象研究的深入,單純的寄情于景已經不足以滿足文人騷客對天地萬物的向往,他們開始將繪畫與文學相融合,嘗試賦予山水形象更多的文學價值。所以對于當代山水畫家而言,首先要培養自身的哲學審美意識,投身天地自然之中,心靈恬靜地感受山水萬物的本來氣息,思考如何為“山水之美”。其次要對傳統山水畫理念的重要性有基礎的認知,懂得如何從古人的山水畫作中感悟到山水之真理,在顏墨與線條的交匯中形成獨特的自我風格,以山水包含個人之情,以畫筆勾勒天地意象。
四、結語
總而言之,中國藝術對于“意”的追求是執著的,任何精神、思想、觀點都要暗含在“意”中進行表達,山水畫也要在把握“意象造型”這一核心理念的基礎上才能綻放光彩。當代中國山水畫家在追求藝術質量的過程中必須對中國傳統的山水意象進行學習研究,自我藝術風格的塑造要建立在理解貫通民族藝術精神的基礎上,要以更加包容通透的態度看待不同的天地景色,甚至實地投身于山水之間,感受山之巍峨、水之連綿、花之四季,以及觀察不同生物與天地自然的交匯程度,既然要將情感暗含于景色之中,自身就要對自然風光有足夠的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