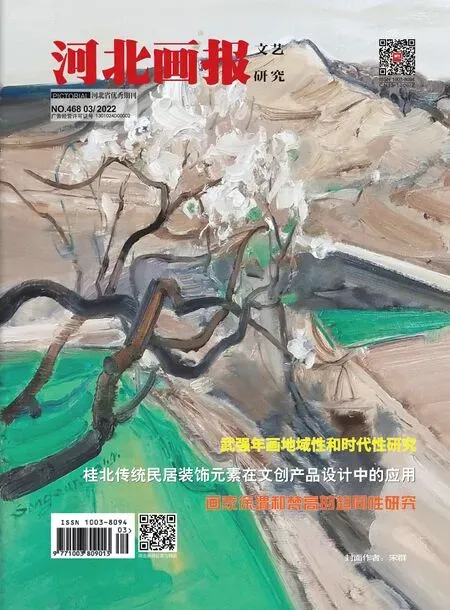吉列爾莫·奎特卡
——繪畫作為劇場
張青
(廣州美術學院)
一、奎特卡的繪畫起點
吉列爾莫·奎特卡,猶太人后裔,1961年出生于探戈舞藝術之鄉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結識的德國現代編舞家皮娜·包希、藝術家培根和詩人博爾赫斯等都對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作為拉丁美洲新秀,其作品輾轉展出于歐美重要城市之間,2007年代表阿根廷參加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繪畫對于奎特卡來說一直伴隨著嚴酷的考驗,這來自奎特卡沒有接受專業的繪畫訓練,與繪畫本身的歷史積淀產生脫節,與世界上主流的現代藝術形式存在差別,并且沒有刻意迎合藝術市場的需求。奎特卡雖然被人們稱為當代藝術畫家,但很難對他的派別作出明確的判斷,主要原因在于奎特卡一直徘徊在抽象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兩種形式之間。奎特卡始終忠于自身的思想和經歷去創作,捍衛著屬于他的邊緣藝術。
奎特卡認為繪畫的原發性至關重要,基于此觀點,他的早期繪畫作品主要為黑色系列且大多具有超現實主義與抽象主義色彩。奎特卡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經歷了獨裁統治,死亡與暴力對他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均產生了影響,奎特卡常常試圖抹去某些事件所留下的痕跡,通過描繪抽象的場景來表現對人類生存困境的迷惑,在很多作品中都涵蓋了不安和恐懼的情緒,這也成為奎特卡作品中的一大特點。在1978-1989年,奎特卡繪制了一系列的石墨畫作品,畫面中那些令人回味的起伏丘陵和漸漸升入天空的抽屜,構成了微妙的空間構圖,暗示出不安的氛圍。數字在畫面中環繞而形成一種移動的視覺效果,數字象征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循環,時間表示記述和測量的記憶符號,標志著某些事件的消逝與追憶。這些即興的創作都可以被解讀為一個年輕心靈的自發表達。
藝術界普遍認為他早期作品中具有突破意義的是《沒有人忘記什么》,這一作品手法簡練,一排毫無特點的人物漂浮于空中,用黑色線條勾勒出人物粗率的背影,人物像即將從世界中剝離一般,逐漸消失在鮮艷與暗澀的色彩交錯中。這引發人們去關注畫面中所指向的事件,涵蓋一個概念性的話題,而這一繪畫的標題正是帶有提示作用的反抗性紀念,即沒有人指向的是任何人;忘記什么指向的是沒有被人們忘記的那些事件。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分不開的,因獨裁的崩潰瓦解和戰爭的犧牲而廢除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人們可能隨時在家中被迫害或是失蹤。但在奎特卡的作品中非常有力地緩和了暴力傾向和恐怖行為,并掩蓋了個人的意向,將自我表達隱藏起來。作品的魅力在于,畫家給出了一個未曾深入的概念,用欲言又止的描述去喚醒人們的記憶,面對沒有人忘記什么這一所涵蓋的歷史事件,像是在一個輕微的打量中完成暗示,引發人們的共鳴。
奎特卡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受到德國現代編舞家皮娜·包希的影響,促使奎特卡對自己的抽象圖像產生了質疑,他開始關注如何凸顯個人的風格面貌,使之呈現出自我的延伸與完善。奎特卡通過擴大所涉及的領域來尋找創作靈感,創作風格也開始趨于不斷探索和尋覓的狀態,并且力求尋找出于本時代最具關連的事物來賦予繪畫新的語言和表達。
二、舞蹈劇場的啟示
皮娜·包希(Pina Bausch)是享譽世界的德國現代派編舞家,1973年任烏帕塔爾舞蹈劇團的團長,皮娜創作了30多部具有革新意義的大型作品,被稱為德國第一舞蹈夫人,對世界舞蹈界與戲劇界都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力,皮娜是真正賦予“舞蹈劇場”完整形態和生命力的編舞家。皮娜的舞蹈劇場中包含了多種劇場元素,其中融合了歌、舞、樂、對白等元素,同時,邀請觀眾也參與到戲劇的演出和交流中,特別是在舞臺設計中有時運用水、泥土、石頭等材料去創作舞臺裝置,營造出富有張力的劇場氛圍來調動舞者的表演。皮娜主張釋放舞者,釋放技巧,主張舞者要嘗試改變身體語言的行為方式,用日常生活中的動作與舞蹈建立關系,并且要表達出生活之中最平常的各種情緒、心理、絕望和喜悅。皮娜正是通過這種更為即興的表演形式使舞臺成為具有美學氛圍的綜合藝術劇場。
奎特卡曾作為皮娜的舞臺總監,皮娜激進的舞蹈劇場所特有的藝術風格、戲劇的概念和對人類情感多視角的解構對奎特卡的創作產生長達近20年的影響,為奎特卡的繪畫注入了新的力量,提供給奎特卡整體的藝術審美取向和理念。皮娜啟示了奎特卡如何理解和運用簡約主義的思想來建立立體的概念;怎樣建立與觀眾的關系而不只限于舞臺;怎樣突破傳統藝術帶來的限制以及如何與自己開展對話并釋放自己。奎特卡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出現的各種元素,如空椅子、舞臺構架、座位圖表等都來自皮娜劇場的回憶,更大的意義是舞蹈劇場理念的觸發之下所展開的藝術實踐。
劇場可以將人們肆意隱藏的東西重獲生命,也可以把最簡單的行走、靜止、沉默或是冥想都作為舞蹈出現,劇場像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宇宙。而畫布作為一個虛擬的空間,不僅將繪畫的各種媒材集合成為空間的組成部分,并且要滲透對于世界的理解,空間是可以來自多方面的,有舞臺的建筑空間,有哲學的意識空間,也有文學的敘述空間。這無疑使奎特卡消化了皮娜的理念,奎特卡在這里尋找到了繪畫與戲劇的共性,即藝術應該是沒有限制的。奎特卡由此而產生把繪畫比作一個舞臺的想法,他把多種空間結合,并使藝術哲學在不同的空間表現中具備了合理的構想。奎特卡是一個能將跳躍的思想緊握在手中的藝術家,他不止于視覺效果帶來的驚喜和獎賞,他一直投入在藝術實踐探索中并經歷漫長的考驗。
三、繪畫作為劇場
奎特卡把在舞蹈劇場中得到的啟發滲透到之后的藝術創作中,創作了一系列的劇場建筑空間作品,他把人們的視線焦點由通常被關注的舞臺引向了觀眾的位置。“水”作為道具應用在皮娜的舞臺設計中,奎特卡同樣將“水”作為作品《32個座位表》的創作媒介,利用現代復印技術將劇場的座位圖表印刷在膠片上,在創作中通過控制水溫來改變原本的空間布局,從而使堅固的建筑空間呈現出分離、錯位、溶解和消失的面貌。這一破壞性改造,反映出奎特卡在戲劇中所提煉的精神:矛盾與對立、解放與沖突的對應關系。
奎特卡在電影中觀察到,當鏡頭減慢了爆炸場景的速度,各種爆炸碎片會在延長的空中盤旋,物體會在空間中產生時間緩慢流動的效果。此時一個最普通不過的事物碎片都會成為被關注的焦點,這個鏡頭也成為奎特卡拼貼形式的主要來源。作品《羅霍劇院》就是奎特卡運用拼貼的形式來展示對建筑空間解體的挑戰。《羅霍劇院》中大面積使用了黑色與紅色去營造強烈的對比關系,他將切碎的紅色紙屑拼貼成無數錯亂的點和線并發散在黑暗的領域中,形成了爆炸般的抽象視覺效果。畫面中激烈的紅色蔓延沖天,像是熱情的火焰點燃了極端而激烈的形態,建筑也像即將倒塌一般,構成一觸即發的危險氛圍,又使人仿佛置身在劇場的演奏中,激蕩的旋律激發出強烈的節奏變化與情感的起伏。
奎特卡繪制了許多以地圖和平面圖為元素的作品。1990年的作品《回家》,將平面圖的框架搬上了繪畫空間,作品描繪了夜幕降臨下的機場跑道,同時也是一張私人公寓的平面圖。作品整體色調沉郁,帶有輕松的筆觸和氛圍。在畫面中,畫家對平面圖的透視關系進行了拉伸處理,并在幾何模塊的周邊結構中用白色的亮點表示出燈光,從而使被拉伸的平面圖成為飛機的跑道。畫面空間也呈現出一種立體的效果,讓人可以一眼見到公寓的全部面貌和生活的日常用品,在畫面中可以找幾把椅子、沙發或是娛樂的麥克風。奎特卡很善于把不同的空間和看似相對的事物進行疊加,從而隱喻出的新的概念和對應關系。
奎特卡在文學中獲得了養分,博爾赫斯使他產生了世界如錯綜復雜的迷宮這個概念。1992年,奎特卡完成了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裝置藝術作品《Le Sacre》,他在54張床上繪制了如同迷宮般的城市地圖,現今收藏于休斯敦美術博物館。床是承載著人們新生和終結的隱私空間,奎特卡把床理解為一個空間,一個避難所,一個劇場或是一塊陸地。地圖則是空間信息的圖形傳輸形式,它表述了世界的蹤跡和空間的距離,地圖中每一個城市的名字都伴隨著歷史與文化的厚重,地圖路線的脈絡則記述著不同地點所存在的界限、連接并展示著文明發展的蹤跡。而奎特卡所繪制的地圖作品將公共與私人的界限再一次打破,他用鮮艷的色彩繪制地圖的脈絡,用床墊本身的凹點或壓痕標注一個地點,使這個城市的路線匯集于凹點,又同時發散出去。具有戲劇性的是,他所標注的城市名稱顯示了相同的名字,所有的啟程最終將會通向起步的城市,人們在迷宮一般的地圖中尋找著城市的定義和自己的位置,人的微小就迷失在這些城市、歷史與變遷之中。奎特卡制造了一個循環往復般的噩夢旅程,暗示了一切事物都可能是相同的或是無處不在的觀念。畫面中的地圖背景出現了水漬效果,像是有著即將被沖刷和消除的危機,進一步加重了空間的混亂。
奎特卡在2000-2001年創作了油畫作品《終端》和《悲悼劇》,兩張作品以寫實的形式描繪了機場行李傳送帶,這一系列的作品具有非常強烈的戲劇性投射,奎特卡引用了戲劇的概念并巧妙地把這一概念對應在全球化的機械設備中。傳送帶作為一個劇場或是一個舞臺出現,畫面中的劇場入口設置在紅色的帷幕之中,設想行李可以在帷幕中進入舞臺,并隨著機械的結構運行而后告別這一舞臺。但這個劇場中沒有演員和觀眾,作品所描繪的是一條空的傳送帶,奎特卡還特意消減了舞臺中應有的劇場元素。奎特卡通過這一系列作品建立隱喻的概念,他認為傳送帶由起點就代表了結束,它承載了期望和等待也代表了限制和結局。
舞蹈劇場的概念啟發了他把世界與繪畫作為一個舞臺的思想。皮娜的舞蹈形式啟示他去探索挖掘藝術中無限的可能性表達。皮娜是為奎特卡照明的藝術家,舞臺為他帶來更廣闊的空間,讓他找到自己可以站立的點,他的整體藝術風格都是建立在把繪畫作為一個劇場的觀念之上。
四、結語
通過對奎特卡不同時期和不同形式的作品解讀,可以發現世界上的文化與藝術都是共通的。奎特卡雖然沒有接受專業的繪畫訓練,但它消化了藝術歷史的遺產,擺脫了藝術歷史的限制和模仿的困境,他在各個領域中吸收養分并結合當代思維表達出屬于個人的藝術體驗,提煉出新的趣味和意義。奎特卡也說明自己的眼睛常被那些與繪畫聯系甚少的藝術家所吸引,繪畫中存在著多種規則、束縛和限制,同時,這也代表著畫家對這一世界的認知和表達方式。奎特卡不依賴傳統繪畫中的邏輯和審美經驗,并不是表達一種與傳統的對立關系,而是不斷地集聚、感悟、提煉與概括。他試圖在溶解界限和改造表現形式的基礎上突破創新,并以此作為強大的革新動力來推動和反映藝術精神在本時代的特征。奎特卡多種形式的創作中可以見到藝術家自身的記憶與創傷,也可以找到戲劇、文學在作品中的投射,建筑與地圖在繪畫中的應用。奎特卡的作品有時作為一種煩瑣的制作與試驗的過程,有時作品體現出冰冷的精確理性,同時,伴隨著感性思維的流露,這都來自各領域文化為他帶來靈感閃現。
奎特卡的繪畫理念對自身的創作帶來積極的引導作用,繪畫的呈現方式并不具有唯一性,要開拓和革新繪畫創作就要不斷地探尋并延伸對更多領域的理解,挖掘出更廣闊的創作可能。作為繪畫工作者,當站在畫布前開始凝視構思、提筆作畫時,就進入了自己的演說場。繪畫如同一個劇場,所表達的內容和情感只有直達內心才會使人動容,要將它視為來自生命內在自由的舞蹈,如皮娜所說:“他們關注的是那些人們如何去翩翩起舞,我們更愿意做的是為何有感而動。”只有有感而動才能展現出藝術與生命的力量,這也成為藝術創作實踐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