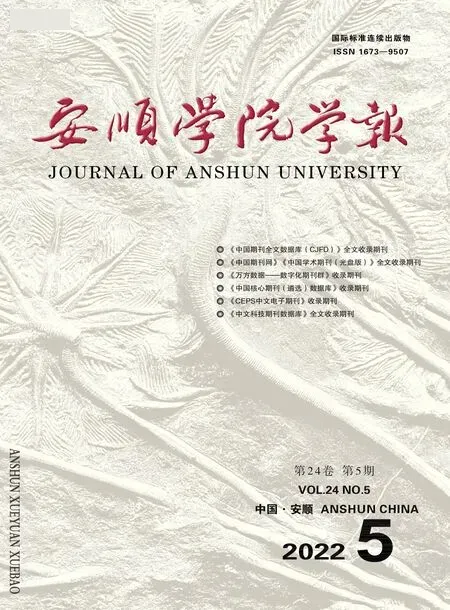道光《平遠州志·藝文》民俗文化研究
張永斌 陳紅梅
(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人文學院,貴州 畢節 551700)
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認為,民俗就是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1]6可見,民俗是一種源于人民,傳于人民的文化。地方志是地方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藝文志更是地方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較為全面具體地匯集了當地某時段的文學作品,其中有不少文人將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事象用詩文的方式記錄下來,使得文學與文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并讓民俗文化得以保存。方志藝文作為地域獨有的資料記載,不僅僅延續了歷史,而且保持了內容真實性,蘊藏著豐富而有價值的史料。道光《平遠州志·藝文》(下稱《藝文》)中就有許多關于平遠州苗民的衣食住行、婚姻喪葬、民俗信仰等民風民俗的文字記載。對于平遠方志藝文內容專門的研究,現僅有楊慶鵬的《乾隆〈平遠州志·藝文〉論略》[2]和譚德興的《從道光〈平遠州志〉看晚清貴州藝文志的儒學色彩——兼論儒學與史學之互動》[3],對《藝文》民俗文化的挖掘尚在起步。本文擬結合現存乾隆年間李云龍、劉再向編撰的《平遠州志》、道光年間平遠知州徐豐玉編寫的《平遠州志》、光緒年間黃紹先編撰的《平遠州續志》等地方志古籍,根據社會現實和政治文化對平遠州的影響所作的相關概述,對《藝文》中提及的民俗文化類型進行初步梳理、分析,透視民俗與當地百姓的生活狀態,并對《藝文》民俗文化在文學中的價值與地位進行探討。
一、《藝文》中的民俗文化類型
1.物質民俗
物質民俗是指人民在創造和消費物質財富過程中所不斷重復的、帶有模式性的活動,以及由這種活動所產生的帶有類型性的產品形式。[1]6平遠州歷史文化悠久,孕育著豐富獨特的物質民俗。從《藝文》作品看來,當地物質民俗內容豐富多彩,是州民生產生活智慧的結晶,彰顯了平遠州具有地域特色的歷史風貌和精神風貌,特別是服飾民俗、飲食民俗和居住民俗。
服飾是人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跟語言一樣,作為一種符號,始終貫穿于人的整個生命歷程中。平遠雖被稱為為苗蠻之地,但其服飾文化也是繽紛多樣的。例如,田雯《濟火論》中就清晰記述了濟火發式:“以青布為囊,籠發其中,若角狀”;[4]94謝琯《新辟水西紀略》中記載了仡佬族男女的出行服飾:“男著短衫,出必披氈。女披大被,中通一孔,繡五色花紋于上。從頭套下,掃地曰‘袍’”;[4]110張大受《重修平遠州學宮碑記》中詳細記述了苗民性格、紋身及飾品:“苗蠻雜處,獷鷙桀驁,雕題儋耳以為容,編彩簪毛以為飾”;[4]105《平遠風土記》中對苗民婦人衣著及發髻的描寫:“其婦人衣長,領裙襞百疊文,如錦如繡而粗澁,又如氆氌亦草履。頭髻或中或偏,或貼云于額,或發際橫一梳而罩以青布”[4]102等等。
從古至今,民以食為天,飲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先決條件,在人民大眾的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1]58平遠民眾也十分重視飲食文化,即便土地貧瘠也能創造豐富的物產,如鄂爾泰《先農說》中祭祀神農氏、后稷的貢品“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太羹,铏實以和羹,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梁,籩以棗栗、榛菱、芡、脯、白餅、黑餅、形鹽、蒿魚,豆實以菁菹、芹菹、筍菹、韭菹、鹿醢、兔醢、魚醢、醓醢、脾析、豚拍,筐實以青色量帛、俎實以羊一、豕一,而品物齊矣!”[4]96,黃元治《平遠風土記》中“其產則漆、雄黃、黑鉛、皮器、小馬、熊膽、麝香、雞樅、鸚鵡、白鷴、箐雞……又有黃柏、桔梗、前胡、白芨。白芨根似荸薺,苗婦取以洗衣甚潔白。”[4]102等都記載了平遠豐富的飲食民俗。
州民居住的建筑記述也生動形象地傳遞著平遠過去時代的信息,如黃元治眼中平遠土城墻之高厚、衙門之亂差:“其城土墻,厚尺許,高不能丈……府廳皆草舍,背負石山……衛衙之墻以竹,鎼隙珊珊,內可窺而盡,川堂而外,梁柱傾欹,門壁空洞”[4]103以及對苗民之群居于洞的描述:“至群苗則皆僻居溪洞籠箐中,如鳥獸之巢穴,不可以近人”;郭賡武對學宮組成結構的具體描寫:“陟降相度,自廟堂、廊廡、臺閣暨學舍書院,舉凡傾圮者,筑救之”[4]106;謝澤對書院地理位置“郡中有義學舊基,尾盤魁論首注平江,諸山屏翰,勢若星拱”[4]106及“就其地而前建龍門”“中建講堂”“左右建館舍數十間”“后建九賢祠”構造的描寫以及周景益對書院更名及組成部分設置的記錄等等都向人們展示了《藝文》中平遠州居住民俗文化的豐富神秘之處。
2.社會民俗
根據鐘敬文先生的觀點,社會民俗亦稱社會組織及制度民俗,指人們在特定條件下所結成的社會關系的慣制,它所關涉的是從個人到家庭、家族、鄉里、民族、國家乃至國際社會在結合、交往過程中使用并傳承的集體行為方式。歷經移民生活、戰亂紛爭的平遠民眾,最終在平遠州定居穩定下來,在特定的結合、交往過程中,他們使用并傳承著特定的集體行為方式和社會關系。《藝文》雖不是展示平遠民俗生活的專著,但也是其民俗文化的重要載體,如婚姻禮俗、喪葬禮俗等,可從社會民俗的角度去加以審視。例如黃元治筆下“女子踏歌,男子吹蘆笙和之,音調諧則配合,行必以群,或采茶、采薪、采野菜,亦背負如男子……”[4]102的苗民風俗描述、謝琯《新辟水西紀略》中“婚姻只忌同姓,婚娶不分尊卑。姐妹之女,親兄弟得而娶焉。倫常倒置,異其常耳”[4]112等關于仡佬族忌同姓、不分尊卑的婚俗記錄以及黃元治《平遠風土記》中“挾仇怨則殺人,父母死無棺,夾以兩木板而橫葬之。擊鼓吹喇叭,親戚宰牛羊雞豕以助,名曰‘作戛’”[4]102等關于苗民喪葬習俗的記載等等,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平遠州民的社會風俗習慣,也從一定角度折射出當地民眾人生階段的變化。
3.信仰民俗
鐘敬文先生認為,精神民俗是指在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民俗。而信仰民俗作為自遠古傳承下來并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信仰事象,可以稱為民間信仰,是精神民俗的一種類型。[4]145《藝文》中所錄平遠州民間信仰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民間所流行的祖先尊崇、自然尊崇、儒學尊崇等信仰形式。例如謝琯《新辟水西紀略》中對神靈尊崇的描述:“紀其人,則椎髻環眼,病不藥治。惟宰殺牛馬豕羊來禳之”[4]112以及對祖先崇拜的記載:“滿三年一普夥,普謂稱仡佬,夥謂祭獻仡佬先靈,不忘根本”[4]112;周景益對神靈尊崇的描述:“古者為民立社而已,后世郡縣天下筑城浚隍,保衛居民,設神以尸之而建之廟,載在《祀典》”[4]109;謝澤《新建平陽書院碑記》“崇道隆儒,捐修黌庠”[4]106以及謝賜《報功祠記》“蓋重道崇儒,興賢育才,自公而前,未始一見也”[4]108等對儒學的尊崇;王守仁《貽安貴容書》和《又與榮貴書》中舉例講述臣為君綱的儒家思想尊崇等等。
二、基于民俗的當地百姓生活狀態透視
1.物質民俗體現鮮明地方民族文化特色
一定歷史時期的地方族群,一度將服飾作為社會角色和等級身份的標志,體現了鮮明的服飾民俗文化特色。隨著家族制度、社會制度和社會等級的變化,身份的尊貴和地位的高低與否,都逐漸呈現在服飾上。[4]67《藝文》所載平遠州民服飾,也反映出當時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與等級觀念,“其男子非充隸役不剃發,發上束,復以青布疊寸闊自腦后經兩耳結于前,余其半并發紉之,作尖髻坐額上,盤曲如螺”[4]102,苗民由發式的不同,區分不同的身份,反映出發式也是一種特殊的標識。男子以有無剃發來判斷是否奴役,非奴役者青布疊寸寬由腦后經兩耳打結于額前,可看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由單一性轉變為復雜性,不同頭式扮演的社會角色不同,凸顯出一定的階級性。又言夜晚只有“……稍富者得衣氈,然無袖,拗其左右使圓之以襯兩肩,到胸項之間結以帶”[4]102,可見唯有稍富苗民才能以衣氈趨避夜間寒冷,貧困者只能“衾枕褥席,眠則籍草,天寒則披蓑,夜則燒煤。”[4]102
居住民俗和生產生活也展現出鮮明的地域民族特征。平遠城四面環山,苗民大多居城外,皆因“城中皆兵,東南二門外流氓落落十數家”[4]102。由此可知當時平遠極為荒涼,為群苗聚居地,漢民極少。群苗“結寨而居,屋以草,編箐為墻。梁柱無鑿枘,以葛藤裹束其椏”[4]102,將其小聚居的特點呈現出來,屋頂以茅草蓋之,編竹為屋墻,梁柱無圓鑿方枘,用葛藤包裹纏繞梁柱枝丫。平遠苗民靠山吃山,利用自然植物來構建民居,展現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謝琯《新辟水西紀略》對水西的地理位置及土地貧瘠加以闡述:“紀其地,則崇山深箐,田多石,土多瘠。”[4]112當時平遠州民的生存模式以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為主。就地形而言,地處喀斯特地形,所種農作物皆為山地耐旱作物,因地制宜,使得物產更加豐富。如黃元治所述:“前胡菜似野芹,土人采而輋之,謂之‘羅鬼菜’。白芨根似荸薺,苗婦取以洗衣甚潔白。”[4]103民眾因胡菜似野芹菜就采而食之,白芨具有漂白作用而被苗婦用來浣洗衣物,寫出了當地居民物盡其用的有智慧、悟性高的性格特點。再加上日常生活中,苗民“頗力耕,稻熟則翦其穗,束而跨諸屋梁,俟極干舂而糶之。或以換鹽布。自飯稗米土碗,出門則以竹篾結兩兜如碗大,一盛飯而一覆之。以純系腰上,遇澗泉則以小木瓢汲淘而下,得鹽少許,置掌心餂之,味甘于肉矣”[4]102,展示了苗民擅長于耕作,稻谷豐收時物盡其用,以竹片編碗盛飯或外出勞作時取水飲用的事象。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但苗民仍選擇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傳承和發展著當地的民俗文化,展現出了鮮明的地域民族特征。
2.婚葬禮俗彰顯獨特社會風貌
俗話說“苗家不跳花,兒女難成家”。“跳花”內容豐富多彩,也是苗族婚戀習俗中最具代表性的節日。青年男女以跳花為媒,以歌舞為傳達情感的方式,這是苗族青年男女戀愛階段必經的過程,使得“跳花”與苗族的婚戀生活產生有機的聯系,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占據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彰顯了苗民獨特的思想魅力和崇尚自由的精神。苗族青年男女于“春夏之交,男女未婚者有跳花之會。預擇平敞地為花場。及期,男女皆妝飾而來,女則團聚于場之一隅,男子于場中各吹蘆笙,舞蹈旋繞。女視所歡,或巾或帶與之相易,遂訂終身。然后通媒妁講聘資。聘資多少以女之妍媸為定。不知正朔,以六月六日為歲首”[4]82,通過苗族青年男女“跳花會”這類社交活動相識相知,體現出他們提倡自由婚戀,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藝文》中詳細記載了苗民男女青年先用絲巾絲帶互定終身,再媒妁之言、討論聘禮到約定婚期的婚姻儀禮。男子以吹蘆笙舞蹈于會中、女子心悅誰就“或巾或帶”贈之定終身的形式,極富民族色彩。再由媒人商談聘禮、婚期等都是對結婚儀禮的重視,維護了年輕人的自由選擇對偶權。苗民對自由戀愛的贊同、男女平等交往、父母開放心態皆突破了封建倫理綱常的束縛,為提倡自由戀愛結婚注入了新的生機。
面對親戚朋友逝世,絕大部分人都是悲痛害怕的。《藝文》中平遠苗民對待親人死亡的態度卻恰恰相反,泰然處之。他們用“趕戛”或“作戛”的方式為親人舉辦喪禮,如黃元治所言:“挾仇怨則殺人,父母死無棺,夾以兩木板而橫葬之。擊鼓吹喇叭,親戚宰牛羊豕以助,名曰‘作戛’”[4]102表現了他們樂觀的生死意識。又如風俗篇中記載:“喪葬祭奠用牛羊,親族往吊,謂之‘趕戛’。夜則群聚戛場,飲酒唱歌,黎明主人打牛分給眾客。用斧擊牛腦,以一擊即死者為吉。”[4]82親人過世,在世兒女親戚并未感到悲痛害怕,反而在戛場擊鼓吹喇叭、飲酒唱歌,共享下祭牲口,極顯對死亡泰然處之的樂觀意識。
3.信仰民俗凸顯民族自我精神認同
當時的平遠州民存在一定的愚昧落后思想,這與其地勢偏遠、經濟發展落后呈因果關系。風俗篇言:“疾病不事醫藥,專務祭鬼。以盆覆水上擊之,曰‘打迷蠟’。或以雞骨看卦,辨吉兇。凡有所疑,皆用雞卜飲。以細竹竿通節插入壇中吸而出之,謂之‘咂馬酒’”[4]82可見,苗民生病不求醫不吃藥,通過一定的媒介——“打迷蠟”和以雞骨看卦辨吉兇,祈求身體健康,迷信色彩濃厚,違背科學。同樣,謝琯“紀其人,則椎髻環眼,病不藥治,惟宰殺牛馬豕羊來禳之”[4]112也詳細記錄了苗民與其他族群雜處地區的之風俗,當地人“疾病不事醫藥”不求醫、不吃藥的風俗習慣,其原因還在于一個崇拜鬼神的落后思想,導致了族群在遇病不求醫方面的認同性。
古代以農耕經濟為主,生產力不發達,農業收成取決于季節氣候和地理環境,因此人們喜愛天地諸神,傾向于向諸神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由于平遠地處偏僻山區,氣候多變,土地貧瘠,就有了程榮壽《祭雹神文》中的“致祭于雹神之前,曰:伏以,圣人在上,無雹育物,對時小民,以食為天,祈年孔夙。”“惟神有靈,代天宣化,暢風霆之神氣,郁散陰霾。”[4]218;鄂爾泰《先農說》中祭祀神農、后稷“祭之日,自迎神以至于初獻、終獻、送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禮舉矣!”[4]96祭祀之禮堪比文廟祭祀,以示敬畏,祈求風調雨順之認同;謝濤《重修牛場河萬緣碑記》中牛場河乃交通要塞,但“然河之勢,險阻非常。而成梁之工役,亦匪易也。……每值夏秋驟雨,四山攢簇,眾壑奔騰,百道瀑泉,傾搖并下,湍急澎湃,淹物之患,亦所不免耳”[4]107的記述。后因里人(今穿青人)張、喻輩集資,與眾民商討修建以對抗山洪暴發,呈現出與自然抗爭的精神品質和認同性。
三、《藝文》民俗文化在文學中的價值與地位
藝文志的功用在于“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改土歸流”政策實行后,便派遣大量官員至地方任職,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了解地方情況,更好地因地因時制宜統治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到平遠的官員在親身經歷中有感而發,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文,把平遠州民眾日常生產生活習俗反映了出來。《藝文》作為平遠州文獻的總匯,有著極其重要的文獻學價值以及文學價值。
1.生活內容的質感化
《藝文》作為道光版《平遠州志》的最后一個部分,也是平遠州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篇幅大且研究價值高。其中詩文作者繁多,篇目更是數不勝數。《藝文》中的詩文本著“紀一方之政治、風俗”的宗旨而作。通過觀察民風的淳樸,考察山川形勢的要害,查戶口、田賦、經營制度、學校教育來了解平遠州的興盛衰亡。結合前人經驗記錄了解當地政府官員廉潔與否;由忠義節烈、理學經濟知孝悌忠信等。文章意在“闡明道德,敷陳經濟,即至一歌一詠,要必有所勸誡,而后為言之有物……”[4]92,藝文遵循“言之有物”原則,做到實事求是。尤其是著述平遠州地方風俗民情、地理氣候、物產生活、族別等方面是非常用心盡力的,為了記述好民俗文化,細致入微地論述了傳統禮儀、綱常倫理、序庠教化,使文學內容更加豐富,更具有生活質感,更好地促進了地方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2.主題內容的形象化
《藝文》描繪了道光時期平遠苗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民俗,形成了一幅只屬于平遠州人民的風情畫卷。這些民俗風情還構成了平遠獨特的地域文化。從《新修平遠州學宮碑記》描述平遠“苗蠻雜處,獷鷙桀驁,雕題儋耳以為容,編彩簪毛以為飾,氣象狉獉,言語侏離,躞躞豕突,跂跂鹿奔”[4]105可見,平遠民眾在各方面都保留著原始痕跡;又如黃元治所言“勢挾弱苗,苛索所有”“苗賊嘯呼剽掠,出沒如鬼蜮”[4]103,進入平遠路上,道路狹窄,苗民還似盜賊般搶奪,如鬼蜮一般,正面描寫了部分平遠苗民的原始封建的生存方式,十分排外的形象特點;《平遠風土記》提到苗民“見官府故作畏謹狀,其心至詭譎不可測,然諭以誠信亦每每折服”[4]102的畏懼模樣;梁玉繩《黔苗詞》也言:“鎮撫依然服良吏,莫將橫目等豺狼;威畏不敢爭先視,蛾伏蛇行拜老王。”[5]可見當時土司制度下民不聊生之狀,思想落后之象。苗民“病不服藥,專事禱鬼。宰磔牲畜,頗不惜費,至有稱貸為之,因而家破者”[4]82,可知其思想落后、大肆鋪張的性格特點,這是不值得提倡和傳承的;又如“六月初九日午時,有賊匪頭裹白巾,手執白扇,自稱‘仙大仙姑’,率眾約千人突前攻營,官兵用炮轟擊,該匪等大呼云:‘打不著!’炮果擊不能中,隨以犬血破其邪術。”[4]113賊匪愚昧頑固與將領英明機智做對比,突出當時戰爭勝利的不易。
平遠苗族、仡佬族各分幾類,等級威信皆不同,文化程度也不一,在這片土地上描繪著精彩的民俗篇章。即如黃元治所說“苗非一類,若羅鬼,若仡佬,若白苗、黑苗、花苗,若蔡家子、儂子家、仲家子。仡佬種有五,羅鬼亦分黑白倮倮二種,安氏黑倮倮也。其白者下安氏一等。如今頭目阿五是。獨仲家子中頗有知文墨者,其最桀驁不馴。則惟羅鬼、諸苗莫不畏憚尊奉之。”[4]102平遠苗族居住也不同,有的“群苗則皆僻居溪洞籠箐中,如鳥獸之巢穴,不可以近人”;有的“結寨而居”;有的“居喜高阜,傍巖依箐為安”;有的“好樓居”。住所結構不一,體現苗民因地制宜的聰明才智。不僅如此,風俗篇開篇還提到“平遠地處遐陬,卉服鳥言,久為輶軒所不采。自隸板圖以來,雖夷漢雜居,而飲和食德,莫不雍雍而丕變。蓋沐圣朝之雅化已兩百年余茲矣!昔為僻陋之鄉,今屬可封之戶。”[4]81往昔“僻陋之鄉”粗野狂驁民眾,如今已為“可封之戶”,形象化地展現了民眾易受教化的特點。又如黃元治初抵平遠所言:“余與太守孫茲庵先生,遂皆以二月去。計余受事僅百日,于茲土無毫發補益。而諸苗父老,反以余二人速去相嘆惜。于此見荒徼人心猶足與為善。余冀官斯土者仁漸義摩,導苗民于為善之路,爰取風土略記之,以告后之君子。”[4]101偏僻荒涼之地民眾的向善之心顯而易見,只要為官之人用心教化,皆能移風易俗。再如謝琯所述:“紀其種則九種之,各分區類以別,習尚各殊,非若附郭漢民,多流寓,耕讀、紡織,尚從淳龐之治也。”[4]112
3.文獻資料的時代化
《藝文》不僅有利于后世閱覽后了解平遠州每個時期的發展變化,從中了解平遠歷史及其民俗文化發展情況,還有利于考究平遠州民風民俗,對發現原始資料,展示其獨特的民俗文化現象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就內容方面而言,《藝文》所輯錄范圍相當廣,涉及一方政治經濟、風情民俗、地理山川及歷史遺跡等,尤其是對民俗文化的記述最為奇特。加之《藝文》收錄著各種體例相異的藝文,其中包括歷代書、論、說、教、記、紀略、紀事、詩等。尤數墓銘碑記保存最為完好,也占相當大一部分,使得其史料價值更加鮮活,便于更好地挖掘平遠州地方文獻資料的價值。有《重修平遠學宮記》《新建平陽書院碑記》《重修牛場河萬緣橋碑記》《報功祠記》《重修城隍廟記》等文章。首當其沖就是把教育事業發展得更好和宣揚對平遠州做出貢獻的人與事。《藝文》還把零散文獻聚集了起來。其中收錄的作品大都是官員、士人或鄉紳的零散詩文,他們之中有一些文人并無文集傳世,《藝文》則將這部分文人的作品收集著錄,利于文學作品的傳世。《藝文》還可作為文獻校勘的史料來源。它記載了豐富的歷史史料,為地方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為充足的史料來源,以便后人在比較文人同一作品時可相互對照。如黃元治的《平遠風土記》可比較《平遠州志·藝文(乾隆)》和《平遠州志·藝文(光緒)》,更好地對照以發現不同之處。不僅能促進文學記述的發展,還利于文體的發展。《藝文》所輯錄的作品,大多是外來為官的文人在平遠所見所聞的杰作,雖不是專門記述民俗文化,但有利于文學作品的保存,促進平遠州文學的發展與變遷,以及對平遠州民風民俗的據實記述。
結 語
《藝文》中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首先表現在物質民俗上,文人作家雖不是特地描寫平遠民俗,但文筆中卻無形地展現著州民的衣食住行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其次是具體勾勒社會民俗中的婚葬習俗,生動地將其崇尚自由和樂觀坦然的精神體現出來,進一步刻畫了積極、豁達的州民形象。最后呈現對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儒學教育的信仰民俗中,凸顯了“改土歸流”背景下官員對苗蠻地區教化的重視。對《藝文》中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定歷史時期平遠州民眾的生活場景,增加人們對過去貴州織金的認識,領略當地民眾獨有的人文精神,讓更多已消失或未被發現的民風、民俗、民情浮出水面。地方志民俗的學習和研究還能讓更多的人發現古今的異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傳承和發揚地方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