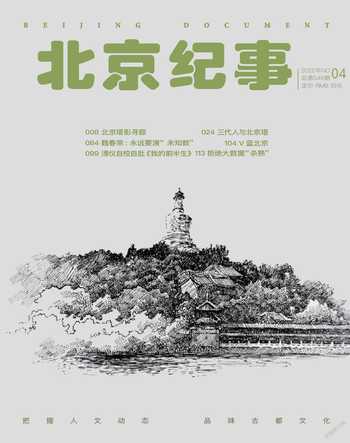魏春榮: 永遠要演“未知數”
馬捷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昆曲舞臺上,演員魏春榮帶領觀眾,進入了一場古老夢境。眼前的她,一身淺粉色花帔,化身《牡丹亭》中,因愛而死因愛而生的杜麗娘,行腔婉轉,水袖翩然,美得如夢似幻。
水磨調中已孕育百年的樂音,從魏春榮的口中流淌而出,彌漫著江南的氤氳水汽,意韻無窮,讓人如至園林,似聞鶯啼。
“要做到讓觀眾即便閉著眼睛聽你唱、聽你念,都能在情景當中。”這是魏春榮在藝術舞臺上,始終追求的境界。昆曲被譽為“百戲之祖”, 作為守護這一唯美藝術的昆曲人,傳承和沿襲的責任,無比重大。
更多的,則是一份堅守。上世紀80年代,10歲的魏春榮懵懂入行,在那時,昆曲并不被大眾熟知。畢業后,市場不景氣,一場演出,往往臺下觀眾寥寥幾人。直到2001年,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沉寂已久的昆曲,才回到大眾的視野。
近40年的相守,魏春榮見證了昆曲“否極泰來”的復蘇。如今,她已是北方昆曲劇院的當家花旦,每逢她主演的場次,臺下的觀眾總會坐滿全場。
2021年12月22日,魏春榮被評為“北京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并接受《北京紀事》的專訪,為我們講述了她的故事。
以下是《北京紀事》和魏春榮的對話:
10歲時,我進入北方昆曲劇院學員班學習昆曲。其實在那個年代,昆曲正處在低谷時期,談不上有所謂的宣傳。
當時是家人在報紙上看到了招生簡章,覺得我嗓音條件不錯,也比較喜歡文藝,可以試一試。但最主要的,是因為有住宿。那時候我父母在國外工作,是我奶奶帶著我和妹妹,姨媽為了解決我奶奶的負擔,就把我托管了,覺得如果我有天賦上這個學校的話,一星期回家一次,還有生活老師管著,這樣挺好的。起初是奔著這種想法去的。
經過了大概四次的考試,就進入到學員班,畢業以后就留在了北方昆曲劇院。那棟樓,那個院子,我從10歲到現在就沒離開過。很長情吧?(笑)
那個苦,真的是挺難熬的。那會兒大概6點半起床,先不吃早飯,洗漱完畢就要去練早功,然后再吃早飯,吃完去練腿功,接著是身段訓練,上午就過去了,然后吃午餐,之后午休一個小時,馬上又開始練身段、唱腔或者聲樂,上完以后吃晚飯,晚飯過后,上文化課。睡覺前,我們還要練一遍晚功。這一天下來是相當累的。宿舍是那種上下鋪,有的時候,腿疼到爬不上床。
沒有。因為我爸爸本身喜歡京劇,他愛唱老生,所以他還挺高興的。
家人一直鼓勵我,甚至還督促我、鞭策我。開家長會的時候,同學的爸爸或媽媽會心疼,覺得(老師)打得有點厲害,我爸就站起來說:“打!打得還不夠狠,不打不成才。”
周六我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我爸會帶著我到故宮后河沿,喊嗓子壓腿。我就很尷尬,不好意思,特別小聲喊,我爸還呲兒我。
我喜歡的角色反而不是杜麗娘。
我特別喜歡的,一個是關漢卿本子里的珠簾秀,還有就是我近期排的《救風塵》里的趙盼兒。因為我的性格吧,會更喜歡那種自主意識很強,敢作敢當的女性。
像珠簾秀,她本身就是元朝的一個伶人,她的唱詞是:“不唱戲老天生我做什么,珠簾秀今生惟在戲中活。”她是那種不瘋魔不成活的女演員,她對于舞臺的那種留戀,讓我有很多感觸。趙盼兒則是有俠女的心腸。
演員切記不可“千人一面”。你所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包括性格、故事、生活的背景,但每一次演繹角色,演員肯定會將自己的感情留在其中。其實一個角色里,裝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劇中人,還有一個就是演員自己。所以說,這也考驗演員保持怎樣一種心境。
昆曲旦角分七門,各有特性。但是在新編戲中,可能需要演員從年輕演到年老,用聲音去塑造年齡的增長,能夠做到讓觀眾即便閉著眼睛聽你唱、聽你念,都能在情景當中。昆曲是一個全方面的塑造,甚至在腳步上,都有講究,都要體現人物的不同。

2001年昆曲申遺成功,北方昆曲劇院帶著《活捉》《游園》《鐘馗嫁妹》三個戲,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做展演,當時我們心中有好幾個問號:我們的演繹能不能夠讓世界人民覺得昆曲是一門非常高雅、唯美的藝術?會不會被他們接受?他們能不能看得懂?
第一折戲演完了以后,臺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當時在中國,昆曲還處于低谷,你很難聽到那么熱烈的掌聲,真的是第一次聽到,終身難忘。
一路走來,有很多人在幫扶助力我,在這方面,我是幸運的。但在這條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是別人幫不了的。在我的詞典里面,好像沒有“挫折”這個詞。
1988年畢業的時候,要說苦悶,肯定是有的,當時市場不景氣,我們演出機會非常少,你在臺上演,臺下就兩三個觀眾看。我當時16歲,剛畢業,滿懷信心,卻遇到這種情況。那算挫折嗎?如果不覺得,就不算。
困難都有,這是必經的人生道路。我的老師跟我們說,臺下即便只有一個人看,你也要認認真真演,把每一次演出都當作是第一次。
現在《牡丹亭》我都演上百場了,但每次演,也都要有初戀似的感覺。我不能說因為演得太熟了,就不重視,那樣演的不是“戲”,而是“數”。所以永遠要演“未知數”。
時至今日,我依然還在學習當中。所以可見,昆曲的博大精深,是需要用一輩子去鉆研的。
昆曲給予我的,是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有人說,昆曲演員身上的勁頭,好像跟其他演員不一樣。我覺得這有賴于昆曲的滋養。它是士大夫的藝術,是文人的藝術,汲取中國傳統藝術之精華,從文本到舞臺呈現,都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而且是極致的呈現。
另外,就是在老一輩藝術家身上,我獲得的精神力量特別多。包括我自己的老師——林萍老師和蔡瑤銑老師,以及前不久去世的張繼青老師。
那一代人非常單純,他們的心,就動在戲上,其他的都沒有。但凡人心純潔、執著,在舞臺上演繹的角色,肯定也是非常干凈的。
比如說像我們近期排的《救風塵》,就比較成功。首先是服化道上,更貼近于現代觀眾的審美。其次,在挖掘關漢卿原本子《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上,編劇又加了一折,叫“雪夜行路”,趙盼兒和她的好姐妹,在雪夜趕路去救另外一個姐妹,邊唱邊行,唱腔也好聽,舞臺編排也好看。這一折恰恰把前后情節銜接上了,又表現了趙盼兒的俠義心腸。大家對這折新加的戲特別喜歡,甚至說單拎出來再豐富一下,可以成為經典的折子戲。
去年,我們到蘇州參加中國昆劇藝術節。專家們評價這出戲集觀賞性和藝術性為一體,非常能夠吸引觀眾走進劇場。
創新這條路上,做實驗總是要有失敗的,不可能次次成功,但是失敗乃成功之母。要先守正,才能創新。我們要先尊重、認可自己的藝術,要先把昆曲積累到一定程度,再往前走。六百年前的昆曲也不可能是現在這個樣子,都是一代代藝術家,通過在舞臺上的收獲、打磨、演繹,再逐漸往里加東西,根據觀眾的審美調整,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現在的。
我們說“大戲看北京”,中軸線沿線有那么多的文化遺產、重點保護單位、名勝古跡,我就想能不能用中軸線來梳理北京城,做一個活化大劇,里面涵蓋戲曲、曲藝、非遺手工藝、飲食文化等等形式和門類,呈現中軸線四季的變化,展現它的風土人情故事,吸引游客來看,讓大家有沉浸式的體驗。
另外,散落在北京城區有很多的老戲樓,包括北方昆曲劇院運營使用的百年戲樓正乙祠。在這樣的戲樓中駐場演出,需要思考在打造中如何挖掘其中的可持續性。
還是傳承,以及堅守舞臺。我覺得我三十歲以后才慢慢成熟,現在應該是在舞臺上相對狀態最自如的時期。所以肯定還是要演,另外我特別希望將來能做一個戲曲導演。
演員時常想的是“我”,而導演要看大局,排兵布陣,想整個舞臺的呈現。我也挺喜歡做這件事情,所以未來,想結合我學戲的積累,往這方面做一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