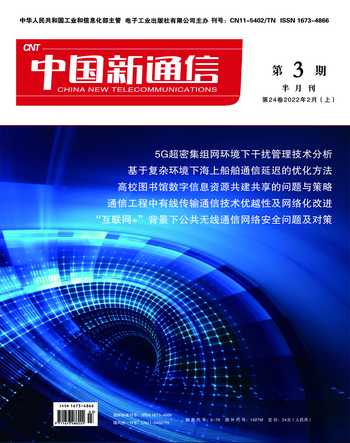網絡犯罪法律適用及完善的探討
【摘要】? ?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涉及網絡領域的犯罪數量倍增,由于互聯網的虛擬性、隱蔽性等特點,導致傳統的刑法理論及規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和認定存在頗多困境。針對這些問題,本文試圖從完善部分法條的罪狀描述、入罪標準、刑罰種類的設置等方面進行分析,為網絡犯罪法律適用、的完善路徑上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
【關鍵詞】? ? 網絡犯罪? ? 網絡幫助行為? ? 困境解析? ? 完善路徑
一、涉網絡犯罪案件的范圍界定和特征解讀
(一)網絡犯罪案件概念和范圍的界定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涉網絡犯罪犯罪案件也日益增多。司法實踐中也急需要明確界定網絡犯罪案件的范圍。2014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及公安部頒布了《關于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法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1],該意見將司法實踐中的網絡犯罪案件的范圍界定為以下幾種:1.危害計算機系統安全的犯罪;2.通過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實施的盜竊、詐騙、敲詐勒索等犯罪案件;3.在網絡上發布信息或者設立主要用于實施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針對或者組織、教唆、幫助不特定多數人實施的犯罪案件;4.主要犯罪行為在網絡上實施的其他案件。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我國法律規定的網絡犯罪,即指以網絡為對象、或者利用計算機(網絡)為工具或者空間實施的其他犯罪,或為幫助實施以計算機(網絡)為對象、工具、空間的犯罪而實施的其他犯罪行為的總稱。
(二)我國網絡犯罪的特征解讀
司法實踐中涉網絡犯罪案件有以下幾個特點:
1.網絡犯罪案件增長明顯,類型多樣化
網絡犯罪案件數量總體上呈增長的態勢,類型趨于多樣化,具體分析如下:一是將網絡作為侵害對象的純正的技術型犯罪有所增加,但整體所占比例小。該類犯罪技術性最強,不易偵破,危害性也最大。二是非以牟利為目的網絡犯罪案件也占有較少的比例,如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偷越國境罪等;三是以牟取非法利益為目的將網絡作為實施犯罪行為工具的傳統犯罪的案件占了大多數且增速較快,涉及盜竊、誹謗、詐騙、非法買賣、非法營銷等各類傳統犯罪,這類犯罪在網絡環境下還不斷異化出新的表現形式[2]。
2.犯罪動機具有牟利性,職業黑客常見
通過案件類型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來網絡犯罪案件的牟利性動機越來越凸顯。擁有相關技術的犯罪分子可以通過出售、提供程序、技術等傳授給沒有計算機相關技術能力的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網絡平臺知識的開放性和共享性也使得有牟利動機的非專業人群可以通過下載學習來掌握計算機程序使用技術,這就為網絡黑客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條件。
二、我國網絡犯罪法律規制的現狀
2010年,兩高一部出臺了《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意見》,該意見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賭博行為,從案件管轄、主觀認定標準到定罪量刑等方面完善了網絡賭博犯罪的法律適用。2013年,兩高聯合出臺《關于利用信息網絡事實誹謗等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對誹謗罪、敲詐勒索罪、非法經營罪、尋釁滋事罪這四類傳統犯罪行為從網絡環境下的新型表現型形式明確了新的量刑意見。2014年兩高一部出臺《關于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從法律上界定了網絡犯罪案件的范圍,并對網絡案件管轄、取證方面的內容做出了特別規定。2016年,兩高一部出臺《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手機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在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審查等方面的規定做出進一步完善。
以上不難看出,我國刑法對信息網絡犯罪相關的規定雖然一直在完善,但仍然屬于較為籠統概括,在實踐方面針對性的指導較弱。
三、網絡犯罪當中司法實踐的困境解析
(一)網絡犯罪隱蔽性強、取證難,涉案人員和犯罪數額難以確定
互聯網具有隱蔽性和虛擬性,犯罪分通過隱藏身份借助互聯網實施犯罪,往往物證書證較少,網絡犯罪案件認定主要依賴電子數據。而電子證據具有易被篡改、刪除、復制等特點,取證和保管環節也不同于傳統證據,從而導致電子證據在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上受到巨大挑戰[3]。如北京海淀區法院2016年審結的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快播案”中[4],控辯雙方就檢察院方面提交的電子證據在提取和保管方面是否具有合法性、關聯性等問題展開激烈辯論。電子證據的取證和保管環節的爭議其實就是證據真實性問題,電子證據涉及原始數據是否完整、搜集提取過程是否有瑕疵等諸多專業技術性較強的問題,加大了證據認定和案件審理的難度。
(二)部分案件定性困難,定性難度較大
隨著網絡虛擬經濟的發展,具有財產價值屬性的網絡產品不斷涌現。從游戲ID、游戲裝備、游戲金幣等,這些網絡虛擬產品有較大的商業價值,能夠帶來較為直觀的經濟利益,所以收到網絡犯罪的侵害。然而由于傳統刑法財產理論的限制,導致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屬性界定頗有爭議:有理論認為虛擬財產具有較大的商業價值,可以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應當認定為財產;有理論認為虛擬財產的本質就是計算機數據。屬性認識的不同造成案件審理和法律適用的混亂。
(三)共同犯罪主觀犯意和客觀聯絡認定困難
傳統的共犯認定,必須在犯罪階段主觀上有明確的犯意聯絡,以協調之間分工配合。而在網絡犯罪中,犯罪分子之間通過網絡進行聯系,相互之間即便不認識任然能夠達到犯罪目的,這就導致了犯意聯絡的明確性和共通性的弱化。同時,網絡共同犯罪的參與和分工突破了傳統共犯的明確性和固定性,出現聚集性和隨機性的特點,使得傳統理論上的實行行為和幫助行為不易區分[5]。
(四)部分新增罪名缺乏具體解釋
《刑法》增設的部分罪名入罪條件不夠明確,又缺乏配套解釋,司法實踐當中容易出現爭議,導致這部分法條使用率不高,有悖立法原則。例如《刑法》286條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首先,該罪主體是網絡服務提供者,那么如何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是一個頗具爭議的點,是具有法人資格組織機構,還是非法人組織或是個人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其次,經監管部門責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是構成該罪的要件之一,那么監管部門是指哪些部門?是否有級別限制?應當采取如何措施才能算是拒不改正?這些在法律都需要有進一步明確。
四、完善網絡犯罪法律的建議
(一)完善相關網絡犯罪司法解釋
傳統刑法理論對虛擬財產的屬性界定模糊,不足以適應新經濟形勢下虛擬財產的保護。且新增的部分罪名對罪狀的描述不夠細致準確,這導致了司法實踐當中罪名的適用困難較大,因此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對相關的概念及法律術語作出進一步完善。
第一,應適當擴大財產的的界定范圍。將具有重大經濟價值的虛擬財產界定為受刑法保護的財產范圍內,但并非所有虛擬財產都可以成為財產,而是能直接帶來較大經濟效益的虛擬產品,且具有一定的人身專屬性的財產。
第二,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術語,明確主體范圍及入罪要件。如前文所述,《刑法》第286條之一的“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義務罪”,應當對該罪名的主體“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概念范圍進一步完善和明確;另外,該罪所提及的監管部門的種類有具體的分類,且有一個最低行政級別的規定。
(二)豐富刑罰的種類
我國刑法對于網絡犯罪采取的重要打擊類型是自由行,而對于財產刑和資格刑缺乏重視。大部分網絡犯罪都是以牟取非法利益為目的,因此有必要在刑罰中加入財產刑和資格刑的設置,在自由刑為主的同時輔助以財產刑和資格刑可以對打擊網絡犯罪產生更好的效果。財產刑主要就是罰金等,不必贅言。資格刑是指在特定時間內不允許犯罪分子從事特定的相關職業。對于那些從事犯罪情節較為嚴重的犯罪分子,通過限制其參與該相關職業,對發揮刑法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作用都有極大幫助。
(三)加大刑法的處罰力度
我國關于信息網絡犯罪設置的刑罰力度總體偏低。刑罰處罰力度偏輕,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犯罪成本,導致縱容犯罪的發生。罪責刑相適應是刑罰的基本原則,犯罪行為的危害性關系到量刑的輕重,因此有必要加大網絡犯罪的刑事處罰力度,做到罪責刑相適應。比如,《刑法》第285條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該罪名涉及安全領域,如果國家計算機信息系統被入侵破壞,則會帶來巨大的隱患,但該罪的刑期只有三年以下,因此需要加強重點領域保護,對部分涉及重點領域的罪名提升其量刑幅度,從而加大對該方面的保護。
五、結束語
信息化社會的不斷發展致使網絡犯罪產生新形勢新變化,是對現有法律制度的機遇挑戰,面對法律規范的缺位和社會危害性的不斷增長的現狀,立足于當下社會的現實條件出發,完善相關概念及法律術語的司法解釋,使之能與當下新的網絡犯罪相適應,滿足刑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一種較為靈活的解決當下網絡犯罪問題的方法。另外,應當采取多樣的打擊治理方式,重點領域采取較為嚴苛的刑罰方式,這樣才能做到標本兼治,打造一個安全和諧的網絡環境。
參? 考? 文? 獻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法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http//www.court.gov.cn.
[2] 游濤,楊茜.網絡犯罪實證分析[J].法律適用,2017(17):85-91.
[3]胡勇強.基于虛實空間交互的網絡犯罪偵查新模式及其意義[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3(06):66-72.
[4]王志剛.從“快播案”看當前電子數據運用困境[J].法制研究,2016.
[5]史棟,杜紅全.試論網絡犯罪中的幾個問題[J].經濟論壇,2012(09):174-176.
作者單位:張翔昱? ? 河北工程大學
作者簡介:張翔昱(199210),男,漢族,河南信陽市人,法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訴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