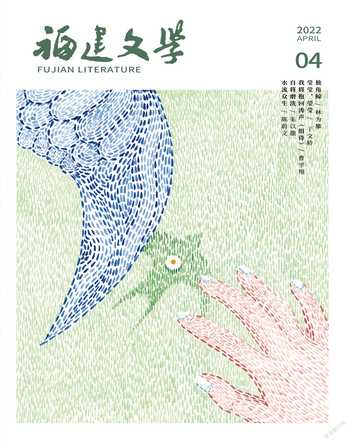東關舊事
馬星輝
一
生命的旅途,長的是歲月,短的是人生。曾經的過往舊事,總是在漸行漸遠的時候開始明澈。時光在指縫間悄然遠去,只留下“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的惆悵與嘆息。
因了創作長篇小說《東關歲月》,在辛丑年歲末的一個多月里,幾回回來到兒時住過的邵武東關一帶尋覓舊事。與這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一景一物的相遇中,生發出許多扼腕感慨,讓人沉思回味。不論時光如何流逝,人世間有些景物是不會忘記的,有些人是不會忘記的,有些往事是不能忘記的。
地處閩北大山的邵武城區,四面筑有基座近兩米高的城墻。古舊的條石上沉淀著濃濃的滄桑;從厚厚的城墻磚里,可以看到燒制城墻的磚工匠的姓氏。先人匠心獨具、一絲不茍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正因如此,歷經千百年的風吹雨打,歲月侵蝕,古城墻至今殘缺而不倒,依然顯雄厚壯觀、龍盤虎踞之威。
古城墻開東南西北四門,老百姓亦稱之為“四關”。四關之中的東關,最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江湖志士、俗世奇人比比皆是,層出不窮。理學大儒朱熹、南宋名相李綱、太極一代宗師張三豐、詩論大家嚴羽、鐵將軍袁崇煥等,均在此流連忘返、衣袂飄飄、光耀四方。
見證東關千年繁華的是一條老街,它長3000多米,寬十余米。鵝卵石的路面顯露出厚厚的歷史包漿。當年,古街兩邊商業店鋪相連,比肩林立,布莊、當鋪、雜貨店、京果店,糧油米面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在東關街巷的周邊,則散布著福州會館、江西會館、基督教堂,美國人創辦的幼兒園、醫院、奶牛場,以及抗戰時期從福州遷移到此的協和大學、之江大學、格致中學以及銀行、保險公司等。農耕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朱子理學、孔孟之道、傳統儒學,在這里相互碰撞、交融、傳承、包容……
二
風雨雷電、江河湖海之中可見證一個邊城的氣勢。
信步在東關的大街小巷,穿梭在舊宅古院之中,于一個個零落成泥的遺址和留存里,可以品味到明清時期的興盛。你輕叩一扇古門,千年的煙云便迎面而來……
天啟二年(1622)正月,京城任都察院守院御史的江日彩回泰寧探親,經過邵武時作短暫停留,認識了時任邵武縣令的袁崇煥,二人見面后互為傾心敬慕,惺惺相惜,相見恨晚。那日正長談時,忽報東關城門口發熊熊大火,燒毀了不少店面民房。袁崇煥聞訊大驚,即刻率員趕往救火。他飛身躍上城墻,于烈火之中來回穿梭,勇不可當。東關百姓親眼看見,皆感動不已,對其勇猛佩服之至。
江日彩覺得袁崇煥不僅雄才大略,且愛民如子。眼下國運艱辛,戰亂頻仍,正是朝廷用人之際,似袁崇煥這樣的豪杰當委以重任才是。于是江日彩連夜潑墨揮毫,向天啟皇帝寫了一份奏折《議兵將疏》,史書中載原文如下:“邵武令袁崇煥,夙攻兵略,精武藝,善騎射。臣向過府城,扣其胸藏,雖曰清廉之令,實具登壇之才,且厚自期許,非涉漫談。其交結可當一臂者,聞尚多人。今見覲于輦轂下。樞部召而試之,倘臣言不虛,即破格議用,委以招納豪杰,募兵練將之寄,當必有以國家用者。”
江日彩奏折正月中旬上疏朝廷,二月份,袁崇煥就調任京城,任兵部職方主事(正六品),連升了兩級。袁崇煥到底不負厚望,守衛遼東六年,兩次大敗后金,收復江山失地700多里,把努爾哈赤打成重傷,最后斃命。讓后金聞之膽寒,不敢輕易再犯中華。袁崇煥屢建奇功,后來擢升為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遼東督師。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太極一代宗師張三豐,在邵武東關顯現仙蹤。在700多年前一個清夜無塵的夜晚,為遣鄉愁的他從武當山悄然回到家鄉邵武,一身蓑衣一魚竿,一柄寶劍一壺酒,在富屯溪東關礁石邊仰天而眠、微酌垂釣三天三夜,悠然自得,當是一種斜風細雨不須歸的大俠做派。邵武人喜歡這位邋遢神仙,對他敬慕容垂。今人在東關溪南邊塑有一尊張三豐真人大小的銅像,其造型飄逸瀟灑、形態可親。孩子們喜愛有加,總在銅像上爬上爬下、反復不止。日久下來,這尊銅像被磨出錚亮一片,金光閃閃。
當年在東關現身的另一位奇士,便是著名的詩論大家嚴羽。在東關北隅有一詩話樓,踞城墻之上,高十余米,登高可望數里之遠。詩話樓原名為“望江樓”,始建于南宋紹定初年。因檐牙有三重,又名“三滴水樓”。清順治四年(1647),戶部侍郎周亮工以按察使入閩,祀嚴羽于樓中,并以嚴羽著《滄浪詩話》而易其名為“詩話樓”。
嚴羽曾三次離鄉,客游江湖,期望能遇到明主,為驅逐蒙古軍隊,保家衛國施展自己的才華。然而他未能如愿。回到邵武后,他大暑天身著羊裘,于富屯溪邊垂釣,以表示對時事的不滿。南宋末年,文天祥鎮守南平,嚴羽又以其年邁之軀離家投軍。抗元徹底失敗后,他不肯投降元朝,避隱民間,不知所終,但留下了一部聞名中外的《滄浪詩話》。
三
在邵武,東關古渡碼頭最具特色。它寬30米,全部用幾十斤乃至幾百斤重的大鵝卵石鋪就,涸水時延伸鋪至河床近十米,根深蒂固,穩穩當當,發再大的洪水也無損于它。碼頭上有一座木頭浮橋,用巨大的鐵鏈串聯起十幾只船形浮墩,連接了南北兩岸的交通。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邵武由于陸路不通走水路,碼頭成為入閩出贛的重要交通樞紐。水運造就了東關的千載繁華,從中原來的貨物,到了邵武搬上大船運往閩江下游的繁華之地;從閩江下游運來的貨物,則從邵武盤上小船,翻越杉關,進入中原腹地。故而,不僅當地富商巨賈聚居于此,大量外地客商亦在此集結,東關這個地方有了廣東幫、江西幫、福州幫、興化幫等十幾個幫派以及眾多的商號,僅米市糧商就有百家之多。
福州幫的商號在東關實力最為雄厚,主要經營京果、鹽米等生意。他們從邵武采購大米運往福州,又從福州販運海產、糖果、食鹽來邵武銷售。福州人開的京果店和“三把刀”(理發刀、裁縫刀、廚刀)等福州老行當也在這里生根發芽,使得這里“蝦油味”香飄四處。在東關的街邊巷尾,不難看到撈化、肉燕、鍋邊、魚丸等極具特色的福州小吃,使得偏遠的山城無處不散發著閩都文化的味道。
一位在東關生活了一輩子的福州老人說:“邵武東關是我此生不愿意再離開的一個地方,我要停留在這里老去,人生要行走在這東關的大街小巷里。”
其實,東關從來就是一個使人鐘情不舍的地方。在更早的1892年,來自美國麻省的愛德華·布里斯漂洋過海,開始了他前往中國的奇異之旅。他用了三年的時間,跟隨小河船完成閩江航行,最后在邵武停下腳步,開始創辦學校,建造診所,待了整整40年,對東關有了很深的感情。他的兒子小愛德華·布里斯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戰亂,我們不得不離開了邵武東關。當在碼頭登上鳥雀船,回首眺望東關,那密集的房屋、廟宇、城樓,一切都是那樣的熟悉,綿綿陰雨下的黑瓦屋頂構成一幅抑郁憂傷的圖畫。正在溪邊飲水的水牛,聽見了遠處的槍炮聲,憤怒地揚起了頭。邵武,不知道什么樣的命運在等著它……”
四
東關與任何地方一樣,有著數不盡的日升月落與留聲過往。但東關卻搖曳著與眾不同的燈火與炊煙,變遷中的一串串回憶,充滿了人間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
抗戰時期,福州的幾所大學和一些銀行、金融保險先后內遷到邵武東關,包括一大批為數眾多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這為落后、封閉的邵武邊城帶來了先進時尚的文化理念。這種五湖四海的交融,不同文化的注入,使得邵武東關人既有大山的粗獷仁義,又有大海的胸懷與豪氣;在民風彪悍的同時亦有著包容大方、肝膽相照的義氣,演繹出豐富傳奇的人生故事。
東關的福州會館是一個例子。1932年夏天,一個長相俊秀、風度翩翩的年輕人,從省城來到邊城邵武,幫助父親經商。在他的精心運作下,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八方興隆。這個福州青年名叫游登哥,他為人豪爽仗義,在當地極有人緣和威信。他在東關建起了一幢氣派不凡的福州會館,背靠碼頭,面朝大街,不僅配套有百余間客房,還有不亞于上海灘的大戲臺、豪華酒樓。海軍將領薩鎮冰為會館手書“福州會館”四個大字。會館落成之日,游登哥設豪宴百余桌,答謝東關紳士名流、民眾代表,還從福州請來“善傳奇”名戲幫,上演閩劇三天三夜。游登哥后來經人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閩贛省委地下聯絡站,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做出了重大貢獻。
佇立在東關城墻邊,靜心地細細聽去,那遠去了的刀光劍影在眼前回閃不止。1933年10月,閩北蘇區和中央蘇區的聯系被國民黨割斷,受黨中央的指示,地下黨領導人曾鏡冰與黃道、曾昭銘等組成省委代表團,在黃立貴紅58團的護送下,進入閩北蘇區開展革命斗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曾鏡冰等人在省委地下秘密聯絡站住了十幾天,策劃了對敵斗爭的重大部署,繼而領導閩北紅軍轉入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
值得欣慰與自豪的是,先人勇猛可嘉,后來者亦是可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東關這么一個小小的彈丸之地,還走出了數百名和平時期的佼佼者,其中包括共和國的將軍、省委書記、在巴西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海外大企業家,以及眾多的國內外知名人士。
毫無疑問,東關居住最多的當然還是那些舊木板房里的底層人物。雖然在記憶中的這些小人物已漸行漸遠,但有幾個人卻始終令人記憶深深,他們可稱得上俗世奇人。
東關興化巷的巷口上,住有一個年逾古稀的中醫叫甘草老人,鶴發童顏,眼不花、耳不聾,身板結實。他尤擅長為人接骨療傷,但見上門的傷筋斷骨者齜牙咧嘴、痛楚萬分,甘草老人不急不慢,目光炯炯地觀察了一會兒后,伸出中食二指,隔皮戳肉,麻利如風,疾如閃電,只聽得“咔咔”兩聲,斷骨已經在瞬間接上,傷者在不覺之中已除痛楚。
還有一個人物叫“大頭寶”,她的頭比一般人大了許多,四肢又短又粗,行起路來一步一撇,像只番鴨。大頭寶雖身殘,人卻聰明,沒上過學,識字不少,沒拜過師傅,裁剪衣服卻內行。最絕的是她的算盤功夫,那雙粗短笨拙的手,打起算盤來讓人驚嘆!不僅打得快而準,而且是雙手同時打,無論加減乘除,左右兩邊的得數都一模一樣,準確無誤。
大頭寶身懷絕技,得以進了廢品收購站工作。她把雜亂無章的廢品站收拾得干干凈凈、井井有條。她還設了個舊物利用專柜。在她這兒能尋到商店買不到的零件。為此上級領導經常表揚她,她連續被評為省、地、縣的系統勞模,只是她從來不去領獎,包括那次全省算盤比賽第一名。
有些手腳不干凈的人偷工廠車間的銅鐵好零件砸碎了賣,大頭寶看了心疼,把這情況向附近的派出所做了匯報。偷東西的人知道了真相,大頭寶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時常有人上門找碴,指桑罵槐,譏笑她和廢品站里的貨一樣是廢品。終有一天,大頭寶離開了廢品收購站。
夜晚,漫步在東關富屯溪邊,過兩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在岸邊的香樟樹上,在或高或矮的建筑上,都垂掛起了節日的彩燈。古城墻在燈光的照射下斑斑駁駁,燈影倒映在水中,呈現出美輪美奐的夜景。不知道為什么,我卻生發出一種不同的感慨:人生多少鮮衣怒馬,也熬不過歲月靜好。在時光里,有些人,走著走著就散了,有些事,記著記著就忘了,有些情,愛著愛著就淡了。人生多少繁華,轉眼如過眼云煙而不復存在。
眼前的東關,依然是舊貌舊顏,低矮、單薄、簡陋的木板房群中摻雜著一些不甚起眼的磚瓦房,與不遠處新城區的高樓大廈相比,顯得很是無奈與頹敗。它蜷伏在一個似乎被人遺忘的角落,只能默默地回憶著曾經有過的傳奇與崢嶸。
最近聽說東關的中山路已被省里批復為歷史文化一條街,政府把東關改造擺上議事日程,這令人欣慰。亦希望在舊城改造的同時注重文化歷史,二者之間相得益彰、相互增輝添色,因為東關舊事是東關的靈魂。
責任編輯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