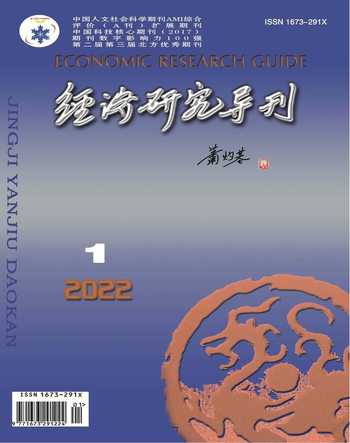自我領(lǐng)導(dǎo)下人工智能對(duì)工作重塑的影響機(jī)制研究
吳睿 劉生敏 田穎

摘 要:人工智能時(shí)代變革的工作情境對(duì)員工行為產(chǎn)生影響。基于交互決定理論,探討智能情境下,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自我領(lǐng)導(dǎo)及工作重塑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即人工智能提高工作自主性,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賦予員工更高決策權(quán)力,促進(jìn)員工自我擴(kuò)張,自我效能感提高,進(jìn)一步激活自我領(lǐng)導(dǎo)。員工采取自我領(lǐng)導(dǎo)策略以強(qiáng)化內(nèi)在動(dòng)機(jī),最終促進(jìn)工作重塑行為的表達(dá)。在此基礎(chǔ)上,闡述組織權(quán)力感知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最后,構(gòu)建自我領(lǐng)導(dǎo)模式下人工智能驅(qū)動(dòng)員工工作重塑的理論模型。
關(guān)鍵詞:人工智能;自我領(lǐng)導(dǎo);工作重塑
中圖分類號(hào):F270? ? ? ?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 文章編號(hào):1673-291X(2022)01-0099-04
人工智能,作為科技發(fā)展和社會(huì)進(jìn)步的產(chǎn)物,正在逐步席卷全球。隨著技術(shù)手段的智能化更新及其與傳統(tǒng)業(yè)務(wù)流程不斷融合,人工智能勢(shì)必會(huì)對(duì)員工工作模式帶來(lái)改變。員工與智能技術(shù)的交互協(xié)作過(guò)程推動(dòng)著員工對(duì)工作進(jìn)行自發(fā)的再設(shè)計(jì)。而這一強(qiáng)調(diào)主觀能動(dòng)性的工作重構(gòu)過(guò)程,即工作重塑,已被證實(shí)具有良好的職場(chǎng)效應(yīng)。因此,研究人工智能對(duì)員工工作重塑帶來(lái)何種影響以及影響路徑已成為組織研究者需要探討的重要問(wèn)題。
一、人工智能的內(nèi)涵及相關(guān)研究
20世紀(jì)60年代,“人工智能之父”Minsky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讓機(jī)器做本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做到的事情的一門科學(xué)。與其他通信技術(shù)依靠既定算法進(jìn)行運(yùn)作不同,AI的關(guān)注熱點(diǎn)更多聚焦于深度挖掘與決策能力等方面。即當(dāng)前人工智能是以替代人類完成特定工作為目標(biāo),以高智能、自動(dòng)化技術(shù)為支撐,通過(guò)計(jì)算機(jī)程序和智能機(jī)器對(duì)大數(shù)據(jù)進(jìn)行深度挖掘和處理,以實(shí)現(xiàn)一定程度的人的學(xué)習(xí)能力和問(wèn)題解決能力的技術(shù)。
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人工智能對(duì)勞動(dòng)力影響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方面展開(kāi):一是基于其技術(shù)變革優(yōu)勢(shì)探討人工智能時(shí)代下工作特征的變化。部分體力型工作將通過(guò)智能設(shè)計(jì)完成機(jī)器替代,將員工從重復(fù)機(jī)械的簡(jiǎn)單勞動(dòng)中解放出來(lái)。員工的腦力勞動(dòng)也逐步通過(guò)計(jì)算機(jī)、搜索引擎等進(jìn)行優(yōu)化,減少員工受知識(shí)、精力和時(shí)間的限制。生產(chǎn)系統(tǒng)的信息化、網(wǎng)絡(luò)化將驅(qū)使員工從從事單一體力勞動(dòng)生產(chǎn)向創(chuàng)造型勞動(dòng)和全面型勞動(dòng)轉(zhuǎn)變[1];另一方面,基于企業(yè)管理實(shí)踐,探討人工智能時(shí)代下勞動(dòng)力社會(huì)屬性的變化。信息化時(shí)代,組織內(nèi)部的扁平構(gòu)架中,指揮領(lǐng)導(dǎo)權(quán)力不再只匯聚于一點(diǎn),每一名員工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權(quán)[2]。數(shù)字技術(shù)將使員工與企業(yè)間關(guān)系由直線科層式向網(wǎng)狀轉(zhuǎn)變。Larson和DeChurch指出,在員工與數(shù)字智能技術(shù)的交互和協(xié)作過(guò)程中,技術(shù)平臺(tái)會(huì)影響團(tuán)隊(duì)的形成方式[3];Gajendran和Harrison指出,人工智能為遠(yuǎn)程辦公提供了技術(shù)支持,影響員工的人際關(guān)系、工作方式與結(jié)果[4],即技術(shù)系統(tǒng)會(huì)影響企業(yè)網(wǎng)狀價(jià)值結(jié)構(gòu)的形成過(guò)程與緊密程度。智能技術(shù)可以對(duì)信息進(jìn)行深度挖掘和快速傳播,使得員工對(duì)知識(shí)和信息的把握更加迅敏,削弱個(gè)體對(duì)組織的依賴程度,凸顯網(wǎng)狀結(jié)構(gòu)中個(gè)體“點(diǎn)”的作用。
綜上所述,人工智能對(duì)勞動(dòng)力影響的現(xiàn)有研究大多落腳于工作特征及員工組織角色的變革。現(xiàn)有文獻(xiàn)更多傾向于系統(tǒng)概述以上影響,卻鮮有內(nèi)在機(jī)理的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工作情境的變化將對(duì)員工帶來(lái)何種影響,以及人工智能背景與員工行為變化二者之間的轉(zhuǎn)化路徑,相關(guān)研究尚有空白。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命題
(一)人工智能與工作自主性
工作自主性是指工作本身客觀賦予員工在工作方法的選擇、工作節(jié)奏的把握等方面的自由決策權(quán)利,是工作的一項(xiàng)核心特征。
大數(shù)據(jù)和云計(jì)算的深度融合構(gòu)建了嶄新的工作情境,賦予了員工更高的自主權(quán)[5]。依據(jù)不同的自主水平和主動(dòng)程度,人工智能的角色可分為三種:一是助理,通過(guò)智能程序完成部分日常型職能工作,提供輔助性功能;二是顧問(wèn),通過(guò)基于云端的應(yīng)用程序協(xié)助使用者獲得專業(yè)幫助,解決復(fù)雜問(wèn)題;三是執(zhí)行者,可以通過(guò)規(guī)則性應(yīng)用程序自主評(píng)估備選方案[6]。
隨著智能技術(shù)手段不斷落地,其與企業(yè)傳統(tǒng)經(jīng)營(yíng)模式和業(yè)務(wù)流程的逐漸融合使得技術(shù)工具本身與員工間的關(guān)系更為緊密。首先,人工智能作為一種虛擬勞動(dòng)力,以深度算法為其核心,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精密的整合和處理,通過(guò)完成復(fù)雜的邏輯思維過(guò)程,協(xié)助復(fù)雜問(wèn)題的分析、推導(dǎo)和處理,幫助員工擺脫知識(shí)、精力和時(shí)間的限制[7],將員工從一些煩瑣化、重復(fù)化的機(jī)械運(yùn)動(dòng)中解放出來(lái)。這為員工在工作中可以自行控制工作進(jìn)程,安排工作內(nèi)容提供了技術(shù)支撐。其次,智能化辦公系統(tǒng)使員工的辦公地點(diǎn)更加靈活,越來(lái)越多的企業(yè)職能部門可以在保障效率的情況下實(shí)現(xiàn)遠(yuǎn)程辦公,進(jìn)一步改變了員工的工作場(chǎng)所及方式[8]。此外,數(shù)字技術(shù)降低了員工與組織間的黏性。智能技術(shù)的數(shù)據(jù)收集、處理功能使個(gè)體獲取信息不再受時(shí)空的限制[8],可以基于過(guò)往數(shù)據(jù)獲得多種備選方案。即員工對(duì)組織的依附度降低,擁有更多自由發(fā)展的選擇項(xiàng)。因此,企業(yè)為擺脫被動(dòng)地位將對(duì)員工實(shí)施充分賦能,增強(qiáng)員工工作自主權(quán)利以穩(wěn)固員工與組織間的聯(lián)盟關(guān)系。由此,提出推論:
命題1:人工智能時(shí)代,員工感受到的工作自主性顯著提高。
(二)人工智能與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
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作為一種有效的組織管理方式,強(qiáng)調(diào)領(lǐng)導(dǎo)與下屬間分享權(quán)力的過(guò)程,旨在讓員工形成自我控制并開(kāi)展自主行動(dòng)[9]。
數(shù)字化工作情境下,管理理念和實(shí)踐日益呈現(xiàn)出復(fù)雜性和變動(dòng)性,組織內(nèi)部權(quán)力流動(dòng)不再呈現(xiàn)單一縱向形式,傳統(tǒng)科層式領(lǐng)導(dǎo)方式將面臨來(lái)自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挑戰(zhàn)[2]。相較于傳統(tǒng)領(lǐng)導(dǎo)模式以“管理+控制”為核心,新型管理模式更加尊重個(gè)體員工的獨(dú)立性,向“領(lǐng)導(dǎo)+教練”模式轉(zhuǎn)變,即要求領(lǐng)導(dǎo)者充分賦權(quán),影響并改變員工心智模式,激發(fā)員工的自主性行為。權(quán)力流動(dòng)由自上而下縱向流動(dòng)轉(zhuǎn)變?yōu)榫W(wǎng)狀流動(dòng)。每一名員工作為網(wǎng)狀架構(gòu)中的一點(diǎn),被賦予的自主決策權(quán)利不斷增大。
此外,基于資源保護(hù)理論,在壓力情境下,個(gè)體將不斷對(duì)現(xiàn)有資源進(jìn)行投資以更快恢復(fù)資源損失[10]。人工智能提供了海量復(fù)雜信息,領(lǐng)導(dǎo)者相較于一般員工面臨更復(fù)雜、更極端的工作要求與壓力。為迅速適應(yīng)變革的企業(yè)節(jié)奏及劇增的風(fēng)險(xiǎn)型決策量,緩解自身心理資源消耗,向員工授權(quán)成為領(lǐng)導(dǎo)者應(yīng)對(duì)工作壓力的重要途徑。同時(shí),智能技術(shù)增強(qiáng)了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領(lǐng)導(dǎo)者的管理措施有效性無(wú)法判斷,因此更可能出現(xiàn)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行為,如提供社會(huì)和情感方面的激勵(lì)、與下屬建立信任、提供與工作有關(guān)的信息和資源等。由此,可提出推論:
命題2:人工智能背景對(duì)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與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
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表現(xiàn)出一系列以分享權(quán)力、鼓勵(lì)員工自我管理和自我決策為核心的領(lǐng)導(dǎo)行為,例如鼓勵(lì)下屬參與團(tuán)隊(duì)管理與決策、向下屬提供自主權(quán)、為下屬自主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等。Amanuel等指出,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直接促進(jìn)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11]。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是自我領(lǐng)導(dǎo)的重要前因變量。
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與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兩者關(guān)系的基礎(chǔ)建立于提高的員工自我效能感。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行為屬于內(nèi)在激勵(lì)的構(gòu)念,并非單純指領(lǐng)導(dǎo)向員工下放決策權(quán)[12],而是幫助員工提高目標(biāo)完成的信念與能力。Dansereau等指出,員工自我擴(kuò)張是領(lǐng)導(dǎo)影響過(guò)程的理論基礎(chǔ)[13]。領(lǐng)導(dǎo)者授權(quán)可以激發(fā)追隨者自我擴(kuò)張的渴望。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通過(guò)“滿足追隨者對(duì)勝任力、自主性和相關(guān)性的內(nèi)在需求”來(lái)滿足員工自我拓張的需求。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者傾向于為追隨者提供持續(xù)的心理自由,滿足他們晉升或成長(zhǎng)導(dǎo)向的自主欲望。自我擴(kuò)張理論進(jìn)一步表明,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是擴(kuò)大自我以融入他人的有益結(jié)果。在感受到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并積極自我擴(kuò)張融入領(lǐng)導(dǎo)者之后,員工意識(shí)到自己與領(lǐng)導(dǎo)聯(lián)系更緊密,關(guān)系質(zhì)量更高[13],他們可以更容易地從領(lǐng)導(dǎo)者那里獲得物質(zhì)、信息和社會(huì)資源[14]。這些積極感受提高了個(gè)體對(duì)完成復(fù)雜任務(wù)能力的信心,促進(jìn)了更高的自我效能感,進(jìn)一步激勵(lì)員工表現(xiàn)出積極的工作態(tài)度,主動(dòng)設(shè)定工作目標(biāo),設(shè)置自我激勵(lì)措施以實(shí)現(xiàn)高工作績(jī)效、在遇到困難時(shí)主動(dòng)進(jìn)行自我調(diào)節(jié)等自我領(lǐng)導(dǎo)行為。由此,提出推論:
命題3: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通過(guò)提升員工自我效能感促進(jìn)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行為表達(dá)。
(四)工作自主性與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
Hackman和Lawler指出,員工對(duì)工作特征的感知會(huì)影響其心理、情緒以及對(duì)工作的態(tài)度[15]。員工對(duì)工作自主性的感知將影響其自我領(lǐng)導(dǎo)的激發(fā)及后效[16~17]。
智能工作情境賦予員工更高的自主決策權(quán)利,傳統(tǒng)領(lǐng)導(dǎo)發(fā)生權(quán)利解構(gòu),員工將積極實(shí)施自我領(lǐng)導(dǎo)以彌補(bǔ)正式領(lǐng)導(dǎo)的缺口。人工智能背景下,管理模式由垂直領(lǐng)導(dǎo)向?qū)挿芾磙D(zhuǎn)化,由命令控制向授權(quán)賦能轉(zhuǎn)化[18]。在員工感受到較高工作自主性的同時(shí),組織正式領(lǐng)導(dǎo)的權(quán)力影響趨于淡化,員工需積極實(shí)施自我領(lǐng)導(dǎo)以協(xié)調(diào)個(gè)人與組織間差異,適應(yīng)企業(yè)變革節(jié)奏。
工作自主性對(duì)員工的影響實(shí)質(zhì)上體現(xiàn)了一種心理授權(quán)以提高員工自我效能感的過(guò)程。當(dāng)工作本身賦予員工自主權(quán)利越大,員工感知到的組織認(rèn)可程度越高,從而獲得更高的心理授權(quán),進(jìn)一步產(chǎn)生極大的自我決定感、勝任感,即自我效能。高自我效能感員工將更有信心完成工作任務(wù),更加從容應(yīng)對(duì)工作挑戰(zhàn)。這一過(guò)程實(shí)質(zhì)上滿足了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的內(nèi)在動(dòng)機(jī),使員工體會(huì)到更高的控制力,進(jìn)而促使其全身心投入工作并最大限度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沈文竹指出,與從事常規(guī)固定的工作相比,當(dāng)自主性工作激發(fā)出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時(shí),員工的內(nèi)在動(dòng)機(jī)越強(qiáng)烈[19]。而內(nèi)在動(dòng)機(jī)是自我領(lǐng)導(dǎo)過(guò)程激發(fā)和持續(xù)的核心[20],員工以此為驅(qū)動(dòng)建立自己的目標(biāo)和行為標(biāo)準(zhǔn),再運(yùn)用內(nèi)部獎(jiǎng)懲策略實(shí)現(xiàn)自我調(diào)整從而達(dá)成績(jī)效。因此,相較于高正式領(lǐng)導(dǎo)、低自治權(quán)的工作情境,當(dāng)員工感知到賦予自己的自主權(quán)利越高時(shí),員工體會(huì)到更多的意義和使命,激發(fā)出更高的自我效能,自發(fā)嚴(yán)格地要求自己,積極地實(shí)行自我目標(biāo)設(shè)定、自我激勵(lì)、自我調(diào)整策略來(lái)指引自己的行為。由此,提出推論:
命題4:工作自主性與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水平通過(guò)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五)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與工作重塑
工作重望是指員工在工作場(chǎng)所中,依據(jù)自身需求自下而上地重塑工作邊界,包括轉(zhuǎn)變對(duì)工作的認(rèn)知、改善工作中的人際交往質(zhì)量,調(diào)整工作內(nèi)容等。
具備高自我領(lǐng)導(dǎo)水平的員工,正向情感增強(qiáng),對(duì)變革的工作方式的接受和適應(yīng)能力也進(jìn)一步提高。員工往往會(huì)具有更多的主人翁意識(shí),產(chǎn)生更高的責(zé)任感。因此,自我領(lǐng)導(dǎo)水平高的員工將更有可能在內(nèi)需的驅(qū)動(dòng)下,積極改善自己的工作表現(xiàn),正向調(diào)節(jié)對(duì)工作模式及內(nèi)容的看法,尋求工作意義和角色認(rèn)同[21]。
同時(shí),自我領(lǐng)導(dǎo)水平較高的員工會(huì)持續(xù)對(duì)外界環(huán)境進(jìn)行評(píng)估并與自身設(shè)定的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比較。這將推動(dòng)員工不斷從組織內(nèi)外部獲取信息并利用智能手段進(jìn)行提取和處理,采取一系列自我領(lǐng)導(dǎo)策略來(lái)減小理想和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差距。包括兩種形式:自我獎(jiǎng)賞以及自我懲罰。員工實(shí)施自我獎(jiǎng)賞策略有助于激活員工強(qiáng)化可取行為的內(nèi)在工作動(dòng)機(jī),幫助員工提高工作努力程度,承擔(dān)額外的工作任務(wù)和改變?nèi)蝿?wù)的執(zhí)行方式,驅(qū)使個(gè)體引導(dǎo)自己的思維和意圖轉(zhuǎn)向變革和改進(jìn)的方向[22];自我懲罰策略有助于激活員工重塑不當(dāng)行為的內(nèi)在工作動(dòng)機(jī),幫助員工重新思考、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進(jìn)而促進(jìn)員工改善工作現(xiàn)狀、完善工作流程及優(yōu)化工作方法等。兩者會(huì)反復(fù)提高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過(guò)程的內(nèi)在動(dòng)機(jī),進(jìn)而增強(qiáng)其工作激情[23],最終表現(xiàn)為工作重塑。由此,提出推論:
命題5:?jiǎn)T工自我領(lǐng)導(dǎo)正向促進(jìn)員工實(shí)施工作重塑。
(六)組織權(quán)力感知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組織權(quán)力感是組織對(duì)員工產(chǎn)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之一。Anderson等指出,組織權(quán)力感是員工對(duì)自己可控制資源的多少及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的一種心理感知[24],既包含“對(duì)他人的權(quán)力感”也包含“對(duì)自己的權(quán)力感”[25]。智能背景下,員工可以更為自主的決定工作節(jié)奏和工作方式,激發(fā)高水平的“對(duì)自己的權(quán)力感”。同時(shí),組織環(huán)境中,領(lǐng)導(dǎo)鼓勵(lì)員工自我管理和自我決策等授權(quán)行為,也會(huì)提高員工對(duì)自身在組織中重要性和影響力的感知。
研究表明,組織權(quán)力感對(duì)員工的認(rèn)知和行為均能產(chǎn)生正面的影響。Fast指出,組織權(quán)力感高的員工具有更高的自尊和自信水平[26]。當(dāng)個(gè)體感受到自己擁有更多可支配資源、具有更高影響力時(shí),將感受到更高的心理安全,從而傾向于更積極的認(rèn)可自我,更加聚焦于自我實(shí)現(xiàn)和自我突破。相反,權(quán)力感低的個(gè)體則較為缺乏自信,進(jìn)而更傾向于只完成工作要求的內(nèi)容。
此外,基于調(diào)節(jié)定向理論,楊文琪指出,高權(quán)力感個(gè)體具有促進(jìn)定向,低權(quán)力感個(gè)體具有防御定向。在面對(duì)不確定性的事件時(shí),高權(quán)力感個(gè)體更看重該事件的積極結(jié)果所能帶來(lái)的潛在回報(bào),對(duì)風(fēng)險(xiǎn)持樂(lè)觀態(tài)度,因而更傾向于獲取工作資源、積極應(yīng)對(duì)挑戰(zhàn)以獲得更多對(duì)工作和自身成長(zhǎng)的掌控感。
由此推論,在自主工作情境、領(lǐng)導(dǎo)充分授權(quán)的情境下,具有高組織權(quán)利感知的員工將注入更多積極情感,更加想要實(shí)現(xiàn)自身成長(zhǎng)和發(fā)展。因此,員工將主動(dòng)自我調(diào)整,最終促進(jìn)自我領(lǐng)導(dǎo)行為的表達(dá)。而當(dāng)員工處于低組織權(quán)力感知時(shí),員工表現(xiàn)出較低的自信程度,追求穩(wěn)妥,因此會(huì)在自我領(lǐng)導(dǎo)過(guò)程中投入較少的時(shí)間、精力和情感,最終抑制工作重望行為的表達(dá)。由此提出推論:
命題6:?jiǎn)T工組織權(quán)力感知正向調(diào)節(jié)人工智能通過(guò)工作自主性及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對(duì)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及工作重塑的間接影響。即當(dāng)員工表現(xiàn)為高權(quán)力感知時(shí),人工智能更容易促進(jìn)員工行使自我領(lǐng)導(dǎo),進(jìn)而表現(xiàn)出較高水平的工作重塑行為;當(dāng)員工表現(xiàn)為低權(quán)力感知時(shí)則相反。
綜上,總結(jié)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研究的理論模型建立于班杜拉的交互決定論基礎(chǔ)上,即環(huán)境、個(gè)體、行為三者間相互獨(dú)立,同時(shí)持續(xù)發(fā)生交互作用。
1.環(huán)境作用于行為。依據(jù)交互決定理論,環(huán)境是個(gè)體行為產(chǎn)生的基本前提。人工智能背景下,智能設(shè)計(jì)逐步替代重復(fù)性體力勞動(dòng)。員工可以更為自由化地安排工作節(jié)奏、選擇工作方式和工作場(chǎng)所。同時(shí),不確定性提高的外部環(huán)境下,領(lǐng)導(dǎo)者為增強(qiáng)管理有效性,避免自身情緒耗竭,管理模式將向“領(lǐng)導(dǎo)+教練”方向轉(zhuǎn)變,施行充分授權(quán)。兩者將激發(fā)員工自我擴(kuò)張的渴望。一方面,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通過(guò)提供給員工較高的心理自由,滿足員工對(duì)勝任力、自主性的內(nèi)在需求來(lái)滿足員工自我擴(kuò)張的需求。另一方面,高自主性的工作情境使員工迅速接觸到更豐富的工作資源,更新穎的工作方式以及更多的喚起性活動(dòng)。高速擴(kuò)張的自主性工作將激發(fā)員工積極的情緒體驗(yàn),而這種積極情緒本身也將促進(jìn)員工開(kāi)展自我擴(kuò)張行為。
2.個(gè)體認(rèn)知作用于行為。交互決定論強(qiáng)調(diào)了個(gè)體因素的重要性。個(gè)體的認(rèn)知貫穿了行為產(chǎn)生、習(xí)得及發(fā)展的全過(guò)程。工作情境變化驅(qū)使員工進(jìn)行自我擴(kuò)張與自我調(diào)節(jié),進(jìn)而以個(gè)體認(rèn)知過(guò)程為中介作用于行為表達(dá)。當(dāng)員工積極進(jìn)行自我擴(kuò)張,融入高自主與高授權(quán)工作情境后,員工感受到更高的組織認(rèn)可程度與更親密的上下級(jí)關(guān)系,這將提高員工對(duì)完成復(fù)雜工作任務(wù)的信心,產(chǎn)生更高的自我效能。因此,員工將更加嚴(yán)格地要求自己,積極地實(shí)行自我目標(biāo)設(shè)定、自我激勵(lì)、自我調(diào)整等自我領(lǐng)導(dǎo)策略以改善工作表現(xiàn)。至此,外界環(huán)境完成了對(duì)個(gè)體認(rèn)知的影響過(guò)程,員工開(kāi)始由認(rèn)知驅(qū)動(dòng)行為調(diào)整。
3.行為反作用于環(huán)境。班杜拉的交互決定理論指出個(gè)體行為并非完全是外界環(huán)境的被動(dòng)反應(yīng)者,個(gè)體的行為最終旨在協(xié)調(diào)自身與環(huán)境的差異,使環(huán)境向適合個(gè)體需要的方向發(fā)展。當(dāng)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過(guò)程被激發(fā)后,將會(huì)持續(xù)比較外界環(huán)境與自身標(biāo)準(zhǔn),采取自我獎(jiǎng)賞及自我懲罰策略來(lái)協(xié)調(diào)兩者間差異,進(jìn)而促進(jìn)員工調(diào)整工作現(xiàn)狀,促使其從事有益于組織和個(gè)人的工作重望行為。而這種工作重塑行為最終旨在重新定義和塑造工作內(nèi)涵,使員工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以達(dá)到高度的人—崗匹配。綜上,當(dāng)人工智能通過(guò)改變工作情境,激發(fā)員工的自我擴(kuò)張與自我領(lǐng)導(dǎo)后,員工施行的工作重塑將會(huì)帶來(lái)下一個(gè)新的工作情境,而新的工作情境也將再次對(duì)員工認(rèn)知及行為產(chǎn)生影響,即整個(gè)影響過(guò)程將會(huì)持續(xù)不斷的循環(huán)發(fā)生。
此外,這一過(guò)程會(huì)受到員工個(gè)人特質(zhì)-組織權(quán)力感知的影響。高組織權(quán)力感知員工具有更高的自信水平,更加關(guān)注積極結(jié)果的達(dá)成,實(shí)現(xiàn)自身成長(zhǎng)及發(fā)展的意愿更強(qiáng)烈。因此,人工智能更為自主和充分賦權(quán)的情境對(duì)員工自我效能的激發(fā)更顯著,員工將在自我領(lǐng)導(dǎo)過(guò)程中投入較多的時(shí)間、精力及情感,主動(dòng)搜尋各種信息以獲得更多的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最終促進(jìn)工作重望行為的表達(dá)。
結(jié)語(yǔ)
人工智能是社會(huì)發(fā)展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產(chǎn)物,帶動(dòng)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產(chǎn)業(yè)升級(jí),同時(shí)對(duì)員工的管理理論和實(shí)踐也帶來(lái)了沖擊。信息化時(shí)代,組織逐漸扁平化、智能化,于企業(yè)而言,必須將員工自我領(lǐng)導(dǎo)納入組織管理視野。建議組織在工作設(shè)計(jì)中,賦予員工更高的自主權(quán)利,為員工挖掘自我潛能提供空間。同時(shí),領(lǐng)導(dǎo)者應(yīng)意識(shí)到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在工作場(chǎng)所的重要意義,領(lǐng)導(dǎo)者可以嘗試以開(kāi)放的姿態(tài)與員工進(jìn)行溝通,為其提供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企業(yè)可以加強(qiáng)對(duì)員工工作重塑的干預(yù)。通過(guò)構(gòu)建包容自主的企業(yè)文化,使員工主動(dòng)調(diào)整自己的工作表現(xiàn),如摒棄低效率的工作習(xí)慣、改善低質(zhì)量的合作關(guān)系等,并引導(dǎo)員工的工作重塑行為與企業(yè)文化保持一致。但同時(shí)也要關(guān)注到員工個(gè)人特質(zhì)差異,因人制宜,因崗制宜,以促進(jìn)員工的工作績(jī)效和個(gè)人成長(zhǎng),增強(qiáng)組織效能。
參考文獻(xiàn):
[1]? 張新春,董長(zhǎng)瑞.人工智能技術(shù)條件下“人的全面發(fā)展”向何處去——兼論新技術(shù)下勞動(dòng)的一般特征[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19,(1):43-52.
[2]? 高山行,劉嘉慧.人工智能對(duì)企業(yè)管理理論的沖擊及應(yīng)對(duì)[J].科學(xué)學(xué)研究,2018,(11):2004-2010.
[3]? Larson L.,DeChurch L.A.Leading teams in the digital age:Four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and what they mean for leading teams[J].Leadership Quarterly,2020,(1):1-18.
[4]? Gajendran R.S.,Harrison D.A.The good,the bad,and the unknown about telecommuting: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mediators and individual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6):1524-1541.
[5]? 黃再勝.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勞動(dòng)的合約特征、實(shí)踐挑戰(zhàn)與治理路徑[J].外國(guó)經(jīng)濟(jì)與管理,2019,(7):99-111+136.
[6]? 黃雪明.人工智能:重新定義人才管理[J].機(jī)器人產(chǎn)業(yè),2017,(2):101-112.
[7]? Edwards J.S.,Duan Y.,P.C.Robins.An Analysis of Expert Systems for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n Different roles[J].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2000,(1):36-46.
[8]? 陳宇航.電力企業(yè)人力資源管理與人工智能結(jié)合的研究[J].中外企業(yè)家,2019,(3):88-91.
[9]? Vecchio R.P.,Justin J.E.,Pearce C.L.Empowering leadership: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ng mechanisms within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0,(3):530-542.
[10]? Hobfoll S.E.,Halbesleben J.,Neveu J.P.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The rea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J].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8,(5):103-128.
[11]? Amanuel G.,Sims H.,Yun S.,Tesluk P.,Cox J.Are we on the same page? effects of self-awareness of empowering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J].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8,(3):185-201.
[12]? Jay A.,Conger B.The empowerment process: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2):471-482.
[13]? Dansereau F.,Seitz S.R.,Chiu C.Y.,Shaughnessy B.,Yammarino,F(xiàn).J.‘What makes leadership? Using self-expansion theory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3,(24):798-821.
[14]? Dys-Steenbergen O.,Wright S.C.,Aron A.Self-expansion motivation improves cross-group interactions and enhances self-growth[J].Group Processes&Intergroup Relations,2016,(19):60-71.
[15]? Hackman J.R.,Lawler E.E.Employee reactions to job characteristic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71,(3):259-286.
[16]? Markham S.,Markham I.Self-management and self-leadership reexamined:a levels-of-analysis is perspective[J].Leadership Quarterly,1995,(3):343-359.
[17]? Houghton J.,Yoho S.Toward a 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when should self-leadership be encouraged?[J].Journal of?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5,(4):65-83.
[18]? 趙澤洪,朱亞蘭.組織扁平化趨勢(shì)中員工關(guān)系管理的變化與重構(gòu)——基于自我領(lǐng)導(dǎo)理論的視角[J].江淮論壇,2013,(4):71-75.
[19]? 沈文竹.變革型領(lǐng)導(dǎo)對(duì)員工工作績(jī)效的影響機(jī)制研究[J].現(xiàn)代營(yíng)銷(下旬刊),2018,(8):177-179.
[20]? 鄭展,張劍.從一般到更高:自我領(lǐng)導(dǎo)理論研究綜述[J].中國(guó)人力資源開(kāi)發(fā),2016,(17):40-47.
[21]? Park Y.,Song J.H.,Lim D.H..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Work Engagement: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Leadership[J].Leadership&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2016,(6):711-729.
[22]? 劉云.自我領(lǐng)導(dǎo)與員工創(chuàng)新行為的關(guān)系研究—心理授權(quán)的中介效應(yīng)[J].科學(xué)學(xué)研究,2011,(10):1584-1593.
[23]? Patall E.A.,Cooper H.,Robinson J.C.The Effects of Choice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Related Outcomes: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Finding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8,(2):270-300.
[24]? Anderson C.,John O.P.,Keltner D.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12,(2):313-344.
[25]? Lammers J.,&Stapel,D.A.Power increases dehumanization[J].Group Processes& Intergroup Relations,2011,(1):113-126.
[26]? Fast N.J.,Sivanathan N.,Mayer N.D.,Galinsky A.D.Power and overconfident decision-making[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2,(2):249-260.
[責(zé)任編輯 馬 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