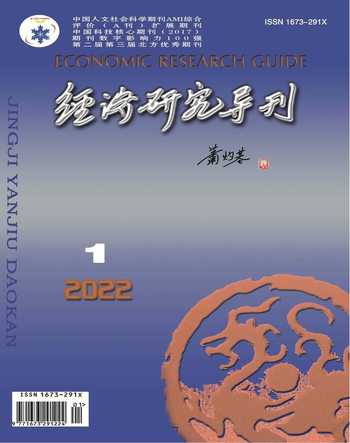民法概括性條款適用與解釋的方法論檢視
宋松宛
摘 要:“公序良俗”原則等概括性條款的適用問題一直是我國民法理論和實踐領域的熱點話題,其適用與作為法學方法的法律解釋相聯系。在概括性條款的適用過程中,存在著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交鋒,而這種緊張關系實際上是由法律解釋的自身的局限造成的。既有的法律解釋的順位并非一種強行適用的規則,不同的規則實際上并沒有絕對必然的優先順位。在需要進行法律解釋的場域中,結果往往在解釋之前就已經形成,而法律解釋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法律事實與結果之間搭建一座聯結的橋梁,使判決的結果具有合理性,法律解釋的目的在于增加判決方案的可接受性,而這種可接受性是以實現法律的社會價值為鵠的。因此,對于概括性條款的法律解釋應當建立在對于法律的共時性與歷時性考察的基礎之上,從時空的角度去認識法律所追求的社會效果的差異性,對可能出現的不同結果進行取舍,尋求最符合當下社會利益的判決結論,從而實現良法善治。
關鍵詞:概括性條款;法律解釋;法律適用;公序良俗
中圖分類號:D923?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01-0152-04
一、由公序良俗原則運用引發的法律適用的反思
“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是民法領域的經久不衰的話題,四川瀘州張?菖?菖訴蔣?菖?菖遺贈糾紛案開我國公序良俗原則適用之先河,盡管此案已經過去近二十年,但是作為法律適用的經典案例,多年來對其討論一直沒有中斷。
“公序良俗”是指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公共秩序包括社會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善良風俗,是指社會公共道德,由全體社會成員所普遍認可、遵循的道德準則[1]。公序良俗原則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作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兜底性原則,任何法律條文都可以囊括進“公序良俗”的范疇之內。也就是說,“善良風俗這一概念的不確定性與法律的穩定性要求相矛盾。”[2]從本質上看,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公序良俗”既非行為規范,亦非裁判規范,如果在裁判過程中不加限制地進行使用,不僅會造成道德審判對法律審判的僭越,同時也會造成法律適用混亂。
通過閱讀相關對四川瀘州遺贈糾紛案評價,諸多報道均提到了該判決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的確,司法權威的樹立需要體現司法公正,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是司法公正的內在要求。而尋求司法的社會效果,更多地表現為該案件的判決是否令社會以及當事人所信服,是否推動了法律對于社會調整、規范、指引作用的實現。四川瀘州遺贈糾紛案之所以能夠獲得大量支持,原因在于其以“公序良俗”將道德評價秘密地植入判決之中,使其披上“實質正義”的外衣,通過道德情感以引起社會共鳴。
的確,法律原則的衡平功能增加了法律適用過程中的靈活性,從而彌補了法律條款天然的“滯后性”。它將諸如公平正義、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具有穩定性的價值引入到法律文本中,以概括條款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僅使法律具有了德性倫理,同時也能使法律能夠與時俱進,在不斷變化的社會實踐中仍不失其內核。但是,如果對這些原則性的概括條款徑直適用,不僅會造成法官不探尋、發現具體規范,徑以概括條款作為請求權基礎,從而破壞“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位階,同時也會造成對于法律問題的思考,不窮盡解釋適用或類推適用的論證,徑以概括條款作為依據[3]。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特別是在《民法總則》頒布生效之后,徑直援用公序良俗原則進行司法裁判的案例有進一步增加的趨勢,這一趨勢所引發的上述危機,不可不察。
對于“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與作為法學方法的法律解釋相聯系。法律適用的任務是:“在解決個案之時,將隱含在法律中的正義思想、目的考量付諸實踐,并據之為裁判。”[4]作為法律原則的“公序良俗”,其適用需要對內容的確定性達到法律規則標準,而要實現這一結果,就必須將概括條款具體化,即借助法律解釋對該原則內容進行確定和固化。然而由于法律解釋方法上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仍有待回答,導致了司法實踐中在并不滿足原則裁判前提條件下適用原則條款,法律適用出現了“向一般條款逃逸”的趨向[5]。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對公序良俗這一法律原則的具體內容進行分析,而是以此作為切入點,對現有的法律解釋方法進行檢視,對當下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法律適用不規范現象進行深層次的探討,并尋找一種可能的化解路徑。
二、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交鋒
正如托馬斯·阿奎那所指出的,“法必須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為其真正的目標。”也就是說,法律規范本身并不是終局目的,人類社會是在透過法律規范追求某些特定目的,而這些目的則是由某些基本的價值所決定的。故這些特定目的以及基本的價值便是法律的意旨所在,因此法律適用和解釋應當反映出這些價值。從這一設定出發,可以認為公序良俗原則就是擔負起這一價值導向角色的重要體現。誠然,有眾多學者嘗試對公序良俗的具體內涵進行闡釋,以尋求一種理性的、可操作的方案,從而規范這一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這種努力實際上是將抽象化的價值判斷轉化為具象化的事實判斷的過程,其基礎仍然是“法律追求實質合理性的實現”這一前提之下的。
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之間的關系是法學理論的一個核心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關于這一關系討論卻常談常新。法律解釋實際上也是由這一核心問題所生發出來的,較為常見的解釋方法,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以及目的解釋。其中,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均是在法律文本所表達的含義中尋求一種形式上的自洽;而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解釋方法則需要對公共政策、立法目的、社會發展水平等進行多維度的考量,從而追求一種實質上的合理性。
在司法實踐中,作為裁判者的法官不可能無視各種社會關切、公共政策以及公眾情感等現實因素。法律是社會生活的規范,法律解釋的作用在于探求法律意旨,而這個意旨即在追求正義在人類共同生活上的體現。故法律解釋必須把握這個意旨,并幫助它實現[6]。對于這一目標的追求,法律需要對社會現實予以關注,保持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聯系。
但是,這一關注應當是通過既有的法律規范予以回應,“法定的規范必須經過澄清、精確化之后才能適用……法官不應只為當下的個案尋找規范,他必須將既存的規范,以其認為正當的方式,適用到每件由其負責裁判的個案上。”[4]同時,規范性的出發點應當是現行法所包含和體現出來的規范與價值,而不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種道德或政策的判斷[7]。“追求法律之內的正義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品質,實現法律之內的正義是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8]如果大量的法律之外的引入被納入到裁判之中,法律文本將會成為具文。任何使法的安定性讓位于個案正義的情形均須予以嚴格限制,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也不例外。這樣一來,對于整個社會來說,由于法律的指引、規范、評價功能不彰,不僅會導致人們難以根據既有的法律規范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還有可能帶來司法人員、執法人員濫用自由裁量權、恣意專斷、徇私舞弊的情況的發生。這也就意味著,司法的中立地位將會受到各種法律外因素的干擾,司法公正也將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形式上的正義對于司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9]。
故在司法實踐中,從文本出發理解和解釋法律似乎具有天然的優先性,但一旦發生爭議,各方對于法律文本的爭論就必定會延伸到法律文本之外的政治道德,難免會借助其他因素對文本的含義進行判斷。正如波斯納所言,“解釋是一條變色龍。”[10]文本所代表的形式合理性似乎是一個偽命題,任何法律的適用都無法排除法律之外的因素。法律解釋似乎最后還是要回歸實質合理性的判斷中來。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都對既有的法律解釋方法的適用順序形成了共識。即文義解釋相較于其他解釋方法具有優先性,其次是體系解釋,再者是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等。文義解釋之所以具有優先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相較于其他解釋方法,文義解釋直接面對法律條文,從最容易理解的層次出發去解釋法律。但是,這種優先性并非不證自明的,或者說,這種文本優先性是“經驗的”“描述性的”,而非“理性的”“規范性的”,這一排序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何種條件下,處于后一順序的法律解釋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取代前一順序的解釋方法所得出的結論。
這一深層次的追問涉及對于法律解釋方法的“終極規則”的探尋。事實上,這種“終極規則”并不存在,既有的法律解釋的順序位階只是為司法判決提供了一種指引,這種指引并非具有制度剛性,如果一個法官在解釋法律過程中打破了慣常的解釋順序,他也不會受到懲戒。
三、作為“靶向療法”的法律解釋
法律解釋的實質,是通過各種解釋的方法來彌合規范與事實之間的空隙,確定該法律規范對某特定的法律事實是否有意義。法律解釋問題并非由法律條文自身天然形成,而是由待裁判或者待處理的案件所引起。在需要進行法律解釋的場域中,結果往往在解釋之前就已經形成,而法律解釋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法律事實與結果之間搭建一座聯結的橋梁,使判決的結果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說,司法過程中的法律解釋并非演繹的,而是“靶向的”,或者說是“結果導向”的。正如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所言,是解釋追隨著解釋結果,而不是相反[11]。法律解釋的過程,當是以問題本身的需要來組織不同領域知識而加以正當性和合法性研究的過程[12]。
梁慧星教授認為:“法律解釋是一個以法律目的為主導的思維過程;每一種解釋方法,各具功能,但亦有限制,不可絕對化。”[13]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曾指出,其所提出的四種解釋因素(文法、邏輯、歷史、體系)各自擔任著不同的任務,但并非相互獨立,應當在解釋時進行結合來發揮作用。德國學者卡爾·拉倫茲同樣認為,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等并非不同的解釋方法,而是一些方法上的觀點(Methodische Gesichtspunkte),解釋時應當將所有的觀點納入斟酌,以獲得正確的解釋結果。故各種解釋因素之間并不具有固定的位階關系,究竟應當以何種解釋為主,應當取決于具體的案情事實[4]。
故法律解釋的結果是否真正實現了“對于法律文本意旨的正確理解”并不是最為關鍵的,從現實意義來看,法律解釋的作用在于為裁判方案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理由。如龐德所說,“法律的功能在于調和與調節各種錯綜復雜和沖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種利益中大部分或我們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以滿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地犧牲。”[14]而由法律所派生出來的法律解釋則是為法律的這一功能服務的。在司法實踐中,法律解釋的功能帶有一種天然的“功利性”特征,成了司法機關為增強其判決說服力的工具。故法律解釋實際上是一種為增強司法的社會支持的策略,既然是策略,那么對于解釋方法的選擇則是以“增強判決說服力”為鵠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公序良俗等原則作為保護社會公益的論據,成了增強民眾接受判決支持度的工具。
從瀘州遺贈糾紛案來看,事實上,遺囑訂立人的意思自治的保護同法定婚姻關系均具有保護的意義,二者都是當事人的正當法律權利。從判決的影響來看,如果承認遺囑有效,從法律適用上看并無不妥,甚至比援用公序良俗原則對遺囑效力進行否定更加符合法律適用的位階,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向社會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即法律默許、承認婚外同居。這種情況顯然與法律對社會的正面激勵背道而馳,極有可能招致社會的非議,司法所代表的正義和權威顯然受到削弱。這一判斷已經超越了法律本身,延伸到了法經濟學的范疇,對判決進行成本收益的比較分析,以期望以盡可能小的成本發揮盡可能大的社會正面效果。但是這種經濟分析最終仍然需要回歸到法律范疇,以法律的正當性來取代經濟分析上的功利性,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結論必須通過法律理由適用到判決之中。在適用法律規范沒有尋找到合適的理由時,那么援用公序良俗的條款似乎便成了更為合理的選擇。
四、并重與讓渡:多重價值沖突的消解
從前文的分析來看,將法律解釋局限在規范與事實的場域中進行討論,那么法律解釋的方法論問題似乎是一個偽命題,關于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的沖突將會無止境地進行下去。因此,對于民法解釋和適用的方法論的考察,必須擺脫純粹的法教義學分析。“因為法律解釋,從其根源上看,不是一個解釋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15]
就法學研究的目標和屬性而言,面向和指導實踐是最為重要的內容。“實踐性構成了法學的學問性格,法學應當回歸實踐之學本身。”[16]從法學的發生學上看也是如此,即法學是由問題產生理論,而非理論早于問題。司法的功能是解決糾紛、定分止爭,那么一切的司法裁判理論都應當是圍繞這一中心而展開的。作為法學方法的法律解釋也應如此。也就是說,法律解釋的目的在于增加判決方案的可接受性,而這種可接受性是以實現法律的社會價值為鵠的。法律解釋雖然具有多種不同模式,本身無可避免地隱含價值判斷,但多種法律解釋方法的對話和交流卻能夠拓展經驗邊界,使得法律解釋趨向于實踐上的合理性[7]。從這一點看,在何種情況下使用何種解釋方法,以及當使用不同的解釋方法帶來不同的結果時,究竟以何種標準進行取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似乎并不那么緊迫了。
正因如此,法律的社會學解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原先的法律解釋方法所造成的困境進行消解。法律的社會學解釋偏重于社會效果的預測及其目的之考量。在實用法學上,社會學的解釋系在自由法運動以及法社會學誕生之后,開始為法學者所運用。當文義解釋的結果有復數解釋的可能出現時,如果不超出文意,那么每一種見解實際上都是合法的解釋。那么究竟何種解釋更為恰當,則并非理論認識的問題,而是政策性問題。如果涉及社會效果的預期或者目的考量,法官則應當作社會學的解釋[17]。就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則來說,如果按照通常的文義解釋則很難確定其準確的內涵,法官在援用公序良俗進行裁判時,所依據的判斷標準仍表現出對“社會道德觀念”的歸依,即按照社會上一般人的價值觀念進行確定,而這一過程實際上就包含了法律的社會學解釋。
臺灣學者楊仁壽認為,社會學的解釋的操作方法,可以分為兩個步驟:一是對每一種解釋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進行預測;二是確定社會統制目的,并由此目的予以衡量各種解釋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何者最符合該目的[17]。在這種社會學解釋的操作方法,需要建立在對于法律的共時性與歷時性考察的基礎之上,從時空的角度認識到法律所追求的社會效果的差異性,從而對可能出現的不同結果進行取舍,從而實現契合當時社會所認可的“正義”標準[18]。
結語
理論(Dogmatik)的進步,需要有法學方法(Methode)的協力,以更為自覺、更為透明的觀點、更為嚴謹的理由構成來支持判決的結論[19]。通過對法律適用和解釋的方法論的檢視發現,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交鋒的場域中,法律解釋具有著功利性的特點。法律解釋的現實作用在于為裁判方案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理由,它通過“具體化”具有“開放性”的價值標準等方法,借此促成關于法律判決的正當性的討論[4]。在這一過程中,隱藏的社會效益的經濟分析化為法律的肉身,以一個個具體的司法案例尋求法律的社會效果。在法律的社會學解釋方法下,法律解釋順位中后一種解釋方法在何種情況下能夠取代前一種解釋方法的追問得以消解,對于概括性條款的法律解釋應當建立在對于法律的共時性與歷時性考察的基礎之上,從時空的角度去認識法律所追求的社會效果的差異性,對可能出現的不同結果進行取舍,尋求最符合當下社會利益的判決結論,從而實現良法善治。
參考文獻:
[1]? 王利明.民法總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 [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M].遲穎,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 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4]? [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 向淼.公序良俗原則司法適用的模式與類型[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161.
[6]? 黃茂榮.法律解釋學基本問題(I)[J].臺大法學論叢,1976,(2):49.
[7]? 丁曉東.人民意志視野下的法教義學[J].政治與法律,2019,(7):67.
[8]? 江必新.在法律之內尋求社會效果[J].中國法學,2009,(3):7.
[9]? 桑本謙.理論法學的迷霧——以轟動案例為素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0]? [美]理查德·波斯納.法理學問題[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11]?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M].米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12]? 王樺宇.領域法學研究的三個核心問題[J].法學論壇,2018(4):111.
[13]? 梁慧星.論法律解釋方法[J].比較法學研究,1993,(1):63.
[14]? [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5]? 桑本謙.法律解釋的困境[J].法學研究,2004,(5):12.
[16]? 舒國瀅.法學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從古羅馬時期的Jurisprudentia談起[J].清華法學,2013,(1):98.
[17]?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
[18]? 許章潤.政體和文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9]?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 文 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