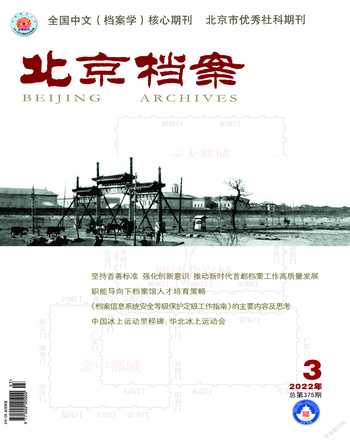民國時期北京市西城區果子市斛律光碑
王石雨
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區的果子市社區北鄰德勝門箭樓,南靠清朝醇親王府。社區內轄有鼓樓西大街、西絳、八步口等具有古老傳說的胡同街巷,蘊含著豐厚的歷史底蘊。然而在民國時期,果子市曾有一塊題為“北齊咸陽王斛律光”的石碑,經查閱檔案及相關文獻史料,亦可發現其背后同樣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北京市西城區果子市斛律光碑,尺寸為34 cm×90cm,碑題為“北齊咸陽王斛律光”,正書。石碑正文共102字,內容為:“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咸陽郡王金子。馬面彪身,神奕雄杰。年十七,為都督,封永樂縣子,進巨鹿郡公,歷位司徒、尚書令。周師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邙山,大敗之。遷太尉,轉大將軍,襲爵咸陽王,進太傅。累破周將韋孝寬之師,加右丞相。后為祖珽所害。”正文后有贊詩一首,曰:“落雕都督結發從戎,周師十萬一鼓而空。筑鎮平隴累戰稱雄,血跡不滅千載孤忠”(碑文及贊詩中標點均為作者所加)。從內容上看,碑文對相貌魁偉、少年得志且英勇善戰的北齊名將斛律光不吝贊美之詞,對其在與北周作戰中的累累戰功也予以頌揚。而對于斛律光忠誠于朝廷,卻最終慘遭小人陷害的悲慘命運則非常惋惜。遺憾的是,歷經戰火,原碑已不見于果子市地區,僅有碑刻拓片及相關記載傳世。根據國家圖書館館藏檔案可知,該碑刻立于民國三十年十二月(1941年12月)。[1]
此外,石碑落款題有張伯英三字,并附印章兩枚。張伯英(1871—1949),徐州銅山縣人,字勺圃,晚清至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作品尤以魏碑見長。由其總纂的《黑龍江志稿》參考了許多珍貴檔案,記載極其全面,包含地理、經政、物產、財賦、學校、武備、交涉、交通、職官、選舉、人物、藝文12類,至今仍是研究黑龍江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的重要材料。[2]毫無疑問,張氏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果子市斛律光碑中的贊詩亦出自其手。
作為晚清至民國時期著名的書法家、學者、詩人,張伯英為何要為一位生活在北朝時期的將領書寫碑銘及贊詩呢?這還要從斛律光的生平事跡談起。
斛律光(515—572),北齊著名將領,高車族人。高車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于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的一個游牧民族,因善于制造并使用“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的車子而得名。據《北史》卷98《高車傳》記載,高車內部有六個強大的氏族部落,分別是: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3]斛律光即出身于高車斛律氏家族。盡管作為北齊開國功臣斛律金長子,但出身顯貴的斛律光卻并非紈绔子弟,自幼便以善于騎射,武藝高強聞名。十余歲時,斛律光隸屬侯景部下,隨同四處征戰,高歡部將彭樂稱其必成大器。[4]
此后,斛律光先作為前鋒跟隨北齊文宣帝高洋出征漠北,大敗庫莫奚軍隊,擄獲牛羊、馬匹、輜重甚多。隨后數年,斛律光又率軍先后奪取了北周天柱、新安、牛頭、絳川、白馬、澮交、翼城等多座鎮戍。在北齊與北周之間的邙山、洛陽、汾水等著名戰役中,斛律光不僅運籌帷幄,還勇冠三軍、戰功赫赫。據史書統計,斛律光一生參與作戰上百次,從無敗績,堪稱一代名將,最后官至左丞相、咸陽郡王。但因其剛正不阿,最終慘遭奸臣穆提婆、祖珽讒害。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滅亡北齊后,感念斛律光忠勇,追封其為上柱國、崇國公。[5]唐德宗建中三年(783),增添歷代名將64人畫像,配享于武成王廟,斛律光即在其中。記載北齊歷史的《北齊書》卷17、《北史》卷54也均為其列傳。從果子市斛律光碑的碑文內容來看,其無疑是綜合參考了《北史·斛律光傳》與《北齊書·斛律光傳》的結果。
由上文可知,斛律光是一位活躍于北朝后期的著名將領,然而距離其生活年代長達1300余年的后人,為何要為其刻碑留念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斛律光忠勇雙全,符合人們心目中英雄的標準。根據史書記載,斛律光“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其父每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在不斷的刻苦練習中,斛律光箭法也逐漸精準,每箭必“麗龜達腋”,斛律金對此贊不絕口。17歲時起,斛律光跟隨父親四處征戰,曾在戰場上馳馬射中并生擒西魏丞相長史莫孝暉。在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564)爆發的邙山之戰中,斛律光大敗北周軍隊,親自射殺名將庸國公王雄。另據《北齊書·斛律光傳》記載:“(光)嘗從世宗于洹橋校獵,見一大鳥,云表飛飏,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嘆曰:‘此射雕手也。’”[6]因此斛律光在當時又有“落雕都督”之稱,可謂是真正的“射雕英雄”。除英勇善戰外,斛律光還為人正直,不折腰于權貴、奸佞。權臣祖珽、穆提婆等占據公田,多行不法,斛律光上奏與之抗爭。而且他從不倚仗權勢貪奢靡廢,個人素養極高。斛律氏“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7]。但斛律光“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8]深有國士之風,頗受士卒及朝野愛戴。正是因為斛律光兼有忠和勇兩種優秀品質,才深深為1300余年以后的人們所敬仰。
第二,國難之際,北平淪陷,需要出現“斛律光氏”的英雄人物。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北平淪陷。在此危局之下,張伯英依然保持著高尚的民族氣節,不僅隱居不出,還屢次寫信給時任徐州偽市長的叔父張云生,勸其莫為偽政權出力。在生活清苦、貧病交加的情況下,即使日本侵略者試圖以10萬銀元購買其代表作《十七帖》,張伯英仍視如糞土,嚴詞拒絕。作為愛國學者,其當然希望華夏兒女中出現“斛律光氏”的英雄人物,可以獨撐危局,甚至帶領同胞光復山河。尤其是斛律光還深諳兵法智謀之道,“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兇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9]。對斛律光的欣賞、贊美及期待“斛律光氏”英雄人物的出現,促使張伯英為斛律光撰寫碑文并為其題贊。
第三,以斛律光為代表的北方民族將領歷史上曾經活躍于北京地區。南北朝至兩宋年間,北京作為戰略要地,是定都于中原、關中的漢族政權與北方各游牧民族及其所建立政權進行交往、溝通的關鍵地域。這一時期內,北京地區廣泛存在著出身于北方民族的將領的活動痕跡。考慮到北朝后期北京地區屬于幽州管轄,為北齊政權領土,且斛律光之弟斛律羨更是長期擔任幽州刺史,斛律光本人也曾經屯兵幽州,故出自北方游牧民族——高車族的斛律光與北京也深有淵源。正是由于以上三點原因,民國三十年十二月(1941年12月),在北平地區一些愛國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斛律光碑刻立于今西城區果子市。
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也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則是各個民族共同努力創造的結果。作為華夏兒女,我們有義務了解包括斛律光事跡在內的中國古代民族歷史;保護處于全國各地的各民族古代傳統文化,更是一項義不容辭的重要工作。而認識、熟悉、保護北京地區珍貴的檔案、文物,了解北京地區的民間文化,避免斛律光碑遺失的類似情況發生,同樣刻不容緩。
注釋及參考文獻:
[1]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碑刻精華,北京9503-60.
[2]萬福麟,張伯英,崔重慶,等.黑龍江志稿[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3]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3270.
[4][9]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1967-1972.
[5][6][7][8]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222-226.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