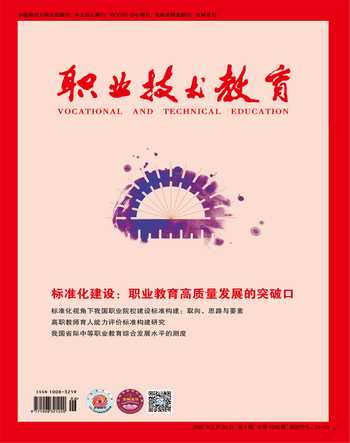民國職業教育輿論建設探析及歷史借鑒
陶仁義?楊雨慧
摘 要 1917年,職業教育在國內倡導伊始,被傳統文人惡意譏諷為“吃飯教育”,黃炎培等職教界人士在以《申報》為主體的輿論支持下,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回應。自此,吃飯(生計)、職業、教育之間的關聯逐漸為世人所接受,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和支持,被納入新的學制體系。回顧職業教育在民國時期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發展歷程,對當下職業教育堅定走類型發展之路提供了歷史借鑒。
關鍵詞 “吃飯教育”;黃炎培;職業大學;輿論建設;歷史借鑒
中圖分類號 G71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2)06-0075-05
1918年1月,職業教育倡導者黃炎培在《教育與職業》第3期發文,對社會上將職業教育譏為吃飯教育的言論予以回應:自本雜志第一冊以幼兒畫飯具揭于面,一時議論蜂起。稱之者曰:“善哉!今后之學子,其得啖飯地矣。”詆之者曰:“鄙哉!乃以職業教育為啖飯教育也。”二說背道而馳,果孰非而孰是乎?請得而釋之。吾人在世之目的與天賦之責任,其決非僅為個人生活明矣。雖然,茍并個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與言精神事業乎?而尚與言社會事業乎?職業教育之效能,非止為個人謀生活,而個人固明明藉以得生活者。以啖飯教育概職業教育,其說固失之粗浮,高視職業教育,乃至薄啖飯問題而不言,其說亦鄰于虛驕。①
吃飯,又被寫為“啖飯”“喫飯”,包含兩層涵義。單獨使用時多取其基本含義,即通過進食來獲得日常生活所需能量的行為;在具體語境中或與其他詞連用時取其引申(社會)的含義,即通過一定的技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常以“混飯”“騙飯”“飯碗”等謙詞的形式出現,與不同時代中的“生計”“謀生”“就業”等詞語義相同。
社會輿論視職業教育為吃飯教育,既與黃炎培在從實業教育到職業教育宣傳、推廣過程中使用“吃飯”“啖飯”等詞有關,更主要的是,在當時的中國,“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觀念仍根深蒂固,掌握話語權的傳統文人對新思維、新理念的排斥和抵制,揪住“吃飯”這一“鄙詞”不放,對職業教育予以嘲諷,對《宣言書》中使用頻率更高的“雅詞”——“生計”選擇性地視而不見。
本文旨在通過對職業教育倡導初期社會視其為“吃飯教育”這一輿論形成、發展、轉變過程的梳理,以史為鑒,結合當下職業大學所面臨的社會質疑與困惑,以期為當下大眾對職業教育思維定勢的轉變提供歷史借鑒。
一、“吃飯”與教育的結合
1913年8月,時任民國江蘇省首任教育司司長的黃炎培針對當時學子“往往受學校教育之歲月愈深,其厭苦家庭鄙薄社會之思想愈烈,扦格之情狀亦愈者”的狀況,開宗明義地指出“自社會困于生計,于是實業教育問題惹起一世之研究”,批判當時舊教育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弊病,“學校普而百業廢,社會生計絕矣”[1],提倡“打破平面的教育,而為立體的教育”[2],宣傳課堂知識與學生生活、學校與社會實際相聯系的實用主義教育,在當時教育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1914年元月底,黃炎培辭去公職,以“旅行記者抱一”的名義寫稿按期發表于《申報》,所有教育情況和評判按期發表于《教育雜志》[3],展開對當時國內經濟中心的蘇、皖、贛、浙數省及政治中心的山東、河北、直隸地區的教育狀況考察。“學校愈多,則造就無業游民亦愈多”[4]現象的廣泛存在,促使黃炎培開始關注畢業生謀生的現實重要性。
報紙受眾的廣泛性要求使得黃炎培行文風格較前發生明顯轉變。期間,黃炎培首次將“吃飯”這一“鄙俗”之詞與“教育”相提并論,“景德瓷工豈旦莫肯受新教育而已,且甚疾視此改良事業……而其最大原因,實由景德為瓷工勢力范圍,己則守成法不肯改,而復心怵于一經改良,將立被淘汰而無所啖飯,遂有合群抵制之一途”[5]。
1915年4月至7月,在受民國教育部指派赴美考察教育期間,黃炎培仍用“生計”一詞與教育相連。在夏威夷,他發現島上土人數量從之前的30萬到僅存2萬,“生計競爭之失敗”是重要原因,而費城商務博物院陳列的中國“苦力生計”物產與紐約教育行政“現定之教育方針,在提倡職業教育,期以教育扶助生計”[6],巨大反差對其造成了強烈刺激。黃炎培認識到“挽近實業益發達而生計問題亦日以急迫,于是復有所謂職業教育,專以職業上之學識技能教授不能久學之青年”,“回念吾國……余固不欲置實業專門教育為后圖要,不能不認識職業教育為方今之急務”[7]。
1916年,黃炎培通過“抱一日記”專欄發表了一系列教育與社會關聯的思考短文,將所睹、所察學生眼高手低、難尋吃飯之地的就業窘境予以揭露,“陳君光甫言銀行引用畢業生,往往不堪其待遇,稍加聲色而即以為虐。夫銀行新事業,乃猶不能堪,吾懼莘莘者無啖飯地矣”,“比歲以還,各地學校青年,學成失業。任何等級之學校,除師范外,畢業生舍升學別無出路。而升學者必居最少數,緣是大多數學生,幾求一飯之地而不可得。此等現象,從前不過有識者顧慮及之,今則事實顯著,無庸為諱,社會前途,深可寒心”[8]。這些現象促使黃炎培的教育理念開始由實用教育向職業教育轉變,“實用教育主義產出之第三年,謂是職業教育萌生之第一年,可也”[9]。
1917年初,黃炎培前往日本、南洋地區繼續考察職業教育。是年2月20日晚,黃炎培在菲律賓普智學校進行講演,他以首都謀生狀況為典型,對比中學、國內外大學畢業生仍無啖飯地的實際情況,“(北京)一年之間,坐食分利者,平空增多二萬。北京既如此擁擠,其他省更可想而知。此數十萬人……非皆為謀做官也,大抵皆為謀啖飯耳。中國行政各機關,一時不能改良,即為謀啖飯之人太多,無有正當之疏通法, 今注重教育,即須于根本上,解決此啖飯問題。去年調查江蘇中學畢業生一百人中,除二十五人升學外,余多謀事而不得事者。在諸君或想中學畢業,學何未大精深,難于社會上謀生活, 必待大學畢業,或外國留學畢業,始有啖飯地乎。兄弟又憶去年友人述北京青年會,有留學生五十人,寄宿會中為謀事地步。嗟夫,未受教育者無啖飯地,已受教育者亦復如此?此等弊病,簡言之,即全在平時所讀皆無用之書。……更望辦學者,相學生所處之地位,施以適當之教育,則他日出而謀社會事業,何患無啖飯地步”。黃炎培同時表示將在上海,“同當世熱心諸君子,倡辦一職業教育社,即欲溝通職業界與教育界,為發展社會生活能力”[10]。
1917年5月6日,黃炎培于上海聯合48位社會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簡稱職教社),10月社刊《教育與職業》發行,封面“幼兒畫飯具”乃是由6歲兒童馮雙修所繪“碗筷勺”素描圖,是引發社會視職業教育為“吃飯教育”兩極言論的導火索。資料顯示,從創刊號至第十二期封面均采用了幼兒畫,但首期封面圖原本采用的是第三期黃炎培7歲兒子黃萬里所作“剪刀、線”寫生畫。這一調整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黃炎培的公心,更應視其為黃炎培長期以來在國內外教育考察過程中對“吃飯”這一最基本生存要求深入思考后所做的慎重決定。
正文首篇《宣言書》中指出,較之普通學校,實業學校、專門學校甚至留學歐美大學的畢業生“其十之六七,乃并一啖飯地而不可得”。顯然這是社會上將職業教育視為吃飯教育的最直接原因。盡管黃炎培在文中一再強調“生計”與“教育”的關聯:“吾儕所深知、確信而敢斷言者,曰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問題,厥惟生計;曰求根本上解決生計問題,厥惟教育;曰吾中國現時之教育,決無能解決生計問題之希望;曰吾中國現時之教育,不惟不能解決生計問題,且將重予關于解決生計問題之莫大障礙。”
不難看出,黃炎培在提出職業教育后,社會上之所以未能形成“生計教育”這一概念,是因為當時“吃飯”一語不登大雅之堂,“不免會受到一般‘士大夫’階級的輕蔑,因為他們以為‘職業者吃飯也,職業教育者吃飯教育也’”[11]。在以黃炎培為首的職教社群體不斷開展的輿論宣傳中,職業教育這一新理念才逐漸為國人所接受。
二、“吃飯教育”的輿論爭論與接受
職業教育在國內倡導之際,亦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之時。黃炎培的澄清無法徹底消除“士大夫”視職業(實業)教育②為吃飯教育的刻板成見,而以《新青年》為首的社會進步力量為之展開的批判則起到了積極的社會推廣作用。在以《申報》為主體的輿論支持下,吃飯、職業、教育之間的關聯逐漸為世人所接受,職業教育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和支持,被納入新學制之中,迎來了全面發展。
1918年6月,《功利主義與學術》刊于《東方雜志》首篇,“雖然彼所謂普及教育者,將僅以穿衣吃飯為目的乎?抑除穿衣吃飯以外,上有其它目的乎?如僅以穿衣吃飯為目的,則鬻字療饑、傭書作活取道與此,計已大迂。如除穿衣吃飯以外,尚有維持文化增進種智之目的,則文化重心自在于高深學問”[12]。顯然就是針對職業教育而來,將職業教育視為功利主義教育的典型。
陳獨秀在《新青年》撰文對此予以正面回擊:“夫古今中外之禮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試剝膚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間接為穿衣吃飯而設者乎?個人生活必要之維持,必不可以貪鄙責之也。東方記者倘薄視穿衣吃飯,以為功利主義之流弊;而何以又言‘猶有一事為功利主義妨阻學術之總因,則此主義之作用,能使社會組織劇變,個人生計迫促,而無從容研學之余暇,是也’,原來東方記者亦重視穿衣吃飯如此,豈非與‘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之非功利主義相沖突乎?”[13]
新文化運動另一中堅人物胡適并未直接參與這一論戰,但其老師杜威在國內關于職業教育的實用主義演講卻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引發了強烈轟動,擴大了職業教育的社會影響。
1919年9月28日,杜威在北京演講教育哲學時提到:“說到實用教育,人家每容易起一種誤會,以為實用教育就是吃飯主義,其實并不然。吃飯固然未始不重要,教師能教得學生得到飯吃也是很好的。”③1920年5月29日至30日在上海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杜威連續做了《職業教育之精義》《職業教育與勞動問題》的演講[14],進一步擴大了職業教育在國內的傳播。在1922年底頒布施行的壬戌學制中,職業教育被納入教育體系,而“這個制度是黃炎培先生們研究好了,(新任教育總長)湯爾和贊成”[15]的結果。在1928年5月的全國教育會議上,再次突出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并存的重要性,“所以高級中學自第一年起,即采用分科制,但分科的方法:第一,應根據教育學上所謂‘一切科目都是含有職業的性質,亦都是含有文化的性質’一個原理,廢除所謂‘普通科’與‘職業科’的名稱,以謀‘自由教育’或‘文雅教育’與‘實利教育’之溝通,不以前者為文飾教育,又不以后者為吃飯教育。然應視一切教育為創造文化之教育,同時又復視一切教育為發展生產之教育”[16]。
在此期間,輿論將吃飯與職業的并稱開始普遍起來。“現在的人,有人問他吃過飯否,他就說騙過了,以為客氣,甚至有正當職業的人也有自謙為騙飯吃的。我想吃飯及正當職業何等光明!為甚么要自貶人格說是騙來的呢?”[17]馮玉祥在其軍隊中開展了職業教育,針對其士兵普遍不識字的情況,便用吃飯予以宣傳:“中有幾條至理名言錄之如下‘當兵是國民的義務,不是職業,作工乃是真職業’‘為人要有正當職業,靠人吃飯最可恥’‘沒有職業的高等游民,不如下等的苦工’‘作工是給自己作的’如此之類都是發人深省之談。全廠資本僅七千元,而現在每月產品之所值反不止七千元。”[18]江蘇省長表示“且認識一千字之后,不是就能吃飯,職業問題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19]。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講公民教育,略謂人生有兩大問題:一吃飯問題,一做人問題。吃飯問題由職業教育解決之,做人問題則由公民教育解決之[20]。“為吃飯而謀職業。是人生的初步。為服務為吃飯才是人生的極軌。這彷佛是分畫成兩橛,實在是起訖一貫的”[21]。
盡管如此,仍有人以此揶揄職教社員,“你們提倡職業教育,何不直捷了當提倡吃飯教育”。雖然他們深知“職業教育的地位和價值,斷不是籠統的‘吃飯問題’和抽象的拜金主義可以概括他的”[22]。為此,職教人士通過依附于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方式使得社會上轉變對職業教育的陳舊觀念[23]。
1930年的中華職教社第十一屆年會上,圍繞《不做工的何以有飯吃?讀過書的何以沒飯吃?做苦工的何以吃不飽?吃飯與做工必須有聯絡》的主題作進一步討論。楊杏佛致詞指出:“從古以來、沒有不做工而吃飯的人,但何以現在不做工而吃飯的人這么多,就可以想到做工而吃不到飯的人又有多少。如不把此問題解決,民生主義就沒有達到目的。所以我們提倡職業教育就是提倡吃飯教育。”黃炎培在演講中表示:“職業教育即為吃飯教育,受職業教育乃自謀吃飯方法,亦即為人謀吃飯方法。”[24]更是將孫中山“雙手萬能”的學校建設方略發展為職業學校的核心辦學理念[25]。
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黃炎培仍用吃飯教育宣講職業教育[26]。在以其為首的職教群體諸多努力下,社會上已轉變了對職業教育的蔑視心態。
當時的教育研究者充分肯定了黃炎培所倡導的職業教育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指出,“職業教育而注重上述的職業訓練,則吃飯教育之譏評可以少減了”[27]。
持有同樣觀點的并非一人。舒新城強調“但是我們要記著現在的職業教育,是現在的經濟制度下一種救濟的辦法。人民迫于生計不得不早離學校就事。于是教育家于其未畢普通教育以前即施以職業教育,或于就是后施加以職業補習教育而不免范圍太狹隘,性質太專門與教授太早等弊端了”。“如將來經濟制度果能改革,使各人都可以受相當的普通教育后再施以職業教育,則吃飯教育之議論則可以全除了”[28]。
此時起,盡管職業教育仍常被簡化為吃飯教育,但各地教育部門均著手將職業教育置于其行政工作的重要位置。“職業教育就是‘吃飯教育’,有了職業教育而不能解決‘吃飯問題’,這種教育就算是失敗了”[29]。“尤其中國一般人多以職業教育為功利主義,非文化教育,甚或稱之謂吃飯教育。然職業教育之真義,并不是專在吃飯,吾人統觀歐美各教育名流,如羅素、杜威、孟祿、桑戴克等,彼等對于職業教育之見地,都以為職業教育有二個重要含義,一是為己謀生,一是為群服務”[30]。徐貽在回應當時社會上的“中學教育改進”運動時提出:“盡可文學陶養淺審美能力差,吃飯問題是應該首先解決的。”[31]“第二種教育的目的顯而易見是專門教人學些吃飯本領,繩以‘衣食足而后知榮辱’的原則,這種教育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至少那一點‘榮辱’的道理應當和吃飯的智能同時灌輸到教育者的腦筋里去。否則,在生產薄弱、物力涸敝的今日,也是非是教‘不奪不厭’的風氣變本加厲而已。”[32]
吃飯與職業的并論在不斷為社會所接受的同時,勢必也對政府產生了相當影響,而政府高層對其重要性的認知更加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1924年1月23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國民黨之政綱”里,孫中山在對外對內政策中均強調了職業教育的重要性[33]。1934年7月,職教社于南昌舉行社員大會暨全國職業教育討論會,蔣介石在大會開幕訓詞中提到:“教育為救國的根本事業,盡人皆知,在各種教育當中,職業教育最合今日之需要,尤為貴社諸君所確切認識。貴社以群策群力提倡職業教育有年;成績斐然可觀,實值得吾人欽佩……近數月來中正發起新生活運動,其目的亦即在此,深望諸君了解此意,并以新生活運動之精神,含濡于職業教育之中。換言之,必使國民明禮義、知廉恥,而后職業教育始能完滿收效也。”[34]蔣介石此舉更多是為其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發聲,欲將職業教育置于新生活理念管控之下,但無疑是包含著對職業教育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技術人才保障作用的一種認可。
三、結語
進入21世紀,我國已實現全國人民溫飽(吃飯)問題的解決。黨的十八大以來,光盤行動、拒絕浪費等與“吃飯”密切相關的活動成為新理念、新風尚,視吃飯與教育并論為異的思維早已消逝。與之對應,職業教育助人獲得生存、發展空間在社會上則已形成共識。
百年前黃炎培等人將職業教育引入中國之際,很難撼動傳統教育在國民心目中的正統地位。“士大夫”階層對這一教育新類型極盡輕蔑、詆毀之詞,但職業教育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適應力,讓這種成見消逝于歷史中。深刻理解百年前國內職業教育萌生之際的民眾思維固化、資訊來源貧乏的狀況,了解職教先賢們推動“吃飯教育”到職業教育的艱難歷程,有助于我們堅定辦好人民滿意的職業教育的信念,提升舉辦具有類型特色的職業教育的自信,為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而奮斗。
參 考 文 獻
[1]黃炎培.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M].上海:江蘇省教育會出版,1913:4.
[2]黃炎培.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M].上海:江蘇省教育會出版,1913:7.
[3]黃炎培.八十年來[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73.
[4]江蘇省巡按使公署政務廳教育科.江蘇第二次省教育行政會議匯錄[M].[出版地不詳]:1915:18.
[5]黃炎培.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一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114.
[6]黃炎培.新大陸之教育·上編[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13-121.
[7]黃炎培.新大陸之教育·下編[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5-7.
[8]黃炎培.抱一日記[J].教育雜志,1917(1):1-8.
[9]黃炎培.實用主義產生之第三年[J].教育雜志,1917(1):15-18.
[10]黃炎培:東南洋之新教育后編·菲律賓[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137-138.
[11]蘇季常.當代人物[M].[出版地不詳]:故事雜志社,1946:59.
[12]錢智修.功利主義與學術[J].東方雜志,1918(6):1-7.
[13]陳獨秀.質問東方雜志記者:東方雜志與復辟問題[J].新青年,1919(3):22-28.
[14]無題[N].申報,1920-05-30(10).
[15]陶仁義,茅曉薇.黃炎培與民國職業教育發展——以壬戌學制為中心[J].江蘇高職教育,2020(4):43-51.
[16]姜琦.整理學制系統案[M]//中華民國大學院.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109.
[17]簽庵.無謂的談話[N].申報,1923-03-22(20).
[18]馮軍之職業教育[N].申報,1923-04-20(6).
[19]南京平教促進會歡迎社員[N].申報,1924-07-08(11).
[20]暑假研究所開講之第一日[N].申報,1928-7-25(11).
[21]天然.為吃飯而謀事和為服務而吃飯[N].申報,1928-12-26(11).
[22]潘文安.吃飯主義與職業教育[J].教育與職業,1927(89):387-390.
[23]傳若愚,徐公達.職業教育與民生之關系[J].教育與職業,1927(89):395-397.
[24]職教會昨日開幕[N].申報,1930-07-21(9).
[25]陶仁義,楊雨慧.理念·遺教·運動:孫中山“雙手萬能”形成與職業教育發展[C]//第三屆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山: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176-187.
[26]中華職教社昨社員聯歡會[N].申報,1937-03-28(12).
[27]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M].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183.
[28]舒新城.中國新教育概況[M].上海:中華書局,1931:47-48.
[29]毛北平,周麟生.職業教育與吃飯問題[J].安徽省教育行政人員養成所所刊,1931(2):105-107.
[30]楊衛玉.小學勞作教育與職業問題[M]//杭州師范學校推廣教育處編輯.小學勞作教育.杭州:星星書社,1933:5.
[31]無題.益世報(天津版)[N].1934-07-19(9).
[32]潘光旦.政學罪言[M].上海:觀察社,1948:145.
[33]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9卷(1924.1-1924.3)[M].北京:中華書局,2006:123-124.
[34]蔣中正.蔣委員長開幕訓詞[J].教育與職業,1934(159):535-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