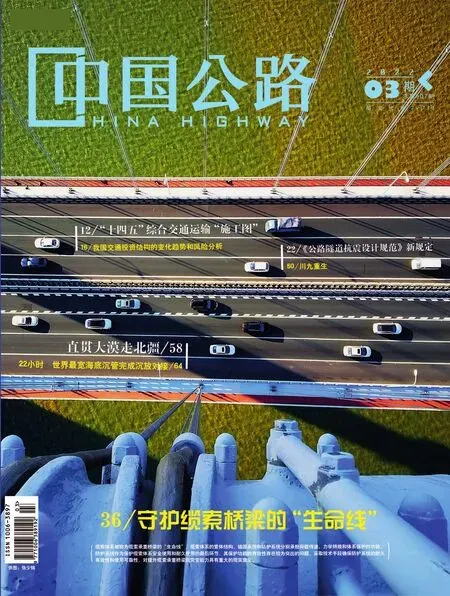高壓旋噴樁加固軟土地基的噴射壓力影響范圍現場試驗與理論分析
何大為 楊建輝 張康榮 張帥 劉夢冉
(1.中電建路橋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2.西南石油大學地球科學與技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500)
高壓旋噴樁施工產生超孔隙水壓力的理論解常用的方法是Vesic法[1][2],廣泛應用的有限元等數值仿真方法也應用于高壓旋噴樁的施工模擬。兩種方法提高了工程師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但是由于涉及較多的假設,結果總不令人滿意。同時,研究者注意到現場試驗是一種較好的揭示高壓旋噴樁施工產生地基土位移和超孔隙水壓力的手段,但因現場試驗花費較高,至今所見有關試驗較少。
本文依托廣東省江門市某舊路拓寬工程的軟土地基加固項目,研究了高壓旋噴樁施工過程中高壓噴射漿液對地基土影響范圍的現場試驗,分析了高壓噴射漿液引起的軟土地基土位移規律與超孔隙水壓力在軟土地基中的傳播規律,確定了高壓噴射漿液對軟土地基的影響范圍。
一、現場試驗
(一)試驗現場土質條件與旋噴樁施工參數
試驗場地選在江門市某舊路拓寬工程zfk52+970~zfk53+040標段。在詳細勘察現場試驗區后發現,現場的土質主要為3層:素填土、淤泥質粉質黏土和粉質黏土,3個土層的物理力學參數如表1所示。該試驗設計的高壓旋噴樁樁長12m,直徑0.5m,穿過素填土層、淤泥質粉質黏土層,且打入粉質黏土層2m,施工參數如表2所示。
(二)監測測點布置及傳感器參數
該試驗的監測位置平面布置圖和每個監測位置處傳感器的布置圖,如圖1和圖2所示。其中S1、S2、S3、S4、S5、S6和S7代表7個監測位置,在每個監測位置沿深度方向放置3個孔隙水壓力傳感器和3個固定測斜傳感器,分別距離地面1.5m、4.5m和7.5m。孔隙水壓力和測斜傳感器主要是監測高壓旋噴樁施工時在素填土層和淤泥質粉質黏土層中引起的超孔隙水壓力和位移的變化。

表1 土體物理力學參數

表2 現場試驗施工參數
現場使用的監測超孔隙水壓力的傳感器是SK-KYJ型振弦式孔隙水壓力傳感器,測量范圍為0.2MPa~0.4MPa。測讀超孔隙水壓力的規則是:注漿前測讀初始孔隙水壓力值,注漿過程中當注漿管每提升4m記錄一次孔隙水壓力值。

圖1 監測傳感器平面布置圖

圖2 監測傳感器剖面布置圖
水平位移監測采用了ZCT-CX300-S230傾角傳感器和GPRS遠程數采系統,每隔1min自動記錄一次測斜儀的傾角數據。
二、試驗結果分析
(一)高壓噴射注漿產生的地基土水平位移變化規律分析
1.高壓噴射注漿過程中地基土的水平位移變化規律
為了揭示高壓噴射注漿情況下地基土的位移特性,在分析S1至S7處傾斜傳感器采集的數據后得出水平位移與時間的關系,如圖3所示,其中未包含施工的高壓旋噴樁與監測位置距離大于8m的S5至S7的監測數據,原因是在S5、S6、S7的監測位置,高壓旋噴樁施工引起的地基土水平位移較小。

圖3 影響范圍內測點土體水平位移監測時程曲線
如圖3所示,在高壓噴射漿液的作用下,所有監測點的位移均表現為初始時地基土的位移,幾乎是線性快速增加,之后位移與時間的關系進入非線性增長階段,最后位移幾乎不隨時間變化,即位移隨時間的變化可以分為快速的增長階段、緩慢的增加階段和最終的平穩階段。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初始快速增長階段,高壓旋噴樁的施工機械開始噴射高壓漿液,且高壓噴射的漿液引起地基土擠壓,這促使地基土產生急劇增加的水平位移;在緩慢增加階段,旋噴漿液的壓力雖保持不變,但地基土在初始階段已被擠壓,且擠壓后的地基土抗壓能力可以平衡部分噴射漿液的壓力,因此目前的噴射壓力只能使水平位移緩慢增加;在平穩階段,地基土抗噴射壓力的能力與噴射壓力基本平衡,因此即使高壓旋噴樁仍在施工,但是位移幾乎保持不變。
如圖3所示,隨著高壓旋噴樁與監測位置之間的距離增加,高壓旋噴樁施工引起的地基土位移隨時間的變化曲線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例如,旋噴樁與S1的距離是1m,與S4的距離是4m,從S1處到S4處,地基土的位移隨時間的變化曲線的圓順性逐漸降低,說明隨著高壓旋噴樁與監測點距離增加,地基土對注漿壓力的耗散能力增強,當兩者之間的距離達到4m時,位移隨時間變化關系曲線的圓順性已減弱。
2.高壓噴射注漿下地基土的最大水平位移衰減規律
在高壓噴射注漿下,地基土的最大水平位移隨旋噴樁與監測點距離的衰減規律是控制高壓旋噴樁影響范圍的重要參數之一。
隨著高壓旋噴樁與測點的水平距離增加,地基土的位移不斷衰減。當高壓旋噴樁與測點的水平距離在1m~6m范圍內,且在同一土體埋深下,其衰減規律可近似用對數衰減曲線描述;當旋噴樁與測點的水平距離在8m~12m范圍內時,深度在1.5m、4.5m和7.5m處的最大水平位移均小于0.5mm。考慮到高壓旋噴樁施工對臨近周邊構筑物的影響,可以認為0.5mm的位移對臨近周邊構筑物的安全性不產生影響,由此可以得到在該類土質和土層條件下,高壓旋噴樁單樁施工的影響范圍約為6m。
3.高壓噴射注漿下地基土的最大水平位移沿埋深的變化規律
高壓旋噴樁施工階段地基土位移沿深度變化的規律是,在高壓旋噴樁施工過程中,地基土產生的最大水平位移隨埋深增加而逐漸減少,且隨旋噴樁與測點水平距離的增加而減小。當旋噴樁與測點的距離在4m~6m之間,地基土的水平位移與埋深的關系近似線性變化,但是當距離在1m~3m之間,地基土的水平位移與埋深近似呈非線性關系。這一結果似乎揭示了當旋噴樁與監測點的距離小于3m時,在高壓噴射漿液的作用下,土體發生了塑性變形,但是在近地面產生的塑性變形大,遠離地面產生的塑性變形小。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遠離地面所受的圍壓較大,因此產生的塑性變形小,反之亦然。
(二)高壓噴射注漿產生的地基土中超孔隙水壓力變化規律分析
1.高壓噴射注漿過程中地基土的超孔隙水壓力變化規律
高壓噴射注漿過程中地基土中超孔隙水壓力的變化,如圖4所示,可知在100min范圍內,超孔隙水壓力出現快速增長階段、增長平緩階段和減小階段。快速增長階段出現在高壓旋噴樁施工的開始階段,這一階段地基土中的靜水壓力較小,而高壓噴射注漿一方面迅速使地基土中的超孔隙水壓力增加,同時地基土的擠壓作用進一步提高了超孔隙水壓力的數值;增長平緩階段位于施工的中期,此時地基土中的超孔隙水壓力已經較高,雖然高壓噴射注漿仍然在持續,但是已存在的超孔隙水壓力平衡了部分噴射壓力,因此超孔隙水壓力的增量變小;減小階段位于施工結束后,此時由于地基中的超孔隙水壓力較高,又由于旋噴樁施工已經結束,所以發生了土體固結與超孔隙水壓力消散;另一方面,旋噴樁施工時是旋噴管自下而上的提升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噴射壓力保持不變,但是隨著注漿管提升到接近地面,需要適當減小噴射壓力,因為接近地面的上覆壓力較小,過大噴射壓力易產生冒漿,其次當注漿管提升到接近地面時,漿液會從孔口流出,這會耗散噴射流攜帶的能量。以上即是超孔隙水壓力的幅值降低的原因。

圖4 單樁時不同深度各個測點超孔隙水壓力隨時間變化

圖5 超孔隙水壓力 隨水平距離變化
2.高壓噴射注漿中地基土的最大和殘余超孔隙水壓力衰減規律
如圖5所示,當旋噴樁施工時,距旋噴樁越近,則產生的超孔隙水壓力越大,該規律與埋深無關,也與一般的理解一致,即超孔隙水壓力隨傳播距離的增加存在明顯的衰減現象。如果認為當最大超孔隙水壓力小于5kPa就可忽略其對周邊土體的影響,在水平距離達到6m時,超孔隙水壓力達到5kPa,即旋噴樁施工引起的超孔隙水壓力的影響范圍是12倍的樁徑。
針對從不同深度測得的超孔隙水壓力,最大超孔隙水壓力值出現在4.5m深度處,而未出現在深度為1.5m和7.5m處,其原因可能是:相對于4.5m和7.5m,1.5m的埋深距地面較近,因此具有較強烈的超孔隙水壓力逸散效應,這造成了1.5m處的最大超孔隙水壓力值較小;在高壓旋噴樁施工時,注漿管隨施工時間的增加而逐漸提升,在這一過程中前期施工產生的超孔隙水壓力會向后期施工點傳遞,這可能是在4.5m埋深處出現最大超孔隙水壓力值的重要原因。
無論最大超孔隙水壓力還是殘余超孔隙水壓力,兩者均幾乎相同地隨水平距離的增加,而超孔隙水壓力減小,但僅比較100min內的變化規律可知,最大超孔隙水壓力比殘余超孔隙水壓力大約40%,說明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較快。
3.地基土中超孔隙水壓力消散過程
旋噴樁施工結束后,相對于施工期間的最大超孔隙水壓力,靜止1天,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率分布于60%~80%之間;靜止2天,消散率稍有增大,集中分布于80%~100%之間。超孔隙水壓力前期與后期的消散速率的差異,主要還在于淤泥質粉質黏土中可能發生的水裂現象,即在透水能力很差的地基土中,高壓噴射的漿液會對土體產生擠壓作用,大的噴射能量會使得土體產生水裂現象,而水裂現象對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有顯著的影響,因為土體中產生的裂縫為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提供了良好的通道,當超孔隙水壓力消散至一定水平后,裂縫逐漸閉合,排水通道再次堵塞,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又將趨于緩慢。
對于上部的素填土,其超孔隙水壓力消散率遠高于淤泥質粉質黏土,在靜止1天后其消散率達到80%以上,靜止2天后消散率基本在90%以上。
三、結語
通過在江門市某舊路拓寬工程中開展的高壓旋噴樁現場試驗,獲得了在高壓噴射漿液作用下地基土的位移、超孔隙水壓力的變化規律,通過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在高壓噴射漿液作用下,地基土的位移分為快速增加階段、緩慢增加階段和平穩階段,但是對于超孔隙水壓力則可分為快速增長階段、緩慢增加階段和減小階段。不論地基土中的位移還是地基土中的超孔隙水壓力均隨旋噴樁與監測點的距離增加而減小。
無論從地基土的位移還是地基土中的超孔隙水壓力變化規律可得到,高壓旋噴樁施工的影響半徑約為6m,也約為12倍的樁徑。與多個超孔隙水壓力理論計算結果比較,發現按照現場試驗確定的高壓旋噴樁施工的影響半徑約為2倍的理論計算方法可得到塑性區半徑,這為確定塑性區半徑提供了一個新方法。
對于該研究場地,若從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情況看,施工結束至少1.5天后,才可忽略高壓旋噴樁施工引起的超孔隙水壓力影響,若要連續施工高壓旋噴樁,則必須要考慮前期施工產生的超孔隙水壓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