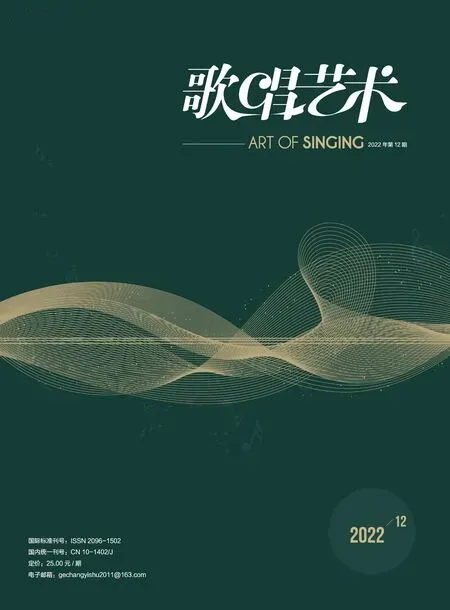喜歌劇
〔美〕查爾斯·羅森著,楊燕迪譯
1778年12月12日,莫扎特在曼海姆寫信給父親,說那里正在制作一種新型的帶音樂的戲劇,并提到制作人邀請自己為這種戲劇作曲:“我一直想寫這種戲劇。我記不起是否告訴過你,我第一次在這兒時有關這類戲劇的事情?那次我看過這種類型的戲上演了兩遍,非常非常喜歡。真的,完全出乎我意料,因為我一直以為這種戲會很沒有效果。當然你知道,其中沒有歌唱,僅僅是念白,而音樂像是在宣敘調中那樣作為某種輔助性的伴奏。有時臺詞是說出來的,而音樂繼續,這效果非常好……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認為大多數歌劇宣敘調就應該像這樣處理——僅僅是偶然唱出來,當歌詞能夠完美地被音樂表現出來時。”①這封信也許不應該僅僅根據字面意義來判斷:莫扎特打算征服巴黎音樂世界的企圖剛剛以慘敗告終,而現在他面臨著最憎恨與最擔憂的事情——回到薩爾茨堡。他的熱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這是否僅僅是一種努力,試圖說服正在薩爾茨堡等得不耐煩的父親,從實際出發,自己最好暫緩回家,眼下可能還有其他希望?但是,莫扎特的態度,他的試驗性探索,還是顯露無遺。他對所謂“音樂話劇”(melodrama,有音樂伴奏的說白)的可能性感到歡欣鼓舞,而他對戲劇效果的感覺絕不僅僅限于聲樂。相反,他對音樂作為戲劇動作的對等物與音樂作為歌詞的完美表現這兩者之間作出了清晰的區分。②更具重要性的是第一個概念,而他會摒棄歌唱而啟用說白,如果這樣做可以讓動作更為有效、生動。
《扎伊德》(Zaide)中運用了一些很有效果的音樂話劇手法,直接指向了《菲岱里奧》,但我們絕不要忘記《后宮誘逃》中佩特里羅(Pedrillo)的小夜曲被突然打斷的片刻,以及奧斯敏(Osmin)歌曲中的說白處理,或者《魔笛》中帕帕蓋諾(Papageno)在準備自殺之前計數到三的片段,否則就會丟失莫扎特曾有一段時間對這種手法非常感興趣而寫下的一切。然而,莫扎特從未喪失進行試驗的渴求,以及他的那種敏感——在歌劇中,音樂作為戲劇動作的重要性應該高于音樂作為表情的手段。這并不是否認莫扎特為人聲寫作的技藝,也不是否認他對于復雜花腔的喜愛。然而,面對那些希望顯擺自己歌喉之美妙的歌手的虛榮心,莫扎特并不總是一再忍讓。尤其在重唱中,如《伊多梅紐》中的偉大四重唱,他堅持歌詞應該更多是說出來而不是唱出來。③莫扎特在曼海姆時對“音樂話劇”手法的短暫興趣顯示了一個年輕作曲家的熱情,此時他剛剛發現,就滿足歌手和表現情感而論,舞臺上的音樂可以做得更多,同樣能夠將情節和復雜曲折卷入其中。但在莫扎特寫作美麗、動聽但較少為人所知的《假園丁》時,他對這一觀念仍是一知半解。
18世紀早期的風格已經能夠對付歌詞文本自身所能提出的任何要求。亨德爾與拉莫的歌劇音樂能夠轉化任何片刻的情感和情境,但是這種音樂卻未觸及動作和運動——簡言之,即任何非靜態的東西。奏鳴曲風格為表達最具動態的舞臺音樂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框架,這種說法僅僅是因為沒有考慮在奏鳴曲風格發展中歌劇風格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顯得過分簡單。意大利喜歌劇(opera buffa)尤其具有影響力,而古典風格在描繪喜劇情境和喜劇姿態時運作得最為得心應手。
這種風格之所以特別適合表現戲劇動作,是因為下列三點:第一,對樂句和形式作清晰表述,因而賦予一部作品以一系列明晰而有別的事件發生的品格;第二,主和屬之間更強烈的對極化,這使得在每部作品的中心有更為清晰的張力提升(以及相關聯的和聲區域有更明確的性格,這也可被用來表達戲劇性的意義);第三,但絕非最次要的是,節奏轉換的運用,它允許織體隨著舞臺上的動作進行發生改變,但又不會在任何意義上破壞純音樂的統一性。所有這些風格特征都屬于該時期的“無名氏”風格;它們是1775年那個時段音樂的“通用貨幣”。然而毫無疑問的是,莫扎特是第一個以系統化的方式真正理解這些風格特征對于歌劇的重要意義的作曲家。從某種角度看,格魯克是一個比莫扎特更具原創性的作曲家,他的風格塑造更多來自一種對自己時代傳統的倔強拒絕,而不是坦然接受。但是也正是這種原創性,妨礙了格魯克企及莫扎特在處理音樂與戲劇關系上所達到的自如和流暢。
注 釋
①引自《莫扎特與其家人書信》(Letters of Moxart and his Family,London, 1966),艾米麗·安德森(Emily Anderson)編訂。
②在1780年11月8日的信中,莫扎特反對在詠嘆調中用旁白的想法:“在對話中,所有這些都很自然,因為旁白的幾個詞可以說得很快;但在詠嘆調中,歌詞必須重復,旁白就會效果很差,即便情況并非如此我也偏好一個不被打斷的詠嘆調,參見《莫扎特與其家人書信》,第659頁。
③1780年12月27日的信,參見《莫扎特與其家人書信》,第6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