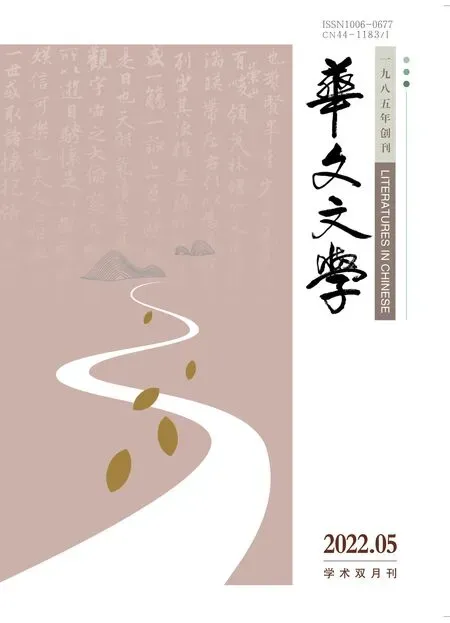論澳大利亞華文詩歌中的地理空間建構
楊紫晗
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研究海外華文詩歌非常適宜,這是由海外華文作家自身獨特的經歷所決定的。以新世紀澳大利亞華文詩歌(以下簡稱“澳華詩歌”)創作為例,大部分的澳華詩人都擁有著“原鄉”和“異鄉”兩段人生經歷,如果只是單純分析文本而忽視不同地理空間對詩人創作的影響,這樣的研究無法探究出澳華詩人創作的復雜性。而從文學地理學的視角出發,便可分辨出澳華詩歌中暗含的兩個創作空間,即籍貫地理空間和活動地理空間。首先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中,澳華詩人的地理感知也有所不同。尤其是新世紀之后的澳華詩歌創作大多屬于“新華人文學”的范疇,這類澳華詩人的身份由留學生轉為國際移民,相較于新世紀之前的詩人而言,他們擁有更為集中的學術性和想象性以及更為復雜的身份認同危機,為澳華詩歌創作帶來更加豐富的“象征資源”。其次,不同地理空間都擁有著各自獨特的文學氣質,海外華文詩人置身于不同的文化境遇之中,在其影響下所形成的創作氣場也不盡相同。“具體詩歌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詩歌版圖的變化,而整體詩歌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詩歌場景的變化方向與節律。”①北美、東南亞、澳洲等國家的華文詩歌組成了多聲部的大合唱,不同地區的詩歌各有特色。不同于充滿著海風椰語的、具有熱帶意味以及南洋色彩的東南亞華文詩歌,也不同于充滿現代色彩的北美華文詩歌,澳華詩歌中包含著獨屬于澳大利亞的自然以及人文地理景觀。而且在澳大利亞20世紀八九十年代持續了8-10年的爭取居留運動的影響之下,澳華詩歌相較于其他地區的華文詩歌而言,其身份焦慮的表達更為突出。因此,面對風格迥異的華文詩歌,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可以探究出海外華文詩歌創作在地理空間上所蘊含的整體性特點,從而進行整體性研究。此外,“19世紀以后的空間圖示:它的核心在于,基地只有在同別的基地發生關系的過程中才能恰當地定位。一個基地只有參照另一個基地才能獲得自身的意義”②。鑒于這一理論,在文學地理版圖上對澳華詩歌進行定位,建立起地理坐標系,可以與中國大陸詩歌形成參照。澳華詩歌中對異域文化的吸收豐富了中國大陸詩歌的創作形式,也為中國大陸詩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標準與參照體系。
一、地理基因:籍貫地理空間的書寫
所謂“地理基因”,鄒建軍教授總結為:“是指地理環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痕,并且一定會呈現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③澳華詩人們經歷了“原鄉”與“異鄉”的雙重地理空間。由于在“原鄉”地理空間中所形成的地理基因以及文化傳統在短期內很難改變,因此在“原鄉”中所定型的價值觀使澳華詩人在作品中流露出鮮明的“中國性”。這種“中國性”在作品中主要體現在詩人對籍貫地理空間的建構,這是從文學地理學視角研究詩歌才可分析出的特色。由于“漢語新文學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現不同的社會環境和人生經驗,但用以審美地處理這樣的環境與經驗,并對之作出價值判斷的理念依據甚至倫理依據,卻是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緊密相連并在現代漢語中凝結成型的新文化習俗和相應的創造性思維。盡管異域文化和文學對新文化和新文學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可現代漢語及相應的現代漢語思維通過文學創作已經對之進行了無可否認的創造性轉化,能夠作為特定的精神遺產積淀下來的一定是為現代漢語所經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達的產品”④,所以,澳華詩人們不論用哪種語言進行創作,受到異域文化怎樣的沖擊,其作品中仍然會體現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沉淀的中國經驗。這種中國經驗是“由集體無意識而繼承的那些屬于本民族的民族記憶、審美趣味等,同時又包括作為華人身份的創作主體在現實文化生活中不斷生成的經驗,這種經驗雖然是新興的,但因為創作主體的中國人的種族屬性,盡管新生代華裔的服裝可以改變、飲食習慣可以改變、語言可以改變,但膚色、種族是不能改變的,依然多少會帶有中國色彩”⑤。因此,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之下,澳華詩歌作品中對于籍貫地理空間的書寫,是詩人深藏于血脈之中中國性的自然流露。
由于創作主體的籍貫是主體自身地理空間的起點,同時也是創作主體最初文學氣質養成的發源地,因此它對創作者的影響十分深遠。盡管詩人的地理位移使澳大利亞代替中國成為詩歌地理上的現實世界,但是精神返鄉的書寫在澳華詩人的作品中常常可見。以旅澳詩人莊偉杰為例來進行分析,其詩歌中的籍貫地理空間是通過自然地理景觀所建構起來的。“走出國門闖蕩外面世界/是從故鄉出發的//走出故鄉開始遠行/是從鄉間小路出發的//走出鄉間小路進入都市/是從一座石頭樓房出發的//走出一座石頭樓房四處流浪/是從某個春天出發的//走出某個春天漂泊歲月/是從那年那月那日出發的//走出那年那月那日學會獨立/是從母親眼眸出發的//走出母親眼眸感受生活/是從千叮嚀萬囑咐出發的。”⑥這首《走出》是《莊偉杰短詩選》開篇第一首詩歌,全詩敘述了一個離開的故事。詩歌巧妙地運用鏡頭,使詩歌中的視線由遠及近,由大到小,穿過鄉間小路、都市、石頭樓房最后落入母親的眼眸之中。詩人從母親眼眸中走出,其對故鄉的記憶也落回到母親的眼眸之上。詩歌開頭第一句立馬就將讀者拉入到詩人故鄉的空間之中,讀者和詩人一同從故鄉出發,思緒一同飄過了故鄉中的鄉間小路、都市、石頭樓房,與母親的眼眸相交匯。詩人的故鄉空間就在鄉間小路、石頭樓房中建構了起來,詩歌強烈的代入感使讀者也進入到詩人的故鄉空間之中,詩句的鋪陳始終與故鄉的地理景觀保持著平衡。此外,還有李普的《秋》、陳積的《回鄉掃墓》、張典姊的《夢回綠溪》、等等的《大王洞的存在》……,他們在詩歌中或表現故國家鄉中的田園色彩,或表現回家鄉掃墓時的荒蕪景象,或表現故鄉青山中的一個古洞,詩歌中故鄉的自然地理景觀十分豐富。可以說,地理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深刻體現在對詩歌整體精神面貌的生成和詩歌氛圍的營造上。
隨著詩人空間的遷移,對于原鄉的記憶隨之產生,鄉情鄉思成為其詩歌的主題。詩人在離開故鄉后,對故鄉的思念與回憶也如潮水般涌來。“想起家以及那個海邊村莊/心底有一股暖意像燈光/每一盞有每一盞的瑰麗/每一線有每一線的繽紛/但笑看另一個世界的悲歡離合/想起的是老祖母曾編織的童話//想起地瓜藤和青石板鋪成的路/黃昏中飄動的花頭巾/無意間觸動故土的血脈/涌起好多好多的嘆息/留下太深太深的思念/想起的是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⑦在這首《想起》中,建構空間的意象更加豐富。這首詩歌中滿載著回憶,詩人僅憑家、海邊的村莊、地瓜藤和青石板路以及飄動的花頭巾等意象,就在詩歌中搭建起一個獨屬于故鄉的地理空間,這類地理景觀的出現也使詩歌極具畫面感。這是現實存在和故鄉世界給予詩人的創作養分,同時也是詩人的精神對應物。這些意象都是生活中最為普通甚至被忽視的景色,但卻是詩人心中難以忘懷的記憶。故鄉的模樣在這些意象中更為明晰,它們共同編織起獨屬于詩人莊偉杰的故鄉空間,同時也喚起海外華文人們共同的鄉愁。
在籍貫地理空間的建構中,除了以上常見的自然地理景觀外,澳華詩歌中還存在著一些人文景觀的書寫。漢字、茶、唐詩、宋詞等也是莊偉杰詩歌中的意象,如在《方塊字的祖國》中詩人寫道:“寫祖國的詩篇/牛毛般多得不勝枚舉/就像祖國身上四通八達的大路小路/你算不過來/更像現代化大都市/密集的樓房/你無從盤點//我多想寫一首詩獻給祖國啊(寫了多年的詩卻未敢輕易下筆)/但我找不到一條通往靈魂出口的線路/也找不到一處可以讓自己詩意安居的住所//想想還是不寫的好,以免貽笑大方……搜索枯腸想來思去輾轉反復/我提醒自己不要如此這般自我折騰/其實祖國就流淌在我們沸騰延續的血脈里/就在我們的五官感覺里在潛意識在夢境里/那是我們天天看著讀著摸著聽著書寫著的方塊字//無論是一點一畫還是一波一磔/所有的線條都靈動構成為祖國的形象/哦祖國屬于我的方塊字的祖國。”⑧濃烈的鄉愁化為一個個漢字,成為海外華人們永遠的陪伴。漢字的一橫一豎靈動地構成了祖國的形象,也搭建起詩人心中祖國的空間。再如西彤的《故鄉十行》中,將鄉愁具象化為童年的歌謠、母親的搖籃曲、讀不夠的家書、永不褪色的底片等,這些都是詩人感情的直接投射。西彤從容地敘述中蘊含著對事物深切的體悟,將復雜的人生經驗投射到對日常事務的觀照中,極為細膩地摹寫體現了詩人超強的表現力。方浪舟的《童年》也是如此,在短短20余字的詩句中,媽媽手中的“甜餅”是全詩中最為突出的意象,也是詩人思國戀鄉之情的最好寄托。澳華詩人通過自然空間和人文空間的書寫共同復原記憶中的籍貫地理空間,讓讀者從景到情感受到澳華詩人濃烈的鄉愁。
綜上分析,澳華詩歌中的籍貫地理空間是在故鄉中的鄉村小路、高山大海等自然地理景觀,以及中國人所割舍不掉的傳統文化如漢字、唐詩、茶等人文景觀的書寫中共同建構起來。盡管地理位置發生了變化,但是地理基因已經深埋于詩人的血脈之中,澳華詩人“精神返鄉”的書寫從未停止。詩人們將陌生的異鄉地理空間隔離在內心空間之外,再將原鄉的地理空間經過內在轉化與提煉,升華為詩歌地理坐標上的“精神家園”。
二、地理感知:活動地理空間的呈現
所謂地理感知,“它是文學創作者對天地萬物的心理化感應以及對人地關系的觀念性感知,是一切自然現象和以地方為生存基礎的人類活動在作家和詩人感官系統上的客觀投射與審美觀照。在微觀維度上,地理感知以即時或間接的方式,與創作主體的社會閱歷、家族環境、修養性情以及地理空間中復雜的權力關系一起,共同作用于作家的文學創作”⑨。由此,作家長期所感知到的地理空間在某種程度上會對文學創作產生影響。澳華詩人長期居于海外,與母體文化相隔絕,隨著時間的推移,澳大利亞的地理風貌、風土人情必將進入到詩人的創作中。何況不同的地理空間會培養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氣質,區域外的詩人們進入其中很難不受到區域文化的影響。例如莊偉杰是福建泉州人,歐陽昱是湖北黃州人,冰夫是南京江寧人,西彤是廣西恭城人,他們先后離開中國,短期或長期居住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文化與中華文化相碰撞,產生一種別樣的文化交流。“文學現代性的流動是通過旅行實現的。所謂‘旅行’指的不僅是時空中主體的移動遷徙,也是概念、情感和技術的傳遞嬗變。”⑩在澳華詩歌中,這種具有流動性的文化交流通過詩人對活動地理空間的建構而呈現出來。
澳華詩人冰夫在定居悉尼之后,悉尼的自然風光就時常出現在他的詩歌中,悉尼的大海、教堂、夏夜、鴿群、街頭等都是他詩歌創作的題材。之所以冰夫的詩歌可以姿態鮮明地屹立于澳華詩歌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創作與澳洲自然地理景觀的深度遇合。“夏天的悉尼/海之旋律變奏鮮明/波濤的行程紛繁/崖岸卻渴求寧靜//浪花在沙灘飄灑長發/鳴鳥挑戰泳者/歌劇院的珠蚌吐出光彩/曳亮了海上熠熠銀河//姍姍來遲的月夜/我仰臥海波微動的水面/帶著隨意的天真/編織異國浪漫的夢境//岸邊的橡樹林里/涌現一張朦朧的笑臉/領我追隨南澳燥熱的風/漫游神奇的愛麗思泉/我知道夏天最后的/玫瑰跟現實夢幻無關//沙漠里無數飄忽的螢火/圍繞我的靈魂爭論不休/恍惚中突然雷聲大作/一絲絲的雨水飄落/于是在腥咸的淚雨里/我漸漸地蘇醒。”(《悉尼夏夜奏鳴曲》)[11]炎熱的夏季,大海的波濤聲、鳴鳥聲、雨聲等共同為詩人演奏一首奏鳴曲,詩人沉醉于其中是聽覺與視覺的雙重享受。豐富的地理景觀使詩歌具有極強的畫面感,讀者似乎也與詩人一同置身悉尼的夏夜中,大海、歌劇院、愛麗思泉、橡樹林就在眼前,南澳燥熱的風正從臉頰拂過。冰夫具有極為敏銳的地理感知能力,能夠迅速捕捉到悉尼大自然的色彩、聲音、線條等要素,從而獲得了愉悅的情感體驗,尋找出別樣的創作題材。地理環境的轉變拓寬了澳華詩歌的表現范圍,增加了詩歌創作的詞匯量,并順利地在詩中建構起獨具特色的澳洲地理空間。
這一類創作在冰夫詩歌中還有許多,再如《短笛吹靜了黃昏》:“波特尼海濱/黃昏巖石上/坐著一個吹笛人//沙灘上堆滿了音符/浪花在傾訴旅程/破譯人生的密碼/一支短笛吹靜了黃昏//大海漲潮了//看不見凋謝的虛線/晚霞盛開了/頻頻回顧含波的側影//遠離笛聲吧/狂妄的人/驕矜的人。”[12]澳大利亞四面環海,詩人似乎也格外偏愛海,大海、浪花、沙灘等構成冰夫筆下常見的意象群。除了對景色的感知外,詩人對于時間也十分敏感。詩中寫出波特尼海濱從黃昏到晚霞出現,大海開始漲潮,海岸線也逐漸模糊,展現了詩人地理感知的敏銳和準確。冰夫以蒼涼的手筆,從內容到形式都展現出海的廣闊和笛聲的清越婉轉。在處理詩藝表達時,詩人充分考慮到自然回聲的雄渾和笛聲的悠揚會給詩歌帶來怎樣的混響,從而營造出立體環繞的音樂美感。除卻冰夫的詩歌,還有陳積在《狼煙》中所描寫的悉尼喬治河畔,如冰在《澳洲大漠》中所描繪的浩瀚蒼茫的大漠,心水在《悉尼誼園》中所展示的中國式的公園等等,澳洲別樣的地理景象時常出現在澳華詩人筆下。可見,澳大利亞獨特的自然地理景觀幾乎貫穿在所有澳華詩人的創作中。
除了對自然景色的展現之外,澳華詩人在呈現活動地理空間時也存在著對人文景色的書寫。自海外華文文學書寫萌芽至今,唐人街始終就是活躍在華文文學作品中的一個空間標識。它作為海外華人們初到異域的一個過渡性場所,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創作者不同時期的空間感知。這種空間感知既是華人空間變換后的懷鄉,也是與他者文化的疏離與抵抗。如莊偉杰的《唐人街寫意》:“是一角月光守護著唐朝的夢/讓孤旅者濺濕那雙黑眼睛//繞著街心徘徊了一圈又一圈/仿佛走過了一季季春夏秋冬//他鄉的路鋪成回家的路/異域的語言變成自己的母語//方塊字的魂魄在這里櫛風沐雨/凝固的歲月在追夢中發芽//把往事和記憶煉成活化石/久違的鄉音絲綢般裊繞耳際。”[13]詩人筆下有鄉音和漢字的唐人街對于華人們來說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它是海外華人在異鄉最具安全感的空間。
除對唐人街的書寫之外,異鄉的人群和街頭文化也是詩人們創作的題材之一。“黎明或暮色/沿著斑馬線微笑/寧靜的面孔/奔馳的車流/和平安詳的樂章/停頓抑或演奏//褐色玻璃墻下/鴿子在啄食面包/白云在晴空遨游/鄰近的海灣浪在喧鬧//長發的男人/短發的女人/同樣展示性感的肌膚/或黑得幽光/或白得發亮//旅游者與流浪漢/不同的步履/相同的行囊/太陽離開了地平線/影子里飄著惆悵。”[14]冰夫的《悉尼街頭一瞥》就展現了異域街頭舒適祥和的氛圍,街頭的喧嘩在冰夫筆下變成安詳的樂章,啄食的鴿子、天空中的白云以及街上各色的人群等都囊括進詩人的筆下,讓人驚嘆于詩人敏銳的感知能力。舒適安逸的慢時光以及有別于國內街頭的街景讓讀者心馳神往,一個異域街頭的人文空間就在讀者心中搭建起來。但在詩歌的結尾,“影子里飄著惆悵”似乎暴露了詩人內心并不美妙的心情。這股惆悵似乎并不來源于對故鄉的思念,詩人籍貫地理空間和活動地理空間的巨大差異,使得他的精神處于一種“流浪”的狀態,這一份無法安放的歸屬感反而可能是他惆悵的原因。詩人們擅長從澳大利亞的地理空間中提取普通事物,對此進行瞬間性地捕捉,將澳大利亞的日常生活經驗復制在詩歌的字里行間,體現濃厚的地理色彩。詩歌題材的拓寬也使得更多現實的主題能夠進入詩歌表現領域,其中既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的雞毛蒜皮,也有對具體空間的理性分析。一方面,地理位移使得詩歌創作題材更加豐富;另一方面,地理環境的變化也使得詩歌詞匯量在不斷擴充,這是地理環境所給予文學的創作養分。
總而言之,從地理感知的視角考察澳華詩歌,不難發現,澳華詩歌中的活動地理空間是層層疊加相互環繞的。其中,既有澳大利亞自然地理景觀的直接顯現,又有融合詩人日常生活經驗的人文景觀的溫情書寫。此外,在地理位移中所涉及的身份認同問題也值得深入探究。
三、不同地理空間交錯背后的身份認同危機
在澳華詩歌中,活動地理空間和籍貫地理空間并未全割裂,兩個地理空間互為參照,交錯出現在詩人創作之中。澳華詩歌中所體現的這兩種空間意識,反映了詩人徘徊于兩種地理、文化空間之中。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認為,社會關系的存在方式是以空間為基礎的,忽略空間的作用那么社會關系只能是“純”的抽象領域。詩人的社會關系、身份認同與空間的生成有著深刻的聯系,兩種空間相互作用分裂了主體自我的身份認同。而身份認同問題一直海外華文文學創作中的中心主題之一,澳華詩歌也不例外。對于澳華文學而言,他們具有多重邊緣性。一方面,他們遠離祖國和母體文化中心,是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的雙重邊緣;另一方面,他們在澳大利亞并未被主流社會所接納,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在文化空間上同樣位于邊緣。他們就如同遷徙的候鳥,努力在確認自己的身份,但在澳大利亞他們被邊緣化,同祖國也切斷了聯系。澳華詩人身處于中西文化交匯的邊緣時空中,再加上爭取居留運動的長期影響,導致他們的身份認同危機相較于其他海外華文詩人而言格外突出,這種危機意識在詩歌創作中體現出來。
身份認同問題是歐陽昱詩歌中反復出現的創作主題。早在20世紀末,在《永居異鄉》中,詩人寫道“我和我的故園/常在電視上見面//而我未來的家園/是漂浮在空中的城堡”[15]故園是詩人回不去的地方,而現在的家園也只是漂浮在空中的“城堡”,這種籍貫地理空間和活動地理空間的錯位使詩人永遠處于異鄉人的位置。在《雙性人》中詩人更為直白地寫道:“我的姓名/是兩種文化的結晶/我姓中國/我叫澳大利亞/我把它直譯成英文/我就姓澳大利亞/我就叫中國/我不知道祖國是什么意思/我擁有兩個國家/或者/我一個都不擁有/我的祖國是我的過去/我的祖國是我的現在/我過去的祖國是我的過去/我現在的祖國是我的現在/我去中國時/我會說我回國/我去澳大利亞時/我會說我回國/我走到哪兒我這顆心/都有兩種顏色……我已經沒有了家園/我已經建立了家園/時間再過兩百年/我就是雙性人的祖先。”[16]詩歌中運用直白的語言以及克制冷峻的敘述,表達了詩人對于自我身份的困惑。詩人將自己定位為“雙性人”,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澳大利亞華裔在身份認同上痛苦的精神狀態。詩人在中國和澳大利亞這兩個地理空間、文化空間中撕扯,對于自我身份的困惑在這首詩歌中展現的淋漓盡致。這里的“雙性人”和《墨爾本上空的月亮》中的“月亮”是同一種屬性的意象,失去文化身份的月亮在詩人眼中是“雜種月亮”。“歐陽昱的文化自覺(或者說迷惑)比起那些根本不懂英語或稍微能夠寫一點英語、得到一點英語世界真真假假的稱許就自以為可以‘去中國’而融入‘世界’的作家,要真誠得多,也深刻得多。”[17]
在歐陽昱創辦的雜志《原鄉》中,談到對于澳大利亞華裔的身份問題時他曾說:“他們很難定性,他們既非中國人,亦非澳大利亞人,他們是一種真空人,一種夾縫人,一種哪兒都不屬于的人,一種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種澳中兩國都可以收歸國有又可以棄之如敝屣的人,一種類似奸細的人,一種沒有歸屬感的人、被歷史掛起來的人,一種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感覺,難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種罵別人是種族主義者,自己也是種族主義者的人,一種連自己同種同族的人都無法容忍的人。”[18]基于對澳大利亞華裔身份問題的深刻認知,籍貫地理空間和活動地理空間經常交錯出現在歐陽昱的詩歌之中。進入新世紀后,歐陽昱強硬的詩風似乎趨向柔和。例如在《老家》中寫道:“老家的人/已經很久不來信/老家的朋友不多——//老家每年照樣在出詩集/詩集里照樣沒有你的名字//老家在哪兒呀——//老家現在該是秋天了/因為這兒像櫻花的花正在開放……在網上一查就可以查到他們/他們的臉看上去比月亮更陌生//老家是什么地方?——”[19],雖然詩中少了對身份認同問題的直白書寫,但還是傳達出詩人處于文化邊緣的游離狀態以及深刻的孤獨感。詩人的詩歌無法進入到老家的詩集中,代表著詩人還是被排除在母體文化中心之外。“老家的秋天”和“這兒像櫻花的花”形成了兩個對立的空間,這樣的對立和碰撞將詩人嵌入兩種文化的夾縫之中。隨著時間的流逝,“老家”這個籍貫地理空間逐漸模糊陌生,而作為活動地理空間的澳大利亞并未給予詩人足夠的文化歸屬感,所以“老家是什么地方?——”詩人的疑問是澳華文學中對于身份認同問題的共同疑惑。除卻歐陽昱,雪陽則將華裔們比作一群螢火蟲,在《河流上的螢火蟲》中詩人寫道:“我們一群沒有籍貫的螢火蟲/飛行在悲劇的河流上/水上逃命的我們/水上閃爍的靈魂/隔著河水游動/身體與靈魂的距離/一半是水一半是空虛。”[20]飛行在河流上的螢火蟲是沒有籍貫的,就如同徘徊在原鄉與異鄉之間的澳大利亞華裔,身體與靈魂之間隔著無盡的空虛。詩人的靈魂中都貫穿著地域的影子,在詩歌中努力確認著自己的身份表征。這種地理空間的交錯還出現在方浪舟的《星光》中,處在澳洲星空之下,詩人發現自己“很難辨認家園”,異鄉常見的星空在此時釘破了詩人的內心,徘徊在“家園”與“星空”兩個空間中,詩人無法找到自己靈魂與身份的安放之地。璇子《缺席的詩人》更是將空間交錯下所產生的身份焦慮暴露無遺,“風再也找不到他的原名/來自故鄉的風/經不住大海的寬容/默默地推進海水/在這里缺席,在那里/成為多余的風景”[21],“故鄉的風”和澳洲的“大海”所代表的是籍貫地理和活動地理兩種空間,詩人不論身處哪個空間都只是“多余的風景”。詩歌中兩種地理空間的交錯轉換,交織成為糾纏不清的身份沖突。所謂“缺席的詩人”,代表的是一種文化上、身份上的雙重失位或錯位,這種進退失據的“錯置感”是詩人產生身份認同危機的根源。
綜上所述,澳華詩歌中籍貫地理空間和活動地理空間相互交錯所體現出的“兩棲”意識,深刻表明了澳華詩人徘徊于兩種異質文化空間之中無法得到認同,進而產生了身份認同上的焦慮。由此,詩人們為了確認自己的身份,往往通過建構敘事文本來擺脫“文化失語”狀態,詩歌中不同地理空間的交錯出現就是詩人表達身份焦慮的重要形式。
盡管本文無法全面的展現澳華詩歌的整體面貌,但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詩歌文本結合文學地理學進行分析,探究出澳華詩歌中對于籍貫地理空間和活動地理空間的書寫。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澳華詩歌創作現場的時空場景,同時也揭示了詩人意識深處對于身份認同的焦慮。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說:“而當今的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同時性的時代中,處在一個并置的年代,這是遠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羅散布的年代。我確信,我們處在這么一刻,其中由時間發展出來的世界經驗,遠少于聯系著不同點與點之間的混亂網絡所形成的世界經驗。”[22]在福柯看來,我們生活在空間的時代,人類生活中的地理空間感知甚至要比時間感知更為重要。而澳華詩歌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就是從文學空間的廣闊視角出發,分析具體的詩歌文本。它不止簡單地停留在對“懷鄉”主題的探究,而是通過對“地理”層次動態的分析闡釋,探究出“地理”對于詩歌價值的內化作用,由此開闊澳華詩歌的研究視域。
①梁笑梅:《臺港澳及海外華文詩歌的地理學關系思考》,《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
②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頁。
③鄒建軍:《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理論術語》,《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④朱壽桐編:《漢語新文學通史》上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⑤沈玲:《中國經驗:海外華文詩歌的文化表征》,《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⑥⑦[13]傅天虹編:《莊偉杰短詩選》,香港銀河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第12頁,第26頁。
⑧引自莊偉杰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4cc03db50100cek8.html。
⑨王金黃:《地理感知、文學創作與地方文學》,《當代文壇》2018第5期。
⑩王德威、王曉偉:《“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11][12][14]冰夫:《冰夫文集詩歌》卷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42頁,第63頁,第59頁。
[15][19]歐陽昱:《永居異鄉》,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9頁,第40頁。
[16]歐陽昱:《墨爾本之夏》,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
[17]郜元寶:《身份轉換與概念變遷——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漫議》,《南方文壇》2018年第2期。
[18]楊邪,歐陽昱:《詩就是自己的一條河:歐陽昱與楊邪對談錄》,《華文文學》2012年第2期。
[20][21]熊國華選編:《海外華文文學讀本詩歌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頁,第279頁。
[22][法]米歇爾·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陳志梧譯,包亞明主編:《后現代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