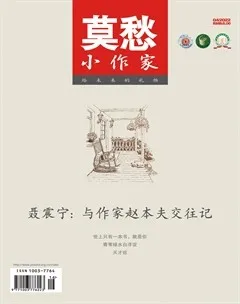天才癥
1
2017年,我32歲,第一次登上大學的講臺。我接手的是同事教了半年的班,同事為了幫我,把她帶的兩個班臨時分給我一個。后來幾年她一直都很幫我,直到現(xiàn)在。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我知道很多事她會幫我,就是憑著一種人之良善的信任。
她和我一樣,在日常生活里,我們并不是太能適應社會生活的人,我們每天活在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不愿意為太多人際與人事瑣事陷入雞毛蒜皮的解釋或爭斗里。輕度社恐為我們贏來了一定的輕松環(huán)境,人際關系簡單,每日躲在書里做書蟲就好,再就是養(yǎng)花養(yǎng)草。她比我多一些樂趣,喜歡看電影和唱歌;我更多時候靠看書或冥想消遣時光。對于世界,我們一致的方式就是不作太多解釋,不聯(lián)系太多的人或事。
我教的是寫作課,我可以把一切要對世界抒發(fā)的內(nèi)容通過字詞組成的句子勾勒出來,甚至,對我而言,標點符號也別有意味。我會以我理解的方式告訴學生我想告訴的。比如會和他們說這樣的話:逗號是纏綿悱惻,是期待與渴望,是建立關系而非斷絕關系,逗號是段而不是篇。句號不同于逗號,句號是要終結(jié)的。如果一首詩不用文字來表達,我其實愿意書寫一個句號。句號是詩。句號有一定的斬釘截鐵。我喜歡句號的徹底,喜歡它的不拖泥帶水。如果標點符號有顏色,句號應該是白色,它很清潔,但也如白云一片,無法鎖住,會遠去。我喜歡的標點符號還有省略號,就如情感世界,我習慣別人對我的省略或我對別人的省略。省略不是空白,只是已經(jīng)沒有必要再繼續(xù)展示。問號是可愛的,世界像個巨大的問號,但一個人應該學會自己給出答案,而不是經(jīng)常提問,畢竟有太多的事不能以標準答案來回答,因為標準答案也是可疑的。嘆號是我反感的標點符號,除了小孩子叫“媽媽”時的顫抖,我覺得很多事不值得為之一嘆。對我來說,嘆號會讓心臟無法承受,而且容易覺得嘈雜。我不喜歡嘆號,可學生還太年輕,容易發(fā)出感嘆,而且有時還三個嘆號疊加。太多年輕的心靈,不知道對世界要克制,受到傷害是必然的,世界會阻止他們不斷哀嘆。分號與破折號都很用力,后者往往在竭力解釋一些東西,前者在努力列出一些平行的事物。這兩個標點符號不是常態(tài),除了需要,不必說太多。我喜歡的還有括號,括號開括號閉,就像一個人降臨這個世界然后又蓋棺定論。括號也是可愛的,它可以溢出太多,讓一篇文章有另一篇還未產(chǎn)生或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投影。
至于其他的標點符號,不必解釋太多,比如冒號和引號,這些都太過嘈雜了。我喜歡分析,而不是對話。
上課使我快樂,因為我在課堂上與學生面對面,可以不用冒號和引號就能完成工作。上課賜予我一種合法且榮譽的滿足感,覺得自己被客觀世界的生活需要,而且還可以賺到面包。當我覺得人生非常泡沫的時候,我就喜歡不斷工作,賺錢,然后拿給家人。并不是賺錢多么有意義,而是錢至少說明那些時光確實就這樣度過了,而不是真的泡沫凍結(jié)了。
我在學生時代就發(fā)現(xiàn)了,當我模擬老師在黑板上講老師們需要的內(nèi)容時,他們是期待的。也就是說,我所講的內(nèi)容為人期待。那之后,包括現(xiàn)在,我這個拙于言辭的人,走上講臺,就會忽然成為另一個為我所不認識的人。幾乎不需要備課,有時只是一個句子,有時甚至一個詞或字,一個符號,一節(jié)課就可以既展開又結(jié)束;甚至墻上的一個斑點,都可以引領著我完成一節(jié)課;有時會是窗外破舊小區(qū)人家屋頂上的一只貓……我不無驕傲地發(fā)現(xiàn),我可以引起觀眾的興趣,而且就像帶著他們穿越隧道一樣,我們一起舉著火把,迷路在交叉小徑,等鈴聲響起我們趕回聚集地,已經(jīng)忘記我們?yōu)楹纬霭l(fā)了。
對我來說,教書就像進入自己的想象世界,比如一幅一幅勾畫出我所感受到的一根線繩的跳動,所感受到的秦嶺山壑在額頭上的片刻打盹,還有城市的樹在夜晚集體撤回山里,一片葉子里居然住著某物的前世今生……原本這些一個人耽溺的幻想,卻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課堂,成為集體癡迷的白日夢。只有在課堂上,我才感覺到自己也可以是個迷人的人。也只有在課堂上,面對更為年輕的生命,我不敢太過耽溺自己沉入灰色世界的底部,不再游動。
2
在我所有的學生里,就那一年,我第一次在大學教書的那一年,讓我感覺她能看出我如何表演課堂的皮影戲,看出我是如何牽動屏幕背后的繩索來持續(xù)進行一場不到點就不能結(jié)束的運動。就那個學生,我第一年帶課班上遇到的那一個,讓我覺得也許我只是因為工作需要沉浸于一些事,也或者因為生命需要,而并不是靈魂需要,我才專心致志看起來心無旁騖地做一些事,而不是背離,逃遁。或者積極生活客觀也是一種逃避,為了避免自己放任自己游入烏托邦。
她長得很有特色,那茅草一般的黃頭發(fā)不像是故意染的,眼神極其明亮。穿著隨意,很少化妝,至多就是頭上扎朵花。這是不同于大多其他女生的,因為師范類的女生一般都妝容精致。她不像其他學生努力引起老師的注意,或者有時故意挑釁老師。她是那種竭力讓老師不去感受她存在的人,但就是能感覺到她的存在。因為她對世界的那種漠不關心。那種漠不關心并不是偶爾一些學生所表現(xiàn)的那種冷漠的漠不關心,和那種帶有挑釁的漠不關心也不同,而是那種明白一切的漠不關心。她進行得那么徹底,那么無所謂。
大多時候她是不在狀態(tài)的,隨時都在走神。我不干涉她的走神,她也不需要努力來配合我不讓我看出她在走神,但我們?nèi)匀辉谀涣鳌N艺f的交流是偶爾的那種目光相會,里面充滿相互尊重。
她的存在對我的教學是一種挑戰(zhàn)。我知道,她對我的課并不感興趣,但是我說的一些題外話,她在思考。教學是需要兼顧大多數(shù)的,深入淺出,如果無法深入,那么就淺淺地端出世界,但一個熱愛寫作的人,會去走他想走的危險小徑。課堂需要有序,需要維護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需要導向相對正面的健康的積極的方向去,而寫作,有時候是失序和混亂才能出好作品。
她常常坐在角落里。在句與句之間,在那些停頓處,我總能聽到若有若無的嘆息。其實并沒有嘆息聲,但是我確實為她屈從于世的安靜與緘默在內(nèi)心哀吟。
我從來沒有覺得生氣,一次都沒有。我其實從一開始就被她打動,那種無動于衷的不合作,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東西,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我知道世界會因此紛紛棄她而去,那時候,她可能會更孤單。
她加了我微信,卻很少交談。倒是她媽媽,也加了我,經(jīng)常給我打電話,說她的事,她看的書。母親既疲憊不堪又提心吊膽,她明顯感覺自己的孩子是格格不入的,但又顯然是看到了她的聰慧與不同常人的洞察力。慧極必傷,做父母的應該已經(jīng)擔憂很多年。
她是媽媽陪護著在學校里讀書的,因為自閉與內(nèi)向?我并不知道。
3
時光飛逝,三年之后,有人給我打電話,說她想見我,意思她陷入了危險。但最后一致的決定是我不必出現(xiàn),她如果有什么問題,有相關醫(yī)生。也確實,醫(yī)生會給出權威的標準的方子,合法的藥物治理,普通人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知道,那是她在向我求救。我們僅僅半年十七八次的相見里,看似課堂上毫無交流,實際一直在交流。我能讀出她眼神的寂寥,以及對于世界的放棄與無可奈何,她也能讀出我積極應對一份工作背后的某種有心無力。
現(xiàn)在,又好幾年過去了,她已經(jīng)離開這座城市,我不知道她選擇了什么樣的生活,只每一年過年的時候她會給我留個問好的信息,然后我會打出她的名字,希望她好好珍惜自己的奇思妙想,寫出來。她會奇怪我居然一直記得她,而她不知道的是,正因為她,無論我多么沉浸于自己的講課方式,也能看見皮影背后自己真實的現(xiàn)狀。對于生活,我同她一樣毫不篤定。
時至今天,我將目光投向窗外的時候,還經(jīng)常想起這個女孩。課程結(jié)束后到現(xiàn)在,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我既希望她保持當時不與世界合作的樣子,又希望她能歡喜地享用這個世界,作一些配合。可是我知道,這對于她來說太難了。
這世界有一小部分人患著天才癥,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規(guī)則毫不在意,不關心自己的所謂“遠大前程”,不圖謀任何“未來”,連現(xiàn)在他們都是放棄的,“活在當下”這種讓自己喘氣至少現(xiàn)下舒服點的方式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他們的不妥協(xié)對他們自身也是一種傷害,但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是放棄的,那么還有何傷害可言?不得不說,他們向我解釋了世界的一種可能,即所謂無用哲學。他們讓人看見了生命可能擁有的另一種厚度,背向世界的那種致命誘惑。
劉國欣: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出版有小說集 《城客》《供詞》《夜茫茫》,散文隨筆集《次第生活》《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等。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