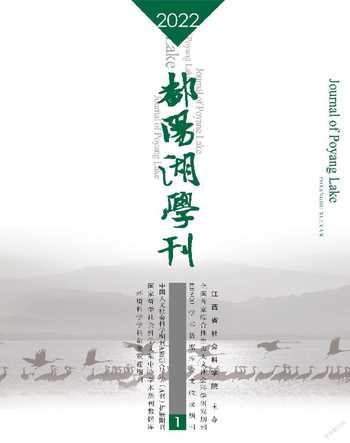我的學術研究的生態轉向
[摘 要]生態語言學是一個以問題為導向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它是語言學的應用,目的是解決與語言和生態有關的問題。文章闡述了作者語言學研究的生態轉向及其生態語言學研究的思路,認為生態語言學的研究重點不僅包括對生態話語的分析,還包括對話語的生態分析。文章著重介紹了和諧話語分析的假定和內容,以及學術界對和諧話語分析的關注,并對生態語言學跨學科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生態語言學;和諧話語分析;以問題為導向;跨學科研究
我曾在《人生處處皆選擇》一文中談到自己在人生的“耳順”之年開始關注語言與生態之間的關系問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從工作了整整20年的中山大學調到華南農業大學。①我18歲那年進入廣州外國語學院(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習英語,受到多年的外國語言學訓練;1986年在廣州外國語學院獲得“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學位;后來到英國留學和工作,其間先后獲得英國愛丁堡大學(應用語言學專業,1992年)和威爾士大學(今卡迪夫大學)加的夫學院(功能語言學專業,1996年)授予的兩個博士學位;1992—1993年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做研究,被聘為助理研究員(Research Associate);1996年從英國學成到中山大學工作,同年擔任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2012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21年獲得“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家”稱號。
從本質上說,我是個英語語言研究者,也是功能語言學研究者和應用者。我信奉的是功能的語言觀(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主要從語言使用的角度觀察和研究語言的功能,并注重語言的社會屬性和語言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
我過去幾十年的研究領域主要有三個:一是語篇分析及話語分析,出版了《語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語篇分析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功能語篇分析》(與葛達西合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和《功能話語研究新發展》(與趙蕊華合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等著作;二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出版了《英語強勢主位結構》(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探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已翻譯成英文將由英國Equinox出版公司出版)、《功能取向》(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什么是功能語法》(與辛志英合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系統功能語言學十講》(與陳瑜敏合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1年)等著作;三是生態語言學,出版了《什么是生態語言學》(與趙蕊華合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生態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與陳旸、趙蕊華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待出)等著作。
在語言學研究領域中,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在最近幾十年才興起,比社會語言學這類學科分支還要年輕。我是從2016年才開始生態語言學研究,也即開始我的學術研究的“生態轉向”。下面我從三個方面談談自己在生態語言學領域的研究:一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二是話語的生態分析,三是和諧話語分析。
一、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
關于生態語言學的興起,一般的說法是追溯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豪根(E. Haugen)所說的“語言生態(學)”(the ecology of language)。①生態語言學涉及語言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所以本質上是交叉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但是,我們注意到學界關于生態語言學的學科屬性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生態語言學是交叉學科,因為它涉及生態與語言的交叉,如范俊軍;②第二種觀點認為生態語言學是應用學科,主要是應用不同學科的理論并將其糅合到生態語言學中以解決實際問題,如我和趙蕊華等;③第三種觀點認為生態語言學是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ity),如何偉將生態語言學定義為“基于并超越生態學、語言學、哲學、生物學、認知科學、社會學、外交學、政治學、文化學等”,④其觀點應該是受了蘇內·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⑤和阿倫·斯提比(Arran Stibbe)⑥等人的影響。⑦
生態語言學涉及語言學和生態學,因此說它是交叉學科或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ity)。生態語言學研究的內容不局限于某一單一學科,它涉及甚至跨越了至少兩個學科,而且不同的生態語言學研究者所涉及或跨越的領域的廣度和深度也不盡相同。
我曾于2019年12月1日在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的第4期生態語言學講習班上,就生態語言學學科屬性問題與丹麥南丹麥大學的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教授進行公開對話,但我們無法達成一致的看法。他認為生態語言學是超學科,語言學屬于生態語言學;我認為生態語言學是廣義的應用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這些學科分支一樣,屬于語言學應用。這一看法表明了我的觀點:生態語言學屬于語言學。⑧
正如我與李文蓓所說的,阿爾溫·菲爾(A. Fill)和蘇內·沃克·斯特芬森在討論生態語言學研究的學科屬性時認為,研究語言生態既屬于自然科學,也屬于人文學科。①他們在其主編的《語言科學》(Language Sciences)專號中,談到了 2009 年在丹麥歐登塞召開的題為“生態語言學:科學的生態”(Ecolinguistics: the Ecology of Science)學術研討會,并說到該研討會的參與者達成這樣一個共識,即想打破原來把生態語言學看作是語言學一個分支的界限,認為這個學科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科學)。②對于這個觀點,我們有不同的看法。③在我們看來,目前把生態語言學看作是獨立于語言學之外的學科領域是一個過于樂觀的想法。我們通過提出區分微觀生態語言學和宏觀生態語言學來描述這種狀態,把微觀生態語言學看作是廣義的應用語言學(這點與社會語言學一樣),把宏觀生態語言學看作是位于一般學科(如生態學、語言學、社會學等)之上的學科,也就是超學科。④在中國的語境中,我們把自己所做的生態語言學研究定位為微觀生態語言學,并把它看作是廣義的應用語言學,屬于維多森(H. G. Widdowson)所說的“語言學應用”(linguistics applied)。⑤
我在不同場合都談到生態語言學是一個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的交叉學科,與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學科分支一樣,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所謂以問題為導向,就是問題驅動,從發現問題和觀察問題開始,然后分析問題并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最終解決問題。我們所做的生態話語分析,都展現了生態語言學以問題為導向的特點。⑥
既然生態語言學是個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科,那么它就期待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看待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因此,生態語言學的發展是問題驅動的,它不像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形式語言學理論或韓禮德(M. A. K. 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那樣有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術語和研究方法。生態語言學是問題倒逼的研究。
二、話語的生態分析
生態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內容就是從生態的角度進行話語分析,即生態話語分析(eco-discourse analysis)。生態話語分析與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生態批評話語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有著密切的聯系。理查德·亞歷山大(Richard Alexander)在《建構關于環境話語的框架:批評話語模式》一書中采取案例分析法,討論了一系列反映環境和生態問題的語言和話語。⑦他的主張是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視角出發。他與斯提比合撰的論文《從生態話語分析到話語的生態分析》區分了“生態話語分析”(即關于生態話題的話語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和“話語的生態分析”(即對任何話語進行生態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并認為后者更加重要。①這個觀點在學界影響很大。我十分贊成亞歷山大和斯提比對任何話語進行生態分析的觀點,并通過對“銀行排隊叫號單”、②給知心姐姐信件、③“甜妹行為”④等語篇的分析展示如何從生態的角度分析不同類型話語。
我基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諧生態哲學觀,提出“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的觀點。⑤“think ecolinguistically”就是“思,以生態語言學為本”,即從生態語言學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act ecolinguistically”就是“行,以生態語言學為道”,即從生態語言學的角度去行動,在使用語言時考慮生態因素。我們曾就“大便后不沖水,就打包回家”這樣的語言表達進行批評,因為這種語言使用的出發點是違反生態的。我們認為,在中國的文化里,“打包”是指在餐館吃飯后將味道好、不舍得作為垃圾清掃掉的食物包裝回家的行為,是節約糧食、反對浪費的生態行為;把“打包”這種使人聯想到“美食”“好味道”“不浪費”的詞語與廁所里的“排泄物”聯系在一起,就是把現代文明帶回到愚昧和原始。⑥
生態語言學和生態話語分析的一個任務是促進生態教育,提高全民的生態素養和生態意識,⑦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生態語言學研究就是參與并致力于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三、和諧話語分析
我在思考生態語言學研究的過程中,始終記住以下三點:其一,生態語言學研究要以問題為導向,因為它是問題驅動、問題倒逼的。其二,中國面臨的生態問題與其他國家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因此研究要努力做到本土化,要時刻記住我們首先要關注和解決中國自己的生態問題。其三,生態話語分析的重點不在于生態批評話語分析,后者只是一個研究視角,而且不是前者的核心內容;生態話語分析的重點應該是關心絕大多數人,應該緊跟社會主流并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氛圍。因此,我們根據這些情況提出了“和諧話語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框架。⑧我曾明確指出,“在中國語境下,‘生態’不僅僅是指生命有機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結構和功能的關系,而是被用來表示‘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⑨這是因為在中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國家理念,“和諧”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關鍵詞,它強調各種關系的和諧一致。⑩
關于構建和諧話語分析模式,我們這些年一直都在思考并付諸實踐,對其哲學根源、研究目標與原則、理論指導、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等進行深層次的探討。①但需要討論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只是提了一些初步設想和原則,總的說來研究還不夠深入,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涉及。目前已經有一些人跟我一起在這方面進行深入思考,我們期待更多的人來參與我們的構建工作。
和諧話語分析的語言學理論指導主要是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②遵循的是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語言學”③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原則,④因此我們推崇辯證唯物主義,主張采取整體論(holism)、多元論(pluralism)和系統論。之所以采用系統功能語言學作為理論支撐,是因為我們把語言看作政治活動的工具,因此突出語言在社會活動中的干預功能,把語言研究和語言使用置于社會政治語境中,同時也把語言與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上下文語境結合起來,在語境中研究語言和語言使用以及語言的功能。
和諧話語分析的哲學根源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就是“生”的問題,“生”的哲學就是生態哲學,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⑤中國哲學中的“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天人合一”都是主張要與自然界萬物和諧相處,以自然界為精神家園。無論是儒家孔子的“天生萬物”還是道家老子的“道生萬物”,都是講世界的本源(天或道)與包括人在內的自然界的生成關系與和諧關系。雖然儒家與道家在“天人合一”的解釋上有差異——儒家側重“人文”、道家側重“自然”,但在“天人合一”這一理念的理解上其基本的含義都是“人與自然的內在統一”。⑥
雖然我們信奉中國的生態哲學,認為動物、植物等都是有生命的,都要得到愛護、保護,但在人與動物的選擇上,我們認為首先選擇的應該是人,因此我們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假定。⑦
明代著名思想家、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在其《傳習錄·錢德洪錄》中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禽獸和草木都是一體,我們都是要愛的,但我們用草木去飼養禽獸;人和禽獸一樣都是要愛的,但我們宰殺禽獸以奉養親人、祭祀祖先、招待客人。①由此可見,人比禽獸和草木更加重要。在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寶貴的。《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②人之所以貴重,是因為人會思維、有意識、有語言、有道義、有組織,能結合成社會群體,群體中有等級名分之分;人能利用意義表達手段溝通協調、團結一致、和諧相處。從這點看,人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責任最大。因此,人類應當最小限度地影響、采用和破壞其他物種,要有節制、有限制地取用自然資源,盡量保持生態的平衡,這也是生態環境倫理學所關注的問題。人類首先應考慮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人的生態素養的培養,認真做好生態教育工作。③
我還認為,從生態哲學的角度來看,有三條原則可以指導我們的生態話語分析:一是良知原則,二是親近原則,三是制約原則。④
和諧話語分析與生態批評話語分析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前者的出發點是構建,而不是解構。我們要展示生態系統中積極、和諧的一面,而不是突出消極、沖突的一面。和諧話語分析的目的是面對問題、分析問題、認識問題,并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使社會越來越好、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不是突出沖突、激化矛盾。和諧話語分析尤其關注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既可以用于分析包含積極因素的語篇,也可以用于分析包含沖突的語篇。⑤
自2016年我的和諧話語分析框架提出以后,得到很多同行的關注和認同。如國際生態語言學學會召集人(主席)、英國格羅斯特大學生態語言學教授阿倫·斯提比就曾多次談到和諧話語分析。他在2016年11月寫給“首屆生態語言學國際研討會”的賀信中這樣說:“話語分析者可以使用黃國文教授提出的和諧話語分析框架,批判當代的破壞性話語,如消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并分析中國的積極話語選擇來源。”(Discourse analysts can critique contemporary destructive discourses like consumerism and neoliberalism, and analyse Chinese sources for positive alternatives, using the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proposed by Professor Huang Guowen.)⑥2018年他在其著作《生態語言學:語言、生態與我們信奉和踐行的故事》(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的中譯本前言中又談到和諧話語分析:
當然,任何一門學科都蘊含著創作者的文化視角,生態語言學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創造出適應中國語境的生態語言學形式,并將中國傳統思想的感悟直接融入其理論和實踐的框架中。為此,黃國文教授與其他學者共同建構了和諧話語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框架。以下是黃國文教授對和諧話語分析的總結:
批評話語分析和積極話語分析都局限于人類社區團體的范圍,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和諧話語分析的目的在于實現不同層面的和諧,嘗試探究語言在人類與其他物種以及物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中所發揮的作用,并探討如何通過語言的選擇來理解、調整、維持和/或加強特定社會中的關系。這突出了語言的使用在解決生態問題中的重要性。
和諧話語分析和生態語言學之所以在當今世界如此重要,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首先,傳統上人們一直認為語言學只存在于人類社會中,而沒有考慮社會所嵌入的更大的生態世界——一個有動物、植物、河流、海洋、土壤和雨水的世界。但是,由于語言與更大的生態系統是相互塑造,只有將更廣泛的生態考慮在內,才能使語言學成為一門更為準確的學科。其次,隨著生態系統的日益惡化,我們的生命、我們下一代的生命以及無數其他生物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脅。因此,將更廣泛的生態考慮在內是十分必要的。①
2021年,斯提比教授的《生態語言學:語言、生態與我們信奉和踐行的故事》一書由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再版。他在書中寫道:
最近,在中國,學者們發展了和諧話語分析。這種方法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的和諧哲學,特別是儒家的良知、親近和制約三大原則,描述了如何在和諧話語分析中,“通過研究話語中與語言相關的生態問題,我們旨在展示人類與其他生態參與者的各種關系,并通過語言促進和諧關系”。和諧話語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生態語言學走遍世界,并根據它所到達的地方的文化、哲學和生態進行重新改造。(More recently, in China,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approach is unique because it is strongly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es of harmony, particularly the three Confucian principles of conscience, proximity and regulation. Huang and Zhao describe how in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by examining language-related ecological problems in discourse, we aim to present the various relations of humans with other ecological participants and to promote harmonious relations via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at it provides an example of ecolinguistics travelling across the world and being reinvented in line with the culture, philosophy and ecology of the place it has arrived in.)②
2022年,斯提比教授《生態語言學:語言、生態與我們信奉和踐行的故事》的配有導讀的中譯本第2版將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
和諧話語分析框架具有中國特色,已經成為生態語言學的一種重要而獨特的形式。黃和趙(2021)是這樣描述的:
和諧話語分析既將“話語”解釋為狹義的語言使用,也從更廣的意義將“話語”解釋為社會實踐中的各種系統,其目標是在兩個層面上開展工作:基于文本的微觀層面,分析語言形式的特征和模式;超越語言的宏觀層面,分析語言系統和其他系統(無論是意義系統、社會系統還是物質系統)在社會實踐中的相互作用。和諧話語分析不僅肯定或批評一種現象、生態哲學或行為,還展示生態系統中的各種關系是如何協調的,以及語言和其他系統如何推動這些關系的協調的。
和諧話語分析中的和諧概念基于中國哲學傳統的道家和儒家思想,融合了“良知原則、親近原則和制約原則”。該框架中的分析充分利用了系統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
[The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nd distinctive form of ecolinguis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uang and Zhao(2021) describe how:
Interpreting “discourse” as language use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in a broader sense in the context of various systems of social praxis, HDA aims to work on two levels: the micro level, a text-based level, analysing features and patterns in language forms; and the macro level, a translinguistic level, analysing the language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whether semiotic, social, or material, in terms of their interactions in social praxis. HDA does not merely confirm or criticize a phenomenon, ecosophy, or action, but also shows how various relations in the ecosystem are harmonized and how language and other systems contribute to harmonizing such relation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 incorporating ‘the principle of conscience,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on’ The analysis within this framework makes strong us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 well as cognitive linguistics.]①
從有關論文檢索來看,已經有一些國內外學者在討論生態語言學和生態話語分析時引用、討論或修正和諧話語分析中的一些觀點或說法,讓我們備受鼓舞。長期以來,中國外語界的研究總是比較輕視中國學者提出的理論、方法,眼睛一直盯住“外國人”。如果說我們要做到理論自信,那么我們的研究就要有本土意識,要努力挖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并結合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尋找中國的解決方案。
近年來,國際生態語言學學會與英國的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聯合組織出版生態語言學專著系列,其主編斯提比教授和國際生態語言學學會的瑪麗安娜·羅西亞(Mariana Roccia)在叢書選題中就特別談到:期待出版“像和諧話語分析那樣的新興理論框架”(emerg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的專著。②
和諧話語分析是在中國語境下提出的,它不僅要研究社會結構中人與人之間的生態關系,還要探索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重點在于研究語言在生命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保持和諧關系和構建和諧共生關系,體現在不同的形式層面和不同的意義表達方式中。和諧話語分析不僅要探討如何通過語篇中語言的選擇來理解、說明、調整、適應、維持和諧共生關系,而且要探索語言是怎樣構建、推廣、強化或解構、抵制、破壞特定環境中的各種和諧的生態關系的。這種研究取向突出了語言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也突出了語言和語言使用在解決生態問題中的作用。因此,我們需要不忘初心,牢記研究目標,拓寬研究思路,探索更多的研究方式,涉及更多語料,根據不同的環境把不同的語篇類型與意義表達緊密聯系起來。這個研究領域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非常多,我們期待更多信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研究行列,共同為生態文明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四、跨學科研究的機會和挑戰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學術共同體十分關注“跨學科”、“交叉學科”和“超學科”問題。這種新的研究范式給解決問題帶來新的機會,也帶來新的挑戰。生態語言學研究當然也涉及這類問題。
我是學習英語出身的,在國外所受的教育是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所以我的知識結構就是學習語言或語言學的模式。語言有人類屬性和社會歸屬,但語言學研究沒有國界。經常聽到有人說,科學沒有國界,不分國外國內,因此我們不說“中國物理學”“英國物理學”,但是科學家是有國家的,是有家國情懷的。因此,科學家所做的研究就有為誰服務的問題。學習外國語和研究外國語該怎樣為國家服務,這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
近年來學界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就是“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和“新文科”以及這“四新”之間的關系,這就帶來了跨學科研究或超學科研究的話題。生態語言學無疑涉及跨學科或交叉學科問題,但每個人必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語言學者做生態語言學研究,得心應手的肯定是語言理論和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就語言與生態的關系而言,研究的學科分支既有語言生態學也有生態語言學。首先提出“語言生態(學)”(linguistic ecology、language ecology、the ecology of language)的應該是語言研究者。①從術語的語法結構看,“語言生態(學)”的中心詞是生態(學),而“生態語言學”的中心詞是語言學。但是,目前做語言生態研究的學者②都是語言學家,他們所做的研究和理論支撐是來自語言學,而不是生態學。正如我和李文蓓所說的,語言學者所做的語言生態(學)研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語言,所涉及的學科除了交叉的語言學和生態學以外,還有歷史語言學、語言人口學、社會語言學、語言接觸、語言變異、語文學、語言規劃和政策、語言政治學、民族語言學、語言類型學等;雖然最近十多年來也有一些語言學科以外的學者討論語言生態問題,但這些學者幾乎都是來自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而很少來自生態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者。③
在自然科學界,語言生態(學)探討的問題的核心學科是生態學,涉及的學科除了語言和語言學之外,還有環境學、氣候學、地理學、土壤學、森林學、園藝學、植物學、動物學、遺傳學等,語言學在其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內容;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數也都是來自自然科學,而不是人文學科。因此,筆者認為,到目前為止的語言學者④所做的語言生態研究,并不是自然科學學者心目中的“語言生態(學)”。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學者本質上就是語言學家,而不是自然科學研究者,他們所采用的研究視角、理論支撐和研究方法都是來自語言學或其他人文科學,而不是來自生態學或其他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的學者和自然科學學科的學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專業知識結構和處理問題的方法,這也是為什么要真正做到跨學科是非常不容易的。
五、結語
當今的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學科已經出現了生態學化。30多年前,李繼宗和袁闖發表了《論當代科學的生態學化》一文,指出當代科學出現的生態學化現象。①在生態轉向的大環境下,很多與生態有關的學科陸續出現,僅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就有生態心理學、生態女性研究、生態社會學、生態批評、環境溝通、生態文學、生態語言學等等。在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語言研究者要有所作為,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積極參與生態教育,為社會提高公民的生態意識和生態素養作出我們專業的貢獻。
我研究生態語言學的理論支撐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從本質上說,我是個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學習者、研究者和應用者,這些年主要圍繞著系統功能語言學創始人韓禮德提出的“系統生態語言學”(systemic ecolinguistics)②進行學術探索。根據這一研究范式,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包括“我們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們對環境的影響”(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這個問題的核心內容就是語言與生態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是在構建和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過程中語言所起的作用。
生態語言學研究的前景光明,可以探討的問題很多。2019年5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記者武勇采訪了我,其中一個問題是關于國內外生態語言學研究的新趨勢,我作了回答,這里就用它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語言與生態問題的研究,是最近幾十年才慢慢發展起來的,中國起步比歐美國家晚。無論是“語言生態學”還是“生態語言學”研究,都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話題。目前,國外學者的研究重點主要有三個:一是語言多樣性研究,內容包括小語種和方言的使用和保護情況;二是生態話語分析,研究內容包括各種題材和體裁的話語,如廣告、媒體話語、政治話語、多模態話語等;三是突出生態語言學的跨學科性和超學科性,強調人類生態意識,強調有利于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哲學觀。第一點主要是語言生態學關注的問題,第二、三點則主要是生態語言學研究的問題。③
責任編輯:胡穎峰
[作者簡介]黃國文,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廣州 510640)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農謠諺語收集整理及其生態思想挖掘研究”(20YJAZH013);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數字化背景下廣州旅游外宣翻譯語料庫建設及應用研究”(2019GZYB36);廣東省普通高校特色創新類項目“廣東景觀語言生態翻譯研究”(2018WTSCX006)
①參見黃國文:《人生處處皆選擇》,《當代外語研究》2016年第1期。
①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 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
②參見范俊軍:《生態語言學研究述評》,《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2期。
③參見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的興起和發展》,《中國外語》2016年第1期;趙蕊華:《基于語料庫的生態跨學科性及學科生態化表征研究》,《中國外語》2018年第4期。
④何偉:《關于生態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國外語》2018年第4期。
⑤參見何偉、魏榕:《生態語言學:整體化與多樣化的發展趨勢——〈語言科學〉主編蘇內·沃克·斯特芬森博士訪談錄》,《國外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
⑥參見何偉、魏榕、Stibbe, A.:《生態語言學的超學科發展——阿倫·斯提布教授訪談錄》,《外語研究》2018年第2期。
⑦黃國文、趙蕊華:《什么是生態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3頁。
⑧參見黃國文、陳旸:《生態話語分類的不確定性》,《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黃國文、趙蕊華:《什么是生態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①A. Fill & S. V. Steffensen, “Editorial: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and the Ecology of Science,” Language Sciences, no. 41,2014,pp. 1-5;黃國文、李文蓓:《作為應用語言學的生態語言學》,《現代外語》2021年第5期。
②S. V. Steffensen & A. Fill,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Language Sciences, no. 41,2014,pp. 6-25.
③參見黃國文、陳旸:《作為新興學科的生態語言學》,《中國外語》2017年第5期。
④參見黃國文、陳旸:《微觀生態語言學與宏觀生態語言學》,《外國語言文學》2018年第5期。
⑤H. G. Widdowson, “On the Limitation of Llinguistics Applied,” Applied Linguistics, no.1,2000, pp. 3-25.
⑥參見黃國文:《論生態話語和行為分析的假定和原則》,《外語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6期;黃國文:《生態語言學與生態話語分析》,《外國語言文學》2018年第5期;黃國文:《生態語言學與語言可持續發展》,常晨光、喻常森主編:《語言的可持續性》,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60—294頁;黃國文、趙蕊華:《什么是生態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黃國文、陳旸、趙蕊華:《生態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
⑦參見R. Alexander, Framing Discourse on the Environment: A Critical Discourse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①R. Alexander & A. Stibbe,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Language Sciences, no. 41,2014, pp. 104-110.
②黃國文:《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生態化取向》,《中國外語》2016年第5期。
③黃國文:《生態語言學與生態話語分析》,《外國語言文學》2018年第5期。
④黃國文:《生態語言學與語言可持續發展》,常晨光、喻常森主編:《語言的可持續性》,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60—294頁。
⑤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的興起和發展》,《中國外語》2016年第1期。
⑥黃國文:《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生態化取向》,《中國外語》2016年第5期。
⑦黃國文、哈長辰:《生態素養與生態語言學的關系》,《外語教學》2021年第1期。
⑧參見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的興起和發展》,《中國外語》2016年第1期;黃國文:《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生態化取向》,《中國外語》2016年第5期;黃國文:《論生態話語和行為分析的假定和原則》,《外語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6期;黃國文、趙蕊華:《什么是生態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黃國文、趙蕊華:《功能話語研究新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趙蕊華、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研究與和諧話語分析——黃國文教授訪談錄》,《當代外語研究》2017年第4期。
⑨趙蕊華、黃國文:《和諧話語分析框架及其應用》,《外語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1期。
⑩黃國文:《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生態化取向》,《中國外語》2016年第5期。
①參見趙蕊華、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研究與和諧話語分析——黃國文教授訪談錄》,《當代外語研究》2017年第4期;黃國文:《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生態化取向》,《中國外語》2016年第5期;黃國文:《論生態話語和行為分析的假定和原則》,《外語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6期;黃國文、陳旸:《作為新興學科的生態語言學》,《中國外語》2017年第5期;黃國文、陳旸:《生態話語分類的不確定性》,《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黃國文、陳旸:《微觀生態語言學與宏觀生態語言學》,《外國語言文學》2018年第5期;黃國文、趙蕊華:《什么是生態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黃國文、趙蕊華:《功能話語研究新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G. W. Huang & R. H. Zha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 Language Sciences, vol. 85,2021,pp. 1-18;趙蕊華、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研究與和諧話語分析——黃國文教授訪談錄》,《當代外語研究》2017年第4期;趙蕊華、黃國文:《和諧話語分析框架及其應用》,《外語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1期;W. J. Zhou,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Harmony,” Language Sciences, no.62,2017,pp. 124-138;周文娟:《中國語境下生態語言學研究的理念與實踐——黃國文生態語言學研究述評》,《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W. J. Zhou & G. W. Huang, “Chinese Ecological Discourse: A Confucian-Daoist Inquir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no. 3,2017,pp. 264-281.
②M. A. K. Halliday & C. M. I. M. Matthiessen,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London: Cassell, 1999;M. A. K. Halliday & C. M. I. M. Matthiessen,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ition),London: Routledge, 2014.
③J. R. Martin, “Grammar Meets Genre: Reflections on the Sydney School,”Arts: The Journal of the Sydney University Arts Association, vol. 22,2000.
④何遠秀:《韓禮德的新馬克思主義語言研究取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⑤蒙培元:《人與自然——中國哲學生態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蒙培元:《人與自然——中國哲學生態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⑦黃國文:《論生態話語和行為分析的假定和原則》,《外語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6期。
①鴻雁編:《王陽明全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五《王制篇第九》,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64頁。
③黃國文、哈長辰:《生態素養與生態語言學的關系》,《外語教學》2021年第1期。
④黃國文:《論生態話語和行為分析的假定和原則》,《外語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6期;黃國文、趙蕊華:《什么是生態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年;黃國文、趙蕊華:《功能話語研究新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
⑤黃國文、趙蕊華:《功能話語研究新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黃國文、陳旸、趙蕊華:《生態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
⑥參見《首屆生態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華南農業大學,2016年,第3頁。
①阿倫·斯提比:《生態語言學:語言、生態與我們信奉和踐行的故事》,陳旸、黃國文、吳學進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vi頁。
②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p. 212.
①斯提比:《生態語言學:語言、生態與我們信奉和踐行的故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2年。
②Arran Stibbe and Mariana Roccia,“Bloomsbury Advances in Ecolinguistics,”https://www.bloomsbury.com/uk/series/bloomsbury-advances-in-ecolinguistics.
①J. L. M. Trim,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Dynamic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Speech, vol. 2,no.1,1959, pp. 9-25;C. F. Voegelin & F. M. Voegelin,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ative America Fascicle One. Contemporary Language Situations in the New World,” Anthropol. Linguist, vol. 6,no. 6,1964, pp. 2-45;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
②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A. Makkai,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Pinter, 1993;馮廣藝:《語言生態學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③黃國文、李文蓓:《作為應用語言學的生態語言學》,《現代外語》2021年第5期。
④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A. Makkai,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Pinter, 1993;M. Garner, Language: An Ecological View,Oxford: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馮廣藝:《語言生態學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Routledge, 2015;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
①李繼宗、袁闖:《論當代科學的生態學化》,《學術月刊》1988年第7期。
②M. A. K. Halliday,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 in J. Webster,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9:Language and Educ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7, pp. 1-19.
③《黃國文:人工智能時代的語言研究與人才培養——訪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黃國文》,2019年5月29日,http://fund.cssn.cn/zt/rwln/xj/xrxp/201905/t20190529_4909140.shtml,2021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