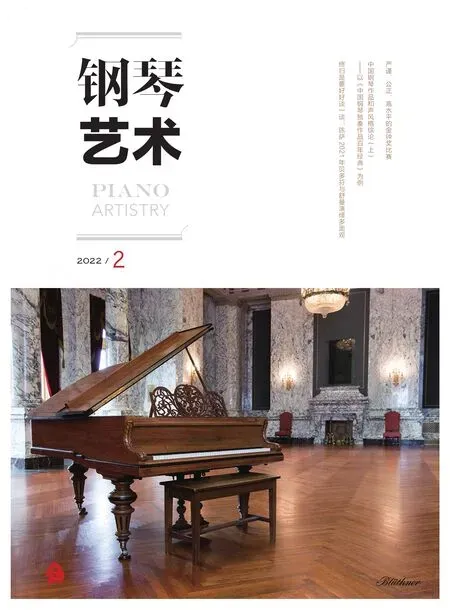『陽關大道』與『曲徑通幽』
——『疊藝』漫步鋼琴演奏藝術論之二
文/ 董海珠、李世衛

這次我們對鋼琴獨奏藝術“有話要說”。
上一講,我們拋磚引玉地聊到了“鋼琴獨奏藝術的重奏溯源”。西方音樂“共曉時期”(Common Practice Period)的成就,幾乎奠定了我們今天全部的音樂生活和活動的語匯構造,也為后來的音樂文庫提供了素材。而鋼琴這件樂器,從誕生到進化,再到最終能代表現代工業制造水平的當代非電子樂器,對激勵整個西方音樂發展,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鋼琴能夠得以有這樣的舞臺去展現自身的潛力和魅力,也是離不開西方音樂對多聲音樂的根本需要,無論是宗教還是世俗,這種對多聲性的審美習慣,已經深入骨髓,成為了西方音樂的標準。無論是以對位為出發點的巴洛克音樂,還是以和聲性為準繩的古典音樂、浪漫音樂,以及近代的多調性多樣化創作手法,乃至無調性音樂,這種多聲(多層次、多線條)音樂始終是西方音樂的靈魂。而且,也是非西方民族音樂進入國際化音樂生態圈,被納入標準化作品形態的必然寫作方式。而在調性化時期(大小調體系被中心化的三百多年),依靠以十二平均律制式研造并調律的鍵盤樂器,自然是作曲家們音樂創作的首選工具性樂器。而作品最初的呈現,往往是用作曲家寫作時依靠的鍵盤樂器,來完成作品的處女演奏。這里不一定非得是公開的演奏,作曲家自己大略的彈奏應該也可以被看作是作品的第一次聲音化呈現。
最初的獨奏,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成本”降低了的“重奏”或“合奏”。這樣反而不難理解在今天看起來“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而在那個時候(比如巴洛克時期)是那樣的稀松平常,那就是—作曲家往往同時又是鍵盤演奏家(鋼琴家),為了讓自己的作品能夠在一開始就“聽起來很棒”,作曲家必須得有很好的鍵盤樂器演奏本領。在西方音樂的“共曉時期”,不乏偉大的作曲家、鋼琴演奏家同為一個人的例子,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大約1850年之前,鍵盤獨奏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與其說是像今天很多流傳廣泛的、有關鋼琴家傳記類讀物中所寫的,一種神乎其神的活動,還不如說,是西方音樂傳播與推廣的一種很有效的常用手段。或許有讀者會有異議,但他們會列舉一堆18至19世紀早期,西方鋼琴演奏圈子的風云人物。但是,我們這里只能理智并略微有點兒“潑冷水”地告訴讀者們,根據常識性的認知,這些名字大概就是值得讓作家們描繪的全部了,而相較于更日常的西方音樂活動,在一個沒有發達媒體的馬車時代,與這些人物同時代的人,要想有幸聆聽或認識他們,機會是很少的,大家一定不要以現今技術媒體時代對信息的了解和獲取的能力,去衡量那個時代的人對于這類信息的反應和處理能力。我們今天對莫扎特的“了解”和“認識”,一定遠遠多于莫扎特同時代的人,那時哪怕是一個“音樂超級粉絲”,他要聆聽莫扎特的音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獨奏,通常可以是作曲家寫作其他形式(樂隊、重奏、聲樂)作品的“熱身”“試水”和初稿;也可以是作曲家把作品呈現給他愿意呈現的對象們的一種方式。今天的音樂會呈現方式與18、19世紀已經很不一樣了。如今,音樂活動的商業味道,是那時候的人們無法想象的,如同今天的人們不了解那時人們的音樂活動方式一樣,所有的了解都是基于主觀色彩很重的文字記載。當時,音樂表演可以在很多地方進行,而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被稱為音樂廳的專業場館。萊比錫布商大廈音樂廳大概是第一個正規公共音樂廳,建于1781年,大約可以容納五百余名觀眾,這樣的規模,在今天,僅相當于一個中小型音樂廳。而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表演場地了。
每個時期的音樂活動,都被這一時期音樂呈現方式的可行性所決定。藝術活動的精神性,必然受到藝術表演“硬條件”的限制。有一個很好的例子:C.P.E.巴赫著名的論文集《鍵盤樂器的正確演奏法》,完全就是針對當時鍵盤樂器,尤其是羽管鍵琴演奏的指導著作。而如果將這部著作完全用于指導現代鋼琴演奏技法,顯然不是十分合適。C.P.E.巴赫既是作曲家,也是著名的鍵盤演奏家,這一點與上文所說吻合。為了更好地呈現自己的音樂,必須先作為自己作品的第一演奏者,將作品呈現給聽眾。今天,在音樂領域分工越來越細的情況下,哪位鋼琴演奏家能寫一點兒曲子、改編一些作品,往往會獲得愛樂者們格外的贊許和青睞。這類情形,在當今古典音樂行業,已成為很稀有的才能,而在18、19世紀的音樂活動中是很普遍的。
今天的“鋼琴獨奏”承繼的實際上是來自被李斯特推向極端的另一種形式,與李斯特之前的獨奏傳承關系較為疏遠。雖然李斯特之前的許多文獻曲目仍是今天鋼琴演奏家的重要演奏內容,但是對于這些曲目的演奏(或表演)要求,其呈現標準實際上是非常“李斯特及其后人方式的”。即從演奏技術的運用到音樂內容的闡述方式,“大劑量”地輸出演奏家的“自我品格”,而對于作品本身應該如何關注,并不是首位的。這種詮釋方式對于“李斯特及之后”的創作文獻而言,也許有必要與必然性。因為確實存在著一種壓力:商業演出的日趨繁榮,藝術品存在著被“過度審美”的壓力。要考慮到持續的流傳性,以及資本主義式的“利潤最大化心理”,演奏家需要從大家“更為熟悉和易接受的音樂語匯”出發,去盡可能多地展示表演上的“翻花樣”以滿足廣大“音樂消費者”的心理需求。要既熟悉,又不會審美疲勞,這對音樂的“供應方”—作品和演奏者是既無奈又必須重視的事情。浪漫主義的表演方式,其影響在程度與范圍的深度與廣度上,對于后來整個古典音樂表演領域造成的傷害,至今沒有被足夠的認識。今天我們在這里并不打算深入探討李斯特及其后之人對今天鋼琴藝術發展的影響,這里提出來是給讀者們預留了一個問題,我們會在下次深入討論。
從鋼琴演奏藝術誕生到李斯特之前,鋼琴獨奏、重奏,甚至與樂隊合作協奏,習慣上都是帶著樂譜上臺的,沒有刻意要求背譜演奏這個“標準動作”,也沒有一種崇拜超人記憶力的習慣,聽眾、觀眾關注音樂本身的興趣要大于演奏家做各種非音樂方面的表演。演奏者因為帶著樂譜,也不會出現因突然的記憶誤差而導致對音樂整體的影響,加之19世紀初以及之前的鋼琴或者鍵盤樂器,并不能在容納較多聽眾的場合發出洪亮而吸引人的聲音,因此,鍵盤獨奏表演相對而言并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開表演和商業表演方式。莫扎特寫的鋼琴奏鳴曲,不像他寫的數量更多的鋼琴協奏曲,后者是考慮為公共演奏而創作,而前者并沒有考慮作為公開演奏的曲目。
在18世紀末之前的歐洲,社會格局尚屬穩定,需要體面生活的音樂家階層基本都由王公貴族、教會權力機構等供養和維系著他們的生計。海頓就是長期擔任埃斯泰哈齊家族的“精神廚師長”,被排在了傭人隊伍的前列。從海頓這份“長工”經歷可以看到當時音樂家的生存方式,他們對于從事音樂創作和演奏活動更像今天我們上班族們有規律的上班,為主人安排好每天的音樂活動,這更像是管理一個重要的生活起居內容,而不是在“表演”。而莫扎特開啟了自由藝術家之路,當然這樣的結果令莫扎特的生活變得異常辛勞和疲于奔波。
巴洛克以及古典時期鋼琴作品(鍵盤作品)實際上是室內樂的一種,可以用單件樂器完成,也可以有多樂器方案來表現。巴赫的鍵盤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可以有多種選擇組合方式的音樂,要認識不同層次線條可以使用什么樂器來替代表現。音樂形態的本質不依賴于固定的樂器音色,甚至可以用人聲去表現,這就是巴洛克作品在詮釋時為演奏留出的空間。由于有這樣多的可塑性,詮釋這樣的音樂在今天對演奏家們反而是有一定挑戰的,但趣味性也顯而易見。這種藝術上的素養只能是來自對重奏藝術“先入為主”的認識,是一種“經驗的”行為而非“超驗的”行為。(注意我們這里提到“超驗的”這個詞,將會在后文中用以探討關于獨奏的重要問題)。
我們時常會聽到對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如下評價:晚期作品中的樂隊化思維越來越明顯,似乎鋼琴已經“裝不下”貝多芬的樂思了。事實上,從貝多芬的交響樂、弦樂四重奏、小提琴與鋼琴、大提琴與鋼琴等作品中,能不斷感受到貝多芬對音樂“質地”的要求。他許多哪怕是很小規模的小品,都會有以上音樂類型的影子。多聲音樂的根牢牢扎在貝多芬的音樂世界中,貝多芬作品的縝密思路體現在當你詮釋他的作品時,很難甚至無法去改動他的記譜,他已經把可能的音樂布局都考慮到了。這是一種重奏性特征很鮮明的獨奏作品,而和聲性的提升,實際是多聲音樂對縱向性密度與強度的一種發展要求,是對橫向推進的一種深入的了解和預見。有人認為這是對復調性的削弱和簡化,以便音樂活動在接納更多普羅大眾后適當放低門檻的一種做法。這樣的觀點盛行一時,我們認為并非全然不對,但不應絕對化。事物的發展并不一定只為單向度的進步而存在,更不是簡單的好與壞,這與討論鋼琴藝術時大家往往下意識地只提及獨奏一樣,屬于片面的認識,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有缺陷的思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