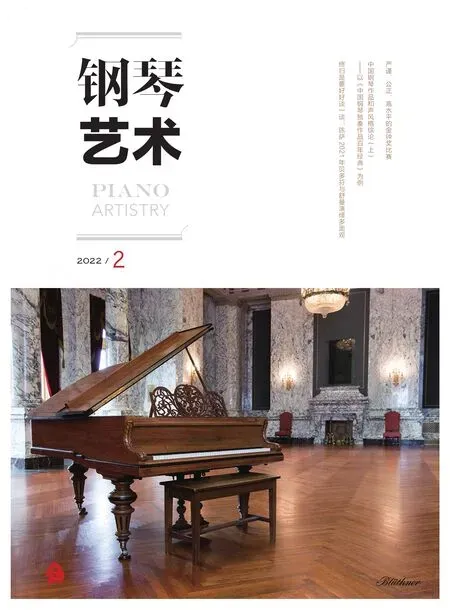別開生面的巴赫盛會
——記巴赫鋼琴協奏曲音樂會
文/ 龍星宇

2021年8月28日,成都金沙國際音樂廳上演了一場別樣的音樂會—I'LL BE BACH,本場音樂會演出的BWV1060、1062、1063、1064、1065等作品皆是首次在中國西南地區亮相。
這些作品是巴赫在萊比錫生活時期,為雙羽管鍵琴、三羽管鍵琴及四羽管鍵琴編寫的協奏曲,它們全部來自巴赫對自己或其他作曲家作品的改編,在此之前鍵盤樂器只作為伴奏樂器在樂隊中出現,它們的問世為鍵盤樂器拉開了全新的篇章。姜維樺、劉昱飛、賈思鈺、羅可可四位青年鋼琴家的演奏為西南樂迷們提供了一個重新發現巴赫的契機。
格倫·古爾德曾這樣評價巴赫:“在我心里巴赫是音樂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是有自己獨立見解、特立獨行的藝術家里的一個極端例子。他并不是所謂的‘超前時代很多、被人誤解的天才’,他當然是被人誤解的,這并不是因為他超前時代,而是因為根據當時的音樂傾向,他反而落后于那個時代好幾代人。但他從未試圖調和自己與時代的差異、與時俱進,反而選擇回溯到更久遠的時代里去,因為他已經超脫于集體的歷史進程之外。”

巴赫在世時因為“落后時代”,其作品一直影響寥寥,如今涓涓流淌三百年的“溪流”終成“大海”,但依然有一些隨波蕩漾的浪花等待我們去發現、感受。我們可以在這些作品中窺見這一時期的巴赫那“超脫集體歷史進程”的表達。曾經湮沒無聞的作品在四位名不見經傳的青年演奏家手中,重新勾勒出了一個更立體、更豐富的巴赫,也更能解釋康德口中J.S.巴赫之存在的歷史必然。
音樂會開場曲目BWV1064,是典型的巴洛克三樂章結構,全曲呈現涇渭分明的快、慢、快結構。第一樂章中音樂圍繞著一個由主屬音之間構成的兩次下行純四度的主題動機展開,姜維樺、劉昱飛、賈思鈺三位演奏家對樂曲開頭旋律的處理干凈、雅致,僅僅幾個小節就為上半場的音樂會拉開了明快動人的序幕。C大調流露出慣有的明媚,在弦樂與鋼琴的相互交融中,顯得朝氣蓬勃,音符的流淌之中,勾勒出一幅屬于新時代的巴洛克圖景。中段鍵盤聲部零碎的十六分音符跑動,并未因為對位和配合的復雜而變得混亂不堪,反而如同夏空流云一般,襯托出弦樂聲部延綿不絕的長線條,而樂句末尾的適當漸強則剛好迎接上帶著f的主題再現,如曙光再臨。演奏家們對樂曲第一樂章的闡述輕松自然,與樂曲的第三樂章形成了巧妙的對照。
第三樂章快板作為全曲的總結依然是C大調。樂章主題的旋律由C大調迂回上行的音階加上一連串下行模進構成。這使得它幾乎像第一樂章的主題旋律,明媚親切的音樂性格一如既往。在第三樂章第142小節出現的小調旋律帶來頃刻深沉,在第一鋼琴姜維樺獨奏的引導下,這種深刻延綿鋪展而開。然而緊隨其后的再現段,卻“不合時宜”地將這種凝滯打破,再次把聽眾拉回獨屬于巴赫的靈動,在四組柱式和弦后,完滿終止結束。演奏家們對巴赫音樂之美的體驗和闡釋理智而優雅,這正是演奏家們希望傳達給觀眾的本愿。
上半場的另外一首作品是c小調的BWV1062,依然是標準的快、慢、快三樂章結構,相比較第一、三樂章的快板,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樂章的行板,主題在第二鋼琴以下行的音階模進開始,隨后以上五度卡農的形式出現在第一鋼琴聲部,降E大調獨特的寧靜與和諧配上弦樂聲部輕柔的四分音符在此化為淺淺細語,姜維樺與劉昱飛對此段的處理亦顯得平靜、內斂,讓音樂在幾經更迭后從容導入主題再現。樂章的中部由雙鋼琴高音區自下而上的大二度反復交替,將這種被刻上理性的抒情發揮到極致,最終風過無痕,又回到樂章開頭的寧靜之中。

下半場的第一首作品是BWV1060(《c小調雙鋼琴協奏曲》),整個第三樂章快板,自始至終沒有停頓,如河水奔向遠方,川流不息。主題動機由c小調主音弱起,并在屬主之間做下行模進,在四個十六分音符的輔助之后向鋼琴中音區做十度大跳,之后主題動機隨著一連串的跑動,融于整體的曲式中。中段鋼琴聲部的十六分音符六連音快速跑動加上弦樂聲部長線條鋪底,作為第三樂章的“休憩時刻”,姜維樺與劉昱飛的演奏輕柔而平緩,沒有因為材料的陡然變化而導致結構出現錯落感,讓聽眾持續沉浸在連貫的樂思之中。
下半場的第二首曲目BWV1063,是巴赫曾經讓兩個兒子(C.P.E.Bach和W.F.Bach)參與首演的曲目,演奏極具難度。尤其是第三樂章,與BWV1060第三樂章類似,BWV1063的第三樂章也是從頭至尾沒有任何停頓,主題動機是兩個大切分所引導的d小調樂句。在開頭處,樂曲便展現出如疾風驟雨一般的氣勢,隨著所有聲部的進入,主題動機中的內在張力逐漸被拉扯到極致,然而,隨之而來的三個插部陡然的聲部抽離,將前景輪換給三臺鋼琴做獨奏,姜維樺、劉昱飛和賈思鈺三位演奏家的演奏配合上弦樂低聲部的三兩點綴,如同暴雨間隙,消除了矛盾的棱角,暫緩了情緒的積累,將樂曲從容地導向了尾聲。
整場音樂會的最后一首曲目是BWV1065,這首作品改編自維瓦爾第著名的弦樂套曲《和諧的靈感》(L’estro armonico)出現在演出的結尾恰如其分。經巴赫改編之后的BWV1065(《a小調四鋼琴協奏曲》)保留了原曲整體清晰透明與多彩細節之間的良好平衡,增加了奕奕生機與肆意靈動的表情。以第三樂章為例,為了遵循原曲,巴赫的改編并沒有使用復雜的對位,在開頭處,通過a小調主和弦的分解齊奏來構成貫穿全篇的主題材料。在隨后的篇章中,依舊不斷地出現大量的和弦分解甚至是更為“直白”的柱式和弦,仿佛是希望通過幾位演奏家對一系列和弦的演繹配合來表現他所謂的“完美諧和”。姜維樺、劉昱飛、賈思鈺與羅可可四位演奏家的演奏像長風灌入溝壑般契合無間,將現場聽眾的情緒推向頂點,最后在大齊奏中完滿結束。
巴赫的這些作品在不屈從時代風潮的同時,也獲得了超越時間的魅力,正如曾經被時代排斥的巴洛克珍珠,在歲月流逝中沉默地保守著關于智慧之美的密語,到如今,這些外形各異的珍珠因其每粒獨一無二的奇幻光彩被人們稱為“上帝之吻”。河流將它冥頑地低語織入大海,每一朵浪花都值得我們凝視,即使偉大如巴赫也依然有許多的作品等待我們去聆聽、感受。美是邂逅所得,是親近所得,正是這樣一場別樣的音樂會讓我們的目光再一次投向那些淹沒在時代光彩中的溫潤光澤。巴赫的作品最終被我們銘記,是因為它們超越歷史進程,因為它們能被任何時代所詮釋,也更能詮釋任何時代,正如中國作家余華所說:“巴赫來往于宮廷、教堂和鄉間,于是他的內心逐漸地和生活一樣寬廣,他的寫作指向了音樂深處,其實也就指向了過去、現在和未來。”
——為鋼琴獨奏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