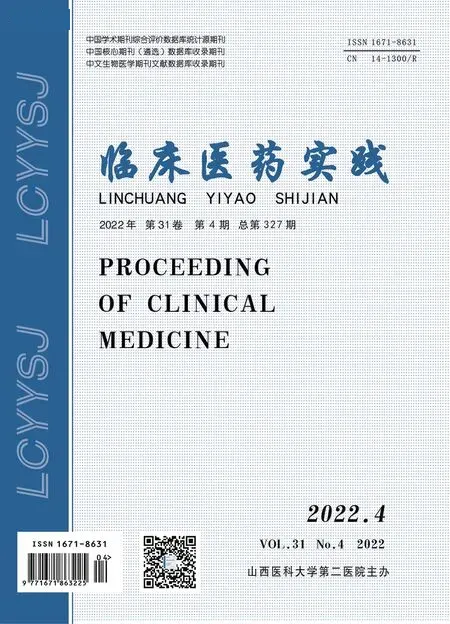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研究進展
劉英,向小爽,2*,沙永紅
(1.吉首大學醫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2.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民醫院,湖南 吉首 416000)
癲癇是神經科第二常見的腦部慢性疾患,是一種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影響著全世界約5 000萬人,我國癲癇患者約900萬,每年新發患病人數高達70 萬[1]。近年來,從臨床研究的角度來看,癲癇共病情緒障礙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但單獨對共病焦慮障礙的相關研究較少,焦慮癥也成為癲癇患者中“被遺忘的共病”。其實癲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焦慮因素,但大約僅30%的臨床醫生重視癲癇共病[2]。癲癇患者的病恥感、癲癇發作的難測性及可能增加的經濟負擔等因素皆可造成焦慮發生,嚴重影響癲癇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質量[3]。本文綜述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臨床表現、評估工具、神經遞質檢測、不良后果及相關治療,進一步揭示癲癇與焦慮兩者的關聯性,以全面、有效地改善癲癇患者的焦慮情緒,助其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1 癲癇
癲癇,俗稱“羊癲風”,是神經科第二常見疾病,屬于短暫性腦功能障礙性疾病,具有癇性發作的特征,由大腦神經元突然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引起[4],具有重復性、刻板性、發作性及短暫性的特點。2014年國際抗癲癇聯盟修訂了癲癇的臨床定義,即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即可確診為癲癇:至少兩次間隔超過24 h的非誘發性或反射性發作;一次非誘發性或反射性發作,但在未來10 年內再次發作風險與兩次非誘發性發作的再發風險相當(≥60%);診斷為癲癇綜合征[5]。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癲癇占全球所有疾病負擔的0.5%[6]。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口老齡化,人類預期壽命在逐漸延長,癲癇患者的數量也將顯著增多,對醫療資源需求也日漸提高,無疑給社會及癲癇患者的家庭帶來沉重負擔。
2 焦慮障礙
近年來,“被遺忘的共病”成為焦慮癥的代名詞。焦慮障礙是指在缺乏客觀刺激下內心不安的一種狀態,它涉及多系統,常伴有明顯的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如過度思考、失眠、肌肉緊張及恐懼等[7],可分為急性和慢性兩大類,即驚恐障礙和廣泛性焦慮障礙。
3 癲癇共病焦慮
3.1 流行病學
癲癇共病逐漸成為癲癇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所謂共病是指某人同時罹患兩種及兩種以上的疾病,即“一人多病”。有數據[8]顯示,癲癇患者中焦慮癥的患病率約為27%。Prisnie等[9]研究表示,在神經系統疾病中,除腦卒中患者外,癲癇患者最容易共患焦慮等情感障礙。美國一項調查顯示,癲癇患者患有焦慮癥的可能性是非癲癇患者的兩倍[10]。李超然等[11]對315 例癲癇患者進行單因素分析,發現全面強直陣攣發作(大發作)、發作頻率每周超過1 次為癲癇患者共病焦慮的易感因素,可見癲癇共病焦慮的發生與癲癇發作類型及頻率具有相關性。何琴等[12]研究發現,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概率會因癲癇發作頻率增加而增加,且由局灶性發作進展為全面性發作共患焦慮障礙的發生率更高。癲癇會提高焦慮癥的發病率,而焦慮癥也會增加癲癇發作的風險。癲癇共病焦慮癥的好發人群一直飽受爭議。有數據表明,同年輕人相比焦慮癥在老年癲癇患者中不太常見,但最近研究表明癲癇共病焦慮在老年患者中較為常見[13]。這可能是因數據的收集方法、數據來源、目標年齡段、診斷標準以及研究群體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從而導致不同研究的數據之間缺乏可比性。
3.2 發病機制
癲癇與焦慮障礙為雙向聯系[14],兩者可能具有相似的發病機制。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發病機制主要與驚恐環路活化、神經遞質異常、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AP)失調、鈣離子通道及特定解剖部位受損等有關。驚恐環路活化又與杏仁核、海馬有關[15],因為杏仁核為驚恐條件反射的關鍵結構,直接電刺激杏仁核可以誘發焦慮[16]。5-羥色胺(5-HT)與γ-氨基丁酸(γ-GABA)皆屬于重要的神經遞質,任何一方表達異常均與焦慮障礙發生有關[17]。癲癇發作時神經細胞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可致HPA軸功能失調,影響皮質醇的正常分泌,一旦皮質醇升高又可導致5-HT受體結合能力下降,從而影響患者情緒,最終引發焦慮癥[18]。此外,在動物實驗中發現,鈣通道阻滯劑能緩解焦慮癥狀,尤其是高壓激活鈣通道還可能通過參與神經遞質釋放過程引發焦慮障礙[17]。大腦右側致癇灶的患者比左側致癇灶患者出現焦慮障礙的概率更高,這可能與右側大腦半球在處理情緒時占據主導作用有關[19]。海馬位于顳葉內側面,即邊緣系統,故顳葉受損容易累及海馬,有造成驚恐環路活化的可能。由此,我們可以猜測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發生與特定解剖部位受損有關。
3.3 臨床表現及相關評估工具
癲癇疾病本身的表現復雜多樣,并且大多數臨床醫生缺乏精神科相關的專業知識,故對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識別力較低。癲癇共病焦慮癥患者的臨床表現除了癲癇相關的臨床表現外,還具有焦慮障礙的相關臨床表現。焦慮障礙的出現和癲癇發作一樣,都具有不可預測性,它可出現在癲癇發作之前、發作當時或癲癇發作之后[16]。癲癇的主要臨床表現有肌肉強直、抽搐、口吐白沫、二便失禁及昏迷等,恢復期時患者神志會逐漸恢復,有乏力、肌肉酸痛等[20]。焦慮障礙的患者常以軀體癥狀的表現為主,具有急性、自限性、復雜多變性的臨床特點,一些潛在的焦慮癥狀包括心慌、精神錯亂和注意力渙散等,主要的臨床表現為肢體顫抖、坐臥不安、肌肉緊張等[21-22]。一項薈萃分析發現,在使用非結構化臨床醫生評估來診斷焦慮的研究中,焦慮患病率為8.1%,而在使用標準化結構化的精神病學訪談的研究中,焦慮患病率為27.3%[23]。可見當臨床醫生沒有使用有效的診斷方法時,焦慮癥往往會被嚴重低估。但對于癲癇共病焦慮癥者的焦慮評估量表目前尚無統一標準,醫院焦慮量表對其敏感性和特異性不高,漢密爾頓焦慮量表雖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但測評耗時長且對評估人員的技術要求高。目前多使用廣泛性焦慮量表(GAD-7)檢測焦慮障礙,它是一種快速、可靠、可行的篩查工具[16],能將焦慮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國內一項研究[24]顯示,GAD-7>6分提示患有廣泛性焦慮障礙,其信度和效度分析提示特異度為91%,敏感度為94%。值得注意的是對有認知缺陷和/或語言障礙的癲癇患者而言,GAD-7也有局限性。
3.4 神經遞質的檢測
測定神經遞質含量對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診斷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相關檢測技術層出不窮。參與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神經遞質主要包括單胺類(如5-HT)和非單胺類(如γ-GABA)[17]。γ-GABA在血漿、大腦實質及腦脊液中均廣泛存在,直接檢測腦脊液中γ-GABA含量屬于有創操作且價格昂貴,臨床上多棄用此法,現多采用簡便易行且價格低廉的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法(ELISA)[25]。
3.5 不良后果
國內外對癲癇合并焦慮障礙的關注度不足,故診斷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相對較困難,即便能夠診斷該病,部分患者也會因疾病本身的不可預測性及其所致的職業限制(如禁止從事飛行員、駕駛員及高空作業等)容易產生病恥感,這常常會降低患者的藥物依從性,從而導致藥物治療反應欠佳[26]。癲癇與焦慮的不良后果往往互為關聯,癲癇患者常因疾病本身、經濟等多種因素而引發焦慮等情緒障礙,而焦慮會進一步增加癲癇發作頻率,并且降低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從而降低抗癲癇藥物的治療效果,使癲癇發作更難控制[14]。有研究表明[27],癲癇共病焦慮障礙患者的自殺意念比單獨患癲癇患者更高。綜上所述,癲癇共病焦慮可能帶來藥物治療反應不佳、自殘或自殺、生活質量差、社會和家庭醫療負擔沉重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4 治療進展
雖然癲癇患者共病焦慮障礙常見,但是由于大多數臨床醫生更關注于癲癇疾病的診療,缺乏精神科專業知識,而對癲癇患者共病心理疾病的可能性欠缺考慮,致使大部分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患者得不到及時診療。有研究認為[28],超過25%的癲癇患者有焦慮問題且需要治療,但由于單純藥物或者心理治療可能具有成癮性,故通常建議采用綜合療法。目前,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治療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藥物治療、認知行為治療及光照療法等[15]。
4.1 藥物治療

4.2 認知行為治療
認知行為療法屬于心理治療方式的一種,能降低癲癇發作的閾值[30]。認知行為治療對焦慮障礙的療效在大量對照研究中是有證可循的,可作為一般人群對焦慮障礙的首選治療方式[30]。在一項小樣本癲癇患者進行的非對照研究中,認知行為療法已被證明可以改善癲癇患者的焦慮情緒[15],并且成為兒童和青少年癲癇伴焦慮者的首選治療方法。近年來,許多研究開始關注線上治療,它幾乎不需要與心理治療師面對面交談而容易被大眾接受,然而,缺乏證據表明這些治療和面對面的個人認知行為治療一樣有效[31]。當單用藥物治療癲癇共病焦慮障礙的效果欠佳時,輔以認知行為治療不失為一種好的治療手段。
4.3 其他相關治療
研究表明[32],對于難治性癲癇患者,適當強度光照療法有助于減輕癲癇患者的焦慮癥狀,雖然該研究對象并未包括其他類型癲癇患者,但總體來說,為今后癲癇合并焦慮障礙的患者帶來了福音。一項前瞻性研究表明[33],由神經科醫生、精神病學家、藥劑師和護士組成的多學科管理計劃可以改善中國東部癲癇患者的焦慮情緒。
5 展 望
如今心理疾病被大眾廣泛關注,癲癇共病焦慮也逐漸被重視起來,成為癲癇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但因其臨床表現具有復雜多樣性,且目前尚無特異性的篩查方法來評估癲癇患者的焦慮程度,故極易被非精神科醫生漏診。此綜述希望能對臨床及時識別及干預該疾病有一定的幫助。目前尚不能完全闡明癲癇共病焦慮的機制,且大多數有關癲癇共病焦慮障礙藥物的研究隨訪時限短且樣本量小,期待更多大樣本、多中心研究應用于癲癇共病焦慮障礙中,為癲癇共病焦慮的規范治療提供依據,以幫助癲癇患者改善焦慮情緒,提高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