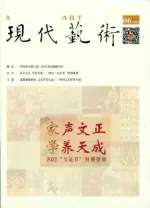回到源頭 恢復思想的彈性
白浩

雍也新著學術隨筆集《回望詩經》風格獨特,是一部在個人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心得之間的跨界作業,它既是向經典的回歸與致敬,更是古為今用,在當代的人、“活”的人的消化中對于中華文化“優根”的清理與再出發,在創新性轉化、創造性發展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新時代”在精神文化領域最重要的轉折就在于鮮明地高舉中國精神旗幟,提出“兩創”,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轉化、創造性發展,精神文化建設上改變了一味地跟著西方跑的路徑。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內在的文化凝聚力建設至關重要。食洋不化固然是走偏,可食古不化也同樣早已為歷史證明窒息生命,時代大導向下的一擁而上固然有氣勢,可如何“化”,如何“活”,這才是“兩創”破局的關鍵,也是在一片“傳承”喧囂中要勘破的門道。雍也新著學術隨筆集《回望詩經》風格獨特,是一部在個人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心得之間的跨界作業,它既是向經典的回歸致敬,更是古為今用,在當代的人、“活”的人的消化中對于中華文化“優根”的清理與再出發,在創新性轉化、創造性發展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作為研習心得錄、學術隨筆體在學術史上本不稀奇,但在當今學科劃分涇渭分明,唯課題、論文為考核標準的學術功利化時代,這樣的文體是難以進入所謂科學化的科研考核體系的,故而學術體系內兢兢業業耕耘的科研民工們是不愿意分心去參與這種感性化、個人化色彩濃厚的“野狐禪”,而眾多學術刊物也不容易發表此類文章,除非偶爾仰仗名家大腕之盛名,可以憑此來展示點“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雅趣”與“人間性”。故而,《回望詩經》是一部在當今時代學術語境中算得稀少的另類,但回望學術史、思想史卻是熟悉溫馨的讀書傳習錄。因此,本著的意義與價值就需要從文章本身和對于當今學術體系的沖擊來談。
學術隨筆側重于對于學術的通俗化、個體化體驗表達,其實近如百家講壇的易中天品三國、遠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都是其中的成功者。面對已經案牘成山、傳承巍峨的經典學術,隨筆體回到經典的起點和源頭,即生活經驗的源頭與鮮活個體的體驗起點,為僵化的經典化學術系統重新賦予原始的生命活力。雍也下手的正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也是中國學術闡釋史源頭的《詩經》,此種黑虎掏心之舉既可謂膽大,卻也是直抵本源的最佳入口,由此波動所及正具有對于學術體系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之效。面對各種注疏、箋注、釋義、正義,龐雜的衍生體系已經占據了《詩經》解讀的主渠道,亂紫奪朱、尾大不掉,正是如此后來諸生居于《詩經》接受的下位,本末倒置,一咳一唾俱需引經據典,唯唯諾諾性靈不彰,常常導致食而不化的影響和焦慮,而破除迷障的捷徑恰就在于回到生活與個性的源頭,如此才能回到與眾多前輩名家的平行位置。學界倡導的讀元典、釋原典,正是要入手點高,免沉淪于二三流境界難以自拔的棒喝之舉,《詩經》正是此類回歸的極佳入口。
《回望詩經》中所論篇目以“風”居多,也最為得心應手,“國風”恰恰是地域文化與民間生活最為鮮明的部分,雍也借用大量地域文化的方言,引用巴蜀文化的民俗風情而形成的比擬、戲說、調侃風格,形成對于經典的本土化接受,這恰恰是最為接近“國風體”本意的。《回望詩經》不被汗牛充棟的高頭講章所嚇倒,而是說人話、說心靈里的話,形成個性化、性靈化輸出,諸如“《詩經》也有幽默”“小公務員的牢騷”“《詩經》里走出來的好干部”等篇都古為今用,宛然可見孔夫子待價而沽的“沽之哉沽之哉”、子見南子的“天厭之天厭之”等諸種人間性和親和力風貌。《回望詩經》出入經典,含英咀華,化而用之,自由隨意,在豐厚的文化底蘊中又大大提升了大俗大雅的文化品味。回歸生活源頭,回歸個性,這樣的解讀才是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也才能真正看到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以主人之姿“開新”的可能性。
本著的最顯著特征,一個是“活”,一個是“靈”,“活”是鮮活,活在當代生活,活在地域文化,“靈”則是性靈。《回望詩經》從時間上來說,自然是“回望”,然而從回歸文學藝術發生的源頭,回歸學術的源頭來說,這條路徑卻是對起點的回歸和再出發。它盡管只是對一些個別篇章和個別角度的點的切入,但引發的反思是系統性的。在闡釋體系的壓迫和學術等級制的拱衛中,一班冬烘腐儒尋章摘句,或者拿住雞毛當令箭,或者亦步亦趨,如同和尚包袱雨傘的學術三件套演練下來,唯獨不見了“我”,皆是銷蝕生命,性靈泯滅。《回望詩經》對于這種體系化、體制化的反向而動具有撥亂反正的探索信號之功,其本質是在文化人格上擺脫體制化壓力,恢復獨立平等的探索和思想權力,在思想路徑上是回望生活、回望心靈、恢復性靈,其功在恢復生活原生態的活力,恢復生活肌膚的鮮活與彈性,也恢復思想的彈性,也是回到更為廣闊的人民接受懷抱,恢復生命之樹常青的意義。這種“野狐禪”將道學化乃至玄學化的學術體系從蝜蝂之蟲的積重難返中拉回,反倒應該是學術的正途。自然,本文的解讀不過是越俎代庖,代為梳理,而隨筆體的弊端則在于可能淪入碎片化之嫌,因此,如何將學術小品進行梳理整理,形成系統化理念的總結歸納,將火種引為燎原之勢,則是可作進一步升華的期待。
本著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身份進行的規范化學術考辨之作,而是以一個作家身份進行的二度創作,其主要價值在于見事見人,即在對于《詩經》解詩說詩之中得以凸顯獨特的作者之個性、見識。如果從規范化學術角度看,其實本著中就留有一些可辯議之處。如因為對理學禁錮作用的討伐而導致對于朱熹解《詩經》的貶斥態度便顯得簡單化了。其實朱熹的解詩能推倒漢學的統治地位,其解放過程倒是與雍也的創造性解讀頗有同道神通之處。朱熹闡述其對于毛詩序的掙脫過程:“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后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后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可自通。于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237頁。]他推翻《小序》,擺脫一味的詩教,而從淫奔自敘自制的抒情詩角度解放了其文學性,而其指斥的24首“淫佚”“淫奔”“淫亂”詩,不過都是青年男女戀人間的相約相會,也恰恰是最為活潑靈動的篇章。恰恰正是朱熹的“淫詩”說將漢儒“后妃之德”的簡單教化觀推進到了樸素民間的直接表達,大大推動了對于《詩經》抒情性、文學性的解放,對此不宜以理學之徒的“存天理滅人欲”而籠統地否定,將解詩的朱熹本人與“朱熹之徒”“理學之徒”加以區分也是必要的。當然本著的主要光彩在于獨抒性靈,而這本就是自帶爭議的。
白 ? 浩
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