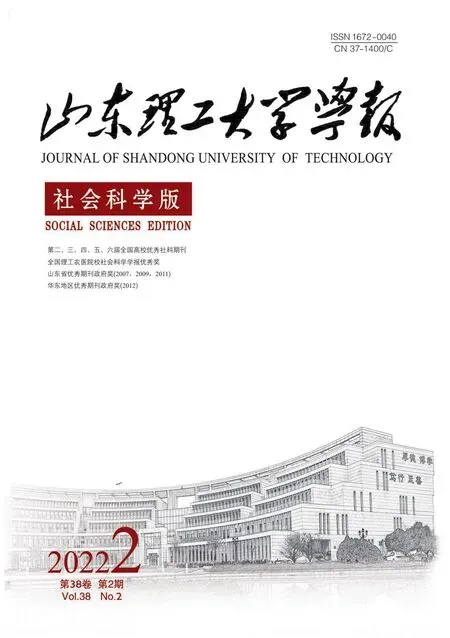經濟發展、農業生產要素與糧食生產能力
——基于糧食主產區2001—2019 年數據分析
張志新,王 迪
引言
2021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2 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而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 億人口的大國,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是“穩”的基石。 糧食主產區作為我國糧食供給的主要來源,糧食產量占據全國糧食總產量四分之三,占全國糧食增產的95%,全國商品糧超80%來自糧食主產區,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供給安全的重大責任。 然而,當前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提升擠占農業生產資源,大量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農村人口老齡化、婦女化、空心化情況嚴峻。 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約束加劇,農業生產投入流向經濟發展系統而威脅糧食生產(邵留長和喬家君,2016)[1],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成為保障糧食供給安全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也會為糧食生產提供充裕的資金、技術等支撐,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財政支持力度,促進糧食生產綜合能力穩步提升。因此明確經濟發展與糧食生產能力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糧食主產區在穩定糧食產能的同時保障經濟發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避免對糧食生產的擠出效應,實現糧食產能提升與經濟發展的協同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機制分析
糧食主產區的功能定位要求我們必須提高其糧食生產能力,但是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糧食主產區的產糧大縣“糧財倒掛”現象十分嚴重(齊蘅和吳玲,2017)[2],且二者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楊博等,2016)[3],因此,厘清“經濟發展對糧食生產能力”作用機制,是提高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生產能力的重要基礎。
(一)經濟發展對糧食生產能力的擴張效應
1.資本擴張效應。 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帶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 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加大農業財政支出力度,構建起了比較完整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在種植、畜牧、水產、農機、農墾等方面都有所支持,加快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實現農業產出的增加(龔斌磊和王碩,2021)[4];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為農業技術研發、創新與應用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對于研發主體來說,糧食主產區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其越可以為糧食生產與技術研發主體提供資金、環境等優勢條件,吸引研發人員、研發資本和知識技術集聚,為糧食生產能力提升提供技術支撐。 而從農戶自身來看,隨著居民收入來源多樣化及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多的非農收入會應用到生產性投資中來, 非農收入的增長可能會促進農戶對農業技術的應用,從而彌補因家庭勞動力短缺而造成的生產效率損失(謝花林和黃螢乾,2022)[5],推動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和使用,顯著提高糧食生產能力。
2.勞動力替代效應。 糧食生產的季節性特征可能使得農村勞動力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呈現出“農閑時外出務工,農忙時返鄉就業”的非穩定性勞動力轉移和兼業活動(欒江和馬瑞,2021)[6];同時也有研究認為,中國仍存在一定數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勞動力轉移對糧食生產仍以促進為主(姚成勝等,2016)[7]。 一方面是通過追加機械品和生物品實現對勞動力的直接或間接替代,農業機械、種子、化肥、農藥等資本要素投入的增加,可以補償由勞動力轉移對家庭糧食生產產生的不利影響(杜鑫,2022)[8],水稻、小麥、玉米均能夠有效借助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全面提升生產效率,有效緩解勞動力價格上漲沖擊(閆周府等,2021)[9];另一方面是因為勞動力轉移對農戶土地轉出具有促進作用,穩定的轉移就業增加土地流轉市場供給(欒江和馬瑞,2021)[6],促進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為土地的規模經營提供前提條件,有利于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
(二)經濟發展對糧食生產能力的擠出效應
1.自然資源擠出效應。 經濟發展對耕地和農業用水均具有擠出效應。 中國是耕地資源最為短缺的國家之一,近30 多年來,中國農業用地和生態用地不斷向城市建設用地轉移,中國大量優質高產的耕地資源加速轉向城市建設用地,這在東部沿海及中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Qiu L,Pan Y,Zhu J,eta.,2018;Yang Hong and Li Xiubin,2000)[10-11],經濟發展的迅猛勢頭使得耕地資源屢被占用,數量不斷減少,質量不斷下降,以致嚴重影響糧食生產的數量與質量(楊博等,2016)[3];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導致農業用水不斷向城市和工業用水轉變,同時也會帶來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等各種問題。 2020 年中國用水總量5812.9 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用水占62.14%,比1998 年的88.2%下降26.06 個百分點,但工業和生活用水占比上漲了20.78%,灌溉面積顯著減少,土壤質量因此下降并威脅糧食安全(姚成勝等,2016)[7]。
2.勞動力轉移效應。 隨著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加上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大量農村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向非農化轉移,農業勞動力出現兼業化和副業化現象,與現代農業生產相匹配的勞動力出現嚴重的結構性短缺(彭柳林等,2018)[12],農村青壯年為主體的勞動力結構被以老年和婦女為主體的勞動力結構所取代(孫小宇等,2021)[13],影響第一產業正常增長。
因此,本文基于現有研究成果,采用PVAR模型,借助GMM 估計和脈沖響應方法,分析經濟發展、農業生產要素與糧食生產能力之間的關系,為糧食主產區實現經濟發展與糧食產能提升提供支撐。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由于經濟發展、農業生產要素與糧食生產之間的影響機制和作用關系較為復雜,本文借鑒蘇芳等(2021)[14]的模型構建思路,選取PVAR 模型檢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脈沖響應,該模型將所有變量設為內生變量,可以避免普通回歸模型導致的內生性和異方差現象,將面板數據和VAR 模型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兩者優點,設定如下計量模型。

式(1)中,Yit為模型被解釋變量,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RGDP)、糧食生產能力(GPC)以及農業生產要素中的勞動(L)、資本(K)和土地(N);i 和t 分別表示省份與時間;β0代表的是截距項向量;βj代表的是滯后j 階的參數矩陣;p 為滯后階數;μi代表個體固定效應;γt代表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擇
在指標選取時依據可得性和科學性的原則,選取了經濟發展、糧食生產能力以及農業生產要素中勞動、資本和土地等共五個變量,具體內容如下。
1.經濟發展水平。 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現有學者多以復合指標體系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等單一指標來表示,相比復合指標體系,單一指標更能直觀展示各省份經濟差距,同時由于各省人口基數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在借鑒馬彪和陳璐(2019)[15]的指標基礎上,選用人均地區國內生產總值(RGDP)來代表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2.糧食生產能力。 對于糧食生產能力的測度,部分學者以糧食總產量(江松穎等,2016)[16]或糧食單位面積產量(余文濤等,2017)[17]等單一指標來測度。 也有學者通過構建復合指標體系來綜合評價糧食生產能力(傅琳琳等,2021)[18]。 由于糧食生產能力的最終結果都將反映在每年的糧食產量上,因此本文選取糧食單位面積產量這一指標,其反映了在糧食實際所占的耕地數量上,單位面積全年所生產的糧食數量(余文濤等,2017)[17]。
3.農業生產要素。 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黃穎和呂德宏,2021)[19]的基礎上,選取了勞動、資本、土地三種代表性的農業生產要素。 其中勞動在借鑒雷紹海等(2022)[20]的基礎上采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量代表;對于資本的量化大多文獻采用物質費用投入、農業機械化程度或化肥使用量來代表,本文借鑒吳偉偉等(2020)[21]的指標采用人均化肥施用折純量表示,即農用化肥施用折純總量除以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土地要素借鑒趙和楠和侯石安(2021)[22]的指標選取,使用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表示。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中國糧食主產區13 個省份2001—2019 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 文章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http:/ /www.stats.gov.cn/)、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9 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1—2019 年)和各省份統計年鑒(2001—2019 年)。 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對于個別缺失的數據,本文采用均值法進行補充。 所有數據在實證前均進行了取對數處理,以消除異方差。 表1 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穩定性檢驗與最優滯后階數選擇
1.穩定性檢驗。 在使用PVAR 模型進行檢驗前,需要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避免出現偽回歸現象導致偏差。 平穩性檢驗通常采用單位根檢驗的方法,因此,本文采用LLC、IPS 和HT 三種方法對所有數據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勞動(L)、資本(K)、土地(N)三種生產要素的數值在LLC、IPS 檢驗下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但所有變量在一階差分后均通過了穩健性檢驗,因此認為變量間是平穩的。
由于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因此需要通過協整檢驗來判斷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 本文采用Kao 檢驗方法得出,t 值為1.6765,p 值為0.0468<0.05,因此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進行后續實證檢驗。

表2 單位根檢驗結果
2.最優滯后階數選擇。 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GMM 估計前,需要確定各變量的最優滯后階數。 本文采用赤池信息準則(AIC)值、貝葉斯信息準則(BIC) 值和漢南—奎因信息準則(HQIC)進行判斷,結果如表3 所示,在設置最大滯后階數分別為3 和4 的情況下,均顯示最優滯后階數為滯后3 階。

表3 最優滯后階數選擇
(二)GMM 回歸
在確定穩定性和最優滯后階數后,本文進行GMM 估計,其中h_lnRGDP、h_lnGPC、h_lnN、h_lnL、h_lnK 是采用前向均值差分( Helmet) 消除掉固定效應產生的序列,L1、L2、L3 分別表示滯后一期、滯后二期和滯后三期。 GMM 估計結論如表4 所示。 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對數(lnRGDP)方程中,經濟發展水平易受到自身的影響,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當期產生正負向影響,且正向影響系數更大,為0.5146。 而從農業生產要素來看,滯后三期的勞動和資本要素均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滯后三期土地要素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影響系數小于前兩者,這表明前期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也會對經濟發展水平產生影響,且勞動要素對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最大。 從糧食生產能力(lnGPC)來看,滯后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均為負向,且滯后二期的經濟發展在10%的水平上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顯著,這表明前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對糧食生產能力產生抑制作用。 農業生產要素中,資本要素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顯著,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產生正向影響,因此農業生產要素中,資本要素的投入使用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更大。 最后從勞動(lnL)、資本(lnK)和土地(lnN)三種生產要素來看,農業生產要素中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的為資本要素,滯后二期經濟發展水平對資本要素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有正向影響,而土地生產要素受糧食生產能力提升的反作用影響,滯后二期糧食生產能力對土地要素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正向影響,這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要素中的資本要素影響較大。
(三)脈沖響應分析
GMM 估計結果顯示出滯后期變量與當期變量之間的關系。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變量之間的動態互動關系,需要對各變量進行脈沖響應分析。本文運用Stata 軟件對經濟發展、糧食生產能力與三種生產要素之間進行脈沖響應,分別對經濟發展與糧食生產能力、經濟發展與農業生產要素、農業生產要素與糧食生產能力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借鑒蒙特卡羅的方法,進行200 次模擬得到滯后10 期的動態交互作用與響應趨勢,如圖1 至圖4 所示,圖中橫軸s 代表滯后期數,縱軸代表脈沖響應程度。

表4 GMM 估計結果
1.以經濟發展為沖擊變量。 圖1 為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沖擊變量時,其自身和其他變量對該沖擊的脈沖響應程度。 從圖中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對自身影響為正,這表明經濟發展存在慣性;從經濟發展對農業生產要素的影響來看,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經濟發展對勞動和資本兩種農業生產要素,均為正向影響,且分別在第二、三期達到最大值后開始逐漸減弱,原因可能是經濟發展雖然會帶動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就業,但勞動力轉移的不穩定性和兼業活動可能使得農業勞動力減少人數并不明顯,尤其是在以農業為主的糧食大省,農業的現代化、規模化經營可能會為農民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吸引更多勞動力前來就業,經濟發展也會通過資本的擴張效應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另一類是經濟發展對農業土地要素為負向影響。在第三期、第五期達到最大負向影響值后開始減弱,這也證實了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確實會對農業土地要素產生擠出效應。 最后經濟發展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為負,并在第一期達到最大負向影響,后經歷波動上升逐漸收斂,其原因可能是經濟發展雖能帶來勞動和資本要素的增加,但是經濟發展對勞動和資本要素的促進作用不足以彌補其對土地擠占所產生的負向作用,導致最終經濟發展對糧食生產能力產生負向影響。
2.以勞動為沖擊變量。 圖2 是以農業生產要素中勞動力作為沖擊變量時,其自身和其他變量對該沖擊的脈沖響應程度。 從勞動要素對其自身影響來看,對自身在初期產生最大正向影響,之后開始下降,并從第三期開始轉為正負交替影響。從勞動生產要素對其他農業生產要素的影響來看,勞動對資本為正向影響,并在第三期達到最大,對土地在第六期之前也均為正向影響,這表明勞動要素的增加也會對土地和資本帶來促進作用。 勞動要素對糧食生產能力僅在第一期為正向影響,并在第一期達到最大正向影響,之后轉為負向影響,這表明短期內勞動力資源的增加會帶來糧食生產能力的短暫提升,但現代農業的發展不再是簡單依靠人力物力的增加,過多的勞動投入會帶來勞動力資源的冗余,加上機械化對勞動力的替代,僅增加勞動要素投入并不會促進糧食生產能力的提升。

圖1 以經濟發展為沖擊變量時的脈沖響應函數圖注:圖中上、下兩條實線代表置信區間,中間實線為脈沖響應程度,虛線直線代表零。

圖2 以勞動要素為沖擊變量時的脈沖響應函數圖注:圖中上、下兩條實粗線代表置信區間,中間實線細為脈沖響應程度,虛直線代表零。
3.以資本為沖擊變量。 圖3 為以農業生產要素中資本作為沖擊變量時,其自身和其他變量對該沖擊的脈沖響應程度。 從圖3 中可以看出,資本對自身除在第1 期為負向影響外,長期來看均為正向影響,并在初期達到了最大正向影響,這說明長期看來農業資本要素投入具有慣性。 從資本要素對其他生產要素的影響來看,其對勞動要素在前三期為負向影響,后轉為正向影響,對土地要素在經歷第一期短暫正向影響后轉為負向影響,并在第二期達到最大負向影響,這說明資本要素的投入長期來看對勞動和土地要素均具有擠出作用。 而資本要素對糧食生產能力在經歷第一期短暫正向影響后轉為負向影響,并在第三期達到最大負向影響,這說明短期內資本要素投入確實能帶來糧食生產能力的提升,但長期來看糧食生產能力的提升并不能依靠資本投入。
4.以土地為沖擊變量。 圖4 為以農業生產要素中土地作為沖擊變量時,其自身和其他變量對該沖擊的脈沖響應程度。 從圖4 可以看出,土地要素對糧食生產能力在短期內為正向影響,其后轉為負向影響并逐漸趨于平穩,這表明提高依靠土地數量的增加長期以來并不會帶來糧食生產能力的增加。 對其他生產要素來說,土地對勞動要素長期內為正向影響,僅在第一二期為負向影響,土地對資本要素一直為正向影響,并在初期達到最大值,這說明土地要素的投入增多也會帶來勞動、資本要素的增加。
(四)方差分解

圖3 以資本要素為沖擊變量時的脈沖響應函數圖注:圖中上、下兩條實線代表置信區間,中間實線為脈沖響應程度,虛線直線代表零。

圖4 以土地要素為沖擊變量時的脈沖響應函數圖注:圖中上、下兩條實線代表置信區間,中間實線為脈沖響應程度,虛線直線代表零。

表5 基于PVAR 模型估計的方差分解結果
為了更精準反映響應程度,本文使用方差分解進一步進行評價。 表5 選取了第10、20、30 期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對其自身的方差貢獻率最大,在第10 期時為78.6%,一直維持到第30 期仍然占據73%。 農業生產要素中對其影響程度較大的先后為勞動、資本和土地,而這些要素的方差貢獻率最高僅在10%左右。 糧食生產能力的方差貢獻率主要來自其本身和經濟發展水平,分別為78.9%和9.1%,且30 期內基本趨于穩定,變動幅度沒有超過1%。 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糧食主產區的生產能力有較大影響。 三種生產要素中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最大的為資本,其方差貢獻率為8%左右。 對于各農業生產要素來說,勞動要素受自身影響最大,其方差貢獻率為88.8%。 對于農業生產要素中的資本來說,對其影響最大的是勞動要素,方差貢獻率占據48.7%,且資本要素自身和經濟發展水平對其影響也較大,分別占據了29.3%和18.3%。 在土地生產要素中,對其影響最大的除其本身占據了60%外,不能忽視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方差貢獻率最高為21.9%,這也是三種農業生產要素中,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的。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運用2001—2019 年中國糧食主產區13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和PVAR 模型,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要素與糧食生產能力之間的動態互動關系進行了驗證,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從經濟發展與糧食生產能力關系看,糧食生產能力主要受自身慣性影響,但不能忽視經濟發展對糧食生產的抑制作用。 方差分解結果顯示糧食生產對其自身貢獻率為78.9%,經濟發展水平對糧食生產具有負向影響,且方差貢獻率占據近10%。
第二,從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生產要素關系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促進農業生產要素中勞動和資本要素的增加,但會對農業生產中土地要素的使用產生擠出效應。 且從方差分解來看,三種要素中土地和資本要素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最大,其對土地和資本的方差貢獻率均在20%左右,而勞動要素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程度不足10%。
第三,從農業生產要素與糧食生產關系看,勞動、資本和土地三種生產要素對糧食生產在短期內均為正向影響,從三種農業生產要素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資本要素對糧食生產影響最大,其方差貢獻率大于勞動和土地貢獻率。
(二)建議
第一,經濟發展過程中要避免對糧食生產的擠出效應,保障糧食生產穩定性。 首先,筑牢耕地數量安全防線。 各省、市、縣依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最低耕地數量防線,嚴格控制土地“非農化”,對于申請“農轉工”“農轉商”的土地審批條件嚴格把控,堅決守住耕地數量紅線不放松。 其次,弱化對土地數量的要求。 實施更加嚴格的高標準糧田政策,提高對現有農業用地利用效率,貫徹落實“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在保證糧食生產數量的同時提升質量。 最后,實行土地規模化經營,將外出勞務人員閑置土地進行流轉,加大對新型規模農業經營主體給予信貸、財政等多方面的扶持力度,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提高機械化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經濟發展對農業生產要素的擴張效應,抓住機遇,穩產增收。 首先,調整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結構,增加優質良種和先進生產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應用,杜絕長期依賴化肥農藥等簡單物質投入的“破壞性”生產方式,加快推進農業信息化、智能化生產,做好科學種糧。 其次,降低對勞動力數量的要求,應提高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素質,地方政府出臺人才引進政策,吸引更多有專業知識技能的專家人才投入到第一產業生產當中;同時提供“幫扶專家”實行專業技能指導,加大對農村勞動人員的科普和培訓,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最后,完善農戶農地投入利益補償機制,主張“誰種地就補給誰”,保障農民種糧收益,對農戶提供精準種糧補貼,提供專項農業貸款優惠,提高農戶種糧積極性。